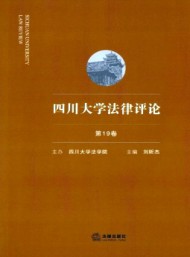民法典重要性及意義范文
時間:2024-03-28 18:12:29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民法典重要性及意義,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一、商法的獨特性及其與民法的兼容限度
(一)民法與商法調整的法律關系的差異性
盡管民法和商法同屬私法領域,但是二者所調整的法律關系卻存在細微的差別。由于民法所調整的法律關系更具有人本性的特征,因此民事法律關系更注重實現人的自由、理性、平等等價值理念,而商法調整的法律關系更具有營利性的特征,商事法律關系更注重實現商事主體的營利性目的。更有學者引用德國學者關于民法和商法關系的論述,來表明民法與商法調整的法律關系的區別,即商法是私法的特別法,而不是民法的特別法。這與通常所表述的商法是民法的特別法這一說法存在一定差異,但是這也恰恰表明了商法與民法所調整的法律關系存在一定的差異性。由于商法堅持限權的基本理念,商事主體承擔法律義務的標準相對較高;而民法采取平等自愿原則,民事主體承擔法律義務的標準相對較低。在這種情況下,強制實行民商合一,將導致商事主體承擔的法律義務被降低,或者民事主體承擔的法律義務被提升。無論何種結果,都不利于相應法律關系的調整,同時也違背了制定民法典的基本初衷。
民法與商法在調整法律關系方面的差異還體現為商法的管制性特征。商法的管制性特征具體體現為商事法律規范中大量的強制性規定,通過這些強制性規定,商法發揮了其管制性作用,對涉及商事法律關系的諸多方面進行有效管制。而民法調整的法律關系更強調個人之間的自愿和平等,這與商法的交易特征極為相似,體現為具體的任意性規定。當事人可以根據自身的具體意愿,訂立相關合同規定各自的權利和義務,只是商法的交易性特征更強調當事人雙方的交易意愿和交易安全。然而從平等自愿這個層面來看,商法的交易性特征與民法的作用具有較高的相似度。在調整法律關系方面,商事法律規范具有較大的彈性,因為商事法律關系的發展和演變速度要明顯高于民事法律關系,因此需要具有較大彈性的法律法規對可能發生的相關情況進行預期性規制。由此看來,民法和商法調整的法律關系具有較大的差異性,而且各自具有鮮明的特征。
(二)民法與商法倫理基礎的差異性
民法和商法的倫理基礎也存在一定的差異性。從民法和商法的發展歷程來看,民法更注重社會倫理,其法律關系的展開體現了社會倫理的基本要求,更多關注人類的自由、理性和平等;而商法更注重商業倫理,其法律關系的展開體現了商業利益等營利性目的的基本要求,更多關注交易關系的建立以及相應關系產生的經濟效益。民法倫理基礎植根于平等的基本觀念,承襲了源自古希臘的對自然理性的追求,更體現為對人本身的尊重,是羅馬法基本倫理的一種自然詮釋和展現,與近代大陸法系國家的民法一脈相承。因此,人類的自由、理性和平等這些自然理性的基本倫理追求都體現在民法之中。而商法的倫理基礎是人類對于利益的追求,強調商事活動可能預期或者具體產生的價值,其更關注經濟效益的增加以及財富的不斷累積。因此,商事法律規范的重要目的并不是保證平等交易,而是確保商事主體能夠通過相應的商事活動獲取經濟效益,帶來財富的累積。所以,從民法倫理和商法倫理的基礎來看,二者之間存在一定的沖突,而且這種沖突是難以調和的根本沖突。
相較于民法的社會倫理,商法的倫理觀更具有擴張性,在利益的驅動下人們的商事活動不斷增加,其增加的程度有可能超出社會倫理可能認知的界限。在這種情況下,民法的社會倫理和商法的經濟利益倫理就會發生沖突:一方面商法倫理的擴張力能夠推動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另一方面商法倫理又能對社會的發展起到破壞作用,致使社會整體都趨于利益化。在二者的沖突中,民法的社會倫理應該對商法倫理進行引導和控制,當商法倫理對社會進步有推動作用時,應該對其進行適當引導,反之,就應該對其進行必要的控制。由此看來,民法的倫理基礎不僅與商法的倫理基礎存在差異性,同時也存在一定范圍內的沖突,二者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
(三)民法的兼容性限度
民法對于商事規范的兼容性,首先體現在民法總則能夠在何種程度上概括廣泛的商事規范的共通性內容,并將其融入民法總則的制定之中。而民法的這種兼容性不僅依賴于民法的抽取技術,同時也依賴于廣泛的被抽取對象,即現存的零散的商事法律單行規范。實質上,無論實行民商合一還是民商分立,都是在抽象程度上存在著差異,并不意味著絕對的合一或者絕對的分立。相較于民商合一,民商分立對民法的抽象能力要求較弱,因為在民法總則之外會單獨制定商法總則。在這一意義上而言,民商分立不僅降低了對民法兼容性的要求,同時也降低了對民法總則抽象能力的要求。
然而對于民法而言,其抽象能力畢竟有限,因為民法總則通常要求一般化的內容具有普遍性,而事實上能夠被一般化且具有普遍性的內容非常少,所以很多商事法律規范很難被一般化而納入民法總則。比如,商事賬簿和商事登記等商事法律規范,其與民事法律規范存在較大的差異性。這些差異性導致這些商事規范難以被抽象化而納入民法總則中,若將其強行放置于民法總則中又很難與各部分相協調,置于其他部分也難以在法理上給予充分的論證。因此,民法的兼容性是具有限度的。此外,民法的兼容性限度還與商法通則的兼容性相對應,因為除了一般性的商事規范外,還存在難以歸入單行商事規范的商事法律內容,這些內容直接歸入民法總則顯然不合適,但是如果將其納入商法總則,則從理論和體系上都有一定的法理基礎。
從商事法律規范自身的特點來看,其具備的可抽象性并不高,不同的商事單行法律規范也缺乏可被一般化的公因項。不同的商事法律規范具有較高程度的區格性,缺乏具有貫穿性的一般性概念和效力準則。一旦對商事法律規范進行過度抽象,其結果必然是商事法律規范自身效能的折損,從而難以實現商事法律規范一般性的功能。因此,商事法律規范本身也對民法的兼容性產生了一定的阻礙作用。
二、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的域外考察
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的爭論常常溯至域外,通常以不同國家采取民商合一或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作為重要論據。通過深入考察域外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的歷史傳統流變及其現實狀況,來反觀我國民法典制定過程中的民商法關系。
從民法和商法的源流來看,其經歷了不同的發展歷程。盡管民事習慣法源遠流長,但一般認為現代民法應該追溯至古羅馬的成文法化時期,其后在中世紀一度衰落,在中世紀末期又逐漸復興;而現代商法則起源于歐洲中世紀的商品貿易過程中,從商事習慣逐步實現成文化。由此看來,二者經歷了不同的發展歷程,盡管在此后一段時期存在民商合一的立法實踐,但是最終還是因商法的獨有特征而逐步走向分立。
法國商法典的制定經歷了習慣法成文法商法典的基本過程。在中世紀末期,法國在商業活動中大量使用商業習慣,其后由于商業活動的增加,法國頒布了海商敕令,逐步實現商業習慣的成文法化,并最終在1807年頒布了《法國商法典》。該法典的制定不僅反映了當時自然法理性主義的要求,同時也體現了法國商事發展的基本情況和規范性要求。盡管德國早期存在諸多商事習慣法和單行法,但這些都是發端于《普魯士邦普通法》,該法匯集并整理了大量的德國商事規范,此后德國又逐步制定了《普通德國商法典(草案)》,對商事法律規范法典化,并最終形成了《德國商法典》。德國商法典的制定與德國地區商業發展情況密切相關。法國商法典的制定不僅對法屬殖民地地區產生了重要影響,同時也促使比利時、希臘、土耳其等國逐漸實現了商法法典化,而日本商法典的制定受到德國商法典的直接影響。
英美法系國家的商事立法呈現出與大陸法系截然不同的特征。基于判例法的傳統,早期的商事習慣和商事判例在英美法系國家起到了較大的作用。但是,隨著商事活動的不斷增多,以及與大陸法系國家商事交往的增多,單行商事制定法也逐漸在英美法系國家占有一定的地位,體現出商事規范獨立的特征,并最終制定了統一的商法典。
到了19世紀中期,由于私法的統一思潮不斷發展,學者們開始質疑民商分立的必要性,民商合一的觀念逐漸受到人們重視并將其運用到立法實踐當中,而且這種思潮的影響一直延伸至20世紀中期。這一時期,民商合一觀念的發展與當時的經濟發展狀況以及法律實踐狀況密切相關。在這一時期,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得到了進一步發展,重商主義的重要意義被逐漸淡化,商事主體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浪潮下并不需要格外的重視和保護,因此商事主體的商法保護意義逐漸弱化,從而影響了人們對商法重要性的認知。經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作用是商事交往的日益頻繁,而相對固化的商法典難以有效應對劇烈變化的商事實踐活動,因此商法典的重要性也遭到了普遍的質疑。
在法律實踐方面,19世紀末是很多國家進行法律變革的重要時期。在這一時期,羅馬法的影響力不斷擴大,得到了諸多國家的充分重視并以羅馬法為基礎開始發展本國私法體系。相較于羅馬法,商事法律的包容性和擴張性相對較弱,因此并未受到足夠的重視,加之經濟社會發展的具體狀況,商法典的重要意義被不斷質疑,由此開始了民商合一的法律實踐。例如,1865年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將大量的商事規范納入民法典中,而不單獨制定商法典;1881年瑞士債法典中規定了諸多商事規范,實行現實意義的民商合一;1934年荷蘭將民法與商法進行統一,從而實現民商合一的私法體制;1942年意大利在制定民法典時,將民法與商法統一規定其中,實行民商合一私法體制。這些立法實踐都與當時的經濟社會環境,以及民商合一觀念的發展密切相關。
然而在最近數十年中,私法學界又開始反思民商合一的弊端。例如,瑞士和我國臺灣地區都屬于民商合一立法模式,在具體的法律實踐中,對商事主體和商事行為不做嚴格界定,同時在債法領域,合同的民事性和商事性也不做嚴格區分。在這種情況下,商事法律規范的運行常常陷入困境,因此產生了大量關于商事主體和商事行為的爭議。由于民事合同與商事合同的界限不明,導致合同在訂立之后難以發揮其應有的效用。為了實現現代國家的重要管制功能,通常需要制定大量的商事單行法規,從而保證對商事領域中諸多重要內容進行有效的規制。因此,無論民商合一還是民商分立,都應以法律的現實效用,以及不同國家或地區的現實經濟社會作為基本考察點,而不應憑空強調民商合一或民事分立的意義。
三、民商合一可行性的異議
在我國民法總則的制定過程中,一個相對主流的觀點認為:民法總則應該對民商事法律關系進行全面的調整,而不應再單獨制定商事通則。在相應的民法總則中,商事總則的內容涵蓋于民法總則之中,商事主體規范由民法總則統一規定,同時商事行為規范也由民法總則統一規定。然而問題是,如果按照這一思路實現民商合一,從立法技術上而言,難以有效對現有的民事和商事法律規范進行抽象性規定,而且在具體的立法實踐中,也很難對民事和商事法律規范進行有效統合,從而導致整體立法上的不足。
(一)對立法技術可實現性的異議
就立法技術而言,如果民法總則所要涵攝的法律關系越廣,那么其所要抽象的程度就相對越高,也就是一般化的程度就越高;相反,如果民法總則將大部分的商事法律規范予以排除,那么其所需要的抽象程度自然就會有所降低,其實現難度也會相應地有所降低。
從民法總則自身的抽象能力來看,如果采取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民法總則必須具備將民事和商事法律規范進行整體抽象的能力。也就是說,民法總則需要按照從特殊到一般的基本歸納路徑,提取民事法律規范和商事法律規范中的共通項,并將其在民法總則中加以概述。這是確保民法典制定的系統化和統一化的重要立法技術。如果僅就民事法律規范的抽象能力而言,民法總則能夠相對較好地完成抽象任務,實現民事法律規范由特殊到一般的基本過程。德國民法典的制定過程充分展示了對民事法律規范進行抽象歸納,進而得出系統化理論化民法總則的可能性。如果將大量的商事法律規范納入民法總則的抽象范圍,其抽象歸納能力便會遭到質疑。因為商事法律規范對于商事主體、商事賬簿,以及商事行為的規定,都難以通過相應的抽取技術進行歸納。如果不對這些商事法律規范進行歸納,其結果要么是生硬地將這些商事法律規范直接納入民法總則之中,要么是將這些商事法律規范置于商事單行法等法律文件中。這樣做的后果是,前者的做法不僅不利于民法典體系的完整性,同時也難以運用相關法理進行解釋;后者的做法又與商事主體、商事賬簿以及商事行為等高度抽象和概括的特征不符。因此,現有的立法技術不能解決全面抽象商事法律規范的問題。
從商事法律規范的可抽象性來看,如果采取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民法總則就必然要面對商事法律規范可抽象性不高的問題。也就是說,大量商事法律規范具有區格性的特征,其主要適用于特定方面的商事關系,而對其他領域的商事關系不產生具體的調整效果,商事法律規范的這種區格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商事法律規范可抽象性較低的問題。而且,商事法律規范的區格性特征降低了對其進行抽象的必要性。在具體的商事活動中,沒有具體的現實需求要求歸納出不同商事領域中適用規范的內在一致性概念或者概念體系。在現有單行商事法律規范的調整下,商事活動能夠順利開展。強行對不同領域的商事法律規范進行抽象,無疑是無用之舉,并不能起到良好的效果,只能增加商事法律規范的復雜程度。例如,如果強行對民事和商事的規范進行抽象和歸納,其結果是削弱了商事規范在現實中的重要作用,同時也會對民法典體系造成混亂。因此,由于商事法律規范自身缺乏可抽象性,使得現有立法技術不能較好地抽象商事法律規范的具體內容,強行為之,只能起到混亂民法典體系,以及影響商事法律規范適用的效果。
(二)對立法實踐可行性的異議
在我國民法總則起草的具體立法實踐中,無論是對商事基本原則的規定、商事主體的基本規定,還是對商事新型權利的規定、商事行為和商事的規定,都存在一些問題,無法實現民法總則對商事法律規范的有效整合,因此民法總則將大部分商事法律關系納入其調整范圍,遭到廣泛的質疑。
從商事基本原則來看,如果我國在立法實踐中采取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那么商事基本原則必須被納入民法總則之中,例如商事主體法定原則、營業自由原則,以及外觀主義原則,等等。一方面,這些原則存在抽象難度大的問題,由于商事主體法定原則、營業自由原則以及外觀主義原則等本身已經是原則層面的規定,在立法實踐中很難對其進一步抽象,如果在立法實踐中直接將其規定于民法總則之中,其本身又難以發揮調整其他民事法律關系的作用,因此將喪失其作為基本原則的意義。另一方面,還可能出現過度抽象的問題,例如將營業自由抽象為民事法律中的意識自治原則,或者通過意思表示理論來進一步抽象外觀主義原則,其效果是喪失了營業自由的部分內涵,切割掉了外觀主義部分重要的意義。因此,在立法實踐中將商事基本原則歸入民法總則是不恰當的。
從商事主體來看,如果我國在立法實踐中采取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那么關于商事主體的規定就必須納入民法總則之中。但是問題是,商事主體仍然存在民法總則難以進行抽象的諸多問題,這樣可能會對民法總則主體規范內容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亂,致使民法總則主體規定處于不穩固的狀態。例如,商事登記制度是具有明顯商事法律特征的法律規范,如果將其納入民法總則的規定之中,其適用范圍僅能涉及相關的商事法律關系,而無法且不能對民事法律關系進行調整,因此這一規定將使商事登記制度陷入兩難的尷尬境地。再如,將商事主體制度納入民法總則的規定之中,還存在規定細化的處理問題。如果將商事主體的細化規定放入民法總則,該規定的一般性就會遭到質疑;如果不將其放入民法總則,那么在相應的立法體系中又缺乏其置身的具置,這一點與瑞士的法律規定極其相似。
盡管瑞士民法典中規定了民事主體與商事主體的不同標準,但是在解決商事主體認定和適用問題時仍然存在困難。對商事行為的規定主要體現在瑞士債法典中,然而不僅其條文的合理性受到質疑,而且商號和商事賬簿與債權之間的關系也受到普遍質疑和詬病。因此,在立法實踐中將商事主體歸入民法總則是不恰當的。
從商事行為來看,如果我國在立法實踐中采取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那么大量的關于商事行為的法律規定也必須納入民法總則之中。然而,將商事行為納入民法總則之中,甚至通過法律行為概念對商事行為進行統一規范,仍然存在不可抽象或抽象過度的問題。首先應該承認的是,法律行為概念具有較高程度的概括意義,其能夠從行為成立、意思表示,以及行為效力等方面對商事行為進行抽象概括。商事行為涉及不同類型商事行為的區格問題,例如,票據、保險和證券等領域存在較大的差異性。此外,商事行為中還存在更為重要的商事組織行為與商事交易行為的區別,如果完全將其抽象為法律行為,商事行為的諸多個性化問題將難以得到有效的解決。從現有的民事法律立法狀況和立法建議來看,如果實行民商合一,商事法律規范將集中于總則和債權編中。從現有的商事實踐來看,無論是將票據行為、經營行為等商事行為規定于民法總則之中,還是規定于債權編中,都缺乏一定的合理性。此外,將商事行為納入民法總則的規定之中,會出現抹殺民事與商事行為間差異的效果。因此,在立法實踐中將商事行為歸入民法總則是不恰當的。
四、當前我國民商法關系的再定位
無論從商事法律的獨特性來看,還是從民法的兼容性來看,民法總則很難承載全部商事法律規范的抽象工作。從立法技術和立法實踐來看,不適宜將商事總則納入民法總則之中,因此有必要對民法典制定背景下的民商法關系進行重新定位,厘清二者之間的具體關系,為民法總則提供必要的法理上的支持。應當明確的是,所謂的民商合一或民商分立都不是絕對的合為一體或是絕對的并行,而是民法與商法在何種程度上安排彼此相關的規定,確定彼此之間合理的定位,以期實現法律關系調整的最優社會效果。
從我國現行的法律體系出發,依據相關民商合一或民商分立的基本劃分標準,在民法典缺位的具體狀況下,我國的民商法關系更類似于民商合一的狀態,而且這種狀態在民法總則的制定過程中被進一步延續和確認。應當看到的是,這種體制存在較為明顯的弊端,其對商事行為的調整缺乏統一性和系統性,造成了商事法律規范具體適用中的困難和混亂。究其原因,忽視了商法的獨立性,同時對立法技術和立法實踐的關注不足。對當前我國民商法關系的再定位,其意義就在于在民法典制定的大背景下,從我國現有法律和未來可行性的角度出發,確立民法和商法在我國私法體系中恰當的位置。
篇2
關鍵字:動機錯誤,表示錯誤,信賴保護
一、引言
私法自治為民法重要之基本原則。“依Flume的經典表述,所謂私法自治就是‘個人依其意志而自我形成其關系的原則’”。 私法自治,在法律上是通過推行法律行為制度來實現,法律行為是以意思表示為要素,并依該表示的發生法律效力的行為。 由此可見,當事人系依意思表示設定其所意欲之法律關系,實現私法自治之功能。故此要求當事人之意思表示系健全、無瑕疵的,始能確保約定之法律效果之正確。而若當事人意思表示時,其主觀認識與現實不一致,即生意思表示錯誤 之情形,此時,表意人即難以依自己內心意思自主追求其所意欲之目的效果,即難謂表意人自我決定之真正達成,故錯誤之存在很大程度上私法自治功能之實現。然而,錯誤于人在所難免,因此,如何規范意思表示錯誤所生的種種問題,因其涉及之利益關系及情事之復雜性,遂成為各國立法者所共同面臨的難題。
在意思表示錯誤問題上,我國民法理論及制度實踐向采借鑒德國法的立場 ,此于當前私法制度背景下,本也無可厚非。只是,必須明確,任何私法制度的移植,均不只是簡單的技術層面的規則繼受,更在于其所附載的制度價值,然價值的吸收、融合乃至共識形成,須依附于特定的情境及文化傳統。僅此一點,即足于提供我們對繼受他國法制反思的力量,切不可在制度建設上只是充當簡單的“拿來主義者”,尤其是在民法典制訂前夕,更需要我們具有一種懷疑批判的精神去反思,于諸多現有及可能的不同制度設計中,德國法上該制度是否具有不容置疑的合理性,以至于我們只須簡單的受用,筆者以為不然。基于此問題意識,本文嘗試著對德國法上的意思表示錯誤理論作一分析檢討,或可提供對于德國法上該制度的不同認識。
二、德意志法錯誤理論的演進及薩維尼理論的提出
古日耳曼法如同其他古代法一樣,注重法律行為的表面形式和公開面貌。古日耳曼法沒有虛假法律行為這一概念,因而承認虛假法律行為的效力。公開行為在法律行為上既然具有無可爭議的價值,因此與羅馬法相同,當事人在許多法律部門中利用公開行為所為的虛假行為仍然有效。同樣,古日耳曼法亦絲毫不考慮錯誤。總之,用近代法律術語來說,傳統的日耳曼法采用表示主義。
但是,自從接受羅馬法開始,情況有了較大的改變。德意志普通法在羅馬法的影響下改用意思主義,因此,凡是由于錯誤而導致的雙方的真正意思不一致,人們就會認為沒有合意可言。凡是由于錯誤意思不一致,或者存在意思表示上的錯誤,法律行為一律絕對無效。上述各種情況都不加區別地統稱為破壞合意的錯誤,其結果均是導致法律行為的徹底無效。德意志普通法以及以后的羅馬法著作選學派稱之為“法律行為的不存在。”
法律行為不存在這種制裁適用于廣義的各種形式的錯誤,因此注釋學派提出錯誤的分類,這在當時并沒有多大的意義,但是,到19世紀下半期、后期的德意志羅馬法著作選學派關于錯誤的理論有了新的演進,即向多種錯誤理論。學理日益重視動機錯誤,人們發現動機錯誤是指意思形成中的錯誤,所以很接近脅迫或詐欺所構成的同樣涉及意思形成的瑕疵。人們主張可以用與脅迫、詐欺相同的撤銷制度來制裁這種形式的錯誤。也就是說,人們開始主張用絕對無效的方式來制裁“不存在”的法律行為,而對于動機上的錯誤用撤銷來制裁。
德國普通法之錯誤論在許多觀點上,不僅影響德國民法的架構,亦廣泛影響大陸法系國家的錯誤論,而在普通法時期給予錯誤論以深遠影響的人則首推薩維尼(Friedlich card von. Sayigng 1779-1861)。薩維尼是第一個明確區分動機錯誤與表示錯誤兩種不同性質錯誤的學者。在薩維尼的錯誤論中,嚴格區別“值得法律保護之表示錯誤”與“不值得法律保護之動機錯誤”,因薩維尼認對法律關系之形成,具有重要性的獨立事實系“意思”,而“動機”只是意思的準備過程,二者應區別,故動機錯誤,雖然是“真的錯誤”,但動機只是意志形成的緣由,并非意思表示(法律行為)的內容,并且動機縱使經表示,原則上亦不認須由法律加以保護,而其根據則是保護交易安全,以免交易陷于無界限之不安定與恣意之中,至于所謂“性質錯誤”,薩維尼則明知非意志與表示的不一致,但因立于忠于羅馬法法源權威之歷史法學派的立場,認本質的性質錯誤與客體錯誤相類,均是意思欠缺,而適用錯誤之理論,惟并非任何性質錯誤均可適用,必須錯誤在交易觀點上重要始足當之。 薩維尼主義所引起的唯一的回應是《德國民法典》第119條第1款。 此后,日本、民法在該問題上基本繼受德國立法。《德國民法典》第119條規定:“表意人所為意思表示的內容有錯誤時,或表意人根本無意為此種內容的意思表示者,如可以認為,表意人若以其情事,并合理地考慮其情況,即不為此項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對于人或物之交易上重要的性質所發生的錯誤,視同于表示錯誤”。 學理上一般認為,德國民法典此條規定中最重要之類型化劃分為表示錯誤 與動機錯誤,對于后者,遵循薩維尼的理論,基本不發生對于合同效力的影響;而對于表示內容錯誤,學理多將其進一步區分如下:①關于法律行為種類或性質之錯誤(如誤贈與為借貸而承諾),②關于標的同一性之錯誤(如誤以為漢英字典,而買英漢字典),③關于當事人本身之錯誤(如誤甲為乙而與之訂約),④關于標的價格、數量、履行期、履行地之錯誤等。
在大陸法系有些國家立法上, 錯誤主要基于其“嚴重性”而發揮作用。按照“錯誤者無意思”的思想,錯誤破壞了同意的完整性,因此基于錯誤而訂立的合同是不應該具有約束力的。 但為顧及交易安全,各國民法均規定只有那些達到一定嚴重程度的錯誤才可救濟。這種思想到了德國民法典那里得到了進一步發展,不僅合同可因錯誤方單方宣告撤銷,甚至連錯誤方當事人自己的過失亦對其撤銷權不生影響。這種不問相對方情況,僅依錯誤的嚴重性決定是否施以救濟的實踐表明:在這些國家中,錯誤制度發生作用的機理主要是對當事人意思質量的關注。 而其錯誤立法的另一個特點是:多對可獲救濟的錯誤種類給予嚴格限定,只有當錯誤屬于法定種類時才可救濟。 此可視為類型化的必然,同時也帶來對錯誤種類歸屬問題上所有的特殊困難。
三、方法論基礎之分析檢討
以薩維尼錯誤學說為基礎,德國學理一般主要將錯誤區分為動機錯誤與表示錯誤,表示錯誤,為意思與表示間之不一致,于交易上認為重要者可產生對于合同效力的影響;而對于動機錯誤,則視其意思與表示間并無不一致,僅在意思形成階段,對于與意思表示有關的事實認識有誤,因認在此之自我決定仍不失為自我決定,因此,于此情形,通常不給予有動機錯誤之表意人以救濟而不認系違反私法自治原則。 由此可知,動機錯誤與表示錯誤劃分的方法論基礎在于錯誤發生階段之不同。依此,動機錯誤為意思形成階段的錯誤,意思的形成,常受許多不同考量因素所影響,如甲決定向乙買某屋,其考量因素有系針對自己之需要(自用、保值、投機)者;有系針對標的物本身(房齡、安全性、房屋之座落、使用之限制、價格)者;有系針對償債之事項(貸款之取得,房屋之收益)者;亦可能針對意思表示之相對人(信用、政商背景、人際關系)者,形形,不一而足。就上述有關考量因素表意人認識錯誤時,則意思形成發生錯誤,被認為系動機錯誤。 表示錯誤為意思表達階段產生的錯誤而致意思與表示不一致,在德國法上被區分為表示行為之錯誤,即誤作非所欲的表示,如誤說、誤寫、誤取等,及表示內容之錯誤,即從形式上看,表意人所說的或所寫的應是他所欲的,但他認為他的表示具有的意義是表示所沒有的,因此產生錯誤。
作為一種以錯誤發生階段為基礎的對錯誤的類型化方法,界限之清晰在理論上尚且可以,只是問題事關心理及動機等有關心問題,實踐上之劃分因此易生、常生問題。其實,正如Flume所指出,法律生活中絕大多數的錯誤案例為性質錯誤及錯誤。 恰是在性質錯誤問題上,德國民法典第119條第2款的規定表現了其不夠成功之處,該款規定,關于人或物的性質的錯誤,如交易上認為重要者,視為關于意思表示內容的錯誤。用“視為”一詞,即表明屬于擬制的規定,在立法上是相當呆笨拙劣的手法。 由此引起對性質錯誤屬性的爭議。性質錯誤的特征是指某項交易中約定的或視為約定的性質與真正的性質有差別。這里所謂性質是指合同范圍內,雙方同意的或者至少一方要求,另一方知情的標的物應具備的約定品質。法學界大多數意見認為性質錯誤指起決定作用的動機錯誤,但是一種特殊性質的動機的錯誤,德國判例多認為性質錯誤屬于決定性動機的錯誤。
在德國,有學者對薩維尼進行了批判,他們認為薩維尼主張的意思欠缺(表示錯誤——筆者注)的主要場合的關于物和相對人的錯誤不過為一種心理上的動機錯誤,而作為立法定式放棄對心理的探求,認為表示內容的錯誤與表示上的錯誤的場合則可以撤銷,將交易本質的性質錯誤與之同樣處理。 而對于性質錯誤與同一性錯誤, 很多學者認為難以區別,而德國學者蒂策則甚至認為無法在表示錯誤與性質錯誤之間作出區分。 事實上,僅僅通過抽象概念的形成,似乎可以抽象出二者之不同, 但實踐中,由于涉及心理及動機問題,常常難以作出清晰的劃分。對此,我國學者沈達明先生也意識到,他認為對于標的物應有狀態的錯誤,是涉及意思與表示關系上的錯誤,所以屬于表示上的錯誤。這里所指的是關于標的物應有狀態的錯誤,而不是關于標的物真正狀態或性質的錯誤。標的物的基本性質不但應從作為產生表意人成立法律行為的意思和動機角度加以考慮,亦應該作為表意人思想上對該標的物的看法的一個組成部分加以考慮。就此他舉了超市購買葡萄酒案。表意人購買葡萄酒,誤認某種商標的酒是甲省產品,表意人購買的是具有甲省產品特點的酒。但實際上酒為乙省產品。對此案件,筆者分析如下:事實上,此種錯誤仍然可以作為動機錯誤或表示錯誤,端視其意思為何,其一,可以說若表意人其內心意思在于購買具有甲省特點的酒,則其意思形成沒有錯誤,而其表示取貨付錢,表示意義則在于購買其取之貨,而其取之貨事實上不具有甲省產品特點,此時,意思與表示之間發生不一致,則錯誤系屬表示錯誤。若說表意人其內心意思在于購買其取之貨,即這種酒,而購買之原因則在于認為這種酒具有甲省產品特點,事實上則否,則因對事實認識錯誤而促其形成買“這種酒”之意思,而其表示沒有任何錯誤可言,因而錯誤系屬動機錯誤。只是,表意人內心意思如何無從確切地知曉,因為其隱藏于內心也,因此,筆者認為在此無法區分性質錯誤與表示錯誤。 對此案件,沈達明先生作了類似的分析。他認為表意人的錯誤可以從兩個不同角度分析,第一,作為表示意思與實際情況之間關系的錯誤;第二,仍然作為表示上錯誤處理,肯定內心意思與表示之間的不一致。他指出,對于標的物應有性質的錯誤必然包含同時發生的,涉及標的物真正性質的錯誤,就是說,始終可以作為性質錯誤處理。 因此,“應有性質”是表意人內心意思層次,其可能同時指向表示與標的物真正性質發生關系,所以,在此欲明確界分動機錯誤與表示錯誤是很難甚至是不可能的。
在錯誤問題上繼受德國法的日本,基于對表示錯誤與動機錯誤所作的分類,以往錯誤論的主要觀點,認為只有表示錯誤具有法律意義,這種觀點被稱為二元構成說,然而對這種二元構成說,很早就有不同觀點存在,主張錯誤應為包括動機錯誤在內的一元結構,此觀點被稱為一元構成說。,一元說被廣泛接受,逐漸成為通說。 對二元構成說提出批評的學者主要有杉之原,舟橋與川島。而批評的論據之一則在于動機錯誤與表示錯誤難以區分。杉之原認為,作為意思表示內容的錯誤與表意人的主觀狀態無關,是否存在錯誤應依當時的具體情形下一般人產生何種認識來判定。為存在這一正常人的觀念屬于心理學上的意思還是動機問題。因為很難把所謂心理的動機錯誤與其他錯誤區別開來。 舟橋認為,動機錯誤也可以產生與表示相對應的真意欠缺這一點與他種錯誤相同,且在實際交易中這種錯誤往往屬于典型錯誤。 而川島的觀點則是:區別意思與動機十分困難。不僅心理的性質錯誤,即使屬于意思欠缺的典型情形的同一性錯誤也不過是一種動機錯誤,事實上,很多錯誤在此意義上卻是動機錯誤。其甚至認為,嚴格地說,引起意思欠缺的錯誤僅限于由于中介機關誤傳而產生的意思表示錯誤。 綜合分析以上諸學說之不同觀點,確切而言,錯誤是與心理的意思相關還是與動機相關是很難判明的。薩維尼基于維護交易安全的目的以心理為劃分基準創立了二元構成理論,該理論存在基準不明確的缺陷,恰如前所分析,性質錯誤與同一性錯誤往往難以區分,而性質錯誤為最典型也最常發生的動機錯誤,同一性錯誤則為表示錯誤之常態,因此,可以說,動機錯誤與表示錯誤其實常常是難以區分的。即使是關于法律行為種類或性質的錯誤,如誤贈與為借貸,而承諾之,在此,錯誤常被解釋為意思與表示之間不一致,但也可以說,錯誤地以為是借貸是表意人作出承諾的動機,因此,似乎可以認為這是動機上的錯誤。這里作為立法定式放棄了對心理的探討而將該類錯誤類歸于表示錯誤,事實上是法律上以內容重要性為判斷并以之為基礎的類型化產物,反映出對于錯誤是否施以救援的一種思維方式,依此思維方式無需進一步探討心理意思與動機問題。因此,可以說,這樣的二元劃分其基準是不明確的。
四、目的論所在之分析檢討
前文對動機錯誤與表示錯誤區分的分析表明,二者之區分即使不是不可能的,在實踐中也往往是很困難的。事實上,對于動機錯誤不予救濟的正當化理由是不夠充分的,一般認為,表示錯誤破壞的是意思的完成,作為意思外在表達的表示,并沒有正確反映表意人內心意思。而動機錯誤在意志形成階段就產生了,因此它破壞的僅是意思的決策。因有瑕疵之自我決定仍不失為自我決定,縱不予當事人以救濟之途,亦不違反私法自治原則。對心理的動機錯誤,因認其不具有意思欠缺而不賦予其具法律意義的處理是意思主義的產物,其實,正如前所引舟橋之觀點,動機錯誤也可以產生與表示相對應的真意的欠缺。如卡拉里斯所言,動機錯誤反映的是對表意人事實決定自由的損害,事實上,若表意人無對事實之錯誤認識,即不可能產生違背其真意之意思從而對其加以表達,在此,其表示即符合其真正意思嗎?表意人真正實現私法自治了嗎?私法自治與合同自由并非因其自身原因而受保障,而是因其首先服務于人的自己決定規則。 這一點在合同法領域顯然是通過法律工具——即通過合同的訂立——而達致。但只有在當事人的意思形成不僅原則上無法律性障礙,而且在事實上亦不受損害的情況下,合同這種工具才能實現其最佳效果,在動機錯誤的情形下,當事人的意思形成實質上已經受有損害,因此,在服務于私法自治及合同自由的實現上,難言其已經有效地實現。因此,從自我決定、私法自治角度正當化對動機錯誤的區別對待顯得有些蒼白。事實上,德國法及繼受德國法之日本、臺灣等國家、地區法律亦未能完全區別對待動機錯誤與表示錯誤,其法典中均有將交易上重要的性質錯誤視同表示錯誤之規定, 而鑒于性質錯誤為現實生活中常發生之錯誤類型,因此,可以說立法者并未能在立法上完全貫徹薩維尼提出的二元構成學說。
有學者認為,動機錯誤不得撤銷的實質理由,并非因所誤認之事實,非他人所得而知,而系基于合理分配危險之思想,表意人對意思形成上有關之事實之認識是否正確,為自己應承擔之風險,而不得轉嫁于相對方,若不愿承擔此風險,則應設法將此事實提升為法律行為之附款(條件或期限),使法律行為之效力系于此等事實之存在或不存在。 在此,提出了危險分配思想,就動機錯誤為產生于自己認識錯誤而應由自己承擔之風險,因表示錯誤而產生的不利益,難道就不應歸因于自己而可轉嫁于他人或由他人分擔嗎?很顯然,同樣是自己錯誤引致的風險,從中并不能提取對錯誤區別對待的根據。而恰恰是危險分配思想,讓不少學者質疑對于因表意人自身原因產生的錯誤加以救濟的正當性。合同自由包含了法律所認可的當事人可通過合同依其意思設定法律效果的權能,由此體現的是意思自治,意思自治的應有之義則為自己責任,所謂自己責任,即自主參與者對于參與所導致的結果的承擔,承擔是參與的必然邏輯。唯參與是自由的、自主的,故而結果便只能歸于參與者。 錯誤固然破壞同意的真實性,但允許因錯誤而解除合同充其量不過是滿足一方的個別正義的要求。“對凡是嚴重的錯誤一律予以救濟,其實質就是要求相對人去分擔損失,這不僅不利于交易確定性之維護,也缺乏起碼的道德上的說服力”。 因此,對于歸因于自己之表示錯誤,除非有撤銷的特別理由,事實上難于從內在于私法自治之自己責任原則上去求得救濟之支持。“必須強調,錯誤原則的根基,是容許補救的特殊性,這個觀念值得贊許,因為它推廣確定性和交易的可靠性。在更高的哲理層次上,比較法律學者往往欣賞普通法的處理方式:為什么合同法在合同出錯時的處理方式與人們在生活中出錯時的處理方式不一樣?這個道理不是明顯的,在生活中,人須為自身的錯誤負責。假如接受這個,便了解到錯誤的風險必須由犯錯的人負擔……若是按這項原則適當地分配風險,因錯誤而撤銷合同,必然是特殊情況。”
在錯誤二元劃分的目的論基礎上,德國學者克拉默認為《德國民法典》對動機錯誤的調整在總體上是錯誤的,他認為判斷表意人是否可因這類錯誤而撤銷表示,必須以對方當事人對錯誤的產生是否負有責任或者他是否本應注意到錯誤的存在為準,至于錯誤是否恰恰涉及人或行為標的物的性質,則在所不問。 在此,克拉默從應然法角度引入了對相對人行為方式綜合評價的思路,從而亦揭示德國法錯誤論上只關注表意人狀況的實踐立場。而日本堅持一元構成說的學者,立基于交易安全保障的立場上,甚至進一步認為,就所有錯誤而言,為交易安全的保障,相對方對表示是否具有善意信賴為關鍵而錯誤在表意人的內心上與意思相關還是與動機相關并非重要問題……,在意思表示的內容與效果以表示為基準的表示主義之下,可以克服意思主義存在的不足。 也許,若是以信賴主義為立場,那么錯誤的風險將由犯錯誤的一方當事人承擔,人們也因此將普遍拋棄那些潛藏在有關錯誤的真實意思原則規范中的不適當殘余。
五、結語
以上是本文對德國法錯誤的主要類型劃分及其適用實踐的檢討。對于德國錯誤法規則的設計,可以說,薩維尼基于維護交易安全的目的以心理為劃分基準創立的二元構成,其不僅存在基準不明確的缺陷,也不符合實際交易中的要求,不能指導正確解決實踐,而且對其正當化也存在理論上的困難。在此須知,類型僅在于提供對錯誤的認識可能及作為權衡思考時之考量因素,切不應將其上升為區別對待根據從而機械適用類型——效力模式,在因于錯誤所涉情事之復雜性,而不可將其作簡單的類型對應從而致一方利益所得之保護不當地建立于他方損失基礎上,致有損正義之精神。從根本上說,“法律基本是關于各種價值的討論。所有其他問題都是技術問題。”故法律制度的生成,法律規范的設計均以一定的價值判斷為依歸。 德國法上錯誤規則的設計當為一定價值判斷基礎上法技術的產物,對于作為其基礎之價值判斷,因視的法律情況而有所不同,對其存在只能作辯證評價而無絕對高下之分。只是當我們試著去建構自己精致有效的錯誤規則時,當我們有意去借鑒他國法制時,切不可忘記問題本身的復雜性及制度背后的價值選擇而作簡單的移植,否則,將只是在對自身無知基礎上危險的武斷。恰如前文所言,在錯誤問題上,可能我們不能再只是簡單地選擇對意思真實的所謂絕對尊重。而當我們站在信賴保護的立場上,引進對相對人行為方式綜合評價思路,則對于錯誤規則的安排,我們不能只是滿足于單一或少數因素的考察。而如科賓所言,把法律規則限制得可適用于許多因素的特定組合, 或可為我國私法開辟一條新的錯誤法思路。
注釋:
[1]本文是在筆者碩士論文《意思表示錯誤對合同效力的》第四部分的基礎上修改而成的。當然,本文不可能就德國私法上意思表示錯誤制度作全面評析,而只是就其中的動機錯誤與表示錯誤的二元劃分作一檢討,以此作為民法典制定前,對錯誤制度的個人意見的表達。
[2]Flume:《民法總論》,1992年4版,§1.1,轉引自卡拉里斯著,張雙根譯,唐壘校:《債務合同法的變化》,載于《中外法學》2001年第1期,第36、37頁。
[3]張俊浩:《民法學原理》上冊,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修訂第3版,第219、220頁。
[4]錯誤乃指表意人因自身原因致其主觀認識與現實之間不一致,而這種不一致并不為表意人所知。意思表示錯誤包含兩方面:一是意思表示自身錯誤,即表意人的效果意思(主觀)與表示(客觀)不一致,如各種表示錯誤等;二是意思表示前提或基礎錯誤,即表意人對意思表示之前提或基礎之主觀認識與客觀現實不一致,如共同錯誤、動機錯誤等。對于意思表示錯誤,學者們所下的定義不盡一致,在此不擬列舉。緣何采此定義,筆者以為其比較符合德國法及中國法對錯誤內涵的界定。
[5],我國民法對意思表示錯誤的規定亟須完備,而理論上對錯誤的還很薄弱,除了教科書式的,對錯誤作德國法式的介紹性文章外,據筆者努力收集大陸資料所及,僅發現有徐曉峰、解志國、唐瑩等人所著論文幾篇,而且多就德國法模式來解釋中國的法實踐,此容易陷入盲從式的怠于反思的治學心態。
[6]以下對德國錯誤法理論的歷史發展描述,主要參照,沈達明等編著:《德意志法上的法律行為》,對外貿易出版社1992年版,第116、117頁;周占春:《表示行為錯誤與動機錯誤》載于楊與齡主編:《民法總則爭議問題研究》,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印行,88年9月二版,第272—277頁;葉金強:《合同解釋:私法自治、信賴保護與衡平考量》,載于《中外法學》2004年第1期,第62、63頁。
[7]轉引自周占春前引文第274頁。
[8][德]海因·克茨著,周忠海等譯:《歐洲合同法》(上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63頁。
[9]按德國民法典之規定,從薩維尼的角度看,意圖和表達之間不匹配,因此撤銷是正當的。
[10]表示錯誤還被進一步細分為表示行為錯誤與內容錯誤。
[11]如德國、法國、瑞士等。
[12]徐曉峰:《民事錯誤制度研究》,載于人大報刊復印資料?民商法學,2001年第1期,第37、38頁。
[13]陳自強:《意思表示錯誤之基本問題》,載于《政大法律評論》,1994年第52期,第334頁。
[14]陳自強前引文,第317頁。
[15]陳自強前引文,第336頁。錯誤亦為錯誤法上一個極復雜的問題。對于計算錯誤,本文不擬專門探討。
[16]沈達明前引書,第126頁。
[17]沈達明前引書,第 126頁。
[18][日]小林一俊:《意思欠缺與動機錯誤》,載于《外國法評譯》1996年第 4期。第68頁。
[19]包括標的物和相對人的同一性錯誤,至法律行為性質錯誤,是否屬于同一性錯誤,尚有爭議,此在德國民法上是為表示內容錯誤之重要類型。
[20][德]卡爾·拉倫茨著,王曉曄等譯:《德國民法通論》(下冊),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507頁。
[21]同一性錯誤之特征,系意思表示中之陳述涉及特定之人或客體,但相對人客觀上所得了解之人或客體,與表意人主觀上所指之對象不同。
[22]此案型似也足于論證日本學者朱倉教授提出的“同一性錯誤與性質錯誤具有相互還原性”的觀點,見小林一俊前揭文第69頁。確實如此,即使是關于當事人同一性的錯誤,如誤甲為乙而與之訂約,經類似分析,仍然可以歸之為性質錯誤,即為動機錯誤。
[23]沈達明前引書,第120頁。
[24]小林一俊前揭文,第68頁。
[25]杉之原舜一《“法律行為的要件”的研究》,《法學協會雜志》43卷11號,轉引自小林一 俊前引文,第69頁。
[26]舟橋淳一:《意思表示的錯誤》,《九大法文學部十周年紀念法論文集》,轉引自小林一俊前引文,第69頁。
[27]川島武宜:《意思欠缺與動機錯誤》,《法學協會雜志》56卷8號,轉引自小林一俊前引文,第69頁。
[28]Flume:《民法總論》,1992年4版,§1.1,轉引自卡拉里斯前引文第37頁。
[29]此規定于《德國民法典》第119條第2款,德國許多研究者認為該款是“不幸”的,見[德]海因?克茨前引書第279頁,注95.
[30]陳自強前引文第335頁,此觀點為學者洪遜欣等所堅持。
[31]張俊浩前引書,第32頁。
[32]見徐曉峰前引文第46頁。
[33]何美歡:《香港合同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83、284頁。
[34][德]卡爾·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下冊,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21頁。
[35][日]小林一俊前引文第69、70頁。
[36]朱慶育:《尋求民法的體系——以物權追及力理論為個案》,載于《比較法學文萃》,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610頁。
篇3
內容提要:在現有的經濟社會背景下,以過錯為核心的傳統侵權法逐漸暴露了其不足。可救濟性損害理論的引入,有效地彌補了過錯這一侵權法理論工具的缺陷,順應了損害救濟理念的發展趨勢,給侵權法理論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可救濟性損害理論的運用,宜采取“一般條款+類型化”模式,并應處理好與過錯責任的銜接關系。
一、引論
物權法起草塵埃落定后,制定侵權法成為了當前我國立法工作的熱點。目前,關于侵權法起草的爭論多集中在侵權法的立法模式、歸責原則和具體侵權行為類型方面。然而,這些討論都未能擺脫過錯這個侵權法傳統的理論分析工具的桎梏,學者們的分歧僅僅在于如何界定和判斷過錯,以及如何編排過錯責任和無過錯責任。[1]在他們看來,以過錯責任為代表的歸責原則在整個侵權法中處于核心地位,是構建整個侵權法的內容和體系的關鍵。正因為這種根深蒂固的觀念,以過錯責任為基礎的侵權法在面對新類型侵權的挑戰時,顯得有些力不從心。即便意識到了過錯侵權責任的不足,在引入了過錯推定和無過錯責任后,侵權法的發展依然步履維艱。應當指出,在社會經濟生活不斷發展和科技日新月異的今天,侵權法所崇尚和追求的充分保護社會合法權益的目標并未如我們所愿而順利實現,立法者無法對侵權法的體系和結構作出根本改變,侵權法在保護現有合法權益和新型法益時,運行仍不順暢。究其原因,是由于傳統侵權法理論分析架構限制了立法者的視野,關于過錯責任、過錯推定責任和無過錯責任等歸責原則的爭論始終困擾著人們。或許,尋找新立法的思路,建構全新、科學的歸責體系才是一勞永逸的解決問題的方法。
所謂歸責,是指侵權行為人的行為或物件致他人損害的事實發生以后,應依何種根據使其負責。[2]臺灣學者邱聰智指出:“在法律規范原理上,使遭受損害之權益,與促使損害發生之原因者結合,將損害因而轉嫁由原因者承擔之法律價值判斷因素,即為‘歸責’意義之核心。”[3]可見,可歸責性是法律借以確定侵權責任歸屬的根據或曰考慮要素,是侵權法價值判斷的核心,其體系的科學性和合理性程度決定了整個侵權法的立法結構和生命力。[4]然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學者們習慣將侵權法的可歸責性簡單地理解為歸責原則,并將過錯作為侵權法最基本的理論工具。這種分析工具的單一性限制了侵權法的開放性,造成了侵權法的僵化和守舊。隨著侵權損害救濟理念的發展,各國都在竭力尋求比過錯更具開放性和包容性的理論工具,以此達到通過救濟實現正義的公共政策目的。以《荷蘭民法典》和《歐洲侵權法草案》為代表的新時期立法或立法草案,逐步引入了“可救濟性損害”這種全新的侵權理論。可救濟性損害理論將鮮活的社會生活與立法者的意志緊密結合在一起,既靈活地體現了公共政策,又不失法律的邏輯性與嚴密性,其出現和廣泛應用勢必對圍繞過錯為核心建構的傳統侵權理論體系造成極大的沖擊,并將促使人們更新侵權法的理念。
本文將通過考察各國侵權法的立法和實踐,揭示過錯作為傳統侵權法理論分析工具的特征及其制度缺陷,闡明可救濟性損害理論產生的背景和根據,并對其含義、特征、類型等進行初步分析,進而對可救濟性損害理論的制度構想提出若干建議。
二、侵權法理念的發展及其制度需求
(一)侵權法理念的發展
1.損害救濟理念的凸顯
關于侵權責任的功能,素來有預防性、懲罰性和補償性三種學說之爭。但隨著責任保險和社會保障制度的引入,侵權法的預防性和懲罰性的功效在不斷減退,而補償性漸強。在新的經濟社會思潮的影響下,侵權法的哲學基礎正在發生變化,近代侵權法的抽象個人主義基礎受到根本的動搖,侵權責任的道德正當性不斷受到沖擊,法律開始轉向關心具體的個人,注重對每個具體個人合法利益的保護。有學者評價:“這種對具體個人關懷的理念在侵權法中的體現就是損害救濟理念的發展,即確定是否構成侵權責任的核心因素不再是侵害人是否有過錯和是否侵權,而是受害人應否得到救濟,如果衡諸受害人方面有進行法律救濟的必要,則往往就會通過各種途徑去認定侵權責任的存在。如此,法律關注的重心不再是加害人的道德上可責難性,也不是個人的主觀權利受到侵害,而是對受害人進行必要的填補,使其得以在物質和精神上獲得必要的滿足,以維護其人格的完善,維持基本正常的生活。”[5]德國學者福克斯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可以肯定,侵權行為法所傾向的重點已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了變化。若探求責任法律制度領域最新的發展至當前的形態的動力,則我們不能回避公民對安全的要求以及由此產生的對社會安定的需求。人們期待侵權行為法和損失賠償法能有助于保障個人的基本生存,并以此建立相應的社會化國家機制。事實上,正是在這種期待中,我們才能探察到侵權和損失賠償法律制度發展至今的決定性動力。就此,法律所強調的重點已從承擔過錯轉移到了補償損失。”[6]這種轉變體現了侵權責任向補償的回歸。“私法責任之本意主要不是談論要不要由加害人承擔責任,更不是如何制裁和消滅侵權和違約行為,而是怎樣合理分擔受害人的損失。”[7]因此,注重對受害人損害的填補和救濟,已經成為了各國侵權法發展的共識。[8]
2.侵權法由行為人本位走向受害人本位
過錯責任是以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為基礎,強調從行為人的角度思考和認識問題,認為人作為獨立自由的理性人,可對自己的行為做出理性的選擇,亦應對自己的錯誤行為負責,由此產生的歸宿點是有過錯即有責任,無過錯即無責任,此謂之行為人本位。其最大的價值在于尊重和保障了行為人的行動自由,但卻忽略了對權利的救濟和受害人的補償。正如我們所知,在現代私法體系中,合同法是鼓勵人們創造財富的法律,而侵權法是保護人們財富的法律。從立法的目的和宗旨來看,鼓勵創造、保障自由是合同法的任務,保護權益、損害救濟才是侵權法的根本任務。行為人本位偏離了現代私法責任的原意,也與損害賠償理念的思潮格格不入。現代侵權法由行為人本位走向受害人本位,已是大勢所趨。所謂受害人本位,是指填補受害人的損害為基本宗旨,強調從受害人的角度思考和認識問題,對行為人行為的評價不再是侵權法關注的重點,什么樣的損害屬于法律可予以救濟的損害、如何進行救濟才是侵權法的基本命題。
當然,所謂受害人本位也僅僅指的是立法目的的傾向性,而不是完全不顧行為人的利益。因為在損害賠償法律關系中,受害人和行為人都是重要的元素,缺一不可。因此,在損害救濟和行為自由之間,侵權法總是要保持一定的平衡的。誠如我們先前所言:“在當前,既要堅持侵權行為法的一般規則,又要增強侵權行為法的補償功能,是侵權行為法建設的重要環節。”[9]
3.侵權責任理念由主觀主義走向客觀主義
近代民法強調意識自覺和自己責任,這在侵權法中的體現是主觀主義,具體表現為:在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中,以主觀要件即過錯為核心;過錯的判斷多采用主觀標準,注重考察行為人的主觀心理狀態;計算損害賠償數額時,以受害人的實際損失為準等。到了現代,隨著經濟交往和社會分工的深入,社會成員間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信賴不斷加強,人們對社會行為表象的信賴程度不斷加大,社會對提高效率和統一行為標準的呼聲也在不斷高漲。在這種形勢下,法律對社會變化做出了迅速的回應,呈現出行為標準外觀化的趨勢,侵權法中的主觀主義開始逐步讓位于客觀主義,主要表現在:第一,過錯概念的客觀化,其判斷標準采用了“理性人”、“善良家父”、“事實本身證明過錯”、“一般注意義務”、“漢德公式”等客觀標準;第二,侵權構成要件核心的客觀化,即作為主觀要件的過錯的地位減弱,作為客觀要件的損害的地位不斷上升;第三,損害賠償標準的客觀化,即損害數額不再一味以受害人的實際損失為準,社會公眾的標準被納入了考慮的范圍,例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將上一年度城鎮或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這一客觀標準作為了計算賠償數額的標準。
(二)制度需求
侵權法是權利的保護法,是現代社會最富有生命力和活力的法律。侵權法與經濟社會發展休戚相關,它反映和回應著變化中的經濟社會思潮和法學理念,注定是要肩負著多重使命的。在現有的以過錯為核心的理論架構下,侵權法應對新形勢和新發展的能力已經有所下降,傳統的侵權法律體系的正當性和合理性產生動搖。在這種情況下,侵權法需要進行自我更新,引入新的理論工具,回應理念發展帶來的制度需求。新的理論工具必須具備以下特點:
其一,充分體現侵權法的發展趨勢,有利于彌補過錯責任的不足。新的理論工具應當首先從受害人的角度考慮侵權責任的構成,從損害救濟的理念確定是否存在侵權責任,將客觀要件損害置于侵權責任構成要件的核心地位,更多地采用客觀的認定標準,并建立多元化的歸責體系。
其二,富有包容性和開放性,有利于把更多的人身權益和財產權益納入到侵權法的保護中來。新的理論工具應當具有相當的彈性,以便在應對各種新類型權益時沒有任何理論難題,實現對侵權法邏輯自足性的超越。
其三,便于科學化和體系化,有利于侵權法的法典化。在私法體系中,侵權法的規則大多是技術性的規則,不像物權法、婚姻法等法律那樣具有強烈的固有性和本土色彩。正因為如此,隨著經濟一體化的深入,各國侵權法的相互融合和逐漸統一的趨勢已經勢不可擋。融合和統一的最終形態就是實現侵權法的法典化。在我國,一部法典化程度較高的侵權法將對我國侵權法理論的發展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因此,新的理論工具應當具有嚴密的體系和嚴謹的邏輯,能夠在發揮一般條款的抽象性規范功能和列舉的具體性規范功能之間保持適度的平衡,從而在實現法典化的同時保持相當的活力。
在這種情況下,可救濟性損害理論應運而生,充當起了侵權法新的理論工具的角色。
三、可救濟性損害理論及其評價
(一)可救濟性損害概述
在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中,損害事實作為損害救濟的基本前提,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損害是一個發展的概念。在當代社會,侵權法的保護范圍不斷擴張,各種受到侵害的權益,無論是否形成權利,均可獲得救濟。損害賠償制度的適用范圍不斷擴大,損害的內涵也隨之發生變化。
侵權法中的損害,具有事實和法律兩個屬性。事實損害是指侵權行為所造成的受害人在人身或財產方面的事實上的不利益,法律損害則是指被法律所認可的能夠獲得賠償的事實損害。“一般而言,萬物相連,一個行為可以牽扯起無數后果,事實損害的邊界可以蔓延無際,而法律損害則必須止于當止之處。”[10]為防止損害的概念過于寬泛,避免行為人承擔“過分苛嚴的責任”,同時也為了涵攝法律政策的判斷,給受害人尋求法律救濟以明確的依據,有學者建議引入一個具有政策導向性的限制措施作為損害“當止”的標準。縱觀當今最新立法例,各國都不約而同地對損害作出了限制,并以此作為體現公共目的的政策手段。例如,《荷蘭民法典》第6·95條規定:“根據損害賠償的法定義務應當予以賠償的損害包括財產損害和其他損害,后者以法律賦予獲得相應賠償的權利為限。”[11]這明確了損害必須在法律認可的范圍之內。正在起草中的《歐洲民法典·侵權行為法草案》則主張應在損害之前加上“具有法律上的相關性”的限定。對于上述論及的法律認可的損害,我們可以歸納為“可救濟性損害”。
所謂可救濟性損害,是指客觀存在的、且法律認可的能夠予以救濟的損害。可救濟性損害,有以下兩層基本涵義:第一,依據一般情形屬于法律所明確規定的可予以救濟的損害范圍;第二,依據案件特別情形可歸責于行為人的損害后果。對于前者,法律依據當時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按照“一般條款+列舉”的立法模式,對可救濟性損害的體系進行科學設計,將亟需加以保護的利益類型通過列舉方式固定下來,并以一般條款的高度抽象性保證損害概念的周延性,為將來吸納新類型的損害提供制度空間。對于后者,法律豐富了法官的歸責手段,通過多種諸如因果關系、過錯、公共政策、合理期待等相對模糊的工具對個案的特別情形進行考量,以此確定某一特定損害結果是否能夠獲得救濟。總之,任何一項損害要屬于可救濟性損害,必須同時滿足上述兩個條件,缺一不可。在現代侵權法中,可救濟性損害理論對侵權責任界限的探尋,主要有兩個方向。第一個方向是通過對損害概念的辨析,確立含義明確而又具有開放性的損害定義,并認真細致地歸納和總結各類損害的共同特征,將各類損害確認為應當或者不應獲得賠償的損失類型;第二個方向是通過多元化歸責體系的確定,[12]向法官提供便于利益衡平的工具,在個案中實現對受害人損害的救濟以及對那些過于遙遠的損害的過濾。這兩個方向在本質上是損害類型化和歸責因素體系化的努力。
(二)可救濟性損害理論的基本特征
相對于傳統責任構成要件損害事實而言,可救濟性損害從理念到制度都表現出了顯著的特點。同時,這也是可救濟性損害理論替代或補充傳統過錯責任理論作為侵權法重要法律技術工具的優勢所在。這些基本特征集中表現在:
從支持的理念上看,可救濟性損害理論體現了受害人本位和兼顧行為人自由的精神。與過錯責任奉行行為人本位、以保障行為人自由為第一要旨不同,可救濟性損害理論將填補受害人損害為首要目的,強調損害救濟的正當性和價值優位性,注重考察損害事實的可賠償性和賠償方式,其核心是如何為應當予以救濟的損害事實尋找正當的法律依據。仔細觀察可以發現,這種理論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價值判斷先行的法律規制方式,即先綜合案件各種情況判斷受害人應否得到救濟,如果認為有救濟的必要,則會通過各種途徑去認定行為人的可歸責性。同時,也正是由于“可救濟性”這一具有相當彈性的概念,可救濟性損害理論得以在受害人和行為人之間達成一定的平衡,不致于使行為人承擔“過分苛嚴的責任”。
從內部的結構上看,可救濟性損害理論是概念清晰、范圍明確的理論體系。過錯一直因為其概念的模糊性和判斷標準的不確定性而頗受爭議;而與傳統的損害概念相比,可救濟性損害的范圍更為明確,且因為其類型化形成的完整體系而實現了質的飛躍。如果單純將“可救濟性”理解為“具有法律的相關性”,顯然不能令人滿意。可救濟性損害理論最為出色的工作就是通過類型化實現了“可救濟性”的具體化。否則,可救濟性理論也只是替代過錯的另外一個模糊不清的概念而已。各種損害的類型化,一方面明確了“可救濟性”的具體內涵,另一方面也為受害人請求損害賠償和法官判案提供了明確的法律依據,成為了侵權法法典化的重要基礎。
從衡平的工具來看,可救濟性損害理論采用了多元化的可歸責性體系。可歸責性是行為人與損害結果、賠償責任之間重要的聯系紐帶。過錯責任一直將歸責原則等同于可歸責性,把過錯視為歸責的最終要件和基本因素,其他的構成要件如損害、因果關系都置于過錯之下,目的都是為過錯要件服務的。“任何一個法律制度都需要一個過濾器,以將可賠償性損害從不可賠償性損害中區分出來。而這一過濾器本身,則因其特征的多樣性和數量之多很難一言以蔽之。”[13]從本質上說,現代侵權法的歸責手段應該是多元的,這是由侵權行為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所決定的。可救濟性損害理論從一開始就采用了多元的可歸責性體系,并沒有對歸責手段進行預先的限制,而是保持了開放的態度,樂于吸納新的技術手段,像過錯、因果關系、行為人承擔的注意義務、受害人的合理期待等,都被運用到這一理論中來。
從概念的性質來看,可救濟性損害是以客觀概念為外觀的主客觀統一體。盡管近年來過錯有呈客觀化的發展趨勢,但在侵權諸構成要件中,過錯仍然首先是作為主觀要件存在的。要主觀要件過錯承載侵權責任標準客觀化的使命,似乎總有些勉為其難。而可救濟性損害,雖然與傳統的損害事實有所差異,但其首先是客觀的概念,是侵權構成中的客觀要件。這無疑與侵權法的客觀主義發展趨勢極度吻合。可救濟性損害理論無論是在責任認定方面,還是在賠償計算方面,都采納了客觀標準,這對實現受害人的及時救濟和提高司法的效率都有著積極的作用。
同時,“可救濟性”這一約束性詞匯的使用,也使法官在認定侵權責任時有了更大的政策考量的空間,便于對雙方當事人的利益進行衡量,充分體現個案的公平。
(三)可救濟性損害理論的評價
第一,體現了侵權法的政策目的,實現了損害救濟和行為自由的平衡。“侵權行為法只有當它避免了過分苛嚴的責任時,才能成為有效的、有意義的和公正的賠償體系運行。……無論是從單個侵權行為人的利益出發,還是為了自身生存的愿望,侵權行為法都必須將那些過于‘遙遠’的損害從其體系中排除出去。”[14]給予救濟和責任豁免之間的互動是侵權法永恒的主題。可救濟性損害理論對損害類型的列舉,既是對受害人利益的保護,也是對行為人承擔的侵權責任的限制。救濟還是豁免,取決于法官對侵權法公共政策的考量。可救濟性損害理論,給法官提供了明確的裁判標準的同時,也提供了各種極具政策性的歸責工具供法官選擇。
第二,豐富了侵權法的理論工具,更新了侵權法的司法觀念。可救濟性損害理論的引入,給侵權法注入了新的元素,特別是多元化的歸責體系,極大地豐富了侵權法的政策手段。以公平理念和救濟理念為基礎,一種新的裁判觀也開始被接納。以往先找法律依據后進行價值判斷的裁判觀念不再一枝獨秀。可救濟性損害理論強調對受害人進行補償,在裁判中往往采取先進行價值判斷后找法律依據的方式,即先綜合判斷受害人應否得到救濟,如果認為有救濟的必要,則會通過各種歸責手段去認定行為人的可歸責性。這種做法,必將對侵權法的司法觀念產生重大深遠影響。
第三,充實和完善了侵權法的邏輯體系。侵權法有兩個基本的規制對象:侵權行為和損害結果。傳統侵權法以過錯為核心,注重對侵權行為的評價和限制,行為合法性與違法性的界限是其研究的重點。可救濟性損害理論迎合了當今侵權法損害救濟理念的發展潮流,將注意力重點轉向損害結果,不再關心對行為的評價,而是著重考察損害結果的可賠償性和不可賠償性之間的界限,損害在侵權法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可救濟性損害理論的出現,扭轉了侵權法失重的框架,實現了侵權法邏輯體系的平衡。
四、可救濟性損害理論的制度構想
理論的力量需要制度的承載來體現。尋求法律規范的彈性和確定性的平衡是侵權法起草孜孜追求目標之一。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借助“一般條款+列舉”的立法模式。[15]可救濟性損害理論在侵權法中的應用,也是通過這一模式來完成的。這一模式很好地發揮了一般條款的抽象性規范功能和列舉類型的具體性規范功能,使可救濟性損害成為既有規范性和全面性的政策工具,又具有相當操作性的責任認定標準。參考各國最新立法例、立法草案以及我國相關的司法解釋的規定,可救濟性損害理論的制度設計可按照以下思路進行:
(一)關于可救濟性損害的一般條款
侵權法立法和實踐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為保持侵權法的開放性和生命力而對核心概念賦予文義上的過分廣泛性是不明智的。《法國民法典》第1382條沒有對過錯的概念進行明確界定,而是賦予了法官廣泛的自由裁量權,因此才有了學者們擔心的“司法肆意”。荷蘭著名法學家Meijers曾經這樣評論:“在教條上不能學習法國,但應借鑒其司法實踐。”[16]實踐中,法國的法官根據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和個案情況,通過不同的案例形成了一系列關于是否存在過錯、是否構成侵權的判斷,具體地實現著第1382條的規定。以此為鑒,在擬定可救濟性損害的一般條款時,應特別注意對什么是可救濟性損害做出文義明確的定義,對這一概念進行基本的闡述,確定可救濟性損害的大致范圍。
《歐洲民法典·侵權行為法草案》(2002年3月19日第4稿)第2:101條(具有法律上相關性損害的含義)規定:“(1)如果符合以下條件,無論是經濟損失或非經濟損害,抑或人身損害均構成具有法律上相關性的損害;(c)本章中的條文對此做出規定的;(d)損失或者損害是侵犯權利或者違背法律所致;或者(e)損失或者損害是侵犯值得法律所保護的利益所致。(2)在任何情況下,本條第1款第(b)項和第(c)項所涵蓋的損害只有在依據本法第1:101條之規定,救濟的權利或者得到保護被認為是公平、正義和合理時,才認為屬于具有法律上相關性的損害。(3)在確定救濟的權利或者得到保護是否公平、正義和合理時,被告承擔責任的基礎、損害的性質與近因、受害人的合理期待以及公共政策應當予以考慮。”[17]這一規定有幾個特點:
第一,對損害進行了基本的分類:經濟損失、非經濟損害和人身損害,明確了可救濟性損害的基本內容;第二,上述損害的分類在邏輯上是周延的,既涵蓋了目前可知的所有類型的損害,也為將來吸納新的損害類型留有余地;第三,確定屬于可救濟性損害的可歸責性因素是多樣化的,包括了傳統侵權法規定的行為人過錯、因果關系等,也包括了一些新的可歸責性因素,如公共政策、合理期待等。而倍受學者青睞的1992年《荷蘭民法典》在可救濟性損害的規定方面也呈現出與《歐洲民法典·侵權行為法草原因從本質上講應該是多樣化的,包括行為、因果關系、過錯、義務的違反、公共政策、受害人的期待等眾多因素。
[5]姜戰軍:《侵以構成的非限定性與限定性及其價值》,《法學研究》2006年第5期。
[6]前引馬克西米利安?福克斯書,第4-5頁。
[7]彭誠信:《主體性與私權制度研究——以財產、契約的歷史考察為基礎》,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80頁。
[8]1940年德國侵權法修正草案在法律名詞的使用上,提出揚棄傳統的“侵權行為”概念,而改稱“損害賠償法”,以表明其強調“損害分擔”之精神。參見邱聰智:《民法研究(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頁。最近推出的由中國人民大學楊立新教授主持的《侵權責任法草案專家建議稿》在用語上亦采用了“侵權責任法”而非傳統的“侵權行為法”,體現了同樣的立法宗旨。
[9]楊立新:《侵權法論》,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頁。
[10]張新寶、張小義:《作為法律技術工具的純粹經濟損失》,《法學雜志》2007年第4期。
[11]王衛國主譯:《荷蘭民法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頁。
[12]針對侵權法可歸責性因素的多樣性,馮?巴爾教授的觀點頗具代表性:“……在許多案件中,非法典上的關于損害之可歸責性的考量也起著重要作用。鑒于這種情況,我們既不能期待結果的同一性,即使在某些情況下結果一致,也不能期待這一結果總是借助同一論據獲得的。”參見前引克雷斯蒂安?馮?巴爾書,第3頁。
[13][德]克雷斯蒂安?馮?巴爾:《歐洲比較侵權行為法(下卷)》,焦美華譯,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1-32頁.
[14][德]克雷斯蒂安?馮?巴爾:《歐洲比較侵權行為法(下卷)》,焦美華譯,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頁。
[15]關于這一立法模式的討論,詳見楊立新:《論侵權行為一般化和類型化及其我國侵權行為法立法模式選擇》,載《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3年第1期。
[16][德]克雷斯蒂安?馮?巴爾:《歐洲比較侵權行為法(下卷)》,焦美華譯,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頁。
[17]梁慧星:《中國民法典草案建議稿附理由(侵權行為編?繼承編)》,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頁。
[18]前引王衛國書,第182-183頁。
[19]參見張新寶:《侵權責任法的法典化程度研究》,《中國法學》2006年第2期。
[20]也有將損害分為財產損失、人身損害和精神損害的做法,最高人民法院近年來關于精神損害賠償和人身損害賠償的司法解釋就有沿著可救濟性損害進行分類的思路。從嚴格意義上講,人身損害并不是一類獨立于財產損害和非財產損害的損害類型,只是法律為了強調人身權益的重要性而將其單列。
[21]例如,《歐洲侵權法基本原則》第10:301條第(1)款規定:“非財產損害賠償同樣可以適用于與遭受致命或嚴重非致命傷害的受害人有親近關系的人。”參見歐洲侵權法專家小組:《歐洲侵權法基本原則》,于敏譯,《環球法律評論》2006年第5期。
[22]參見張新寶:《侵權責任法的法典化程度研究》,《中國法學》2006年第2期。
篇4
被監護人(以未成年人為主)致人損害是一種常見的侵權現象,現代世界各地的立法或判例無不對之作出明確規范,這當然也包括我們自己的立法,即先前的《民法通則》第133條及現行的《侵權責任法》第32條。從比較法上看,此種以特殊人群為標識的侵權類型,在規范模式上顯現了相當鮮明的“地域特色”。個性十足的《民法通則》第133條雖然曾飽受詬病,但《侵權責任法》(第32條)還是幾乎原封不動地把它延續下來。立法的因循守舊非但沒有鎖住學者的思維,反而激起了他們對舊制予以新解的想象力。簡言之,《侵權責任法》頒布近兩年來,有學者立足我國民法的特性,對以被監護人承擔獨立責任、監護人承擔補充責任為架構來解釋該法第32條第2款的舊觀點進行了深刻反思,提出了兩種頗具說服力的新看法:一是認為,該款不是為了確立一種監護人補充責任形態,而是在遵循監護人是唯一責任主體的一般規定下(第1款),授權法官以損害被監護人的財產利益為代價,來實現對受害人的充分救濟[1]122;二是主張,該款僅僅調整了監護人與被監護人之間的內部責任分擔關系。[2]108
受這兩種觀點的激勵與啟發,本文擬以侵權責任法之權衡行為自由與權益保護的機能為指針[3]7,以我國現行民事甚至是刑法的具體規定為基礎,對《侵權責任法》第32條關于被監護人致人損害的侵權責任配置機制作出一種全新的闡釋。基本看法是:第32條的兩款規定既非各自為政的并行關系,又非一般規定與例外規則的關系,而是一種一般規定與補充規定的關系,即第2款是為了彌補第1款在保護被害人權益上的救濟缺漏,而向被監護人與監護人強加的一種衡平責任。下文分三個部分詳細闡述此種觀點。
一、解釋被監護人致人損害之侵權責任的基調
學者們多年來之所以對被監護人致人損害責任理解不一,除了法律規定本身的概括、模糊之外,對立法持有不同評價立場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一般認為,“任何完整的法律規范都是以實現特定的價值觀為目的,并評價特定的法益和行為方式。在規范事實構成與法律效果的聯系中總是存在著立法者的價值判斷”[4]55。法律解釋因此必須首先爭取發現主導法律規范的價值觀或價值判斷。被監護人致人損害的侵權責任作為侵權責任法的組成部分,雖然地域色彩極其顯著,但各地的法制還是貫穿著一項總體思想,即盡可能在本地法律文化的框架內尋求行為自由與權益保護之間的平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監護人不對所有未成年人造成的損害承擔責任,可看做各地關于未成年人致人損害責任的共同法律評價。父母或監護人以及未成年人自身應各自承擔何種程度的損害賠償責任,則各地法律評價不一。因此,可以這樣說,法律解釋工作就像房屋裝修,在不可改變承重墻的前提下,居住者可根據居住需要,優化房屋的空間格局,從而使房屋達到最佳居住效果。在本文看來,在以法律解釋重構《侵權責任法》第32條的規定時,該條第1款就是我國被監護人(未成年人)致人損害責任制度的“承重墻”,只有對它的規范地位及可能造成的整體影響作出客觀評價或分析,才能對第2款,乃至對第32條之整體,作出相對合理的解釋。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既然要作出法律評價,自然不可能將視角僅僅局限于第32條第1款本身,而應依據更上位的法觀念對“承重墻”之合理性作出評判,以此作為法律解釋的一種基礎。
除了以“侵權責任”取代“民事責任”、以“其”代替“他的”、將“適當減輕”刪節為“減輕”這些無關大局的修改外,《侵權責任法》第32條第1款完全承襲了《民法通則》第133條第1款的架構,即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造成他人損害的,監護人承擔嚴格責任(無過錯責任)。對此,學者們今日之觀念與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的看法,幾乎毫無差異。①也許是因為看法較為一致,相對于第2款,舊法條與新法條的第1款,在法解釋上并未引起太多的深入討論(立法論上的討論則相當多)。在本文看來,我國被監護人致人損害責任的解釋玄機其實正隱藏于第1款之中,它是解釋第2款時無論如何無法抹去的一道背景,以前面所作比喻來講,很多時候正是因為“承重墻”之局限或限制,才凸顯了房屋整體結構的特性。
只有經由比較與外部觀察才能看出第1款的“廬山真面目”——獨特之處。所有歐洲國家的民法都認為,父母對被監護人致人損害所負責任的范圍取決于孩子的年齡,父母親對年齡更小的孩子比對年齡大一些的孩子的責任要嚴格一些,這是普遍規律。[5]182東亞的日本、韓國及我國臺灣地區的立法同樣遵循了此種一致性。根據這些地方的立法,父母只對無識別能力的未成年人(有無識別能力或以年齡予以形式判斷,或依據個案事實予以實質判斷)負較為嚴格的賠償責任。而《侵權責任法》第32條的規定則是,不管年齡大小、不論有無識別能力,父母一律為未成年人的致人損害承擔侵權責任。反言之,不管父母是否盡到了監護責任,未成年人皆不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這種規定難免會造成如下兩種后果:
第一,事實上具有意思能力或識別能力的未成年人,如接近成年年齡的未成年人,因絕對受保護之法律地位而相對于受害人而擁有絕對的行為自由。盡管監護人,尤其是父母,對未成年人的家庭懲戒與教育,有可能對未成年人的行為自由形成一種限制,但是,孩子們其實也明白,相比于法律的威嚴,父母的懲戒無論如何都可能因“心慈手軟”而不了了之,或者大事化小。因此,家庭內部的懲罰不可能對未成年人的行為自由構成真正的限制。至于,令父母總是為孩子的不當行為“買單”,是否會撥動孩子的惻隱、愧疚之心,從而對未成年人的行為形成一種內在限制,根本難以作出評判。
第二,在致人損害的被監護人概不承擔責任的情況下,當監護人以盡到監護責任為由減輕其侵權責任時,受害人的權益就難以得到有效保護。這種情況在未成年人因缺乏意識能力不負責任而對未成年人負監督義務之人又以盡到義務不負替代責任的規范模式下也會發生,如德國民法典第828、832條的規定。不過,德國民法典的制定者預見到了這種結果,因而在民法典第829條作出了這樣 的規定:為實現公平之需要,法官可考慮當事人的經濟狀況(包括保險狀況),迫使無過錯的致害人賠償同樣無辜的受害人的損失。[6]899-900我國《侵權責任法》第24條雖然作了“受害人和行為人對損害的發生都沒有過錯的,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由雙方分擔損失”這樣的規定,但此種亦需“由受害人分擔損失”的“公平”條款,與應由未成年人或其監護人分擔損害賠償責任的規定,在規范意旨上存在重大差別。因此,第32條第1款第2句所設責任減輕規定,必然會造成受害人縱使毫無過錯,甚至是在社會共同體內已盡了足夠的謹慎、勤勉義務,而仍然會因他人無法預防、無法控制的不當行為而遭受不測損害的后果。受此影響,盡可能不使被監護人接近自己的權益,可能是理性人唯一可采的“防身術”。不過,須質問的是,在被監護人人口數量相當龐大的社會情勢下②,人們能夠采取此種“避世”措施嗎?
《侵權責任法》第1條開宗明義地將協調權益保護與行為自由之沖突(“為保護民事主體的合法權益”、“預防并制裁侵權行為”)作為其規范意旨。然而,通過上述分析則不難看出,這種規范意旨在被監護人致人損害的規范設計上出現了嚴重“失調”,《侵權責任法》第32條第1款不僅明顯忽視了對受害人權益的周全保護,而且過分容忍了事實上具有意識能力的被監護人的行為自由。尤其是后者,如果再參考德國民法典第828條第2款第2句所作“已滿7歲未滿10歲的人未成年人故意引起損害的,需為自己行為所加損害負責”的規定,可以明顯看出,我們的法律對未成年人行為自由的寬容已到了何等地步!考慮到一個人的重要生活觀念,皆發端、養成于未成年階段,立法對未成年人致人損害的此種寬容,與其說是在保護他們,不如說在縱容、溺愛他們。自己責任乃現行民法私人自治原則的當然之義,一概不為自己行為負責的被監護人致人損害責任制度,明顯也背離了民法的立足之本。
另外,依據《民法通則》關于民事行為能力制度的規定,也可以對未成年人致人損害規范方式的合理性在現行法體系內作出進一步分析。
根據《民法通則》第12條的規定,十周歲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可以進行與他的年齡、智力相適應的民事活動;其他民事活動由他的法定人,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人的同意。這意味著,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可以憑借自己的理性能力參與交易生活,與他人訂立合同(《合同法》第47條第1款),獲得收益或積累人生經驗。由于合同行為,大多著眼于未來(對未來事務的一種安排),所以無論是從交易安全之維護還是從未成年人利益保護上考慮,立法準予未成年人獨立參與民事活動,實質上肯定了未成年人的理性能力,尤其是他的認識能力與預見能力。③
依侵權責任法之預防與制裁功能看,在侵權行為法領域,法律評價實際上僅僅立足于致害人對其行為之危害性的認識,即只要識別了自己行為的不當性,即可通過責任之強加而達到預防與制裁的目的。由生活經驗可知,這不是一種在認知能力上要求過高的認識,即使是幼童,稍加教育即可推己及人地培養此種認識能力。就像法律行為領域內的意識能力那樣,人的識別能力也存在由無到有的發展過程。為了不使未成年人因心智未開而承擔過重責任,當今世界各地的立法或判例皆抽象出責任能力或侵權責任能力的抽象概念,作為一種保護未成年人的安全閥。但不同于法律行為能力,各國或地區關于責任能力的規范,要么采取無行為能力之人一概不具備責任能力,要么采取依據個案對責任能力進行實質判斷的做法。
我國法不是沒有承認責任能力概念,而是采取了將法律行為能力與侵權責任能力熔于一爐進行構造的做法。這種做法的優點是,簡便易行,但必須承認,其缺陷更為明顯,即嚴重忽視了侵權責任能力與法律行為能力之間的本質差異。[7]68-69就前面對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所作分析而言,這種統一立法的難以避免的一個弊端是,限制行為能力人可以自己實質上具有理性能力而從法律交易中獲益,而卻完全不承擔因自己的行為給他人造成損害的不利。這種唯使之獲益而不使之負侵權責任的做法,明顯不是一種合理的制度安排。
總之,以協調權益保護與行為自由的侵權責任法規范機能,未成年人保護在法律行為能力與侵權責任能力兩制度中的不協調,以及參酌世界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立法或判例看,《侵權責任法》第32條第1款在法政策與法體系兩方面,皆存在不合理之處。
法律解釋非盲人摸象般地認識、詮釋立法,而是借整體法觀念指導對哪怕是一個條文的一句話也予以體系性思考,以使各個法律規范像蛛網那樣構成體系。法律解釋的目的不是單純對同一制度構造中的某一個條文作出合理說明,而是通過法律解釋盡力實現法律制度的整體效益。就《侵權責任法》第32條的規定而言,協調監護人與受害人之間的關系固然重要,但此種重要性遠比不上協調致害人、監護人、受害人之三方之間的關系。只有充分認識到第32條之整體狀況,才可能解決該條之局部問題。
二、第32條第2款新舊解釋的綜合分析
如前所言,關于被監護人致人損害的侵權責任制度,學者關注的焦點是《侵權責任法》第32條第2款,或者《民法通則》第133條第2款。大家基本上對這兩個條文中的第1款確立的監護人責任不存在太大的分歧。根據前文關于第1款的總體評價,在闡述自己對第32條的整體理解之前,有必要對上述兩條文第2款的解釋意見作出分析。
第32條第2款規定:“有財產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造成他人損害的,從本人財產中支付賠償費用。不足部分,由監護人賠償。”相比于《民法通則》第133條第2款,這一規定在兩處修正了舊法。一是刪除了“由監護人適當賠償”中的“適當”一詞;二是刪除了第2句規定中的但書,即“但單位擔任監護人的除外”。對于此種修改的意義,頗受重視的一種解釋認為:第一處加重了監護人的責任;第二處意味著,單位承擔監護人的,也要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8]125由此可以說,這兩處修改僅僅涉及了監護人及其賠償責任的范圍或程度,并未改變《民法通則》第133條第2款的整體架構。因此,關于新舊法條第2款的解釋意見,完全可以放在一起予以分析、評價。
(一)《民法通則》第133條第2款的解釋意見
關于《民法通則》第133條第2款,二十年間大致形成了如下幾種解釋意見:第一,這只是關于損害賠償方面的規定,無涉責任主體。④第二,這是關于責任主體方面的規定,即有財產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造成他人損害的,被監護人以其財產承擔獨立責任,監護人負補充賠償責任。[9]535持此種觀點者,通常把第2款當作與第1款相并行的一種規定。第三,這只是對監護人責任的一種責任限制措施,“在這種情況下,《民法通則》133條第2款規定有獨立財產的被監護人為第一賠償義務人,而監護人為補充義務人”⑤。
(二)《侵權責任法》第32條第2款的解釋意見
關于《侵權責任法》第32條第2款的規定,新近的解釋意見是:第一,該規定確立了被監護人的公平責任,此種責任的主體不是監護人,而是被監護人。公平責任是一種獨立責任,監護人責任是一種補充責任。[10]57-59第二,該規定不是為了確立被監護人的獨立責任,而是旨在解決監護人與被監護人之間的損害賠償額分擔問題。關于如何分擔損害賠償額,有兩種不同意見:其一認為,第2款授權法官“可以”判決從被監護人的財產中支付賠償費,但并非“必須”從被監護人的財產中支付賠償費,因此,“不足部分,由監護人賠償”所涉及的并非監護人的補充責任,而是對監護人作為基本的責任承擔者的身份的確認。[1]121-122其二認為,第2款調整的是監護人與被監護人之間的責任分擔關系(內部關系),被監護人只在此種關系中承擔公平責任,成為責任主體;對被害人來說,只有監護人才是他的責任人。[2]108
(三)對新舊法條解釋意見的綜合評價
由上述有點粗疏的總結可以看出,在被監護人致人損害的規范方式上,由于新法整體接收了舊法的模式,所以法解釋的架構二十余年來未有根本改變,在此方面的法律進步主要表現在解釋方法的日益成熟。概言之,第32條第2款到底是特別規定了被監護人的獨立責任,還是僅為監護人責任之損害賠償方式的具體規定,作為兩種較為對立的觀點,從20世紀80年代一直延續到今日。王衛國教授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提出的責任限制觀點,即第2款是監護人責任的一種責任限制措施,其實更接近于被監護人負獨立責任的觀點,因作為第一賠償義務人,被監護人如若有足夠的財產賠償受害人,監護人責任即不復存在。
可以從法律技術與法政策、法體系兩方面分析上述解釋意見。法律技術方面的評價,所關涉的是,解釋本身能否自圓其說——解釋的周全性及可能存在或遺留的問題。
王利明教授一直認為,“從本人財產中支付賠償費用”這一規定確立了有財產的被監護人的獨立責任,此種責任的存在理由有三:一是強化了被監護人的自己責任,體現了責任的公平合理性;二是有利于預防侵權行為;三是增加了受害人獲得賠償的可能性。[10]59僅僅就此來講,由于很好地兼顧了侵權責任法的權益保護與行為自由的規范機能,這種意見很有說服力。然而,如若聯系到其如下看法,王利明教授的觀點也存在值得商榷之處:其一認為,此種責任是以財產為基礎而承擔的獨立責任,法官在考慮被監護人是否要承擔責任時,不必考慮其年齡大小、行為能力狀況等,甚至也不考慮損害的嚴重程度。其二,這也是一種不以過錯為條件的公平責任,它不以實際損害為標準進行賠償,法官可以根據公平考慮(未成年人的成長和發展)來確定賠償數額。[10]59-60試問:不以過錯為基礎的責任,能起到預防侵權行為的作用嗎?不管損害嚴重程度的責任,能做到公平合理嗎?顯然,這些問題值得反思。
關于“不足部分,由監護人賠償”的含義,王利明教授認為,監護人的責任范圍以被監護人能否承擔責任、承擔多大的責任為前提,即如果被監護人具有充足的財產來承擔全部責任,則監護人的責任事實上已不存在;如果被監護人的財產有限或者其根本無財產,則監護人需要承擔大部分甚至全部責任。[10]53這種具有嚴格順序的責任,在性質上更類似于一種一般擔保責任,而非補充責任,因為當被監護人的財產足以承擔損害賠償額時,監護人事實上根本無責任可言。
在將第2款解釋為關于責任分擔規定的學者中,有人明確指出,第2款的規范目的主要是,當監護人欠缺賠償能力以致受害人無法得到有效救濟時,法官可自由裁定,打破監護人與被監護人財產分離的邏輯,讓具有財產的被監護人來承擔本來應該由監護人承擔的責任。[1]121這種看法,在如下方面值得質疑:純粹以有無財產來判斷被監護人是否為責任主體,固然“取消了責任承擔的內在的道義基礎”,于理不通;但是,被監護人僅僅因為自己擁有了財產,就應當承擔本來應該由監護人承擔的責任,明顯違背了只有責任主體才須承擔責任的常識,于法所不容。
把第32條第2款解釋為旨在解決監護人與被監護人內部的責任分擔問題的觀點,同樣存在非為責任主體的被監護人為何會成為實際的損害賠償人的問題。
以責任分擔為架構解釋第32條的學者,由于堅決否認有財產的被監護人負自己責任,所以權益保護思想——如何更好地救濟被害人——幾乎成為其唯一的解釋根據。
另外,絕對不能忽視的是,在解釋《民法通則》第132條或《侵權責任法》第32條的規定,鮮有人提到,當監護人以盡到監護責任而得以減輕責任時,如何公平保護受害人權益。
綜上所述,第32條的模糊與僵化為法律解釋提出的一道難題,既有的解釋不僅自身存在難以自圓其說之處,而且還存在對第32條第1款的規范缺漏視而不見的問題。顯而易見,在解釋第32條規定上,學者們仍然需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三、替代責任與公平責任并用的侵權責任配置
無論是從實際案例還是從參酌外國法制看,法律關于被監護人(未成年人)致人損害之侵權責任的規定,主要是為了協調被監護人、監護人的行為自由與受害人權益保護之間的沖突。在這種利益沖突格局中,作為致害人的被監護人,應否為自己的不當行為負責或者應對自己的不當行為負何種程度的損害賠償責任,由私人自治的民法理念看,自然是必須關注的首要問題。而從私權保護的角度看,當被監護人不能獨立承擔責任或無能力承擔全部賠償責任時,受害人的權益如何能夠得到有效救濟,當然也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問題。受此影響,監護人應否為被監護人造成的損害承擔侵權責任或者 應對被監護人造成的損害承擔多大程度的侵權責任,則取決于兩個方面的考慮:被監護人自我承擔責任的狀況及受害人權益被保護的狀況。因此,在解釋被監護人致人損害的侵權責任制度時,應首先考慮被監護人的行為自由與受害人的權益保護之間的利益關系,然而再以受害人救濟為導向,進一步思考監護人與受害人之間的利益沖突。應當說,以前的法解釋有些偏重于對受害人與監護人之間利益的協調。⑥
另外必須注意的是,法律解釋不是一種邏輯演繹,而是認識、評價法律的理性行為。如果不能對法律條文的語言清晰度、體系妥當性作出一個初步認識,法律解釋難免不會迷失方向。除此之外,仔細分析先前解釋意見的合理性,并發現其存在的問題,也有助于法解釋的成熟與完善。基于如上認識,下文對《侵權責任法》第32條作出如下解釋:
(一)第1款——減責規則導致的救濟漏洞
該款確立了監護人的嚴格責任,即監護人須為被監護人的致人損害承擔侵權責任。這是學界通說,無須贅述。值得深究之處有如下三點:
第一,綜合該款兩句話的規定,當其舉動造成他人損害時,被監護人完全不對自己的不當行為負責。根據《侵權責任法》第6、7條關于過錯責任、過錯推定責任及無過錯責任的規定,被監護人不為自己的不當行為承擔侵權責任的理由,顯然不是因為其在作出致害舉動時事實上不具有任何過錯,因為不作這樣的解釋,根本無法解釋如下問題:一個已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會因故意致人損害而負刑事責任⑦,為何卻不能為此類犯罪行為或者不能為比此類犯罪行為損害較輕的舉動,承擔性質較輕的民事責任。能夠拿來解釋被監護人(未成年人)不為自己的不當行為承擔侵權責任的唯一理由,只可能是,在立法者看來,被監護人根本無侵權責任能力。既然連侵權責任能力都不具備,遑論獨立承擔侵權責任以及具有作為侵權行為構成要素之一的過錯了。如此之下,在我們國家,民事行為能力其實包含著民事責任能力的含義。⑧這種不顧實際情況完全不使被監護人自負責任的立法,很大程度上構成了以解釋重構第32條之規范空間時的“承重墻”。這種墻既然不能被拆除重置,只能盡可能采取辦法消除其不當之處。因此,第32條第1款第1句的缺陷成為解釋該條其他規定時必須注意的重要問題。這當然首先體現在對第1款第2句的具體解釋上。
第二,區分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來解釋“盡到監護責任”的思路值得肯定。[10]37/45具言之,在理解“監護人盡到監護責任的,可以減輕其侵權責任”時,應區分被監護人是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還是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對未成年人而言,按照年齡越大父母親責任越輕的普遍做法,當無民事行為能力人致人損害時,在判斷監護人是否盡到監護責任時,應在監護人負更高程度的監督保護義務的法律評價下,從嚴認定監護人是否盡到了監護責任;當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致人損害時,考慮到被監護人已具備一定的識別能力⑨,且具有一定的獨立行為能力,監護人控制、管教被監護人的難度較大,不應使監護人負有較高的監督保護義務,原則上從寬認定監護人是否盡到了監護責任。
第三,關于為避免監護人負結果責任而設立的“減責規則”,不應忽視《侵權責任法》第32條第1款第2句對《民法通則》第133條第1款第2句的修正,即把“可以適當減輕他的民事責任”修改為“可以減輕其侵權責任”。“適當”一詞的刪除,對監護人與受害人的利益產生重大影響:減輕了監護人的替代責任,增大了受害人的救濟漏洞。這不可避免地會造成這樣的結果,即監護人減輕責任的可能性增大了,被害人獲得救濟的機會隨之減少了。如此之下,本來就明顯存在的對被害人救濟不周的問題,因新規定而顯得愈發突出。
總之,在理解第32條第1款的規定時,應注意其在規范模式選擇與規范設計上存在的問題,以及學者為此所提出的應對性解釋方法,只有這樣才能不使第2款之解釋陷入盲目之中。
(二)第2款:救濟漏洞的補救辦法
不同于以前的兩種解釋主張,本文認為,第2款是醫治第1款之弊病而設立的一項補救性規定。所謂第1款之弊病,如前所言,指在被監護人一概不為自己的不當行為負責的前提下,當監護人以盡到監護責任而獲準減輕責任時,受害人的權益就得不到有效保護。法律不能視而無睹此種狀況。在承認未成年人不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而未成年人的監督義務人僅負過錯推定責任的民法典中,如德國民法典(第829條)、瑞士債務法(第54條)、意大利民法典(第2047條第2款)、希臘民法典(第918條)、葡萄牙民法典(第918條)、我國臺灣地區民法典(第187條第3款)等,均為應對此種情況而制定了特別規則,即衡平責任或公平責任規則。[3]399-400
作為一項特別規定,第2款只適用于監護人的減輕責任訴求成立而被害人因此得不到周全賠償的情形。以此而言,第2款既非以財產為理據確立了被監護人的自己責任,又不是關于被監護人致害責任之損害賠償方式的特別規定。它是濟第1款之窮的一種補充規定,是基于保護受害人權益的公平需要而向被監護人與監護人強加的一種公平責任。
具言之,當因監護人盡到監護責任而得不到完全賠償時,受害人才可以請求有財產的被監護人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如被監護人的財產仍然不足以賠償其所受損失,受害人可以再次要求監護人承擔賠償責任,因監護人此時所負損害賠償責任,屬于一種公平責任,或者可稱為一種結果責任,所以監護人根本無法以盡到監護人責任為由而請求減輕責任。這一解釋清楚地闡釋了《侵權責任法》第32條為何在繼承《民法通則》第133條時,將“不足部分,由監護人適當賠償”中的“適當”一詞給刪除掉了。
在第32條所確立的侵權損害賠償序列中,受害人之救濟必須以監護人承擔侵權責任為起點,但未必以監護人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為終點,即使救濟終結于監護人的損害賠償責任,監護人前后所負兩種損害賠償責任,其屬性、地位與賠償范圍完全不同。前一種損害賠償責任,是監護人必須無條件(不問有無過錯)為被監護人的致人損害負責的一種特殊侵權責任,它是《侵權責任法》規定的為他人行為負責的侵權責任類型之一,其責任范圍取決于監護人履行監護責任的程度。后一種損害賠償責任,屬于一種為滿足保護受害人權益之公平需要,在《侵權責任法 》第6、7條規定的過錯責任、過錯推定責任、無過錯責任等常規化歸責機制外,基于衡平觀念,只于特殊情形下存在的一種損害賠償責任,其責任范圍,取決于被監護人是否已完全滿足了受害人的賠償請求,而與監護人是否已盡到監護責任毫不相干。
此種解釋也很好地說明了,為何“財產”這一與侵權責任的構造不相關聯的要素,會成為被監護人獨立承擔責任的基礎,因為這種責任僅僅是為滿足公平之所需而向被監護人強加的一種結果責任,其性質本身決定了救濟結果而被監護人的主觀狀況才是最值得考慮的因素。至于被監護人與監護人在承擔公平責任上的法律地位,第32條第2款規定中的“不足部分”實際上給予了相當清楚的提示,即必須先由被監護人承擔賠償責任,只有被監護人仍不能滿足受害人的救濟需要時,監護人才再次承擔責任。監護人的這種第二次責任,事實上屬于一種一般擔保責任。因此,從責任承擔的角度上講,這種責任最終可能無須履行。
由第32條可知,被監護人并非絕對不為自己的不當行為負責,至于其應當在多大程度上為自己的不當行為承擔責任,要看監護人履行監護責任的狀況。也就是說,在被監護人致人損害的規范模式上,為平衡監護人與被監護人之間的利益沖突,我國法律實際上將被監護人的獨立責任與監護人的監護責任聯系在了一起。這是一種饒有趣味的立法。如果法政策要求被監護人應承擔更大的責任,那么,只要降低判斷監護人是否履行了監護責任的標準即可;反之亦然。在監護人必須為被監護人的致人損害承擔侵權責任的一般規則局限下,為實現預防與制裁侵權行為的目的,本文前面已提出過,對于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監護人,應降低其監護責任,使其有更多減輕侵權責任的機會。當然,監護人為體恤被監護人,尤其是自己的孩子,完全可以不主張自己“盡到了監護責任”,而選擇為被監護人的致人損害承擔絕對責任。但是,如果監護人是單位或關系較為疏遠的親屬、朋友,監護人與被監護人之間的關系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種情形,被監護人獨立承擔侵權責任的幾率要大得多。
從實際案例看,第32條第2條之適用通常以監護人不愿為被監護人造成的損害承擔賠償責任為前提,由于在已盡到監護責任而減輕責任之后,仍存在第二次承擔責任的可能性,所以,理性的監護人在決定請求減輕責任時,不可能不對被監護人是否有足以滿足受害人賠償請求的財產有所了解,畢竟被監護人的財產處于監護人的保護之下(《民法通則》第18條)。監護人與被監護人之間的這種利益格局,其實為得不到充分救濟的受害人提供了良機,受害人應不難由監護人處了解被監護人的財產狀況。被監護人與受害人之間可能發生的此種“合作”,由于并非為了損害被監護人的利益,而只是使被監護人為自己的行為獨立承擔責任,因此不屬于違背善良風俗之列。當然,為了未成年人的生計或人格發展,最高人民法院可考慮對“財產”的范圍作出限縮性解釋。
總而言之,《侵權責任法》第32條的兩款規定構成一個不能分割的體系。此種體系既非表現為,以有無財產為標準對被監護人的致人損害作出了兩種并行的規定,又非表現為第2款是旨在解決第1款之責任承擔方式的例外規則;而是表現在,第2款是為了彌補第1款在保護受害人權益上的缺漏,基于衡平思想,而向被監護人與監護人強加的一種結果責任。這種責任的主旨是,要求有財產的被監護人須承擔獨立責任。如果受害人憑此還不能獲得完全賠償,對于剩余部分,監護人須無條件地予以賠償。也毋庸諱言,像先前的其他一些解釋那樣,由于立法過于簡略、僵化,此種全新的解釋意見,也難免會存在如下兩點不足:一是不能更大程度地伸張被監護人須為自己行為承擔自己責任的問題;二是當被監護人無財產時,應如何補救受害人的救濟漏洞。對于第二個問題,可能的補救方法是,求助于《侵權責任法》第24條的規定。
四、結語
《侵權責任法》第32條關于被監護人致人損害侵權責任的規定,雖然為承襲《民法通則》第133條的結果,但近兩年來依然受到一些學者的關注。分析新舊解釋可以看出,雖然解釋方法日益規范、合理,但解釋架構與觀念仍未真正顯現新舊之別。協調權益保護與行為自由之關系為《侵權責任法》第1條明定的規范意旨。從案件實際與國外相關立法例可知,規范被監護人(未成年人)致人損害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在被監護人與監護人之間分配責任,并以此使受害人獲得充分救濟。然而,分析第32條第1款可明顯看出,當監護人以盡到監護責任請求減輕責任時,受害人權益很可能得不到周全保護。正是為了彌補此種救濟漏洞,第32條才設置了第2款規定。基于此,第2款絕非第1款的并行規定,而是第1款的必然的邏輯延伸。這意味著,之所以令有財產的被監護人“支付賠償費用”,目的是為了滿足公平救濟受害人的需要,而向被監護人強加的一種獨立責任。當被監護人的財產仍不足以賠償受害人的損失時,監護人必須對不足部分承擔賠償責任。由于監護人的后一種賠償責任在性質上屬于一種公平責任,所以,其不能以盡到監護責任而請求減輕責任。總之,第32條兩款規定之間具有緊密的邏輯關聯,它們之間不是一般與例外的關系,而是一種一般規定與補充規定的關系。以此而言,第32條第2款既非關于有財產的被監護人自己責任的規定,又非關于監護人責任之承擔方式的特別規定,而是為彌補第1款在保護受害人權益上的缺漏,根據衡平思想而作出的補充規定。
注釋:
①參見王利明:《侵權責任法》(下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頁;王利明、郭明瑞、方流芳:《民法新論》(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535頁;王家福主編:《中國民法學·民法債權》,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528頁。
②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第1號),我國大陸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現役軍人的人口中,0-14歲人口為222 459 737人,占16.60%。
③《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3條規定:“十周歲以上的未成年人進行的民事活動是否與其年齡、智力狀況相適應,可以從行為與本人生活相關聯的程度、本人的智力能否理解其行為,并預見相應的行為后果,以及行為標的數額等方面認定。”
④參見魏振瀛:《民法》(第三版), 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726頁;江平主編:《民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581頁。
⑤王家福主編:《中國民法學·民法債權》,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529-530頁。類似觀點認為,監護人責任并非一種絕對責任,在法律規定的情況下,該責任可以減輕或免除,第133條第2款就是這樣的規定之一。參見王衛國主編:《民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637頁。
⑥如有著述認為,民法通則第133條,“意在充分保護受害人的同時,對盡責的監護人有所照顧”。參見王家福主編:《中國民法學·民法債權》,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528頁。引用部分由王衛國教授撰寫。
⑦《刑法》第17條第1、2款規定:已滿十六周歲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搶劫、販賣、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
⑧參見佟柔、周大偉編:《佟柔中國民法講稿》,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46頁;梁慧星:《民法總論》(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8頁。
篇5
地位。但是,自從進入現代社會以來,由于社會的經濟、文化、政治以及價值觀念的多元化形態所致,使得規范說缺陷顯得愈加明顯。與此同時,學術界對該學說的質疑和抨擊不絕于耳,加之一些新興學說的勃興,給傳統意義上的證明責任分配學說體系造成重大沖擊。在理論上,無論是批評者對于規范說提出的改造舉措,還是作為一些新型學說締造者在大刀闊斧對規范說作出顛覆性悖離的闡釋,都是以規范說為坐標的產物,故均可被稱之為修正規范說。鑒于規范說目前尚不能為其他任何一種有力的學說所完全替代,并且傳統的規范說與這些修正規范說之間仍存有協調、互補的余地和空間,從而鑄成了當前“一強多元”證明責任學說體系。
關鍵詞:證明責任學說;規范說;局限性;路徑選擇
一、對“規范說”淵源與學說地位之考察
德國的實體法或程序法并未就一般性證明責任分配法則作出規定,因而如何建立一種普遍性適用的證明責任法則,是德國百余年來證據法學者的努力目標。
臨近19世紀末端年間,由于對德國民法典的設計與制訂所充滿的熱忱與期盼,導致人們對于法律規范本身的重視程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境態,從而標志著待證事實分類說的衰退已經達到了無可挽回的境地,其原有的支配性地位旋即被法規分類說①取而代之。可以說,法規分類說的脫穎而出,是對證明分配理論的一場重大變革,自此開啟了人們通過法律構成要件作為研究方法創設證明責任規則的先河。在此期間,德國民法第一草案于1888年公布,直到1898年民法第二草案公布,兩者相差十年,當時以韋伯、貝特曼-霍爾韋格和那些主張因果關系說的學者共同倡導的基礎事實說居于支配地位,這一學說所采用的法律要件分類方法對于德國民法的起草產生了重大影響。133229.COm其中,德國1888年的民法第一草案當中第193條至第198條專就證明責任分配作出了特別規定。
時至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德國民法典的實施為從法律構成要件這種思維模式來創設證明責任分配規則說開創了現實的空間。在德國民法典于1900年正式實施之后,德國學者羅森貝克①于1900年出版了《證明責任》,德國的另一位學者萊昂哈特(leonhard)于1904年出版了《證明責任》,這兩部專著的面世標志著法律要件分類學說的正式創立,盡管羅森貝克和萊昂哈特在一些具體的理論建構上有重大分歧,但是,長期以來,由這兩位學者和其他學者所共同創立的法律要件分類學說理論體系在德國涉及有關證明責任分配學說上處于支配地位。
在研究證明責任分配的學術觀點上,主要分為學派:一種認為證明責任分配只得就個別具體的事件由法官作出適當的裁量,決定何人應就何種事實負擔證明責任,無法統一在原則上進行分配;另一種觀點認為,證明責任的分配可以采取抽象統一的分配方法。羅森貝克持后一種觀點,他認為,作為民法的法律規范自身已具備證明責任分配的規則,這是因為,立法者在起草法律時將證明責任分配的問題在各法條中已有相應的考慮與安排,學者僅須對全部民法的法條進行分析,就會發現證明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1](p·16)。羅森貝克的證明責任分配學說是在德國民法實施之后創立的,因其觀點以民法法條的分析歸類和法條用語的表述為方法,直接由法律條文形式作為證明責任分配的依據,故被德國學界稱之為規范說(dienormentheorie)。羅森貝克的學說因其內在邏輯性強、實務可操作性強以及能夠維持法律形式上的公平,從而有利于增加法律安全適用性等優勢所使然,直到20世紀60年代,以規范說為重心的法律要件分類說在一些傳統的大陸法系國家或地區仍處于支配地位,被譽為通說。
近百年以來,在大陸法系的德國、日本以及我國臺灣地區,大都沿用羅森貝克所創立的法律要件分類說中的規范說以及在此基礎上所產生的修正規范說,作為其證明責任分配的理論依據,所謂通說,主要指的是一種以羅森貝克規范說或為基礎、或為重心、或為側重點的法律要件分類說。
當代德國學者漢斯·普維庭教授于數年前曾指出,在證明責任分配上,最重要的也是最著名的觀點,當屬羅森貝克的規范說。羅森貝克的規范說在德國法上穩居絕對的統治地位[2](p·262)。在德國,其證明責任通說是以規范說出發的修正規范說,其基本原則仍是以羅森貝克的規范說為基礎。②這一學說經羅森貝克提出后,在德國曾蔚為通說,迄今其重要性基本上仍未減弱。雖經學者批判并試圖提出取代一般性的規則,但仍然難以動搖規范說的一般原則性地位[3](p·199)。所謂修正規范說是指,新時期一些學者針對規范說提出了按照某個實質性原則來分配證明責任的命題,這些命題首先是由普霍斯、萊納克和瓦亨多夫推動而發展起來的。對此,有臺灣學者認為,因規范說具有若干盲點,例如,區分權利發生要件與權利障礙要件有困難,并且如僵化地以此規則適用于所有類型案件,可能導致不公平,因此,便有修正規范理論產生。③
據悉,在日本,法律要件分類說曾經被稱為通說,④并且,經過修正之后,法律要件分類說至今仍被日本理論界和司法界奉為通說,而這種法律要件分類修正說是從維護法律要件分類說的需要出發,對權利根據事實和權利障礙事實在實體法上的區別提出質疑,并認為不應僅注重法律條文的表現形式對二者作出區分,而應當綜合實體法的立法宗旨、目的以及方便和確保交易的安全、原則和例外關系等實質性的因素或層面來加以判斷。可見,法律要件分類修正說試圖通過法解釋,尤其是根據實質性考量來修正傳統法律要件分類說的不足,以強調這種學說的實際運用價值[4](p·208)。但是,從更嚴格的角度講,正是因為羅森貝克的規范說,才促使法律要件分類說作為通說的觀點得以確立。
二、關于“規范說”的思想內核
規范說屬于法律要件分類說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稱羅森貝克為該學說的鼻祖一點也不為之過矣,并且在大陸法系的學術界,有許多學者步羅森貝克之后塵對該學說進行勤勉雕琢、精心闡釋,力求使其發揚光大,因此,該學說之集大成也系凝聚了不同國家其他學者辛勤與智慧的結晶。應當說,規范說的基本思想既能夠反映出與法律要件分類說在大體范疇上具有同質屬性的內容,也能夠反映出與法律要件分類說中的其他分支學說在表現形式、基本特征上因存在差異而具有獨特的層面。在此認識的基礎上,筆者認為,規范說的思想內核主要表現在以下諸方面。
(一)關于抽象法律規范類型化的思想
在成文法體系下,通常是以沿循三段論法作為思維方式與裁判方法。經立法者的預先設計與安排,法律的表現形式是從人們日常生活中所反復從事的形形民事行為,通過擬設、塑構,為實現特定的立法意圖,使之成為一種法律上抽象的權利或義務規范。在適用抽象的法規范時,將這種法規范作為形成裁判的大前提,但是,這種法規范的適用效果必須通過法規范的具體化才能得以體現,從個案情況來看,抽象法規范的具體化,只能通過當事人為使其所主張的具體事實達到一定法律效果所進行的證明行為來實現。羅森貝克認為,證明責任的分配可以采取抽象統一的分配方法。作為民法的法律規范自身已具備證明責任分配的規則,這是因為,立法者在起草法律時已將證明責任分配的問題在各法條中作出了相應的考慮與安排,學者僅須對全部民法的法條進行分析,就會發現證明責任分配的一般抽象而統一的原則。法院在審判上是以法規范作為大前提,而以要件事實作為小前提,從而導出以產生特定法律效果為目的的認定事實與判決的運用過程。證明責任分配的問題已在民法立法時為立法者所考慮及安排,而證明責任的分配應從法律規范之間的關系中獲得。法律規范應區分為權利發生規范、權利障礙規范、權利消滅規范及權利制約規范四種類型。
(二)關于證明責任發生的成因
關于證明責任發生成因的學說是規范說“活”的靈魂。在受規范說支配的語境之下,至近代以來,各國民事訴訟法所采用的是,通過假定(擬制)該事實存在或者不存在來作出裁判的方式。這就是所謂的根據證明責任作出裁判的方式。嚴格地講,通過證明責任被假定為存在或者不存在的對象是法律要件要素,而不是與法律要件要素相對應的具體事實即主要事實。①按照證明責任理論約定俗成的習慣, 人,還是主張權利受到障礙、消滅以及制約所依據的對立規范的當事人,其試圖所證明的要件事實,在有關當事人負擔主觀證明責任并經法官自庭審對案件事實獲得親身感受之后,在審判上無非會出現以下三種結果:其一,法官確信有關要件事實已被證明,且可作為裁判的基礎;其二,證明導致否定的結果,即法官確信有關要件事實未被證明;其三,有關要件事實是否已被證明或者是否未被證明仍處于真偽不明狀態。而按照實體法的明確指示卻只能是,只有當有關要件事實被證明之后才能作為裁判的基礎,法官只能在此基礎上,才能夠適用相應的法規范并產生相應的法律效果;當有關要件事實未被證明時,法官不能適用相應的法規范,在這些情形下,也不能夠導致相關法律效果的產生。但是,在審判上,當出現第三種結果,即有關要件事實處于真偽不明狀態時,法官無法依據實體法獲得明確的指示來決定如何作出裁判。由此而決定了作為證明責任裁判的法則本身的內部構造分為兩部分:其一,因案件事實真偽不明所涉及的事實構成要件部分,它體現了用來表達立法者意圖的大前提與司法裁判者盡其所能而查明的小前提之間因缺欠相應的對稱性而難以產生預期法律適用效果的危機;其二,為克服這種證明上出現的困境而不得以對作為裁判基礎的小前提作出硬性擬制部分,它體現了法官為了實現裁判的目的而不得不作出一種無奈選擇。
(四)關于“不適用法規(nichtanwendbarkeitdernorm)”的基本思想
在古羅馬法時期,法官對于案件事實的裁判只限于獲得兩種結果之一即可,它包括案件事實“被證明”和“不被證明”。自近代以來,法官在裁判過程中才開始認識到,對案件事實的認識除了在裁判上獲得“被證明”和“不被證明”之外,還有可能獲得“真偽不明”這種結果的可能。羅森貝克在其有關證明責任經典論著中的觀點①與證明說在真偽不明條件下的法律適用相類似。他明確摒棄了萊昂哈特的觀點,即實體法律規范僅具備訴訟上的內涵。②羅森貝克認為,證明的結果應當是三種狀態而不是僅僅為兩種狀態,也就是在“被證明”和“被駁回”之外,還另外存在的一種獨立結果,即“真偽不明”狀態。自近代社會推行法制主義以來,即使在真偽不明情況下,法院也不得拒絕作出裁判,因此,法院必須對于“是否適用實體法”這一問題作出決斷。按照“不適用法規”原則的觀點,當實體法法律要件被證明時,實體法才得以適用。
(五)關于法規范性質之判明與識別
在涉及“如何判斷是有利法規還是不利法規”的問題上,規范說認為,對此應當從實體法律的相互邏輯關系中求得解決的路徑,因為從法規范之間所存在的邏輯關系來看,這類邏輯關系分別表現為相互補充、相互依從(支持)或者相互排斥的關系。即從實體法的性質出發,實體法律規范可被劃分為,作為權利發生根據的權利根據規定、妨礙根據規定,法律效果發生的權利障礙規定,以及一旦形成就會使權利消滅的權利消滅規定三個類型。并且,對于作為基礎性規定的權利根據規定進行主張的人,就是權利人,相反,如主張性質相反的權利障礙規定與權利消滅規定的人,就是義務人。這兩種主體分別對各自主張的實體規定的要件事實負擔證明責任,因為對于權利人與義務人而言,這兩種性質相反的規定分別就是對其有利的規定。由此而決定了法規范性質的價值取向,即因受當事人利益驅動所支配并為此而劃定了其承擔證明責任的空間領域。
(六)僅以實體法律規范為依歸的證明責任分配原則
按照司法原則與法制理念,對案件事實的認定以及對當事人之間所存在的爭議,法官不得因為欠缺法律規定或者缺乏必要的證據而拒絕作出裁判。這實際上就會在相當程度上和一定范圍內造成制定法與“法官法”之間的摩擦或沖突。所謂“法官法”是指,當法官在訴訟上就個案作出裁判時,如發現缺乏必要的法律規范或者如適用現有的法律規范將損害社會的公平與正義時,享有以立法者的身份對所應凡是單獨談及“證明責任”這一術語時,或者不存在特殊的背景或特定的前提條件下,通常指的是“客觀證明責任”。正像人們自近代以來所認識到的那樣,當某一案件至訴訟終結而由法院作出裁判時,除了作為適用法律的要件事實有可能“被證明”或者“未被證明”之外,還有可能出現既不能被認定為“已被證明”,又不能被認定為“未被證明”的一種特殊事實存在狀態。在審判上,即使面臨這種沒有進一步的證據來確認要件事實是否存在的窘況,法院也不得據此拒絕裁判。因此,在訴訟終結時,當某一實體法上的要件事實在訴訟上作為待證事實處于真偽不明狀態時,是產生證明責任問題的基本成因。在這種情形下,立法者通過預先設定的實體法律規范,告知法院應當通過假定(擬制)該要件事實存在或不存在來作出裁判。由此而帶來的直接后果是,導致其中一方當事人遭受不利益。
(三)關于證明責任規范的適用及其效果
在處理適用有關法律規范與適用證明責任規范問題上,證明責任規范因涉及權利要件事實的產生、障礙、消滅以及制約的內容,因此,它屬于實體法規范。無論是主張權利產生所依據的基本規范的當事當適用的法律作出選擇或進行解釋而形成的規范。而按照羅森貝克的規范說,在證明責任分配上,為了排除每個法官的實質性考慮,以避免造成不同法官作出不同證明責任分配的結果,而只能求助于立法者所預先設定的制定法規范(實定的實體法規)來進行。“每一個在訴訟中主張法規范效力的當事人,應承擔具備該法規范的前提條件的證明責任。需要證明的事實的范圍,只可通過對實體法的解釋來找到。”2(p·122)在實務上,鑒于人們往往會混淆證明責任的分配規則與法官的證明評價之間的界限,羅森貝克的規范說著重強調證明責任規范的存在是以抽象的形態預先設定的,具有某種客觀上的必然性,并且與法官在證明評價上以具體形態為主要特征所表現出的主觀性與或然性具有明顯的不同。證明責任規范貫徹和輸出的是一種立法者的意志,并且獨立于法官的個體行為。可見,作為證明責任規范,無論在其設定的路徑、存在的形態以及發生的方式上均有其獨特的內質與層面。
三、關于規范說缺陷與局限性之基本透析
(一)對規范說的檢討與反思
羅森貝克有關證明責任分配學說長期以來成為德國的通說,即使在日本,該學說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也被奉為通說。但是,自1966年以來,德國學界開始有人撰文對此學說表示質疑,也就是從規范說的基本思想及學理兩方面進行批駁,至此,其通說地位受到些許撼動。實際上,從此之后,更確切地說,居于通說地位的應為修正規范說。
羅森貝克的規范說提出了證明責任的分配原則,該說為法院提供了在決定證明責任歸屬問題上的裁判準則,這對于法律的安定性具有重要意義。但是,在實務運用上,羅森貝克所提供的原理常常使人感到不知所措。在20世紀60年代以前,盡管在實務上及學者之間對于規范說持有某種程度上的懷疑態度,可惜并無學者能夠集睿智與膽識于一體而挑明其學說的謬誤所在,更無人能夠推出較為完善的新興理論借以替代其證明責任分配原則。直到1966年,德國學者萊波爾特(leipold)在其著述①中對羅森貝克的通說理論提出質疑,隨后,布朗斯(bruns)及格輝司基(grunsky)等學者也紛紛撰文②對于規范說所存在的理論缺陷發表批評見解,從而促成了理論界和實務界共同對這一學說進行檢討趨態。在這種情況下,德國聯邦最高法院隨后作出的新判例標志著對這場論戰所表達的直觀反應,端顯出對規范說不得不產生某種動搖的跡象。在此之后,德國學界的爭論波及到了日本,并且對日本學界產生了相當的震撼,日本學者也紛紛撰文剖析這種學說在理論上的缺陷,由此而引發了作為學者的石田穰與實務界的倉田卓次之間有關證明責任分配理論的激烈論戰[1](p·4)。但是,也有一種提法稱,一貫追隨德國民事訴訟理論的日本,在反規范說證明責任分配理論上,卻比德國學者發表相同的學說提前了三年[5](p·208)。
(二)學術界對規范說存在缺陷和局限性的基本認識
縱觀各種批評言論和質疑,筆者認為,羅森貝克的規范說的缺陷和局限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其一,規范說過于注重法條結構形式,難以顧及雙方當事人之間在個案當中所存在的實質上的公平正義。因為權利發生、權利障礙、權利消滅及權利制約規定的分類,以及普通規定與例外規定分類屬于純粹從法律形式上所作出的區分,無法同時顧及證明責任分配對于雙方利益的衡量效果,不能從法律價值的角度來作適當的分配,體現的是概念法學上的證明責任分配形式。③規范說的適用是將成文法的法律規范嚴格分為四種類型,故它的適用只能以成文法為前提,在實務上,這種法律規范所設定的法律要件作為適用法律的大前提,如果立法上缺乏這種大前提,特別是我國有關民事實體法對民事行為的規定有許多空白,在此情況下,規范說的運用就受到了相當的限制。即使存在民事實體法,有時很難對這些實體法律規范就上述四種規范類型進行實際歸類,也影響了規范說的適用效果。
其二,就規范說而言,因其證明責任分配的形式標準對于當事人與證據接近的難易問題以及保護社會弱勢群體的需要來看,均無法考慮其證明責任應當予以減輕的舉措。①按照規范說的觀點,主張有利法律效果的當事人,應就有關規范的法律要件事實負證明責任,但在實際上,卻無法僅憑某一權利發生規范而引出對當事人有利的法律要件事實來提供證據加以證明,這是因為,某一權利發生規范對于主張的當事人是否有利,僅能在綜合所有與此相關的規范作出判斷之后才能獲得,就此而言,規范說的四種規范分類方法似顯多余之舉。②例如,在涉及借款合同糾紛案中,主張權利的一方當事人為證明其權利形成的要件事實時,提出抗辯主張的一方當事人可以分別就權利障礙要件事實(如雙方明知被告的借款合同目的是為了購買走私槍支彈藥或者販賣等)、權利消滅要件事實(如原借款項已經返還)或者權利制約要件(如還款期限尚未屆滿或者原告已承諾延長還款期限)事實負擔證明責任。并且,在理論上,對每一個要件事實雙方,當事人都可以進行爭執,因此,最終的裁判結果并非僅取決于就某一要件事實所形成的證明效果。
其三,規范說的重大缺陷就在于較多地寄托于法律規范的形式要件,而與法律規范本身所確定的價值理念與實質公平有所距離,顯示該學說一味拘泥于法律條文,甚至從形式上對法律規范所涉及的證明責任分配作出牽強附會的解釋。
規范說是以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第193條、第194條為依據,認為立法者已采用法律條文的用語作為表達形式,將證明責任分配規則,按照普通與例外、權利發生、權利消滅與權利障礙規定形式納入各法條之中。在實質上,這種對立法者的意圖所進行的解讀并不正確,因為,從法典上所表現的各種用語來看,立法者僅考慮其實際上表達的自然與簡明而已,并未就各條文構造處處考慮其證明責任分配問題。對此,可從立法者將草案第193條以下明文作出刪除的理由中可以見得,這是因為,立法者認為證明分配的標準為公平、合目的性及推理,并不認為另外有形式上的標準。③
其四,規范說無法應付昔日立法者從未考慮過的涉及今日的特殊法律問題,例如公害、醫療糾紛、交通事故、商品制作等損害賠償法所涉及的證明責任分配。此類損害賠償的證明責任分配如果想獲得真正的公平,無法僅憑規范說的法律形式來作出分配,必須重新考慮設計新的證明責任分配標準。④對此,有學者認為,如果根據規范說的論斷來應對所有案件類型訴訟,則就若干現代型訴訟,例如產品責任、公害責任、醫療責任等訴訟類型所發生的證據偏在與武器不平等的問題,均不能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法,足見如果過于強調規范說,除了無法解決基于理論上的基本缺陷以外,對于個案實質正義所需要的彈性顯然也有所欠缺[3](p·201)。
其五,羅森貝克在涉及“不適用規范”(nichtanwendbarkeitdernorm)理論時只是在闡述當事實處于真偽不明時如何加以處理,而不能說明為何在此時不能適用法律,或者說不能真正提供不適用法律的根據。當事實處于真偽不明時,在邏輯上并不必然要導致法規的不被適用,而是應當通過某種考慮對法規的適用或不適用進行指導。⑤雖然這種觀點本身也不失為一種抽象論的反映,但在相當程度上對規范說的基礎造成了松動。
羅森貝克及萊昂哈特的理論基礎是建立在“不適用規范”的原理之上,認為主張有利于自己的規范的當事人,應就其法律要件事實提出主張及證明,如主張之人不能證明其法律要件事實存在時,法官不能適用該類規范作有利于該人的判決,也即當事實最終處于真偽不明狀態時,法官僅能視為該法律要件事實不存在,而拒絕適用該方當事人主張有利的規范。這種觀念其實是采用實體法的規定以訴訟作用來作為觀察其狀態的方法。實體法所規定的為當事人生活關系的準則,因此,規范上不考慮當事人的權利將來能否證明的問題。其規定的方式為,法律要件存在,則法律效果發生,如果法律要件不存在,則法律效果就不發生。法律要件是否存在,取決于構成法律要件的一定事實,因此,事實存否決定法律要件的存否問題。一旦事實存否不明,則法律要件也發生存否不明,使得法律效果的發生與否也呈現真偽不明狀態。換言之,在實體法領域,除了事實存在及事實不存在兩種情形之外,另外還有事實存否不明的第三種情形。由此而產生的證明責任分配原則,正是用來指示法官在事實不明時應如何作出裁判的規則。但根據羅森貝克及萊昂哈特的理論,法律效果的發生與否,并非取決于事實的存在或者不存在,而是取決于事實是否獲得證明或不獲證明,因此,事實僅能分為已獲證明與不獲證明兩種情形,并無第三種可能性,既然沒有第三種可能性,則根本不發生證明責任分配規定的需要,因為在審判上,法官并不能產生不能作出判斷的情形。就主張權利的當事人而言,如果不能證明事實,則視為該事實不存在。
其六,權利發生規范與權利障礙規范的區別并無實際的區分標準可言,也就是,在權利發生的觀點上無法區分所謂權利障礙與權利發生兩種概念上的實質意義。對此,萊波爾特(leipold)認為,因權利發生要件事實與權利障礙要件事實在發生的時間上屬于同一時間點,并無先后之分,因此成為權利發生要件的事實,其事實的不存在同時將成為權利障礙要件的事實;成為權利障礙要件的事實,其事實的不存在同時成為權利發生要件的事實。處于此種對立矛盾關系的兩種要件事實,其所形成的兩種法律規范,在實體法內容上并無區別的意義。另外,萊昂哈特(leonhard)在其名為《證明責任》的論著中,干脆拒絕權利障礙規范的存在及其合理性。他僅承認權利形成規范和權利消滅規范,萊昂哈德否認權利障礙規范具有特殊法規范的特性[2](p·138)。
值得一提的是,羅森貝克本人雖然于1963年12月18日去世,但是,他的那部有關證明責任理論的教科書仍被奉為權威性的標準,該書后來經德國學者施瓦布修訂而不斷重版。1969年,施瓦布對該教科書再次重版時,在討論妨礙抗辯(rechtshindernde einreden)當中誠懇地接受了萊波爾特對羅森貝克權利發生規范與權利障礙規范區別的批駁,最終也不得不承認權利障礙規定與權利根據規定原本在理論上確實無法加以區別。從總體上來看,該教科書對于證明責分配的原則仍然維持其規范說的基本觀念,以法律不適用原則及法律規范的分類法作為分配方法,并不接受普霍斯等學者①所主張的證明責任應當按照危險領域的分配方法所具有可操作性的觀念。但對于證明責任的轉換問題,則以合乎公平的要求為由,表示贊同近年來德國的判例及學說。②后來所出版的版本已經刪除了權利障礙規定的概念,這被認為是萊波爾特在理論上的重大勝利[6](p·239)。1977年該教科書第12版對于證明責任的轉換問題,就證明妨礙、職業上義務的重大違背、生產者責任以及說明義務的違背等詳細情況進行研討,參酌法官自由心證及證明責任分配問題而承認此種特殊問題處理的妥當性,可見,羅森貝克規范說因學者間紛紛提出更具實質意義上的證明責任分配標準發生動搖,并非一成不變[1](p·32)。
其七,羅森貝克認為間接反證事實也適用客觀證明責任的分配原則,不負客觀證明責任的一方當事人也不負證據提出責任(主觀證明責任)。這種觀點在理論上難以找到有力的支撐。
當然,作為一種曾經力挫群芳的杰出學說,能夠在發展的社會中不斷接受社會各方面的挑戰而暴露出一些缺陷亦屬在所難免,因為它畢竟為推動證明責任理論向前發展作出過卓越的貢獻,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它確實起到了在特定時期不可替代的承前啟后的橋梁作用。時至今日,在大陸法系的視野范圍之內,尚未出現過任何一個能夠完全取代規范說在理論上所占有支配地位的新興學說。
四、克服規范說局限性的思考與路徑選擇
20世紀50、60年代再次興起的工業浪潮呈現出的是一場前所未有的科技創新,這場工業浪潮中產生的效應所波及的社會領域極為廣泛,不斷為各種法學理論及學說既開辟了新的視野又提出了新的挑戰,使得諸如產品質量責任、交通事故、醫療事故、高度危險作業、環境污染等糾紛的解決,對于運用規范說來設置證明責任分配規則隨即構成嚴峻的挑戰。一些大陸法系國家或地區的法院通過判例的形式借助對一些新興價值觀念的吸納,進而對規范說作為證明責任分配的原則進行大刀闊斧的變通或改造,通過半個世紀司法實務的檢驗,并伴隨著各種新興的社會文化及法律價值觀念的應運而生與不斷滲透,使羅森貝克的規范說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歷史考驗,使諸種價值觀念的運用發揮著補充、甚至部分替代羅森貝克規范說的功能。當時,一些順應歷史潮流涌現出的新興學說,如危險領域說、蓋然說、損害歸屬說等
首先從德國勃興,其共同目標在于克服羅森貝克規范說中日漸顯現的一些局限性。
一些深受制定法傳統影響的大陸法系國家或地區在過去的一百年間,在民事證明責任分配的理論與實務上受到羅森貝克規范說的支配與左右,時至今日,這種影響仍未消彌。隨著時代演化、社會變遷、時間推移,發端于當時歷史背景下的規范說,在當今看來呈現出一些與現實情勢不盡吻合、不相適應之處,這是一種在所難免、不足為奇的現象。筆者認為,之所以要針對規范說的局限性設法予以克服,這是因為,至今我們還無法擁有足夠的智慧與想象力來締造一種足以取代規范說的蓋世學說。因此,我們今天還不得不繼續沿循規范說的基本原理并且對其加以修訂和改造,以便使規范說的生命力能夠不斷得以延續。實際上,我們今天所思考的如何對規范說的局限性進行克服和補救,無非是在延續類似大約在半個世紀或者數十年以前萊波爾特、穆茲拉克、施瓦布、普維庭等學者就開始為對該學說進行修訂而付出的努力。這正是羅森貝克學說的偉大而不朽之處的最佳體現。
筆者認為,在新的歷史背景條件下,從理論上對證明責任分配原則與規范進行梳理和重新整合,是非常必要的,因為它承載著多年來實務界的殷切期盼,因此,在理論上必須突破這一瓶頸,以開辟對實踐具有指導意義的思想路徑。為此,有必要從以下若干層面進行必要的探討。
(一)關于證明責任的基本原則與規范說
自近代社會以來在證明責任分配領域先后經歷過由待證事實分類說、法規分類說以及法律要件分類說交替占據統治地位的歷史場景。自現代社會以來,由于社會的經濟、文化、政治以及價值觀念的多元化形態所致,導致從近代以來采取單一性的理論學說就完全能夠占據支配和主導地位的局面成為過去,轉而步入了以某一理論學說為重心兼采諸種學說為輔這樣一種格局為特征的歷史階段。這種格局在當代可被稱之為“一強多元”模式。所謂“一強”主要指的是羅森貝克的規范說,而“多元”則是在羅森貝克的規范說不斷受到修正、補充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且在一定的空間領域能夠對規范說產生排斥、制衡作用的學說與價值觀念。
雖然羅森貝克規范說在學術上的霸主地位至今仍無人能夠與之相匹敵,但其衰勢卻使人依稀可辨。半個世紀以來,德、日兩國所出現的修正規范說至少能夠說明兩方面的問題:其一,尚未出現巨匠般的大師及其重量級的學說能夠足以替代羅森貝克及其規范說,以至于使得有關學者通常在對羅森貝克學說提出質疑之后,還不得不仍須依賴羅氏學說并在此基礎上進行修修補補,尚未達到完全擺脫羅氏學說而另起爐灶的程度。例如,有學者指出,近年來在德國,也不完全把仍作為通說的羅氏學說予以推翻,只是把其學理上有不足之處加以補充、修正。如果把這套理論廢掉,那就得重新再來,但在德國,大部分學者仍主張羅氏學說有維持的必要,對那些不符合時代的部分(分配方法)要加以修正。①在一些國家,特別是日本,有一些學者如石田穰、新堂幸司等在否定羅氏學說基礎上所創立的新說尚不足以對抗規范說的整體影響力。①其二,羅氏學說正在日漸喪失其只有在昔日才能展現的那種“四兩撥千斤”般的氣勢與力度。正如有學者所評價的那樣,在實務上,規范說便于利用,可直接由法院就應適用的民法條文來進行分析,借以決定何種事實屬于權利發生要件事實,何種事實屬于權利障礙及權利消滅要件事實,從而以此種形式上的分類來確定證明責任分配的歸屬。但是,依照規范說的方法來對證明責任進行分配,并不考慮當事人之間的實質公平等要素,因此,可能引發實質上無法真正實現符合具體公平或者法律目的的情形。但是,采用羅氏學說所作出的分配結果,并非完全不合公平宗旨,其中大多數也符合公平的結果[1](p·82)。這種評價可謂一褒一貶,褒貶分明。從“褒”的方面來看,羅氏學說雖有弊端,但仍有可取之處;從“貶”的方面來看,從時展的角度而論之,羅氏學說的弊端或欠缺有一個逐漸暴露的過程,然而因目前仍然欠缺一個具有相當重量級的學說來將其取而代之,因此只能對其進行局部改良,尚不存在足以將其完全顛覆的條件。
這樣一來,在我們談及對證明責任分配規則及其體系進行梳理和重新整合時,有一個無法回避的前提條件是,首先要對羅森貝克的規范說不斷進行修正并在此過程中仍仰賴其為證明責任的基本原則,而這種基本原則依然是我們在探求相對真理路徑上的一個重要基石。
(二)關于證明責任分配的單一性原則與多元化原則
就大陸法系而言,作為證明責任分配規則在理論學說上所呈現的基本模式,在近代社會條件下,曾經出現過“一枝獨秀”或者“一統天下”的獨霸格局。這與當時歷史背景下社會經濟形態、文化特質、法制建構不甚發達,民眾的思想不甚開化以及法官的職業化水準較低等因素密切相關。自進入現代社會,特別是在當今社會歷史背景條件下,在證明責任分配的學說領域,由于某一種學說的創設就能夠足以雄踞天下而獨霸的格局模式恐將不復存在。若按此邏輯與思維模式來推展歷史與未來,隨著時間的推移,如果持續性的導致羅氏學說實質要素的日漸淡化與稀釋,目前的“一強多元”模式必將為“同一主題下的多元論”所取而代之。
但是,至少在目前社會條件下,由于修正規范說的強力推動,使得有關證明責任理論在“一強多元”模式的支配下暫時居于一種穩定狀態而難以受到撼動。數十年以來,修正規范說的出現、發展以及所作出的學術貢獻,既是對羅氏規范說的完善,同時又是對羅氏規范說的改造。②所謂對羅氏規范說的完善,是指在羅氏規范說的基礎上摒棄其中不符合現實社會發展狀態的那些缺陷,給傳統的規范說注入新的生命活力,使其能夠不斷適應新的歷史條件下所涌現出的新類型案件以及因社會的不斷發展在解決民事爭端問題上所體現的新的價值取向;所謂對羅氏規范說的改造,實際上是對羅氏正統規范說的悖離,或者是對羅氏傳統規范說的異化。
規范說的一個重大缺陷在于,并未重視其隱含于各種法律規范中的實質價值及實質公平問題。有些反對規范說的學者在基本立場上顯得十分強硬,他們主張應全面放棄規范說的概念法學方法,不再維持統一抽象的形式標準,而改從利益衡量、實質公平、危險領域及社會分擔的更為具體而多元的標準,借以解決證明責任分配問題。③有些認為,規范說的理論及分配方法不妨繼續維持,但對于有疑問的部分應當予以修改,并就若干當今社會所發生的特殊法律問題,例如公害、醫療糾紛、交通事故及商品制造等損害賠償方法上的特殊證明責任分配問題,應另行建立其具體公平的分配方法,不能墨守規范說的分配方法。①但是,筆者認為,從所造成的社會影響以及判例實務來看,對規范說持全盤否定的學者所作出的努力而產生的實際效果卻并不比那些主張修正規范說的學者所作所為顯得更為成功。羅森貝克規范說之所以在當今仍具有生命力的主要原因在于,該學說所體現的思維方式與實體法規范所具有的抽象性相適應,同時也與大陸法系三段論裁判方式所形成的既定模式相契合。在以成文法為傳統的立法建構下,雖然規范說過于注重法條結構形式,而顯露其具有濃厚形式主義的色彩,這與羅森貝克本人深受近代古典主義哲學思想的洗禮不無關系。羅氏學說將法律規范從形式和性質上劃分為基本規范與對立規范,并分別將歸屬于這兩種不同類別的規范,相應地設定由主張權利的一方當事人和提出抗辯主張的一方當事人作為負擔證明責任的根據。該學說強調的是,應當由追求某種法律適用效果所依據法律規范而獲得利益的一方當事人,對作為適用該法律規范前提條件的要件事實負擔主張及證明責任。由此可見,總體而言,羅氏學說是采用概念法學上的邏輯語言,將立法者制定法律規范的思想意圖詮釋為一種證明責任分配規則,以便使抽象意義上的公平正義及其價值理念適合于所有類型的案件。但問題是,一方面,這種過于注重法律規范外在形式以及權利規范屬性的學說,在相當程度上忽略了個案的具體情形,特別是忽略了雙方當事人的舉證能力、與證據的遠近距離、是否存在證明妨礙行為等這些與社會公平正義緊密關聯的情事或層面。在進入現代社會以來,由此而暴露出來的一系列社會矛盾,在那些諸如環境污染、醫療糾紛、產品責任等特別領域顯得更為突出。另一方面,羅氏學說也忽視了法官在個案當中當遇有因適用規范說將有損于社會公平正義時他所應當作出的理性判斷。早在數十年以前,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在有關判決中就對有關證明責任的分配所作出的有悖于規范說的做法,②其意義不容小覷,它們不僅僅是對規范說進行修正,更重要的是,它們為新興學說的創立提供了重要的實證源泉與判例根據。例如,危險領域說的問世正是建立在德國長期司法判例基礎上的產物。
在當前社會條件下,在大陸法系主要國家或地區的立法、司法及學說當中能夠就證明責任分配規則起到一定支配地位或者重要作用的“一強多元”模式而言,其中“一強”與“多元”之間的結構關系主要表現為一種基本規則(或規范)與例外規則(或規范)之間的邏輯關系。③所謂“一強”主要是指的是羅森貝克的規范說。但是,也不排除系法律要件分類說當中的其他特別說,或者與羅森貝克規范說相結合的一種綜合說。所謂“多元”,更進一步指的是包括公平原則、武器平等(或對等)原則、誠實信用原則、舉證難易或者證據距離原則、利益衡量原則、危險領域原則、蓋然性原則等理論學說或者價值觀念。在實務上,關于“一強”基本規范與“多元”例外規范之間的應用關系是,在通常情況下,應適用基本規范,例外規范只是起到必要的補充作用,但是,當法官在個案當中認為適用基本規范有違社會公平正義時,有權決定改采例外規范。在學理上,通常認為,作為這種一般抽象性基本規范的規范說因符合法律安定性要求,故此具有可預見性、可預測性的特質,包括使得交易行為或社會習慣的主體對證明責任的法規范能有必要且合理的預見性。只是基于克服和避免其內在的某種僵化性且有利于解決個案的彈性問題,才考慮在必要時采用其他各種新興學說來解決在個案當中所出現的實質性公平與個別正義問題。可見,盡管傳統學說與新興學說之間存在某種彼此不相兼容的齟齬關系,但是,如果從針對不同的具體情形各自所發揮的不同功能角度來觀察,這兩種類別的學說之間仍有相互協調的余地和空間。
(三)關于在實務上對公平地采用基本規則(或規范)與例外規則(或規范)的基本認識
在采用基本規則(或規范)與例外規則(或規范)問題上,鑒于基本規則適用于大部分類型和數量的案件,因此,它所體現的是一種抽象意義上的公平或者概括公平。例如,按照規范說當中所體現的證明責任分配的基本規則(或規范),凡主張適用某一法規范的當事人,應當對適用該法規范所依據的要件事實負擔證明責任,其中,正是因為有關當事人所追求的法律適用效果能夠給其帶來訴訟利益,因此,按照抽象意義上的公平觀念,應當由因適用該法規范而享有預期訴訟利益的一方當事人,對有關要件事實負擔證明責任。假如在這種情形下,由相對一方當事人對有關要件事實負擔證明責任,則不符合抽象意義上的公平觀念。但是,就這種基本規則而言,雖然它符合一般意義上的抽象公平觀念,但是,未必符合個案中的具體公平觀念。因此,在遇有證明責任分配的基本規則不符合個案中的具體公平觀念時,應當由法官據情改采證明責任分配的例外規則,即涉及證明責任分配多元論的原理學說與價值觀念。正如我國有臺灣學者所言,古今民事證明責任分配法則雖有多種,但其基本原理則均在“公平”這一點上。任何一種分配法則的產生,雖然固均有其成為法則的理由,但都僅能適用于多種情況符合公平,無法達到適用于一切情況均符合公平的理想狀態。因社會生活的復雜性及世間無奇不有所決定,以一種證明責任分配法則,斷不能應付萬變的訴訟事實。因此,法官應體察證明責任分配的旨趣,對每一待證事實決定其證明責任歸屬時,宜參酌所有證明責任分配法則,根據一切情況,以公平合理為依歸,詳為考慮后,始為決定[7](p·621)。
在言及前述“多元”論所涉及的諸種學說或價值觀念當中,所謂武器平等原則是公平原則在特定場合或條件下的具體體現。對此,有觀點認為,就武器平等原則而言,它指的是當事人無論其為原告或者被告地位或者訴訟外可能存在的上下隸屬關系,但是,在法庭內應一律受平等對待。①法官在個案中,在認定事實適用法律程序上,應對于雙方以公平無私態度來加以對待,以期作出正確裁判。雖然學說對此理論的認識淵源已久,但是,其在證據法上的重要影響,是在德國聯邦于1979年7月25日裁判后[3](p·202)更加顯著。該裁判的少數見解,肯認武器平等原則在憲法及證據法上的意義,尤其在后來為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產生了頗多反響。②另外,就誠信原則而言,雖然在德國的實務界曾認為,根據一般證明責任分配法則應負證明責任的人無法探查事實,而非證明責任相對人顯然能對該事實作出必要說明時,誠信原則就能夠對證明責任發揮相當作用[3](p·203)。但學說與實務一般采取較為保留的看法。③應當注意的是,雖然誠信原則也容易造成法律不安定性,故難以成為一般證明責任分配法則,但為了克服證明困難而作為證明責任減輕類型設定過程而言,應當視為誠信原則有其重要意義。④上述這些觀點的精辟闡釋,對于多元化價值衡平機制的形成,不無裨益。
(三)制定法原則與法官法原則
在實務上,按照規范說的觀念,對證明責任及其分配基本規則的適用,應當由法官對立法者所制定的法規范按照規范說的基本原理進行分析,然后獲得相應的依據。而對于證明責任及其分配例外規則的適用,實際上是對規范說的悖離,也就是當法官在對個案進行審理過程中,當認為適用規范說有違社會的公平正義時,將尋求采用新興的理論學說或者價值判斷標準對證明責任分配規則作出認定。由此可見,對于有關證明責任分配基本規則的適用涉及到對制定法的解讀與應用問題,因此,可將其稱之為制定法原則。相較而言,對于有關證明責任分配例外規則的適用,則實質上涉及到法官的據情裁量及判斷問題,因此,可將其稱之為法官法原則。
應當注意的是,在實行法官法原則時,涉及到法官針對個案情形,當認為適用基本規則有違公平正義時,有權裁量適用特定的例外規則判案。從具有可操作性的角度來看,對某一類新型案件的類型化,需要有一個逐漸認識、形成和發展過程。從以往的經驗來看,特別是根據德國危險領域說的形成過程來觀察,由此所形成的既定模式為,對個案中反復出現的某些特別情事,借助法官在裁判當中所作出的解釋與闡明,從而成為新學說的形成根據。這種模式似乎已經成為大陸法系創設判例法學說的標準。由此可見,對案件的類型化并從中抽象出一般性的原理,是學者為創設某種學說的方法論問題,并非屬于法官在判案過程中的職責。當法官在對個案進行審理并認為有必要對規范說(即有關證明責任分配的基本規則)進行悖離時,他必須通過尋求有關理論學說上所載明的有關證明責任分配的特別規則(例如,危險領域原則、蓋然性原則、舉證難易原則或證據距離原則、利益衡量原則等)來處理案件。
另外,即使當法官窮盡為他掌握的一切必要理論學說,仍無法對有關證明責任分配問題作出公平、合理的判斷時,在這種情形下,法官應以不得拒絕裁判為由,按照為他所認知的通情達理的公平標準,來對個案中遇有的證明責任分配的疑難問題作出獨立的判斷。當然,在此情形下,由于受到審級制度的衡平與制約,為一審法院所作出的這類判決,應當被視為甘冒被上訴審法院駁回或糾正的風險,但這本來正是審級制度的功能與價值所在。
在此,應當注意的是,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7條規定:“在法律沒有具體規定,依本規定及其他司法解釋無法確定舉證責任承擔時,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綜合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確定舉證責任的承擔。”按照規范說來對該條進行理解所取得的直接效果是,有關法律或者司法解釋對通常所遇到的證明責任分配問題,一般不會作出具體的規定,而只能作出抽象性的規定,以便能夠涵蓋盡可能多的類型和數量的案件。對于抽象的證明責任分配規則,有必要根據規范說的基本原理,對有關法規范進行分析和識別之后才能得以具體的適用。凡是不能夠被抽象的證明責任分配規則所覆蓋的類型和數量的案件,通常屬于特殊類型的案件,對于某些特殊類型的案件有關法律(包括訴訟法)或者司法解釋會作出具體的規定。例如,我國民事訴訟法第64條第1款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2條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后果。”該司法解釋第5條第1款規定:“在合同糾紛案件中,主張合同關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當事人對合同訂立和生效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主張合同關系變更、解除、終止、撤銷的一方當事人對引起合同關系變動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上述這些法律或司法解釋有關證明責任分配的規定,均屬于抽象性的基本規則,它們能夠覆蓋許多類型或數量的案件,但是,在適用過程中,如果不采用有關的理論學說如規范說等,就無法正確、合理地引伸出具體的證明責任分配規則。而按照規范說的基本原理,具體的證明責任分配規則應當從民法條文中求得,也就是將民法條文所涉及的各種規范分為基本規范與對立規范,由此而派生出不同類型的權利規范,再根據當事人所主張適用的法律規范的性質來決定證明責任的分配。
相對而言,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4條有關8種類型特殊侵權訴訟的證明責任規定,則屬于法律對證明責任分配問題的具體規定。上述規定第7條中,“在法律沒有具體規定,依本規定及其他司法解釋無法確定舉證責任承擔時”的內容屬于制定法原則的范疇,而“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綜合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確定舉證責任的承擔”,則屬于法官法原則的范疇。
(四)正確地界定和處理不同證明責任規范(或規則)法源之間的界限與關系
因民事訴訟法通常采取辯論主義,因而證明責任分配的理論向來為各國民事訴訟法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但雖經法學者、實務家常年努力,迄今仍難稱已有一放諸四海而皆準的證明責任法則。但一般認為,證明責任分配原則仍須學說與實務見解作為補充①。包括羅森貝克規范說在內的各種學說,在沿用其相應的方法及觀點時,其所努力的共同目標均系試圖為公平正義地解決實務問題提供一個適當的標準。因此,有關證明責任分配規則的設定與解讀往往受有關理論學說的支配。從構成當今各國證明責任分配規則的淵源來看,它包括實體法、程序法、判例法、司法解釋、理論學說,其中,按照實體法的民法條文來判斷和尋求證明責任分配規則,不得不依據有關的理論學說,如規范說。而規范說的局限性則表現在,它所主張的證明責任分配規則基本上僅限于對于有關民法條文本身的理解,即主張某一法規范的適用效果的當事人,應當對因適用該法規范所依據的要件事實負擔證明責任。因此,規范說所涉及的法律適用規范僅指實體法規范,而與程序法規范無關。當今程序法(主要指訴訟法)規范的發展趨勢有與規范說相悖離的傾向,例如,我國臺灣地區“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于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示公平者,不在此限。”可見,我國臺灣地區民事訴訟立法的有關內容既具有對規范說進行修正的功能,也具有與規范說相悖離的功能。我國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既有對有關民法條文進行解釋的內容,也有對民事訴訟法條文進行解釋的內容。例如,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2條、第5條第1款(即合同糾紛案件中有關證明責任的分配規則)系就證明責任分配說設有的概括性一般規定。
但是,筆者認為,鑒于當事人主張的事實相當龐雜,很難以一、二個原則來概括所有證明責任的分配,故此應就個案的具體情形,根據實體法的規定,并參酌有關學說來確定當事人的證明責任。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4條(即涉及特殊侵權糾紛案件中有關證明責任的分配規則)、第7條(有關證明責任的例外分配規則)則具有對規范說進行修正或悖離的功能。相較而言,德國、日本等國的民法及民事訴訟法均未就證明責任直接設有概括性或通則性的一般規定,故通常均委由學說、判例補充。可見,在實體法、程序法、判例法、司法解釋、理論學說均作為證明責任體系當中有關分配規則淵源的情況下,從克服規范說的局限性的角度來看,有關實體法規范可以體現證明責任分配的基本規則,而程序法、判例法、司法解釋、理論學說則可以體現證明責任分配的例外規則,而這些例外規則之間可以相互協調、互相補充,既能夠發揮對規范說進行修正的功能,也能夠發揮對規范說進行悖離的功能。
參考文獻:
[1]陳榮宗:《舉證責任分配與民事程序法》(第2冊),三民書局有限公司1984年版。
[2] [德]漢斯·普維庭:《現代證明責任問題》,吳越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3]姜世明:《新民事證據法論》,學林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3年版。
[4] [日]中野貞一郎:《あとがき》,《判例夕イズㄙ》,第553號。轉引自陳剛:《證明責任法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5]陳剛:《證明責任法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9月版。
篇6
一、二十世紀人類國際私法理論之嬗變軌跡
(一)美國國際私法理論之演進:功能主義勃興之后的概念主義復蘇
無可否認,人類二十世紀的歷程是美國強盛的歷史見證。在二十世紀人類國際私法理論與實踐發展中,美國國際私法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它與歐洲國家國際私法一起成為二十世紀人類國際私法發展的兩大中心。
1、美國傳統國際私法的理論淵源
美國傳統國際私法的主要理論淵源來自于歐陸的“國際禮讓說”(十八世紀),與英國的“既得權理論”(十九世紀),「3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以斯托雷(Story)為代表(十九世紀)和比爾(Beale)為代表(二十世紀前葉)的美國國際私法理論流派。斯托雷認為,一個國家在其自己的領域內享有絕對的和管轄權,所以一國的法律只有在其該國的領域和管轄范圍內才有效力,只有在“國際禮讓”的情況下,才能讓外國法在內國領域發生效力。「4比爾的思想體現在以其為首編撰的1974年美國《第一次沖突法重述》(RestatementofUnitedStates,ConflictofLaws,First,1934)中,其認為,跨國(州)民事糾紛實際上是當事人之間的權利之爭,內國并不承認外國的法律在內國的效力,內國僅承認根據禮讓可以獲得承認的外國的權利。「5
2、傳統美國國際私法理論的特征:概念主義的國際私法觀
“美國沖突法是美國法中少有的具有大陸法系傳統的法律部門之一”,「6因此,傳統美國國際私法理論同大陸法系國際私法理論較為近似,都體現為概念主義的特點。所謂概念主義,以法國民法典的冠名者拿破侖的名言最有代表性:“將法律化為簡單的幾何公式是可能的,任何一個能認字并能將兩個思想聯系起來的人,就能做出法律上的裁決”。「7因而德國法學家耶林批判此種觀念所指導的法學理論為“概念主義法學”。這一特征集中體現在1934年美國《第一次沖突法重述》中,根據該示范法,為了使外國的權利根據禮讓可以在美國法院獲得承認,建立了一套概念主義國際私法觀的沖突法規則體系,其通過連結點這一抽象概念將某一權利固定在某一地域(該地域必定是該權利得以產生的地方),形成了一種概念化的系屬公式以及固定的沖突規則來解決適用何國法律的問題。“毫無疑問,概念主義占據了比爾在《第一次沖突法重述》中所采取的方法中的主體地位,這一制度是建立在具有形而上學意味的既得權理論基礎之上的……”「8美國法學家龐德曾經指出:“十九世紀的法學家曾試圖從司法中排除人的因素,他們努力排除法律適用所有的個體化因素。他們相信按嚴密邏輯機械地建立和實踐封閉的法律體系,在他們看來,在這一封閉的法規體系的起源和適用中承認人的創造性因素是極不恰當的。”「9盡管龐德的評論是針對十九世紀所有法律領域而言的,但我們仍可以將之視為對美國傳統國際私法理論的精辟論述。
3、美國“沖突法革命”-概念主義的衰微與功能主義的勃興
概念主義的國際私法觀指導下的傳統沖突規則具有明確性與穩定性的特點,但其最大的缺點“在于機械地抽象預設單一連結因素以供做選法之媒介,法院依此模式機械的操作,往往將導致不符合個案公正(individualjustice)之判決結果。”「10傳統的沖突規則“過于僵硬和機械,使得法官必須運用一切可行的例外條款,如識別、公共秩序、程序問題與實質問題的劃分甚至反致制度來尋找公平的判決結果,《第一次沖突法重述》也因為這些例外條款而受到重視。由于頻繁而廣泛地適用例外條款,《第一次沖突法重述》漸漸地被認為不足以實現它的制定者所肯定的法律確定性及可預見性目標。反過來,這樣的結果進一步促進和刺激了20世紀60年代早期的沖突法革命……”「11
1933年,凱佛斯(Cavers)教授于《哈佛大學法學評論》發表了《法律選擇過程批判》(ACritiqueoftheChoice-of-lawProcess)一文,「12拉開了沖突法革命的序幕。作為這一場大批判運動的第一人,凱佛斯以其冷靜的思維、敏銳的視角揭示了傳統規范的痼疾所在:傳統的沖突規范是一種管轄權選擇規范,并不是對實體法做出選擇,這種選擇方法根據一個機械的沖突規范,通過單一連接點的盲目指引,確定某一國法律具有管轄權,將其實體法用于審理案件的是非曲直。「13到了六十年代,美國國際私法革命浪潮風起云涌,更為激進的柯里(Currie)教授指責傳統國際私法理論是“概念式的”、“毫無用處的”,“是一個詭辯的、神秘的和失敗的領域”,「14他極力鼓吹要徹底拋棄舊的沖突法,取而代之以政府利益分析方法,即“沖突法的核心問題或許可以說是……當兩個或兩個以上州的利益存在沖突時,確定恰當的實體法規范的問題,換言之,就是確定何州利益讓位的問題。”「15他的學說中新的視角、獨特的分析方法是國際私法學說史上的一大進步,因為他揭示出一切法律沖突背后所隱藏的實質,而在傳統的理論幾乎全“用一些被普遍適應的抽象的規范來掩蓋法院實際上最先考慮的問題”,即選擇什么法律才符合本國對內對外利益,其作用影響深遠。與之同時,還有艾侖茨維格(Enrenzweig)與利佛拉爾(Leflar)提出的“法院地法說”與“較好的法律規范”等大量學說先后涌現,「16目的都在解決傳統沖突規范只指引管轄權法律的弊病,試圖從實現實體正義的最大化出發來重構理論體系。
可以看出,美國沖突法革命的實質是功能主義國際私法觀對概念主義國際私法觀的革命,所謂國際私法的功能主義,是指“通過對案件中涉及的法律規范所體現的立法者的目的和政策的考察,更確切地說,就是考察立法者對于其法律在該案件情勢中適用的期望和意圖以及在其適用中的利益,確定是否適用該法律,以解決法律沖突問題……功能主義的基本特征就在于排除沖突規范的運用。”「17
4、“沖突規則的回歸”-概念主義的復蘇「18
沖突法革命之后的各種美國現代沖突法學說雖為美國各州公共利益的實現和公平解決個案糾紛提供了理論上的可能性,但純粹功能主義的美國現代沖突法學說運用于司法實踐,往往帶有很強的主觀性,容易造成法官在選擇法律上的擅斷,致使所追求的實體法上的公平目標大打折扣。與此同時,各種靈活的現代方法實際上都有不同程度上的“戀家情節”(homewardtrend),即擴大法院地的適用,以至有損于內外國法的平等地位;其次,過猶不及,美國現代沖突法方法一味追求以功能主義的“政策定向”解決法律沖突,使得法律選擇過于靈活,再加上各種方法五花八門,同一種方法又有不同版本,而且新方法層出不窮。方法上的混亂使得法律選擇的穩定性、連續性、統一性及可預見性蕩然無存。此外,這些功能主義方法的運用往往需要綜合考慮多種因素,分析過程復雜,適用這些方法的結果,使得法官不堪重負。
因此,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起,隨著各種激進的功能主義國際私法觀缺陷的日漸顯露,以及面對不斷遭到美國司法實踐冷落的現實,已有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重新檢討純為法律選擇“方法”的功能主義學說,逐步認同概念主義的沖突“規則”在解決法律沖突中所具有的一些不可替代的優勢。這種理論上的轉型導致了七十年代以來沖突規則在美國回歸傾向的出現。1971年,美國法學會公布了由里斯(Reese)教授負責起草的《第二次沖突法重述》(RestatementofUnitedStates,ConflictofLaws,Second,1971),該重述以最密切聯系原則為理論基礎,將傳統的概念主義國際私法觀與現代的功能主義國際私法觀協調起來,建立了一套全新的沖突法體系。
(二)二十世紀歐洲國家國際私法理論演變歷程:功能主義對概念主義之改良
1、傳統歐洲國家國際私法的理論沿革-概念主義的國際私法觀
傳統歐洲大陸國家的國際私法理論源自德國法學家薩維尼(Savigny)的“法律關系本座說”。薩維尼從普遍主義的觀點出發,認為為了使涉外案件無論在什么地方,均能運用同一個法律,得到一致的判決,涉外民事關系應適用的法律只應是依其本身性質確定的其“本座”所在地的法律。在薩維尼看來,每一個法律關系根據其自身的特點,總是與一定的地域的法律相聯系,聯系所在地即法律關系“本座”,該法律關系的準據法即是其本座法。「19薩維尼及其后來的學者在法律關系“本座”學說的基礎上,抽象出每一種涉外民事關系的“本座”,建立起一套穩定的沖突規則體系。薩維尼的學說是典型的概念主義思維方式的體現,即將法律關系與“本座”的聯系固定化、機械化、公式化,唯心地認為每一個性質的法律關系只有一個本座法與之相適應、相聯系,并將它作為一種硬性的沖突規范,以為就可以解決國際私法中法律適用的所有問題。「20“他們最終都以構造基本相似的普遍適用的抽象的沖突規則來解決各種法律沖突。可以說國際私法在幾百年的發展史中,學者們追求的是法律適用的明確性、一致性和穩定性,即普遍性規則的統一適用。”「21自十九世紀以來,許多歐洲國家的國際私法立法受到薩維尼的影響,根據法律關系本座說,人們只要通過對各種法律關系的性質進行分析,就可以制定出各種雙邊沖突規范去指導法律的選擇,因而該學說對各國國際私法立法乃至制定國際私法法典都起到了相當大的推動作用。這些立法都明顯地出現了對涉外民商事關系進行集中、系統、全面、詳細規范的趨勢。「22
2、二十世紀后葉歐洲國際私法新動態:規則、方法并重-功能主義對概念主義之改良
六十年代大洋彼岸的美國“革命浪潮”波及到了歐洲,1964年,德國國際私法學者克格爾(Kegel)在海牙國際法學院作了題為《沖突法的危機》的著名演講,「23揭開了歐洲傳統國際私法改良的序曲。與美國學者完全摒棄沖突規范的作法不同,歐陸國家國際私法的改良(而不是革命),「24還是以沖突規則為主來構建國際私法法典,只是在其中引入了功能主義的方法。對此,美國國際私法學者西蒙尼(Symeonides)的評論頗為精辟:
“舊的沖突法規則不是被徹底摒棄,而是逐步得到改進。此外,歐洲國家對于落后規則的主要反應不是以立法取代它們,也不是在司法實踐中拋棄它們。通過立法方式干預沖突法的變革是少見的,即使有也是經過了充分的辯論。司法領域對沖突法的修正是謹慎并且尊重現有規則的存在價值和功能。歐洲國家的國際私法從來沒有傾向于拋棄沖突法規則而采取美國國際私法意義上的‘理論’方法-即開放式系屬公式。此種系屬公式并不明確指定準據法,而是規定法院確定法律選擇方法時應考慮的因素和指導原則。實際上,大陸法系國際私法的長處在于其認為所謂的方法與法律法典化的觀念格格不入。因此,對于法典化的國際私法體系來說,由里斯教授提出的困擾美國國際私法的‘規則’與‘方法’之間的選擇問題得到了一個簡單的答案-壓倒性地傾向于規則而不是‘方法’。另一方面,正如幾個世紀以來法典化實踐所表明的那樣,采用成文沖突法規則并不一定意味著必須排斥司法裁量權。相反,司法裁量權在新的國際私法立法中得到了大量的反映。理論上傾向于法律靈活性的國際私法立法者可以選擇多種立法工具實現法律的靈活性,最常見的是可選擇連接點(alternativeconnectingfactors),彈性連接點(flexibleconnectingfactors)和例外條款(escapeclauses)。”「25
西蒙尼教授所指出的功能主義的工具集中體現在最密切聯系原則當中。以1999年通過的德國國際私法改革法案為例,該法案在傳統的沖突規范的基礎上,引入了大量的功能主義的新方法,出現了由“規則”向“方法”轉變的趨勢。「26例如在非合同債權關系上,其接受了“意思自治原則”,其第41條采納了“例外規則”的規定,“只要另一國的法律比本法所確定的法律存在實質性更密切的聯系,則適用一國法律。”這就是最密切聯系原則。事實上,二十世紀晚期幾乎所有的歐洲國家國際私法改革立法及國際立法均采納了最密切聯系原則,如1978年奧地利《國際私法法規》第1條的規定,1989年《瑞士國際私法法典》第15條的規定,1992年羅馬尼亞《關于調整國際私法法律關系的第105號法》第73條、第77條的規定,1996年列支敦士登《國際私法法規》第1條第2款,第19條第2款的規定等等。最密切聯系原則是歐陸國家功能主義國際私法觀對概念主義國際私法觀進行改良的重要手段。
二、最密切聯系原則:功能主義與概念主義交互作用的結果
從上文之論述可以看出,二十世紀國際私法理論發展的基本軌跡是功能主義與概念主義的交互作用,而這兩種理論的斗爭與妥協的重要結果之一便是最密切聯系原則的產生。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
“最密切聯系原則的產生和發展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歷史根源的。一方面傳統國際私法的沖突規范由于呆板、機械的缺點,已很難適應變化中的形勢發展需要。另一方面,種種現代學說又由于‘矯枉過正’而使法律適用的確定性受到嚴重威脅。在這種情況下,最密切聯系原則應運而生。它對傳統國際私法并未采取完全否定的態度,而是對其進行了揚棄,即它吸收了‘法律關系本座說’的合理因素,但同時指出:‘本座’不是只有一個,應視具體情況而定。最密切聯系原則不象‘本座說’那樣希望人們接受其結論,相反,它本身并沒有結論,而只是試圖告訴人們走到目的地的途徑。這種合理的改良主張是為那些習慣于歷史漸進沿革的人們所樂于接受的。「27同時,這一學說又借鑒了‘結果選擇說’、‘政府利益分析說’等學說的內容,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國現代、當代國際私法理論各派的學說,凝聚了它們的總體力量。顯而易見,最密切聯系原則是在‘法律關系本座說’基礎上發展起來,但它不是簡單地照搬,而是在批判的基礎上吸收其精華,它們之間反映了一種否定之否定的辯證發展。因此,可以說,最密切聯系原則是國際私法傳統法律選擇方法與現代法律選擇方法的融合與折衷,是國際私法發展史上的里程碑。該原則具有極強的生命力,目前已為世界許多國家的立法所效仿,在司法實踐中也得到了運用,呈現出勃興之勢。”「28
(一)最密切聯系原則的形式淵源與實質淵源
1、密切聯系原則形式上的淵源來自于概念主義國際私法理論
根據通常的理解,最密切聯系原則的主要內容是:“在選擇某一法律關系的準據法時,要綜合分析與該法律關系有關的各種因素,確定哪一個地方(或國家)與案件的事實和當事人有密切的聯系,就以該地方(或國家)的法律為法律關系的準據法。”「29用規則表述就是“某某法律關系適用與該案件的事實和當事人有密切的聯系的地方的法律”,因此從形式上看,這與傳統的概念主義的國際私法觀指導下的系屬公式-“某某法律關系,適用某某地方的法律”是一致的。實際上我們可以將最密切聯系看作一種新型的連結點,一種新創的、并列于傳統的國籍、住所、物之所在地、行為地等的又一連結點,盡管在這個問題上學者們還存在著分歧,「30有人認為最密切聯系是法律選擇適用之原則性指引規范,而不是連結點。對此問題的認識,我們認為應從分析連結點概念入手。所謂“連結點”是指一種把沖突規范中“范圍”所指的涉外民商事關系與一定地域聯系起來的紐帶或媒介,從而在實質上反映了該涉外民商事關系與一定地域之間存在的實質性的聯系。而最密切聯系原則要求通過對具體案例中各個連結因素進行比較分析,在綜合比較的基礎上做出利害的抉擇,其注重的是爭議問題與選擇法域法律的實質上的利害關聯性,體現著實質上的“最密切”。雖然在具體的連結因素上不確定,最密切聯系原則的運用在具體個案中取決于法官對其司法經驗、理性認識的把握來權衡確定,但這一過程本身是一個確定連接點的過程,即在諸多連接因素中選擇出最為反映本質利害沖突的連接因素,完成客觀媒介指引準據法的作用。從其形式到實踐應用都應當認為“最密切聯系”是作為連接點在產生具體的作用,而不是一種概括的宏觀的從思想、認識上的指導原則性規范。
2、最密切聯系原則在實質內容上的淵源來自于功能主義的國際私法觀
最密切聯系原則從其誕生起便在于打破傳統沖突規范的僵化,媒介連結點的單一化,在選擇法律時要求突破舊的框架局限,從一個新的浮動連接點“最密切聯系”出發,以功能主義的靈活的法律選擇方法取代概念主義的傳統國際私法規則的機械與盲目,無論是從范圍到視角、還是思維過程,最密切聯系原則都對傳統進行了革新,賦予社會公正理念的追求于其中。因此在看待最密切聯系原則本身性質時,也不可拘于舊有“連結點”的框架,不可否認最密切聯系的具體實用的媒介指引。
不僅如此,最密切聯系原則還標志著人們對國際私法功能的傳統認識的改變。國際民商事交往需要有序的法律規制,但各國均將其納入本國法調整,使得國際民商事關系沒有一致規則可循。在各國實體法律無法統一的情況下,人們只能企圖在適用哪一國國內法上達成一致,從而間接實現法律適用及法院判決的一致,以實現法律關系的穩定性。這就是國際私法產生的緣由。此外,由于長期以來無法寄希望于直接協調國內法,久而久之,人們習慣于認為只有沖突法才能在國際民商事關系調整中起作用,漸漸將國際私法等同于沖突法,將其功能局限于在各國立法管轄權之間統一分配案件,而忽略對相關實體法(實際上后者才直接決定案件的結果)的關注,不管這種分配是否適合于案件的實際。于是人們十分強調沖突法指引的確定性,對同一類法律關系往往只規定一個連結點,以確保案件無論在何處訴訟都適用同一法律,取得相同的判決,不得已時,不惜削足適履。傳統國際私法的種種不合理性如機械性、僵化即根源于此概念主義的理論。最密切聯系原則則與此相反,它認為國際私法不應只起到路標的作用,為當事人提供公正的行為規則才應成為其宗旨,也就是說,合理調整國際民商事關系才是其功能,在個案中,公正的解決才是首要的追求,其價值高于確定性、可預見性及一致性等目標,而這就要求對案情進行全面分析,以確定適于解決案件的相關法律,以對案情的全面分析代替“閉門造車”的演繹過程,有效地克服傳統國際私法之盲目性、機械性。另一方面,最密切聯系原則又通過對傳統沖突規范的改造,增強其適應力,在沖突法范圍內盡可能促進國際民商事關系的合理調整,將其從激進的美國“沖突法革命”的炮火中挽救出來,并為之開辟了廣闊的道路。作為“革命”成果,它終于成了美國國際私法學界占主導地位的理論,《第二次沖突法重述》便是充分的證明,并且在司法實踐中,這一理論也得到廣泛的承認與運用。「31
(二)最密切聯系原則之不同立法模式「32
1、功能主義國際私法觀為主導的模式(美國)
功能主義國際私法觀在美國目前還是占據主流地位,這從《第二次沖突法重述》中關于最密切聯系原則的解釋可以看出,其第6條規定法官在進行法律選擇,判斷何地的法律是最密切聯系的法律時,要考慮“州際和國際制度的需要;法院地的有關政策;在決定特別問題時其他有利益州的有關政策及其相應利益;公正期望的保護;構成特別法律領域的基本政策;法律的確定性可預見性和統一性;法律易于認定和適用。”「33綜合“革命”的各派學說所總結出的這七條聯系因素,并不強調其先后優先順序排列,相反起草者只希望法院在沖突法的不同領域分別有針對性的對某一特定因素或某些因素的重要性做出自己的判斷,即賦予法官以充分的自由裁量權,以求實現所選擇出的實體規則的具體個案功能,達到功能主義所追求的目標。
2、概念主義國際私法觀為主導的模式(大陸法系國家)
第一,以最密切聯系原則作為沖突規則的一般原則。以奧地利為代表,在其國際私法典中第1條便開篇名義地提出以最密切聯系原則為其法典的普遍性原則,最密切聯系原則有著一般指引的意義。其規定:“與外國有連結的事實,在私法上,應依與該事實有最強聯系的法律裁判。本聯邦法規(沖突法)所包括的適用法律的具體規則,應認為體現了這一原則。”這條規定明確指出,最密切聯系(最強聯系)原則是整個奧地利法規的基礎,法規在確定每一項法律適用時都體現了這一原則。
第二,以最密切聯系原則作為沖突規則的補充原則。以瑞士為代表,其在立法之初便考慮到法律本身固有的滯后性,為了防止這一缺失可能帶來的不利后果,在立法時便早先為之預留余地,其在《瑞士聯邦國際私法典》的第15條的例外規范中規定如下:1)、如果從全部情況來看案件顯然與本法指定的法律有很松散的聯系而與另一法律卻有密切得多的聯系,本法所指定的法律即例外地不予適用。2)、前款規定在當事人已進行法律選擇的情況下不予適用。可以發現,瑞士的做法是界于美國與奧地利之間的,較為合理的處理了穩定與靈活的矛盾,形成較為客觀的統一。
第三,將最密切聯系原則作為一個具體的沖突規范。如中國《合同法》第126條第2款的規定:“涉外合同的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與合同具有最密切聯系的國家的法律。”此外還有《民法通則》第145條、《海商法》第269條等類似模式的規定。在這種立法模式中,最密切聯系被當作一個連結點而使用。
三、功能主義與概念主義之互動:最密切聯系原則于當代國際私法之意義
首先,最密切聯系是功能主義的產物,其本身是一個不確定概念,其外延界定是一個浮動框架,有著彈性的伸縮機制,與傳統的以國籍、行為地、物之所在地等明確概念界定,相對固化的雙邊或單邊沖突規則相比,前者的靈活性優勢明顯,其突破了條塊局限,為選擇法律提供了一個充分、完整信息化的前提條件,從而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法律的公正性實現,有利于案件中實體權益的保護即“結果最優”。在當代社會這樣一個發展迅速的環境中,各種新問題、新矛盾層出不窮,而面對這些不斷涌現的問題僅以傳統的單一、封閉體系來解決問題,缺點是顯而易見的,社會發展的動力便在于不斷的變革,“變則通”,最密切聯系原則便是對傳統的變革,在面對具體個案中個別、例外的情形,舊有的連結點指引相關的準據法將導致案件處理不恰當的情況下,最密切聯系原則的運用便提供了較好的解決方法,最有可能實現法律公平正義的秩序追求。
其次,在最密切原則的具體運用、法律選擇的過程中,主要依賴于法官的司法判斷,這就賦予了法官極大的自由裁量權,使得法官能在整個案件的審判過程中充分運用其司法實踐積累的經驗與法律邏輯思維,本著法律公平正義理念來實現法的社會價值能動追求,這一特色是受最密切聯系原則的產生地-美國的判例法特征影響的。因為在英美法系國家中,注重于司法審判的實踐,判例也成為其司法制度的正式淵源,為司法審判所援引,在他們看來,司法審判過程不僅是一種簡單的機械法律條文運用操作過程,而且為法官在法律精神指引下運用法律進行再創造性勞動提供可能。「34正是基于這一觀念,最密切聯系原則也得以在其國內最先予以確立并為司法審判所運用,成為對舊有概念主義國際私法的突破。
再次,法律沖突在本質上是一種利益的沖突,因而以最密切原則來解決沖突,就是通過對于當事人意思、當地政策、案件的性質以及不同的法律領域等各方面客觀影響的考慮,來把握其關鍵的、不局限于表象的、本質的利益上的矛盾因素,即要求法院對不同連結點在具體案件中的相對重要性做出認定,從而確定最密切聯系。從利益沖突本質來把握問題,便不會在一些細枝末節問題糾纏,法律的最高價值是公平正義,但也因具有效率性追求,有限的社會成本應力求其效用最大化,運用最密切的聯系原則,就是在把握“主脈”,尋求利益爭端焦點,以期最迅捷化解糾紛。
最后,最密切聯系作為功能主義對傳統規則的變革,其出發點便是在于對舊有封閉沖突法的突破,擺脫簡單的靜態的公式化模式,以期實現在制度層面的彈性化、體系的開放化、個案的公正化等社會功用的價值目標。將此問題上升為法理學的思考,將演化為對于法律的秩序與公平價值的衡平。隨著社會的發展,以秩序束縛而犧牲個體利益的作法日益為人們所拋棄,相對于概念主義的傳統沖突法模式的簡單的、靜態化的統一,最密切聯系原則突出其靈活性,其要求從多個連接因素中,權衡確立決定因素所指引的準據法,即由偏重于秩序、穩定而轉向注重具體個案中的正義公平的追求,這是時展的必然趨勢,秩序與公平在大多數情況下是一致的,但在有的情況下也會發生齟齬,如何平衡兩者成為最密切聯系原則的確實目的。
四、功能主義的矯枉過正:最密切聯系原則之隱患
第一,如何避免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濫用?如何實現最密切聯系原則的規范化?權力是一把雙刃劍,在我們考慮最密切聯系原則賦予法官自由裁量的靈活性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放任了自由裁量權力本身,使其有了隨意適用的空間,這對法律內在的穩定秩序、追求可預見性目標構成威脅。設立司法制度目的便在于追求法律公正目標的實現,在此存在著一個預先的假定前提,即法官能本著客觀公正的觀念,毫無偏差的領會法律的精神,并具有高度的技巧,能妥善的處理面對的案情。然而,“由于最密切實際原則本身沒有提供必要的嚴密而精確的分析方法,就使得它的運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法官的分析和判斷。法官通過自己的分析判斷,對發生沖突的有關法律獲得一個大致的印象,然后根據這一印象確定法律的適用。這種做法潛在的弊端是:缺乏精確性;無法排除法官的地域偏見;比較適合于判例法國家而不太適宜于法典化國家。”「35所以為了使法律制度的運作在具體的實踐中不偏離其原有的初衷,為了避免學者們以上批評所指出的問題,有必要形成一些原則性規范來對最密切聯系原則進行補充修繕,即有必要進行最密切聯系原則的規范化。
任何理論的成熟都必須經過一個從實踐到理論再進入實踐的不斷循環前進的過程;在一開始并沒有現成的模型可以直接運用,便應在不斷實踐中去發現、歸納、總結、完善,然后提升為結論予以確立。最密切聯系原則在發展的過程中經歷了萌芽、發展與推廣,已日趨成熟化,也即最密切聯系原則的規范化已成為一種趨勢。美國紐約州最高法院的富德法官是在司法實踐中引入最密切聯系原則的的第一人,其在1963年審理的貝科克訴杰克遜案(Babcockv.Jackson)「36成為國際私法發展史上的經典判例,在該案中富德法官采用的是一種抽象的最密切聯系原則,而到了1972年在同為富德法官審理的紐邁椰訴庫切納案(Neumeierv.Kuchner)「37中,便明顯的體現了最密切聯系原則從任意性而漸漸轉化為規范化的趨勢。該案從性質上同于貝科克案,亦是關于免費乘客遭受交通事故侵權的案件,在該案中富特法官提出了三條規則:1)、如果免費乘客與駕駛者在同一州有住所,且汽車是在該州注冊登記的,那么該州法律就應支配和決定駕駛主人對其客人的注意標準。2)、如果駕駛者的行為發生在他的住所州,而該州法律不要求給予賠償,一般情況下免費乘客就不能因為其住所地法規定其可以獲得賠償,而要求駕駛者承擔責任。3)、如果乘客與主人位于不同的州,一般應適用事故發生地法。此三條規則成為在交通事故侵權案件中適用最密切聯系原則的規范,從而避免了最密切聯系原則適用的隨意性。
由于法官自由裁量的擴大而導致法律判決的隨意性,是片面關注個案“具體的公正”而對法律普適性、秩序安全性的最大破壞,從特殊正義為出發點而最終導致普遍不正義的做法將為社會最終淘汰。判決的隨意的惡果是嚴重的,是對法律根本價值目標的違背,人們之所以在社會治理模式中選擇法治、舍棄人治,其原因便在于相對于人治,法治更為穩定,使人們可預見自己行為結果,從而維持心理的安全感,秩序與安寧是與公平并存法律價值追求。由此,我們有必要對最密切聯系原則予以規范,這種規范更應偏重經驗上的歸納總結性,即選擇法律的管轄范圍有個大概構架,而不是重新將法律選擇問題置于固化,否定靈活機動的最密切聯系原則本身。規范最密切聯系原則絕不是建立于對概念化國際私法規則簡單的“否定之否定”的基礎上,而是在發展過程中對傳統觀念的不斷的超越、重構、充實與完備。
第二,如何避免在適用最密切聯系原則時,片面強調法院地利益的“返回家去的趨勢”?富特法官在審理“貝科克案”中,將最密切聯系原則與政府利益分析方法相結合,從此這兩種理論似乎結成不解之緣。在今日推崇“至上”,政治國家林立的現實世界中,法官雖然是司法運行程序中的“中立者”,但亦絕不可忽視其所處的社會環境對其施加的影響,權力對司法的干預從來便不曾間斷過,尤其在涉外案件的處理中,涉及爭議的是本國或與本國相關的利益與外國利益之爭,法官基于其主觀前見,在法律選擇中不免有所偏重。這樣一來,最密切聯系原則有時在實際運用中往往成為了一場虛假游戲的道具,這是對最密切聯系原則精神實質的違背。在當今這樣一種經濟全球化局勢下,以政府利益分析方法為根本出發點,片面強調法院地法優先,來適用最密切聯系原則的作法將被唾棄。隨著各國經貿往來的增加,相互間經濟上的依存性也日漸加深,在目前這樣一個利益日漸復雜化的網狀結構中,司法的透明、公正成為必要,否則引致的負面效益將是不可估量的。經濟沖擊的壓力下使政治干預威勢在日減,“市場是天然的法制經濟”,相信在市場一體化的大潮中,政治權力對于司法的滲透將得到排除。
第三,如何避免最密切聯系原則顛覆整個國際私法規則體系?最密切聯系原則在國際私法領域適用范圍的過于寬泛化,最終可能導致這樣一種后果:即從整體上拋棄舊有國際私法規則體系,而忽視其中一些行之有效的經驗性的積累,最后所有的國際私法規則全部變成了“某某涉外民事關系,適用與其具有最密切聯系的法律”這樣一條規則。這種全盤推倒重來的態度是不負責任的,在法律選擇這一本來就比較混亂的領域中希求以模糊不易把握的最密切聯系原則來解決一切紛爭,無益于在渾濁的池水中再攪拌幾下,使得更為混濁不堪。批判的目的只應為更好的繼承。因而,最密切聯系的適用不可過于寬泛化,而應量入為出,即在適時必須時運用,而不可凡是都援用,而將經歷實踐運用行之有效的舊有沖突規則擱置。綜觀歷年的實踐我們不難發現,作為軟化傳統概念主義國際私法的彈性規則-最密切聯系原則在充斥變量因素的侵權法、合同法等領域發展迅速,并伴隨經濟的不斷發展而歷有革新。這是因為,傳統沖突法以法律關系的“本座”為出發點,單一化的強調侵權行為地在法律適用中的絕對化作用,而在今日隨著法律關系變化的迅捷,行為地的支配性地位日益受到挑戰,尤其網絡經濟中大量存在的侵權行為與侵權結果地的分離,再簡單地以靜態的行為發生地作為指引規則將不合適;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合同法領域,由于合同本身的技術性,意思自治便不再是簡單地以單邊或雙邊規則機制可以解決,因此在這樣一些領域內最密切聯系原則的突破成為必然。然而并非國際私法所有的問題最密切聯系原則均可包辦,在一些傳統領域如婚姻、家事領域,概念化的傳統沖突規則更具有市場。
總之,新生事物往往在一開始,由于寄托了人們過多的熱情而感情化,不可避免的存有隱患之處,只有經歷實踐的不斷磨礪,新理論才能在不斷的提升與總結中形成理性化的成熟形態,最密切聯系原則亦是如此。
篇7
關鍵詞 集團訴訟 民事訴訟程序 功能主義比較法 群體性糾紛
集團訴訟是當代世界共同關注的一個重要的法律和政治問題。[i]國際社會在制裁集團害和保護分散性利益等方面面臨著相同的課題,并都在致力于為公眾提供有效的救濟機制。然而,各國對于集團訴訟的態度、政策、制度設計和實踐卻是千差萬別,顯示出一種多元化的趨勢。顯而易見,對這個問題的決不能停留在純的分析和普適性原理的照搬上,而必須借助法律社會學的實證研究和比較法的方法,以探尋現象背后的原因和更深層次的發展,并需找適合本國實際的合理解決方案。在比較法社會學的視野中,任何制度的存在都有特定的原因和條件。人類社會在面對相同的課題和實踐需求時,既可能采取相同或相似的應對,也可能也會有完全不同的選擇——面對相同的問題,基于不同的理念和側重點,設計建構出迥然不同的制度。形式不同的制度既可能承載相同或相似的功能,殊途同歸;也可能沿著自身的價值選擇和內在邏輯,走向截然不同的方向。每一制度在運行中又可能或多或少地與預期目標發生游離,衍生或演變出一系列新的方法或制度。對于各國形形的制度,可以采用相同的標準進行比較和衡量,例如,社會效果、利弊、效益等等,同時這種比較和衡量又必須與該制度所在的特定環境和時代背景相契合。而這些研究最終應服務于一個實際目的,即借鑒移植或制度建構。
一、功能主義比較法的研究路徑
規范的比較法研究是從法律規范和制度的比較出發的,即對世界各國相關的法典、判例和制度進行從概念、原理到法律技術和具體設計方面的比較。然而,比較法決不能停留在這個起點上。否則充其量只能看到各種制度與規范之間的同異,而難以發現其背后的原因,也無法揭示其中的規律,更不能實現比較法的實踐目的——對本國的制度建構提供合理可行的方案。因此,比較法研究更重視一種功能主義的方法,或稱之為一種從問題出發的方法,本質上也是一種法社會學方法。“具體地說,就是應該這樣提出問題:”在本國法律秩序中有通過這種法律制度處理的某種法律需求,而外國是通過什么方式滿足這一需求的‘,而調查的范圍,除了制定法和習慣法外,還必須遍及判例、學說、格式合同、普通合同條款、交易慣例等等該法律秩序中構成法律生活的一切形式。而且正因為比較法要求如此廣闊的視野,所以,與其提出個別性的問題,不如把相互關聯的各種問題包容在一起,作為綜合性問題提出更為恰當“。[ii]
在集團訴訟問題上,功能主義比較法不失為一種很好的研究路徑。其思路是,對于小額多數侵害的救濟是社會必須共同應對的問題,但每個國家以何種方式去解決這一問題,卻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理念和具體做法。這一問題不僅涉及法律制度的設計,而且取決于一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程度,政治體制,司法權威和功能,法律職業,當事人,社會觀念以及法律文化等多種因素,只有充分掌握這些因素,才有可能找到最適合本國社會基礎和現實條件、成本與風險最小、最適用的解決方案。否則,就可能在盲目移植過程中付出深重的代價。
當代各國的集團訴訟(group litigation)基本上可分屬四種基本形態,即共同訴訟或訴訟合并(Consolidation)、代表人訴訟(Representative proceeding)、團體訴訟(Verbandsklage)和實驗或典型訴訟(test action或model Suits)。其中每一種都各有利弊及局限性,但是又有一個共同點,即最初都是為了實現訴訟經濟的目標而建立的,但都可能被作為現代小額多數侵害的救濟途徑而發揮作用。比較這些制度的優劣,“是一個老大難的問題。很難說清某一法律下的各類經驗對其他法制有多大的重要性,但至少可以說越是扎根于某國特殊的政治、法律環境的制度,越難嫁接到其他國家去。許多證據都表明所有的民主國家都逐漸認識到更有效地確保擴散性片斷利益的必要性,但當想要將某國為此所設立的制度推廣到其他國家時,不能不進行十分慎重的考慮。因為這里采用的集體訴訟、分擔律師費原則等等方法……并不是如制鐵技術、闌尾手術般非常容易進行移植的‘法律技術’。確切地說,大多數制度都與該國的政治構造、三權分立的具體形態密切相關。……僅僅是對各國為促進公共利益而采用的方法進行一番,也遠遠不能預測出其中哪些對其他國家也適用,如果加以采用,也會同在母國一樣起到同樣的效果。”[iii]
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和不同的政策取向下,人們由于受到不同的價值觀和社會意識形態的,對每一種制度的評價都會有所不同。比較法研究不僅應對各國集團訴訟的立法和制度進行規范分析,還應進一步比較這些制度和理念的同異及其原因。在一個民主和理性的社會中,在引進或創建任何一項制度時,最重要的是保持各種信息渠道和言路的暢通,形成各種社會利益之間的平衡,保證公平與效益的統一,追求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最大化與相互協調。
二、相同的問題,不同的對策
當代世界各國共同面臨著集團害造成的小額多數權利救濟問題,并由此產生了相同或相似的社會需求,即:盡快制止這種侵害的繼續并對違法者予以制裁;以及對已經造成的侵害給予救濟。盡管各國由于經濟社會發展程度不同,市場和的規模有大小之分,但是由于經濟全球化的影響,這兩個問題都不同程度地擺在每一個國家面前,并且正在以跨國界、跨區域的形式發展。不僅如此,由于當代消費者運動的推動,全球性的群體害及其救濟問題已經迫在眉睫,并迅速波及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圍繞著上述基本問題,還會衍生出一系列相關問題,包括,如何有效地通過事先防范性措施(包括民主化的大眾監督方式)避免侵害的發生,如何通過司法救濟、特別是民事訴訟處理社會中發生的新型糾紛和利益沖突,公益訴訟的理念,訴訟成本與效益問題、司法資源配置及司法功能等等。這些共同的問題和共同需求聚合為通過特定的司法途徑或訴訟程序實現社會公共利益的目標,并為此進行了各種以相對經濟和集約化的方式為受害者提供救濟的嘗試和努力。在這一過程中可以看到這樣幾個特征:
首先,世界各國都在嘗試建立某些新的機制、特別是新的訴訟形式,以發揮特殊的功能,解決傳統訴訟制度中無法解決的問題,無論采用何種形式,集團訴訟和公益訴訟都已被納入到當代世界各國司法體系之中,并仍將有一個較大的發展空間。
其次,新機制的建立必然會與傳統的民事訴訟和司法原理、技術發生一定程度上的沖突和矛盾,在一些最根本的問題上,如當事人適格、訴權讓與、判決效力擴張等仍存在著較大障礙。一旦這些障礙被突破,必將帶來集團訴訟或公益訴訟的大發展;但是,由此也可能帶來制約與控制的失效,導致濫用和混亂,甚至由此引發民訴法學原理和體系的徹底顛覆。由于世界各國在這方面的嘗試都尚未提供完全成功的經驗和確定的答案,因此,這一嘗試和經驗積累的過程仍將持續下去,突出的特點是謹慎立法、不斷改革和司法機關的嚴格控制。
最后,如果僅僅從應然的理念和邏輯推理出發,人們可能很容易將現代集團訴訟視為一種帶有普適性的法律制度或法律現象,并確信某些符合當代社會特定需要并具有重要價值的集團訴訟模式或制度,可以無障礙地移植或引進到其他國家或社會,成為當代人類社會共同的法律文化和司法的必然發展趨勢。這種信念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能成為一種強烈的意識形態,使人們不愿意看到事物的另一面或其他路徑及方式。然而事實上,在世界各國,同類制度的構想盡管具有相似性或共同性,但無論是基本理念和原理,還是制度設計及運作方式上,都存在著巨大而明顯的差異。每一種制度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優勢、重點和一定的局限性甚至弊端。這就對其他試圖借鑒這些制度的國家提供了多樣的選擇,也增加了選擇和制度設計的難度。
那么,面對相同的時代課題,世界各國為什么會有如此不同的對策和制度選擇呢?首先,面對這一新問題,傳統的經驗和既有制度中很難找到適合的現成方案。當代世界各國的集團訴訟模式,幾乎都是在實踐中探索和發展的;甚至是與立法者最初的制度設計相背離的。而在未經實踐檢驗前,決策者有時并不能在眾多的選擇中先驗和主觀地判斷哪一種制度為最佳方案。而迄今為止的實踐結果表明,幾乎并不存在一種完美的群體性救濟模式。這就更加造成評價和選擇的困難。其次,不同的法律傳統和文化,往往會奉行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或觀念,這些理念因素對于制度設計和運行都會產生深刻的影響。根據不同的理念,會出現選擇中的不同側重。第三,出于不同考慮而作出的不同選擇往往都具有其合理之處,不可能通過比較而簡單確定最佳或唯一合理的方案。因此,多元化的選擇和制度建構就成為必然的結果。
應該看到,面對小額多數侵害的問題,無論是從盡快制止侵害還是為受害者提供救濟的角度,并非只能以司法途徑和集團訴訟方式解決。一項國際比較法學研究指出:“某一法制下,有許多種途徑可以有組織地保護擴散性片斷利益。法院的公共利益訴訟僅是其中一種途徑而已。再一個可能的方法是,將違反法令行為定為刑事犯罪,讓司法長官有足夠的人員可以有效且可信地執行刑事訴訟。此外,還可以不單靠訴訟,而且主要通過給予或是取消禁止命令(cease-and-desist orders)、表明應遵循的行動標準的詳細形態或過度征稅等方法抑制集團違法行為,將公眾利益的責任交由具備足夠資金和調查權的公共機關。……因此,是否有必要采用促進公共利益訴訟的方法,只能因國家的不同而定,在各國內部也必須區別考慮要求執行的是哪個領域的法律。”[iv]顯然,即使面臨著同樣的問題,采用集團訴訟方式也并非像很多學者以為的那樣毋庸置疑,很多國家仍然希望從以下幾方面尋找更為合理和有效的替代方式:
首先,多樣的救濟方式。在高度評價集團訴訟的重要作用的前提下,很多國家及其法律界人士認為,集團訴訟并非唯一的選擇,不僅可以直接通過其他機制起到相同的作用;即使建立了相應的訴訟制度,仍可以各種非訴訟替代性機制減少其負面作用。救濟方式的選擇實際上與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程度和國家及其運作方式直接相關,只有對該國群體性糾紛的性質、特點、頻度和范圍有一個的估計,并對各種糾紛解決和救濟機制的有效性進行綜合權衡,才能做出合理的選擇。從當代社會的實際需求看,最合理的選擇應該是建立一種多元化的糾紛解決及權利救濟機制,其中訴訟、尤其是集團訴訟應該是嚴格節制使用的尖端武器和最終途徑;而行政監管、預防和社會救濟協調機制,以及個別訴訟則應是常規機制。
其次,實現法律目的的適宜主體。集團訴訟被認為是一種通過民眾促進法律實施的有效機制。但很多國家認為,盡管民眾和當事人可以在執法中發揮積極作用,但是社會不能期待以集團訴訟方式保證法律實施;由國家執法機關作為制止集團害的主體,比以民眾訴訟或集團訴訟的方式,即由民事主體作為主角更為合理和有效,也更容易受到法律的規范。這樣,可以通過合理配置資源,賦予執法機關一定的調查權、決定權和起訴權,減少私人訴訟中的舉證、當事人適格及訴訟成本等負擔。由行政機關通過法定程序直接介入某些集團侵害的調查處理,如環境污染問題,顯然更為有效和經濟;而由檢察官或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的方式則比民眾訴訟更容易得到認同。由于國家權力是一種容易受到腐蝕的權力,確實可能出現執法機關不作為或監管不力的現象,乃至于失去公眾的信任;但是,這一問題可以通過制約監督機制和加強法律責任加以改善——在法治社會,行政權力畢竟比群眾運動更易于控制和規范。
第三,合理確定訴訟的目標與重點。對于集團侵害或小額多數分散利益的救濟,不同的制度有著不同的側重點,例如美國集團訴訟在損害賠償方面最為有效,而德國團體訴訟則將重點放在停止侵害方面。前者著眼于事后救濟,主要采用給付之訴的方式;而后者則重在制止侵害的繼續或防止其發生,主要采用停止侵害(禁止)之訴的方式,并可能采用行政訴訟或準行政訴訟程序。如何選擇訴訟的重點,特別是是否有必要推廣大眾侵權損害賠償訴訟,將會是本世紀世界各國司法改革的持續目標,其中的爭論及反復將在所難免。
第四,選擇適當的責任承擔方式。集團侵害的加害者或違法者承擔責任的方式可以通過不同的訴訟形態體現出來。多數國家認為,民事訴訟的功能主要是填補損害,而不是懲罰和制裁。基于這種理論,在制裁違法行為方面,應該將刑事懲罰與民事訴訟的功能嚴格區分開來,對于環境犯罪、嚴重的責任事故或由于違法行為導致大規模的人身傷害事件,應該由國家機關盡早介入進行偵查或調查,提起公訴,對于違法者追究刑事責任、進行刑事制裁;或者以行政方式要求其停止侵害,撤銷其行為資格,并課以行政制裁。在民事訴訟方面,也應該將禁止之訴與賠償給付之訴區別開來,不宜大規模地引進懲罰性賠償解決民事侵權賠償問題。而禁止或停止侵害之訴都無需以集團訴訟方式進行。過多地采用懲罰性賠償,一方面可能誘發大規模的集團訴訟和無休止的訴訟潮,對市場和社會造成壓力,影響司法程序的運行;另一方面也可能會在和解中使違法者逃脫應有的制裁。毫無疑問,針對集團害,刑事制裁、行政制裁和民事制裁缺一不可,但應是嚴格權限、懲罰適度、公平高效,這就需要判斷、分析和選擇。
第五,權衡訴訟效益。在分析糾紛解決、訴訟和集團訴訟問題時,效益不僅指個別糾紛案件的成本與產出比,而且還必須考慮到其整體。集團訴訟產生于訴訟經濟的考慮,其前提是,與其他的方式比較而言,集團訴訟方式應具有更高的效益,倘若不采用集團訴訟,可能會導致更高的成本、更長久的拖延、以及更大的不公正。但是,如果相反,將集團訴訟視為一種常規程序,大量曠日持久的集團訴訟不僅難以產生預期的效益,反而會造成社會秩序和市場秩序的混亂,并成為某些特殊利益集團、如律師獲利的機會,就可能招致主流社會的抵制。在這種情況下,即使集團訴訟的目標是正當合理的,仍可以考慮選擇適用其他更加便捷、經濟和有效的方式。盡管建立了集團訴訟,也仍然必須通過嚴格的法院管理進行限制與監督。
第六,建立合理的激勵機制與制約監督機制。世界各國雖然已經或可能在將來建立各種集團訴訟模式,但是出于不同的政策和態度,其運作情況和實際作用仍可能表現出明顯的差異。如采用激勵機制鼓勵當事人積極利用集團訴訟,就需要對其頻繁發生有足夠的準備。而如果立法和司法政策對集團訴訟采取一種謹慎的態度,就會更多地注意設計集團訴訟的制約監督機制,加強法院的管理和監督,并鼓勵倡導采用可能的替代方式以減少集團訴訟的風險和成本。
三、集團訴訟的移植——社會條件與法律文化比較
有關集團訴訟問題的討論往往歸結于移植的可能性。美國集團訴訟在其鼎盛時期,曾經給世界各國法學界帶來了極大的刺激和希望,被稱之為“美國的法律天才們最具特色的成就”,在關注這一制度發展的同時,不少國家都曾經討論過移植的可行性;中國則在1990年代初快速將這一理想付諸實施。然而,此后隨著集團訴訟在美國本身的沉浮,在世界范圍,這種移植的意圖和腳步卻進展緩慢。迄今為止,除了美國之外,還有英國和加拿大、澳大利亞的部分地區建立了集團訴訟制度。[v]在歐洲,蘇格蘭、芬蘭、瑞典、挪威等國探討了集團訴訟的可行性或已經開始實施,南非也有這樣的動向。[vi]但是在實踐中,很少有哪個國家的集團訴訟出現了美國那樣的運作規模。這是因為,各國家的立法者和司法機關大都深知,特定的制度往往需要特定的條件和基礎,如不具備相同的社會條件,則即使建立了相同的制度也未必能產生同樣的結果。德國曾經一度對美國集團訴訟極為關注,自1970年代以來發表了若干介紹美國集團訴訟的論文,并有人提出了導入該制度的提案。[vii]但多數人對此持消極態度,理由是:第一,集團訴訟的既判力向第三人擴張,違反了德國基本法103條一款關于審判權的保障的規定;第二,兩國在訴訟費用及律師報酬方面的制度不同;第三,集團訴訟的損害計算及賠償金分配方面非常困難。[viii]
2000年7月,來自20個國家的90位法律界人士聚集在日內瓦,就集團訴訟問題召開了一次國際研討會。在會議上,不同國家的報告人分別介紹了本國集團訴訟的情況和社會評價意見,并集中探討了美國式集團訴訟的移植問題。從報告和討論中可以看到,各國法學界人士對此存在激烈爭議和巨大分歧。[ix]美國人對其集團訴訟本身就存在著截然不同的評價。而更多的討論則圍繞著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展開:一種看上去頗具優勢的制度,是否可以毫無障礙地移植到任何其他國家,并發揮同樣的功能和效用?問題是,引進一個制度不僅需同時考慮其利弊,還需要考慮這種制度賴以建立和運行的基本條件,如果不能接受或認同其所蘊含的理念和倫理,不能創造相同的條件,那么即使移植,也不可能真正使其成活,甚至會使其失去在本土上的生命力。不僅如此,由于社會條件和許多不特定因素,很多制度在實踐中往往會脫離立法者最初設計的軌道,出現無法預料的結果。一般而言,與集團訴訟直接相關的社會因素至少包括。
第一,政治體制與司法體制,這是關乎集團訴訟價值理念及運行條件的最關鍵因素。有關集團訴訟的爭議經常涉及其正當性問題,尤其是當集團訴訟已經超越糾紛解決的范疇而進入資源與利益分配等決策性問題的時候,可以看到司法權的限度和民主政治的基點都開始出現了某種程度的傾斜。“這類爭論的結果和對公共利益訴訟的定位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一個國家關于法律形成過程中立法和司法的作用的思考和行為模式。這種模式是多種多樣的。……歐洲的法律專家在審視美國現代的法律舞臺時,恐怕會對憲法及法律在重要的社會各制度的結構和運用上所進行的缺陷改革中,法院活動范圍之廣深有感觸。雖然如此,但許多國家并不太希望模仿美國,不管是政治結構和社會經濟發展階段與其迥然相異的國家,司法威信不如美國高的國家,還是更依賴于官僚程序的公平的國家,社會結構更均衡的國家,或者是民事訴訟制度更易產生糾紛的國家。”[x]具體而言,這方面的差異包括:
首先,司法的功能(能力)、權威和權限。即使同樣是以三權分立為政治體制基點的西方國家,司法的功能及地位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隨著當代司法權限的擴大,世界各國的民事訴訟制度出現了一種分化趨向,即所謂“糾紛解決模式”和“政策修正模式”[xi],二者分別代表了傳統司法理念和“司法能動主義”觀念,[xii]并反映在不同國家的訴訟制度和理念中。美國的集團訴訟、公共訴訟在當代的高速發展,都是與司法能動主義理念分不開的,即試圖通過這些新型訴訟推進制度的改革。然而,一般而言,由立法機關代表的議會民主仍然具有最高權威,在面臨著重大的利益紛爭和社會政策時,唯有立法機關具有作出決策的正當性。20世紀后半期以后,多數國家的司法權已明顯擴大,但至今仍有許多國家,例如法國,恪守著對司法權的嚴格限制,法院無疑不可能具有通過集團訴訟促進司法決策的正當性。以德國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國家的法院也仍然恪守著法律執行機關的定位,并不準備采取司法能動主義的姿態,也不認為普通法院有能力完成決策的使命;而其民事訴訟基本上仍然保持著糾紛解決模式,并沒有成為社會決策的契機。由此,必然產生對訴訟的不同期待和對策。實際上,多數國家都不鼓勵司法權的過度擴張和司法能動主義。因此,不僅在選擇集團訴訟模式時必須對政治體制及司法的功能有準確把握;同時,如果司法機關不擁有足夠的資源和能力,就必然會采取自我限制的政策;那么,即使在制度上引進了某種集團訴訟模式,也未必能發揮其原型的功能和作用。
其次,國家結構。美國的集團訴訟在運作中之所以會出現與立法預期目標不同的結果,與其聯邦體制、二元法院體系和法院管轄權的高度自由密不可分。美國紐約大學的琳達·瑟伯曼教授認為:“美國的集團訴訟成型于這樣一個制度中:(1)依賴于強烈的對抗傳統,(2)由充滿進取心的律師所激勵,(3)與強大的司法創制文化相適應,和(4)被一個錯綜復雜的雙重法院制度(即聯邦制)變得更加復雜化”。[xiii]其中最后一個因素在其集團訴訟的發展和運作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由于各州的立法存在極大的差異,因此,一旦一些律師發現某一個州的立法能夠使集團訴訟獲得有利判決,就會到該州提起集團訴訟,而無論原告或被告實際上在何地居住、生活、營業,或糾紛的事實(侵權或合同)在何處發生。同時,不同法院(法官)對集團訴訟的態度和政策也是原告律師選擇管轄法院的重要因素。正因為如此,2005年《集團訴訟公平法》才規定對州法院管轄權進行限制。即使如此,美國高度自由的法院管轄權仍會使得每一個原告律師都會首先從選擇有利于自己的法院開始進行集團訴訟。毫無疑問,聯邦制國家并不一定會出現同樣的結果。這是因為其他聯邦國家在實體法和法院體系上并沒有美國這樣的差異性;而且,在美國這一因素只有與其他因素結合起來共同作用,才有可能出現這樣的結果。確實,這些綜合因素既是美國集團訴訟異常活躍的動力,也使其容易被濫用或失控的原因。
最后,法體系的劃分及行政訴訟機制。美國法本質上沒有嚴格的公私法的劃分和區別,也沒有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的區別,因此,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政策問題都可能以民事訴訟提交法院,僅僅在訴的類型上區別為給付之訴、確認之訴和禁止之訴。英國則不同,發達的行政法庭和行政執法體系抑制了群體性訴訟的需求。而在歐洲大陸國家,不僅在訴訟中將公權與私益、行政訴訟與民事訴訟、公益訴訟與個人私益訴訟區分得非常明確,而且不能允許將刑事、行政制裁與懲罰性賠償相提并論;同時主管的機構也并不僅僅是普通法院,還包括行政法院、專門法院和其他專門機構等等。這些差別會使得各國對集團訴訟的功能會有完全不同的理解。
第二,訴訟文化、技術與傳統,這些要素與司法體制密切相關,決定著集團訴訟的模式與實踐。主要包括:
首先,體系的出發點。在比較法上,歐洲大陸法系國家被稱之為成文法國家,而英美普通法國家的法律體系則被稱之為判例法或法官法,前者屬于一種“規范出發型司法”,而后者則屬于著眼于解決原發性糾紛的“事實出發型司法制度”。這并不是形式意義上的劃分,而是一種法律技術的出發點。盡管在英美法系國家,成文法和議會同樣擁有最高權威,而大陸法系國家也同樣重視判例的作用,二者在形式上已經趨同,但是這并不會改變二者在法律技術、法律思維和基本原理上的差異。成文法國家傳統上就是以法律規范和體系為出發點的,盡管今天在法律規則出現缺漏時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已經得到承認,司法的獨立性同樣毋庸置疑,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整個法律體系和秩序可以由法院和法官在司法實踐中自由地創造,更不意味著法官可以在一種自由的程序中去發現法律規則和原則。大陸法系國家強調法律體系的內在邏輯的嚴謹和周密,強調規則應該是確定、公開和可預測的;強調程序法應服從實體法,為實體法設定的根本目標服務。不僅如此,當事人的權利也同樣需要受到實體法的嚴格限制,不允許任何人代表他人行使訴權,并作為改變政策和既有規則的武器。
而英美法本質上屬于一種事實出發型司法制度,具有經驗法的特點。其本質特征是以程序為中心,由具有較高法律素養和經驗的法官從司法實踐和具體案件中發現規則。在使用陪審團的情況下,由于規則和事實的確定性程度相對較低,使審判的結果往往難以預料,更加刺激了當事人通過訴訟嘗試獲得權利和利益的動機。美國司法的這一特質,在陪審制+懲罰性賠償+聯邦制多元化管轄條件下的集團訴訟程序中,被發揮得淋漓盡致。同樣,這既是促使其發揮功能的基礎,也成為刺激社會成員積極利用乃至濫用這一程序的動因。一旦這些因素被減少或取消,則利用的積極性、社會功能和濫用的可能性都會相應減少。例如,如果取消陪審制,集團訴訟的誘惑力和壓力就大大減少,和解的動機就會減弱;而通過強化法院的職權管理,既可以減少自由程序可能誘發的訴訟潮,也可以減少原有的對抗傳統在集團訴訟中的作用,以便更好地對集團訴訟進行制約和控制,但由此民事訴訟的當事人主義原則和對抗制傳統卻可能受到貶抑。[xiv]
法律體系的這種特質深刻滲透在一個國家的法律文化和每一個具體制度和程序環節之中,對于制度移植和建構而言,是必須充分重視的要素。日本民事訴訟法在原有的大陸法體系中引進了許多英美法的制度或程序,但由于體制上的不協調,始終無法避免運行中的各種困擾。[xv]美國式集團訴訟的引進之所以在大陸法國家困難重重,即使不考慮其弊端和濫用的可能性,僅僅是引進之后能否被有效利用、與現行法律體系如何協調就足以令立法者和司法機關卻步了。
其次,司法理念。美國集團訴訟之所以能產生巨大威力,就在于它允許任何人不經明確授權就可以代表所有集團成員提起訴訟,并可以作出實體處分、包括和解;其判決的效力可以向未參加訴訟的人擴張。這一規定作為其顯著標志,也成為激進法學家的最高理想。但是,在絕大多數國家,這種理念是違背司法基本原理乃至憲法原則的。因此,它們即使采用相似的制度,也未必能接受這一做法。德國學者認為既判力向第三人擴張,違反了德國基本法103條一款關于審判權保障的規定。而英國仍堅持一對一訴訟的基本構造,要求集團訴訟的所有當事人必須進行登記。毫無疑問,這種制度設計必然使得集團訴訟的威力大大降低。
此外,集團訴訟在美國的實踐表明“更自由的程序規則具有鼓勵訴訟的性質”,[xvi] 而這是多數國家的司法理念和傳統所不贊成的。[xvii]尤其是當代西方民事司法改革中已經提出減少訴訟,降低司法期待,以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為民眾提供接近正義的機會和途徑,減少司法資源的浪費和訴訟成本,提倡協商性司法、降低訴訟的對抗性,提倡法院職權管理,等等,這些理念都與集團訴訟的理念存在某種沖突和矛盾。在這種背景下,很多國家在觀望和討論中實際上已經開始更多地以其他替代性方式來解決集團訴訟提出的,或者以嚴格制約和限制為前提建立這一制度。而美國自己也在調整集團訴訟的作用方式與范圍,以降低其帶來的負面作用。
再次,法律技術。集團訴訟通過與不同的法律技術相結合,會產生不同的效用;而如果缺少相應的法律技術,其作用也會相應降低。其中最重要的幾個法律技術環節或制度包括:當事人起訴方式,代表人的資格,陪審團,懲罰性賠償,法院管轄權的選擇,證據開示制度,律師及其報酬,法院管理等。引進集團訴訟時,如果沒有這些法律技術環節的配套,就可能使其成為一個無用的擺設。例如,德國在討論在侵權損害賠償方面引進美國集團訴訟的可能性時,強調德國法的損害賠償制度與刑事制裁不同,應以填補受害人的損害為重點,傾向于否定以損害賠償實現制裁違法者或防止違法行為的目的。所以,德國立法在構建調整群體利益的訴訟和司法救濟制度時,認為將其作為個人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加以規定既不適當也不必要,而更妥當的是將其作為團體的權利加以考慮。對懲罰性賠償的拒絕,成為否定引進集團訴訟的主要原因。
最后,訴訟文化。集團訴訟之所以在其發源地英國默默無聞,而在美國卻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與美國民族的訴訟文化密不可分。美國學者奧爾森認為,好訟已成為美國的法律文化,它包括鼓勵訴訟的社會理念(意識形態),和由于解除了對律師和訴訟本身的制約而激發了訴訟爆炸的訴訟制度乃至整個法律制度。[xviii] 美國總統布什在2005年簽署集團訴訟公平法案時,批評美國人的損害賠償訴訟遠遠高于其他國家,并宣稱要改善或結束美國的這種訴訟文化。[xix]集團訴訟本身已經成為美國訴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沒有同樣的訴訟文化背景,集團訴訟就不可能發揮相同的作用,但也可能相應減少其風險。然而,美國的訴訟文化并非人類社會的共同方向和共同價值,每個社會都有權根據自身社會的需要創造更有序和更合理的訴訟文化。
第三,社會發展程度,不同的社會經濟發展程度決定了各國在侵權損害賠償的標準、范圍和方式方面有所不同,也決定了救濟的重點、形式及途徑的不同。這方面的因素對于包括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制度設計最為重要,主要是:
首先,社會發展程度與救濟方式的選擇及救濟的標準的關系。集團訴訟的出現是與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產業規模的不斷擴大和集中化同步的,在這個發展階段,一方面,大規模集團侵害已成為社會關注的重要問題,另一方面,市場的成熟使其規范程度日益提高,技術水平、檢測手段、措施等不斷加強,相應的法律制度與自律機制相對完善,承受風險的能力也逐步在提高。在這種情況下,小額多數侵害的司法救濟問題被提上日程,不斷促進國家和社會通過新的規則、程序和機構組織處理這些問題。這就需要大幅度地增加司法和其他公共資源,建立社會保障和保險機制,確立國家標準和行業標準,并且依靠國家的宏觀調控和行政監管,對各種行業中發生的不法行為及時進行管理和介入,通過產品召回、無過錯責任等制度加重產品生產商、服務提供者和銷售者等相關主體的責任。眾所周知,無論是權利義務的分配、還是承擔責任的方式,實際上都是與社會經濟的發展相適應的。發展中國家的社會條件與發達國家有很大不同,其大量發生的群體性在起因、訴求,處理方式、緊迫程度、當事人能力及社會承受力方面都很難與西方國家相提并論;例如,涉及當事人生存權的勞動報酬、工作權和移民、拆遷及征地等問題與小額權利救濟不可同日而語;其中很多問題屬于社會轉型期的階段性糾紛,法律規則乃至政策不確定因素較多,往往不得不借助比司法訴訟更為直接有效的方式解決處理。
特別需要注意的是,現代集團訴訟重點是解決小額多數侵害的救濟問題,這種訴求主要來源于中產階級,屬于權利的擴大;正如許多者指出的那樣,其真正受益人并非處于社會底層的真正意義上的弱勢群體。而超大真正受到集團訴訟打擊的程度,遠比中小企業或一般的大企業要小得多。相比之下,發展中國,由于社會兩極分化程度較高,弱勢群體的生存問題顯得更為重要和緊迫。因此,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群體性訴訟的目的、訴求和形式都會有不同的體現,在司法資源短缺的情況下,其側重點和司法政策也會有許多區別。即使一些與西方國家相同的現代新型糾紛,如環境糾紛和消費糾紛等,也不能簡單采用西方國家的處理方式。例如,在產品質量方面,一些違法生產和小企業造成的危及人們生命安全(如假酒、奶粉等)、農民利益(如農藥、種子、化肥、農機等坑農事件)等損害,遠比知名企業、跨國公司的產品瑕疵產生的危害更大,對二者處理的方式也可能完全不同;對于前者采取刑事和行政制裁更為迫切,民事賠償的作用則相對較低。由于市場初建,許多領域的國家標準、行業自律乃至法律規范尚付諸闕如,企業抗風險或轉移風險的能力極低,稍遇糾紛就可能陷入破產,即使采用集團訴訟方式也很難達到充分救濟受害人和制裁違法行為的目的,并可能導致更多的糾紛連續發生,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對于侵權損害賠償不得不趨向相對較低的標準;并傾向于采用更為經濟、快捷和有效的行政執法和政府協調方式處理。
其次,社會發展程度與調整模式的關系。與發達國家法制相比較而言,發展中國家更適合采取規則出發型的模式。德國漢堡大學的沙弗爾(Schaafer)教授認為,在發達國家,法律規范的模糊性常常并無損害,相反倒對法律體制是一種好處,因為將模糊的標準轉化為詳細規則所需的信息,是由法庭以一種分散的決定程序予以收集并進行處理的。然而,這種機制要求行政和司法人員受過良好的專業訓練,擁有能在不太清晰的標準的基礎上做出精確、有效率的決定的技能和信息。但是,在很多發展中國家,這一要求常常被忽略了,而且創造適應這一要求的各項條件也是成本非常高,甚至是浪費資源。如在印度和中國這些國家,要想提高整體法律訓練和法官、公務員的訓練可能是一項非常無望和成本過高的計劃。這樣,通過法官的自由裁量及判例形成規則將會是一個成本很高的極慢的過程,并且會增加法律的不確定性和腐敗的機會。因此,他主張,在發展中國家應盡可能地運用詳細的規則,以替代模糊的法律標準(法律原則),以克服司法人員素質低的問題和法律技術和程序中的局限,并有利于防止腐敗和提高司法效率。沙弗爾指出:世界銀行業已指出:在發展中國家移植別國法律文化的進程中,接受民法典作為其民法傳統的國家較之引進普通法的國家更為成功,因為與判例相比,以系統的、法典化的規則為基礎做判決更容易一些。這似乎顯示出以系統的法典為基礎做判決更容易且更適合于發展中國家。[xx]這種見解對我們考慮集團訴訟問題應是具有啟發性的。
最后,社會發展程度與訴訟成本的關系。訴訟是糾紛解決中最為奢侈的方式,但卻未必是效果最好的方式。同時,訴訟要求國家提供充足的司法資源和法律職業的專業服務,這些需要大量的財政支出和社會負擔支撐。訴訟固然有積極的社會作用,但本質上屬于一種負價值,因此世界各國都采取一定的制度或措施限制或分流訴訟,以減少訴訟給社會造成的負擔和損失。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更應該注重采用最為經濟和合理的方式,優先處理個體當事人的訴訟主張和涉及弱勢群體生存問題的權利救濟,并注重提供更多元化的處理途徑,以降低處理的成本。其目標應該是:一方面,追求糾紛解決和權利救濟的低成本和高效益,使國民經濟收入不至于過多地消耗在訴訟之中;另一方面,應盡量減少訴訟給社會帶來的對抗和緊張,促進社會的和諧、秩序和穩定,保證社會的健康發展。總之,集團訴訟的方式應服從社會糾紛的特點及處理的需求。一般而言,多數發展中國家尚不具備整體引進美國式集團訴訟的社會條件和能力,也很少有此動議;相比之下,公益訴訟和團體訴訟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則比較容易得到社會認同。
第四,法律職業,這一要素對于集團訴訟的運行至關重要。小島武司教授指出:“人們對法曹(司法界)的信賴是集團訴訟成長的關鍵。對法官的信賴可以排除人們對廣泛且具有彈性的裁量權授予的猜疑和抵抗。對訴訟的主角——律師的信賴與對法官的信賴具有同樣的重要性。”[xxi]如前所述,對法官的信賴與司法的權限和能力問題直接有關,如果社會對司法擁有巨大裁量權的正當性和合理性缺乏認同,則集團訴訟不僅難以實現期待的社會功能,而且會給司法機關帶來巨大壓力,并給正當程序帶來無法承受的。至于律師的作用,則更是集團訴訟成敗的關鍵。其中涉及的問題極為復雜,主要是:
首先,集團訴訟存在巨大的風險、并需要付出極高的成本,如果由當事人自行承擔,則集團訴訟的利用率必然極低,對其社會功能的期待就可能落空。而如果由律師承擔集團訴訟的風險,即采用勝訴酬金方式,將對集團訴訟起到極大的激勵作用,但由此會產生一個兩難困境:如果不給予律師充分豐厚的回報,他們不僅不會積極發動集團訴訟,甚至可能成為阻礙其的力量;而如果集團訴訟獲得的賠償或補償大部分落入律師的錢袋,則其正當性就值得懷疑。
其次,集團訴訟濫用的最大可能性恰恰來自律師,不僅美國律師獲取勝訴酬金受到公眾的質疑,德國團體訴訟中律師的濫用也曾受到社會的高度警覺和抵制。因為,律師積極啟動或參與傳統的律師職業道德規范及社會公序良俗相違背,如果任其發展,就會鼓勵律師和社會的一部分人將訴訟作為生財之道,從而徹底顛覆法律程序的公平和社會正義的準則。
最后,由于律師個人的利益與集團訴訟息息相關,乃至于人們無法將其公益性、正義性與其獲利動機加以區分。一些律師以社會公益的名義發動的集團訴訟盡管并非沒有公益色彩,但也可能實際上是變相的個人宣傳和廣告;這種做法不僅破壞了傳統的律師職業倫理,也會無形中使真正的公益訴訟蒙上了可疑的色彩,這樣就難免會招致社會的懷疑與警惕……
比較法學家蓋茨認為,集團訴訟“受到歡迎是不無道理的,它是美國的法律天才們最具特色的成就,使接觸到美國法律的眾多法律專家有一種全新的感覺。但我仍舊認為脫離美國特有的環境將集體訴訟移植到歐洲,不進行相當程度的修改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這些歐洲國家只有與美國一樣建立一系列環境:(1)律師不怎么反對訴訟對象擁有管理者似的利害關系;(2)提供優厚的條件,(當事人代表)勝訴時律師可獲得很大的利益;而且(3)(當事人代表)敗訴時,也并不讓律師或集體承擔對方律師的費用,才可能使集體訴訟產生與美國同樣的效果。”[xxii]盡管作者以極其謹慎的措辭避免對美國集團訴訟的批評,但是實際上,這些問題正是美國國內對集團訴訟及其濫用的主要反對意見。而歐洲大陸國家一般法律職業自律嚴明,法律服務受到國家監控,律師攬訟和廣告宣傳被嚴加禁止;律師收費依法明碼實價。既不可能允許律師主動出擊、尋找當事人啟動集團訴訟;也絕不可能聽任勝訴酬金玷污司法活動和法律職業的清明。
勝訴酬金對于集團訴訟的激勵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雖然歐洲大陸由敗訴方承擔訴訟費用的激勵機制也具有相同的作用和意義,但是,相比之下勝訴酬金受到的道德批判異常激烈。在美國,勝訴酬金使律師受到巨大利益的有力刺激,去謀求最大數額的金錢,也造就了很多一夜成為百萬富翁的人,一些對此深惡痛絕的法學家認為,律師才是集團訴訟的最大受益者。[xxiii]從1970年代開始,美國就嘗試限制集團訴訟律師的獲酬比例,為此還進行過若干著名訴訟,由于法院最終支持律師有權按約定獲得勝訴酬金,因此,這個問題迄今并沒有任何轉機,乃至2005年集團訴訟公平法案不得不再次對此進行規范。由于這種情況客觀存在,各國對律師參與集團訴訟的權、特別是和解權限及其收費方式進行了長期的探討,曾提出過各種方案,似乎并沒有哪一個方案能夠有效地解決這一難題,然而相比之下,德國采用的由敗訴方承擔訴訟費用的方式,在同樣可以達到公平、降低“維權”成本的前提下,造成的法律職業道德危機相對小得多。
我國很多學者主張引進勝訴酬金制度,以鼓勵集團訴訟的進行。實際上,我國法律并未禁止律師采用勝訴酬金方式(即風險)訴訟,在經濟糾紛訴訟和仲裁中,這種方式甚至較為常用。然而,在一些采用風險的侵權訴訟案件中,已經出現了與其他國家類似的爭議和質疑。[xxiv]毋庸置疑,勝訴酬金具有使當事人無需承擔訴訟費用和風險、有利于弱勢群體尋求司法救濟的重要意義,但是其特有的律師獲利動機、鼓勵訴訟、違背律師職業倫理的弊端也非常明顯。在律師職業社會公信力較低的情況下,當事人和社會公眾對此的懷疑和道德批判會更加強烈。針對不同的訴訟、不同的當事人確實可以嘗試性地采用這一方式,但是如果將其作為一種以集團訴訟相聯系的制度配套采用,則必須極其謹慎。中國社會和法律職業自身之所以對勝訴酬金并沒有明顯的警惕與抵制,不僅在于其尚未在侵權訴訟中普及,更主要的是由于中國律師職業倫理本身尚未真正形成、行業自律程度較低。[xxv]然而,在社會對法律職業評價低的情況下,對勝訴酬金的腐蝕作用更應提高警惕。與其采用勝訴酬金作為集團訴訟的激勵機制,不如更多地從法律援助的角度加以建構。因為法律援助以事先審查當事人的訴訟主張是否具有勝訴可能性或合理性為前提,既有可能幫助弱勢群體獲得司法救濟,亦可能篩除、至少是不鼓勵那些不必要的訴訟。同時也可以考慮在群體訴訟中,確認強制律師制度(即將律師作為訴訟程序的必要條件),將律師費計入訴訟費用,由敗訴方承擔。
除了以上各種因素之外,集團訴訟的制度設計和運行實踐在不同的社會條件下還可能會有更多的選擇和結果。比較法學的實用功能就在于在制度建構和論證時將每一種要素加以充分的考慮和比較,對應社會需求和現實條件進行論證。
四、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集團訴訟
國際法學界清楚地認識到,集團訴訟是一個極為復雜的問題,其中體現了不同的文化、倫理、社會觀念、法律與政治價值觀、以及不同的心理因素在如何保護集體權利問題上的多方面的沖突。面對這些困難,需要更為廣闊的視野,并應尋求更有效的替代性途徑加以解決。[xxvi]而且,集團訴訟仍然處在發展過程中,其實踐結果和人們對它的認識還遠未結束。比較法視野中的集團訴訟問題應該是一種面向現實、促進法律發展和改革的研究,需要以一種動態和全局性的視角來分析其發展趨勢和。在研究集團訴訟問題時,既需要關注各國的傳統和法律文化,又需要密切注意的發展給人類社會帶來的共同挑戰和趨同的契機。在今天的經濟全球化的時代,面對共同的課題,每個國家都不能孤立地僅僅考慮國內的傳統和體制,而必須采取積極的態度參與國際合作。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集團訴訟問題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生產的集團化使得一些大規模跨國企業造成的集團害可能迅速成為世界性問題,近年來的一些涉及食品安全、醫藥安全和產品質量問題的事件,由于與跨國企業有關,幾乎牽涉到世界上每一個國家的消費領域。一些跨國界的環境污染、移民、人權保護等方面的問題,可以通過國際性或地區性合作的方式制定原則、規則、標準,創建多邊合作的處理機構和糾紛解決程序實現更有效的處理解決。一些國家行之有效的技術標準、管理措施、歸責原則、救濟方式也可以成為世界各國的共同財富,相互借鑒。例如,近年來國際消費者保護和產品責任方面的一些法律原則、規則和制度,例如產品召回、消費警示、投訴反饋機制等,已經為世界各國普遍施行。集團訴訟問題無疑也是國際合作中的一個重要領域。
其次,經濟全球化的另一種結果是一些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經常將其生產過程的危害或風險從國內向發展中國家轉嫁,使得集團害發生轉移。而由于發展中國家的標準和技術往往低于發達國家,這就事實上造成了發達國家的消費者權益、環境和勞動者權益保護程度明顯高于發展中國家的不平等結果。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平等地主張權利、尋求救濟,就成為當代世界各國需要共同努力解決的問題和法律的目標。國際社會也應該更加關注如何在增強跨國企業法律責任的同時,對發展中國家增加法律援助和支持,促進權利保護的平等,在處理解決集團害的救濟方面,相對于受害者個人或群體的努力,更應強調政府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