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生態倫理傳統啟示
時間:2022-09-13 11:14:00
導語:儒家生態倫理傳統啟示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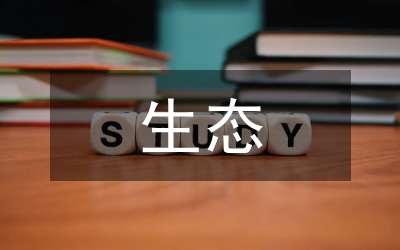
儒家的生態倫理思想,作為東方農業文明的實踐經驗和生存方式的總結,其對待人與自然關系的基本態度是正確的和可取的。與主客二分、天人對立的西方近代思想相比,儒家的生態倫理思想更符合我們這個復雜世界的真實情況,也更有利于人類正確地對待自然,從而更有益于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它能夠彌補西方科學理性的不足。就研究方法而言,研究儒家生態倫理思想,必須在現代知識的背景下,吸取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研究方法。所以,要堅持以科學的態度和研究方法去正確對待儒家生態倫理傳統。儒家生態倫理傳統的現代價值包括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克服、對科技理性過度膨脹的遏制和對可持續發展的指導等方面。
一、儒家生態倫理傳統與人類中心主義
通常,人們容易將儒家的道德擴展主義等同為一種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似乎儒家強調人類在宇宙中的最高價值,并且主張貴人賤物,一切從人的價值實現和利益滿足來對待人類之外的所有自然物。但是這種理解并不正確。
人類中心主義生態倫理觀認為我們保護生態環境是僅僅因為它們“對人類具有工具價值”。人類中心主義可以分為兩種形態,一種是歷史上那種主張征服自然、統治自然,把自然界當成滿足人類幸福的工具,可以對任何非人類的生物進行殘酷屠殺和對自然資源進行毀滅性開發的人類沙文主義;另一種則是當代那種主張理性地認識人與自然的生態關系,把自然當成滿足人類需要和利益,實現人類目的的工具,提倡合理地利用自然資源和保護自然資源,以便使自然界能夠長期滿足人類生存和發展需要的現代人類中心主義。對于前者而言,儒家的環境道德觀肯定不是這種人類中心主義,而且也堅決反對這種人類中心主義。對于后者來說,儒家的環境道德觀的確與其存在著共同之處,這就是雙方都承認人是自然進化中具有最高價值的存在,人類應該合理地利用和保護自然對象的工具價值,人類是唯一具有道德意識的存在,而且人類對待同類的道德關心應該置于最優先的地位。但是現代人類中心主義只承認人類唯一具有內在價值,而否定一切自然物具有內在價值,只把人類同胞當成道德關心的對象,否定自然物的道德客體地位,最多把對自然物的關心當成對人的關心的一種間接影響和擴展。而儒家的道德觀則與此有明顯的不同,它不只承認人類具有內在價值,應該以最高的道德強度去關心人類,同時也承認所有自然物具有內在價值,也是道德關懷的對象,除了要從人類道德擴展的意義上去關心動物、植物乃至無生命的自然物和人造物,而且還要從事物內在價值的意義上去關心自然物,尤其是對有苦樂感知能力的飛禽走獸,要從心理上去感受它們的不幸和痛苦,對其施以同情和關愛。可見,儒家的環境道德觀要比現代人類中心主義的環境倫理觀更為仁慈、寬容和博大,它比現代人類中心義的倫理觀要合理得多。
儒家的“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的道德擴展主義,對于人類將道德對象和范圍從人類自身逐步擴大到人以外的自然物,有其比較合理的現實性,而且符合人類道德進化的方向。因為儒家的道德人文主義,不只承認人類一個物種的利益和價值的人類中心主義,儒家在肯定人在自然界中具有最高價值的同時,也肯定了無機物、植物和動物在自然的進化鏈上具有高低不同的自身價值。強調要“恩及禽獸”、“節用”、“愛物”,把人類的仁愛關懷按照血緣親疏關系擴大到人類以外的自然萬物,并且以生態倫理來約束人類對自然的行為。儒家的道德擴展主義似乎確有人類中心主義的傾向,但是,儒家并非只是完全出于人類與自己關系較近的角度來考慮對動物生命的保護,它也關愛其他低等動物的生命,甚至關心非生命的存在物,如對瓦石亦有顧惜之心。如果說儒家的道德擴展主義也是一種人類中心主義的話,那么也只能算是一種程度非常微弱的人類中心主義。
從環境倫理的角度看,“贊天地之化育”這一價值論原理的提出,較好地解決了當代西方環境倫理學中人類中心主義與自然中心主義的對立。盡管人類中心主義的環境倫理觀與自然中心主義的環境倫理觀均關注人類環境的保護,但它們的理論根據與出發點是彼此對立的。從自然中心主義出發,很容易導致一種否定人類的生產實踐活動,甚至連人類致力于保護自然環境的實踐行動都會被取消的無為觀點,這客觀上并不利于自然環境的保護,也與人類保護自然環境是為了使包括人類在內的所有自然生命體都能更好地持續生存這一初衷相違背;反過來,從人類中心主義出發,盡管我們的主觀動機是為了保護和愛護自然環境,但它是一種從人類利益出發加以考慮的環境倫理,這使我們在保護自然環境的行為實踐中容易產生偏差,也就是說,它常常會使我們在環境保護行為中喪失目標和方向感。甚至,它還可能使我們在符合人類利益的要求下采取極不明智和有害自然環境的各種行為和政策。而“贊天地之化育”這一環境倫理是既非自然中心主義的,也非人類中心主義的,而是以“天—人”關系為中心的,這樣,它既考慮到自然的價值,同時也充分考慮到人類的主觀能動性與價值。在儒家看來,人類的價值就體現在它能體認到“生生之謂易”這一天道原理,并自覺地去實踐這一原理,從而實現了“天—人”關系的統一。
二、儒家生態倫理傳統與科技理性
儒家生態倫理傳統的天人合一觀具有注重價值理性的特點,這對于遏制現代人科技理性的過度膨脹,將會發揮制衡作用。
對“生生不息”這一宇宙最高原理的體悟,又稱之為“德性之知”。儒家歷來強調有兩種知識:“德性之知”與“聞見之知”,認為“德性之知”比“聞見之知”更為重要和根本。程顥說:“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聞見。”(《語錄》)張載論到“德性之知”不同于“聞見之知”時說:“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正蒙•誠明》)儒家區分“德性之知”與“聞見之知”的看法,對于我們今天科技時代人類的生存與文化發展戰略具有極大的警醒性。為什么呢?因為在今天,我們人類已經掌握了空前的征服與改造自然的能力和知識,但由此而來,我們人類也日益變得自高自大和盛氣凌人,仿佛我們人類真的已經從根本上降服了自然。我們將自然的謙遜和忍耐視為軟弱。殊不知,人類在自然面前這樣妄自尊大的結果,受害的還是人類自己。目前,人類生態環境的空前惡劣,可以說就是自然對于人類狂妄自大的一種報復。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重溫儒家關于“德性之知”與“聞見之知”的說法是有教益的。至少它可以使我們在自然面前變得謙遜。
“德性之知”的重要,首先在于它是一種關于存在的知識,這種存在的知識是對于宇宙本體的一種通觀和透徹的理解;有了這種對于宇宙本體的透徹理解,我們才能理解和獲得人類生存的意義。因此說,“德性之知”又是關于人生意義與價值的學問,它教誨我們做“人”的根本,揭示我們生活的目的與真諦。人生的目的與生存的意義何在?按照前面儒家的說法,是在“贊天地之化育”。這種“德性之知”不同于我們在平常世界中為了生存而發展出來的“聞見之知”,也不是從日常世界的“聞見之知”中可以產生的。它需要的是一種“合內外于耳目之外”的“體物”的方法。關于“體物”,張載是這樣說的:“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
世人之心,止于聞見之狹;圣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正蒙•大心》)又說:“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為人也大矣。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于身,則藐乎其卑矣。”(《正蒙•大心》)可見,所謂“體物”的方法其實就是“與物同體”,它要求我們擺脫和超出人類自身利害的考慮,平等地看待和對待自然萬物,視物為我,與物合而為一。其次,“德性之知”要求我們對現代科技文明可能帶來的弊害保持警惕和深刻的認識。科學技術無論如何發達,它本質上是一種“聞見之知”,就是說,它本身并不能提供我們關于宇宙本體以及如何“做人”的知識。不僅如此,由于科學技術是一種聞見之知,假如我們以科學為萬能,以為人類只需要有科學就夠了,那么,這對于人類的生存與發展來說都是非常危險的。因此,儒家提出“德性之知”與“聞見之知”之分,這與其是強調它們二者的對立,不如說是對囿于“聞見之知”的一種批評和提醒。張載說:“天之明莫大于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于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御,莫大于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后能。”(《正蒙•大心》)就是說,無論人的聞見之知如何廣大,總是有其局限性的,而要真正克服“聞見之知”的局限,不在擴充聞見之知,而在“盡其心”,發展人的“德性之知”。
這是對現代人一味崇拜科學,以為有了科學技術,人類的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的“科學拜物教”的最好提醒。事實上,人類為了生存和發展,需要科學技術,而且科學技術在成就人類文明方面具有巨大的貢獻。但是,科學技術畢竟是一把“雙刃劍”。實踐證明,它既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歷史上,人類運用科學技術危害人類自身的情況屢見不鮮。這就產生了一個如何控制和管理科學技術的問題。顯然,對于科學技術的控制與管理,這是一個超出了科學本身,而屬于價值論領域的問題。科學與價值具有不可分離的統一關系,因為“科學不僅僅是一種客觀知識,它同時是一種活動”。即使是科學事實也是一種價值,“每一個事實都有價值負載,而我們的每一個價值也都負載著某個事實”。海德格爾對現代科技文明進行反省時說:危險的不是技術……技術的本質存在才是唯一的危險。這里所謂“技術的本質”,就是說技術本質上是一種“聞見之知”,假如我們以這種技術的“聞見之知”代替和取代了人的存在的“德性之知”,這才是真正危險的。
在當今時代,發達國家中的一些思想家已經注意到“科技理性過度膨脹”這一社會問題。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一書中尖銳地指出,在當達工業社會里,由于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在技術控制和物欲的操縱下,只是“作為工具,作為物而存在”,變成了只有物質追求而沒有精神追求的“單向度的人”。儒家傳統倫理學特別注重價值理性,對于解決這種社會問題,可能會有所幫助。
三、儒家生態倫理傳統與中國的可持續發展
自1992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大會召開以來,可持續發展作為一種新的發展觀在世界范圍內得到了人們的認同。人們已經意識到,支撐工業文明的發展觀,以掠奪性地開發自然資源和破壞生態環境的方式來追求經濟增長,滿足人類的物質需求是錯誤的。它破壞了人類賴以長期健康生存的地球生態系統的穩定,結果導致了人類自身發展的衰退。人類要生存,就必須維護地球的自然生態基礎,使發展與環境取得協調。但是,對于不同發展水平和文化傳統的國家來說,除了對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需要協調的共識外,各國可持續發展的內涵也有所不同。中國現在的生存和發展置身于自己長期形成的生態傳統之中,即使人們忽視它的存在,它依然會或者明顯或者潛在地產生其影響和制約作用。而正視這個傳統,則有利于我們將其合理因素作為一筆寶貴的資源來使用,并自覺消除其消極影響,從而推動人與自然關系重歸和諧,促進可持續發展。對于發展中的大國中國而言,毫無疑問,可持續發展的主題當然是發展。因為不發展就不能改變人們的貧困生活狀況,而貧困也會產生嚴重的環境問題,引起生態系統的退化。
但是,我國現行的可持續發展實踐及其效果說明,我們的可持續發展道路在一定時期內并未真正擺脫西方的傳統模式,我們的發展觀還存在著嚴重的片面性。我們的可持續發展概念“并沒有根本突破現展觀的藩籬,即仍然把經濟增長當作發展的必要條件”。我們追求的是西方以工業化為基礎的現代化道路,而且是一種趕超型的現代化,環境保護只不過是服務于現代化目標的工具而已,因而必然導致“邊發展,邊污染,邊發展,邊破壞”。總的形勢當然是破壞多治理少,治理趕不上破壞,局部有所改善,而整體繼續惡化。因此,在我們的可持續發展概念中,不應該受西方的現代化目標和模式的影響,尤其不應該制定一個時間表,把屆時應達到人均GDP多少的強制性目標放在首位,由此規定每年必須平均達到的經濟增長目標。如果我們這樣繼續努力下去,我們也許根本就達不到這個目標,因為早在到達這個目標之前,我們的經濟增長就已經被環境災難和由此產生的社會代價所抵消,甚至經濟本身也因失去生態環境的支撐而無法繼續增長了。退一步說,即使我們達到了這個目標,但環境嚴重惡化,社會問題叢生,人們的生活質量反而出現了大倒退,那么這又有什么意義呢?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我們主張為了維護環境不要發展,而是說我們必須在維護生態系統不再繼續惡化并且逐步好轉的基礎上追求合理與適度的發展。這就必須在我們的可持續發展觀念中確立新的生態倫理觀。儒家傳統的生態倫理觀可視為這種新的生態倫理觀的一種哲學表達。
根據儒家的生態倫理觀,我們發展的目標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應該是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協同進化為根本方向,以維護自然生態過程,使其發揮正常的功能為先決前提,以既符合生態規律又能滿足人們健康的多樣化需求的生產技術方式為主要開發手段,并且還要以一系列的道德原則和規范來調節人們對待自然的行為。只有以新的生態倫理觀作為支撐,可持續發展才可能真正擺脫傳統的工業現代化的影響,才能在人與自然關系方面樹立健全的思想,用以指導人們解決發展實踐中的各種難題,避免由于指導思想上的片面性而導致對自然環境的嚴重破壞。從可持續發展的全球協調關系上看,儒家生態倫理傳統中樸素的自組織思想和系統思維方式,把自然界和人類社會視為一個相互作用的動態有機整體,不僅要求社會內部要協調好人與人的相互關系,而且要求人類文明適應自然的生態規律,人類活動不要超過自然系統規定的限度,以協調好人與自然的關系,這對于我們利用國際條件來促進中國和全世界的可持續發展,解決環境問題的全球性與國家利益的矛盾,也具有一定的啟發性。
拯救養育了我們人類和所有生命的大地母親并使其重返青春,是今天全人類面臨的重大使命和嚴峻挑戰。由于近代以來人類的極端自私、貪婪和無知,使地球生物圈正處于瓦解的危機之中。人類要能夠擔當起拯救大地母親這一歷史重任,就必須利用所有的文化資源,以彌合自己的知識、道德、力量與承擔這一歷史重任之間的巨大差距。儒家生態倫理傳統作為人類農業文明中最悠久、最深刻和最博大的傳統,是東方生態倫理傳統的典型。盡管這個傳統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而顯示出其嚴重的局限性,但是它在形上學、價值觀、生態倫理和思維方式等方面,至今依然具有深刻的合理因素。今天我們深入、系統地研究這個傳統,繼承且弘揚它的合理因素,摒棄其落后的方面,并在現代知識背景下來重建這個傳統,就是從歷史中吸取力量,也就是從文明之根源吸取力量。這個在現代文明的知識背景中重建起來的儒家生態倫理觀,不僅有助于中國創造性地發揮自己“天人合一”的傳統,推動自己的可持續發展事業,為全人類的可持續發展事業作出自己的巨大貢獻,而且也將有助于世界避免由工業文明跌入生態毀滅的狀態,引導人類走向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協同進化的綠色文明之未來。
- 上一篇:假如我是校長精彩演說
- 下一篇:農村綜治整頓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