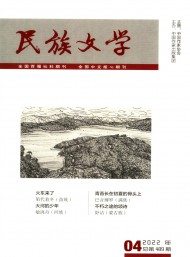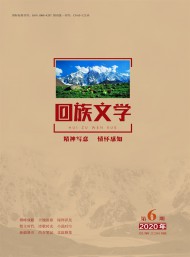文學(xué)論文范文10篇
時(shí)間:2024-01-03 00:27:31
導(dǎo)語:這里是公務(wù)員之家根據(jù)多年的文秘經(jīng)驗(yàn),為你推薦的十篇文學(xué)論文范文,還可以咨詢客服老師獲取更多原創(chuàng)文章,歡迎參考。

文學(xué)翻譯研究論文
論文關(guān)鍵詞:文學(xué)翻譯;歸化;異化
論文摘要:文學(xué)翻譯中的歸化和異化是翻譯理論研究的重要問題之一。本文從簡(jiǎn)單回顧了歸化、異化理論的生成及其演變。指出歸化和異化都是重要的翻譯策略,兩者相輔相成,對(duì)文學(xué)翻譯實(shí)踐具有重要意義。
引言
歸化與異化是文學(xué)翻譯研究中非常重要的策略.本文簡(jiǎn)單回顧歸化和異化策略在文學(xué)翻譯中應(yīng)用的歷史,從晚清時(shí)期的19世紀(jì)70年代開始的一百年歸化為主調(diào),20世紀(jì)最后20年對(duì)異化、歸化的重新思考,二十一世紀(jì)的文學(xué)翻譯:歸化和異化的繼續(xù)發(fā)展。并指出歸化和異化相輔相成,對(duì)立統(tǒng)一。譯者應(yīng)根據(jù)在翻譯中涉及的多種因素進(jìn)行取舍,創(chuàng)造高品質(zhì)的譯品。
1歸化和異化概述
直譯與意譯是歸化和異化討論的源頭。直譯和意譯是翻譯的兩種主要的方法,八十年代初,張培基等學(xué)者所編的《英漢翻譯教程》中解釋直譯(literaltranslation)為:“所謂直譯,就是在譯文語言條件許可時(shí),在譯文中既保持原文的內(nèi)容,又保持原文的形式--特別指保持原文的比喻、形象和民族、地方色彩等。但直譯不是死譯或硬譯。”……九十年代出版的翻譯教程闡釋直譯:“直譯指翻譯時(shí)要盡量保持原作的語言形式、包括用詞、句子結(jié)構(gòu)、比喻手段等等,同時(shí)要求語言流暢易懂”(范仲英1994:90)。而意譯則認(rèn)為語言有不同的文化內(nèi)涵和表達(dá)形式,當(dāng)形式成為翻譯的障礙時(shí),就要采取意譯。翻譯的歸化/異化概念直接來源于1813年德國學(xué)者Schleiermacher(施萊爾馬赫)《論翻譯的方法》一文,文章指出翻譯有兩種途徑,一種是引導(dǎo)讀者靠近作者,另一種是引導(dǎo)作者靠近讀者。但并未授以具體名稱。1995年美國學(xué)者L.Venuti的《譯者的隱形》定義這兩種方法為異化/歸化。Venuti是異化派翻譯的代表。他提出“反翻譯”的概念。指出翻譯的風(fēng)格和其他方面在目的語的文本中要突出原文之“異”。他說:“反對(duì)英美傳統(tǒng)的歸化,主張異化的翻譯,是要發(fā)展一種抵御以目的語文化價(jià)值觀占主導(dǎo)地位的翻譯理論和實(shí)踐,以表現(xiàn)外國文本在語言和文化上的差異。”(郭建中1999:192-193)在討論異化翻譯時(shí),他對(duì)歸化翻譯的策略作出了描述:遵守目標(biāo)語文化當(dāng)前的主流價(jià)值觀,公然對(duì)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從而達(dá)到讓譯文符合本土典律、出版潮流和政治的需求。歸化翻譯的最大特點(diǎn)就是采用流暢地道的英語進(jìn)行翻譯,在這類翻譯中,翻譯者的努力被流暢的譯文所掩蓋,譯者為之隱形,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也被掩蓋,目的語主流文化價(jià)值觀取代了譯入語文化價(jià)值觀,原文的陌生感已被淡化,譯作由此而變得透明。從后殖民理論吸取營養(yǎng)的異化翻譯策略則將歸化翻譯視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和征服的共謀,是文化霸權(quán)主義的表現(xiàn)。所以,Venuti提倡異化的翻譯策略。美國翻譯家奈達(dá)(Nida)是“歸化”理論的推崇者,他提出了“功能對(duì)等”和“讀者反映論”的觀點(diǎn)。在各種不同場(chǎng)合,他重復(fù)“最切近的自然對(duì)等”概念這一觀點(diǎn),既“譯文基本上應(yīng)是源語信息最貼近的自然對(duì)等”。“歸化派”認(rèn)為,不應(yīng)該將源語中的語言體系和文化現(xiàn)象強(qiáng)加在譯文讀者身上;文化差異必然帶來交流和理解上的障礙,既然翻譯的主要任務(wù)是文化交流和傳播,就應(yīng)該避免文化障礙,而“異化”則不可避免地帶來這種障礙;對(duì)譯文讀者的想象力和智力也不應(yīng)該有過高要求,而是應(yīng)該將源語以最貼近目的語的形式呈現(xiàn)給譯文讀者,使之理解起來更容易。
文學(xué)翻譯研究論文
一文學(xué)翻譯及其變異現(xiàn)象
文學(xué)翻譯首先必須明確什么是文學(xué)。綜合中外論者對(duì)文學(xué)一詞的闡釋,我們知道文學(xué)具有以下主要特性:文學(xué)是語言的藝術(shù),是用語言來反映生活、反映現(xiàn)實(shí)、表達(dá)思想、抒發(fā)情感的,是emotion-centered;它有審美價(jià)值,其語篇功能主要是用藝術(shù)的語言敘事、畫物、言情,達(dá)到感染人、娛悅?cè)恕⒔逃说哪康摹N膶W(xué)的這些特性也是它有別于其它文體的地方。要說清楚文學(xué)是什么雖然不易,但人們卻能很容易地告訴你:小說、詩歌、散文、戲劇、影視等是文學(xué)。如此說來,文學(xué)語言就該是這些文學(xué)作品的語言,文學(xué)文體也就該是這些文體的總和。盡管小說、詩歌、散文、戲劇、影視中又能分出各種流派、各種風(fēng)格的作家作品,但我們的注意力這里主要集中在英語各體類之間的文學(xué)共性的東西,即小說、詩歌、散文、戲劇、影視的語言特征及其翻譯。
長(zhǎng)期以來,文學(xué)翻譯一直被認(rèn)為是派生的、模仿性的、第二位的文學(xué)形式,處于文學(xué)研究的邊緣,極少受到文學(xué)研究者和文學(xué)史家應(yīng)有的重視。評(píng)論文學(xué)翻譯的標(biāo)準(zhǔn)大多是先驗(yàn)性的,重原文文本輕譯文文本。20世紀(jì)70年代以后,人們開始對(duì)先驗(yàn)性的“等值”標(biāo)準(zhǔn)提出質(zhì)疑;描述性的、動(dòng)態(tài)的翻譯研究應(yīng)運(yùn)而生。人們不再用“等值”、“正誤”、“好壞”、“對(duì)錯(cuò)”等標(biāo)準(zhǔn)來評(píng)判翻譯文本,而是將翻譯文本中出現(xiàn)的“差異、謬誤、摸棱兩可、多元指涉,以及‘異質(zhì)’的混亂”視作“文化意識(shí)形態(tài)直接影響特定文學(xué)抉擇的寶貴資源”。
研究文學(xué)翻譯的變異現(xiàn)象,首先要給文學(xué)翻譯的常規(guī)與變異下一個(gè)定義.從社會(huì)學(xué)的角度看,文學(xué)翻譯活動(dòng)首先是一種社會(huì)性的活動(dòng),與社會(huì)學(xué)中行為規(guī)范的功能類似。文學(xué)翻譯的常規(guī)是用來辨別合適的或不合適的翻譯行為的準(zhǔn)則和標(biāo)準(zhǔn).它由具體的文學(xué)翻譯的原則、標(biāo)準(zhǔn)、過程、方法等理論組成.與社會(huì)學(xué)中的越軌行為一樣,文學(xué)翻譯的變異是指違背了文學(xué)翻譯常規(guī)的翻譯行為或活動(dòng)和不恰當(dāng)?shù)氖褂梅g技巧等行為.文學(xué)翻譯作品中的變異現(xiàn)象表現(xiàn)為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程度.由此更是增加了文學(xué)翻譯的難度。
三、文學(xué)翻譯中的變異現(xiàn)象及其文體效果
文體學(xué)和文學(xué)緊密相關(guān),一直被用來分析和評(píng)價(jià)文學(xué)作品。同時(shí)它也是翻譯工作者的必修課,翻譯工作者具有文體學(xué)知識(shí)將有助于發(fā)現(xiàn)原文的特色,從而忠實(shí)地翻譯原文。
文學(xué)傳統(tǒng)研究論文
關(guān)鍵字: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現(xiàn)代性
我們所即將告別的20世紀(jì)文學(xué),將會(huì)為源遠(yuǎn)流長(zhǎng)的中國文學(xué)史留下什么?換言之,這個(gè)世紀(jì)的文學(xué)在浩浩中國文學(xué)史長(zhǎng)河中將占據(jù)怎樣的位置和作出怎樣的貢獻(xiàn)?這是近十多年來文壇關(guān)注的焦點(diǎn)之一。一些學(xué)者于1985年提出“20世紀(jì)中國文學(xué)”概念,試圖把一向從屬于政治劃分的中國現(xiàn)代和當(dāng)代文學(xué)統(tǒng)合起來研究,引起學(xué)術(shù)界的廣泛關(guān)注。然而,這并不表明20世紀(jì)中國文學(xué)研究趨于終結(jié),而只是掀開了新的一頁。因?yàn)閺哪菚r(shí)以來,人們關(guān)于“20世紀(jì)中國文學(xué)”的討論連綿不絕,形成雜語喧嘩局面。我們?cè)谶@里也只是想從中國文化的現(xiàn)代性這個(gè)特定角度,加入到這場(chǎng)有關(guān)20世紀(jì)中國文學(xué)及其相關(guān)問題的世紀(jì)末喧嘩之中,提出別一種觀察,以就教于方家。
一
中國文化的現(xiàn)代性或現(xiàn)代化,是在現(xiàn)代進(jìn)行的一項(xiàng)長(zhǎng)期而根本的“工程”。這種“現(xiàn)代性工程”(projectofmodernity)起于何時(shí)?學(xué)術(shù)界有不同意見。我們雖然認(rèn)為它根源于中國文化內(nèi)部的種種因素的長(zhǎng)期復(fù)雜作用和演化,但在作具體劃分時(shí),還是不得不把目光沉落到1840年鴉片戰(zhàn)爭(zhēng)這個(gè)影響深遠(yuǎn)的重大歷史事變上。我們所謂現(xiàn)代性工程,大體以鴉片戰(zhàn)爭(zhēng)為明顯的標(biāo)志性開端,指從那時(shí)以來至今中國社會(huì)告別衰敗的古典帝制而從事現(xiàn)代化、以便獲得現(xiàn)代性的過程,這個(gè)過程涉及中國的政治、經(jīng)濟(jì)、法律、教育、宗教、學(xué)術(shù)、審美與藝術(shù)等幾乎方方面面。當(dāng)這個(gè)閉關(guān)自守的“老大帝國”在西方炮艦的猛烈轟擊下急劇走向衰敗時(shí),按西方先進(jìn)的現(xiàn)代化指標(biāo)去從事現(xiàn)代化,“師夷長(zhǎng)技以制夷”,似乎就成了它的唯一選擇。確實(shí),面對(duì)李鴻章所謂“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的古典“中心”地位和幻覺都遭到了致命一擊,只能脫離傳統(tǒng)舊軌而邁上充滿誘惑而又艱難的現(xiàn)代化征程,以便使這“老大帝國”一變而為“少年中國”或“新中國”。李伯元在小說《文明小史》(1903—1905)楔子里,就把走向現(xiàn)代化的“新中國”比作日出前的“晨曦”和風(fēng)雨欲來的“天空”:“諸公試想:太陽未出,何以曉得他就要出?大雨未下,何以曉得他就要下?其中卻有一個(gè)緣故。這個(gè)緣故,就在眼前。只索看那潮水,聽那風(fēng)聲,便知太陽一定要出,大雨一定要下,這有甚么難猜的?做書的人,因此兩番閱歷,生出一個(gè)比方,請(qǐng)教諸公:我們今日的世界,到了甚么時(shí)候了?有個(gè)人說:‘老大帝國,未必轉(zhuǎn)老還童。’又一個(gè)說:‘幼稚時(shí)代,不難由少而壯。’據(jù)在下看起來,現(xiàn)在的光景,卻非幼稚,大約離著那太陽要出,大雨要下的時(shí)候,也就不遠(yuǎn)了”。這里可以說同時(shí)展示了中國眼前的衰敗景致和即將到來而又朦朧的現(xiàn)代化美景。現(xiàn)代化(modernization),在這里就是指中國社會(huì)按照在西方首先制定而后波及全世界的現(xiàn)代性指標(biāo)去從事全面而深刻的社會(huì)轉(zhuǎn)型的過程。而相應(yīng)地,現(xiàn)代性(modernity)則是指中國通過現(xiàn)代化進(jìn)程所獲得的或產(chǎn)生的屬于現(xiàn)代的性質(zhì)和特征。
要在這個(gè)具有數(shù)千年文化傳統(tǒng)的“老大帝國”實(shí)施空前宏大而艱巨的現(xiàn)代性工程,必然會(huì)牽涉到方方面面。對(duì)此,原可以從不同角度加以分析。在這里,我們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只能選取一種特定角度。在我們看來,中國的現(xiàn)代性問題,可以從中國文化對(duì)于其在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所遭遇的種種挑戰(zhàn)的應(yīng)戰(zhàn)行動(dòng)角度去考慮。在這個(gè)意義上,現(xiàn)代化意味著被迫納入現(xiàn)代化進(jìn)程的中國舊體制經(jīng)受一系列尖銳、嚴(yán)酷而持久的挑戰(zhàn),如產(chǎn)生“道”與“器”、專制與民主、巫術(shù)與科學(xué)、科舉與教育、王法與法律、傳統(tǒng)思維與現(xiàn)代思維等等劇烈而持久的沖突。有挑戰(zhàn),就不得不有應(yīng)戰(zhàn)。應(yīng)戰(zhàn)就是面對(duì)挑戰(zhàn)而采取必要的應(yīng)對(duì)措施,在現(xiàn)代性內(nèi)部的種種沖突中嘗試和尋找適合于自己的現(xiàn)代化道路。因此,可以說,中國的現(xiàn)代性集中而明顯地體現(xiàn)在面對(duì)現(xiàn)代化過程的種種挑戰(zhàn)而顯示的應(yīng)戰(zhàn)行動(dòng)上。這就需要我們從挑戰(zhàn)性課題與應(yīng)戰(zhàn)行動(dòng)的角度去理解現(xiàn)代性所牽涉的種種復(fù)雜問題。
大體說來,現(xiàn)代性涉及這樣一些主要方面:其一為科技現(xiàn)代性,主要體現(xiàn)為如何師法西方現(xiàn)代科學(xué)和技術(shù)而建立中國的現(xiàn)代科學(xué)和技術(shù)體制,并且在這種現(xiàn)代科學(xué)和技術(shù)體制參照下重新激活中國古典科學(xué)和技術(shù)傳統(tǒng);其二為政體現(xiàn)代性,要求把奉行天下一體的古典帝制轉(zhuǎn)變?yōu)楝F(xiàn)代世界格局中的一個(gè)“民族國家”(nation-state),這引發(fā)種種政體變革;其三為思維現(xiàn)代性,涉及古典宇宙觀與現(xiàn)代宇宙觀、中國哲學(xué)與西方哲學(xué)、中國思維與西方思維等沖突及其解決上;其四為道德現(xiàn)代性,要確立中國人的現(xiàn)代道德規(guī)范,涉及人際交往、禮儀、感情、戀愛和婚姻等方面,如破除“三從四德”、“三綱五常”,規(guī)定個(gè)人、戀愛和婚姻自由及社會(huì)義務(wù)等;其五為教育現(xiàn)代性,意味著借鑒西方教育制度而在中國建立現(xiàn)代教育制度以取代衰落的中國古典教育制度(但后者作為傳統(tǒng)仍有其生命力);其六為法律現(xiàn)代性,要求把古典王法轉(zhuǎn)變?yōu)楝F(xiàn)代法治;其七為學(xué)術(shù)現(xiàn)代性,即把古代學(xué)術(shù)體制翻轉(zhuǎn)為以西方學(xué)術(shù)體制為樣板的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體制,涉及從學(xué)術(shù)觀念、學(xué)術(shù)思維、治學(xué)方式到學(xué)術(shù)機(jī)構(gòu)等一系列根本性轉(zhuǎn)變,如從古典文史哲到現(xiàn)代文學(xué)、歷史、哲學(xué)和美學(xué)等;其八為審美現(xiàn)代性,表現(xiàn)在從古典審美—藝術(shù)觀到現(xiàn)代審美—藝術(shù)觀的轉(zhuǎn)變、面對(duì)新的現(xiàn)代生活的審美表現(xiàn)能力、及如何借鑒西方藝術(shù)樣式如文學(xué)、繪畫、電影、音樂、舞蹈和戲劇等方面;其九為語言現(xiàn)代性,主要指漢語現(xiàn)代性,體現(xiàn)在從古代漢語到現(xiàn)代漢語的轉(zhuǎn)變中,如現(xiàn)代白話文取代古代文言文和古代白話文。可以說,這僅僅是不完全列舉;同時(shí),其中任何一個(gè)方面都需要運(yùn)用專業(yè)知識(shí)去作專門論述,而在這里由于個(gè)人能力和興趣所限是不可能的。我們只能討論與我們的論題密切相關(guān)的后兩方面——即審美現(xiàn)代性和漢語現(xiàn)代性。
文學(xué)論爭(zhēng)分析論文
新中國成立后,美學(xué)界、文藝?yán)碚摻缇汀靶蜗笏季S”問題展開過兩次大規(guī)模的論爭(zhēng)。第一次是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歷時(shí)十年左右;第二次是七十年代末期至八十年代中期,持續(xù)了七、八年時(shí)間。兩次論爭(zhēng)的時(shí)代背景、知識(shí)背景不同,但理論使命相似,即探討“形象思維”是不是獨(dú)立于并相對(duì)于抽象思維(邏輯思維)的另一種思維形式?“形象思維”是不是藝術(shù)創(chuàng)造的特殊規(guī)律?前一個(gè)問題帶有濃厚的哲學(xué)尤其是認(rèn)識(shí)論色彩,后一個(gè)問題則試圖探討美學(xué)尤其是藝術(shù)創(chuàng)造心理學(xué)的真諦。
一個(gè)來自異域的美學(xué)觀念(第一次論爭(zhēng):1955—1966)
中國第一次關(guān)于“形象思維”問題的論爭(zhēng),發(fā)生在本世紀(jì)50年代中、后期。這是一個(gè)特殊的歷史時(shí)段,冷戰(zhàn)的國際格局,規(guī)約了中國對(duì)外部世界的基本態(tài)度,也嚴(yán)峻地影響并規(guī)約了當(dāng)時(shí)中國的學(xué)術(shù)界、思想界,促使他們?cè)趯W(xué)理價(jià)值取向方面趨于單一,思想資料來源過于偏枯。現(xiàn)在回顧中國當(dāng)時(shí)那場(chǎng)關(guān)于“形象思維”問題的論爭(zhēng),就會(huì)發(fā)現(xiàn)它實(shí)際上只是前蘇聯(lián)關(guān)于同一問題論爭(zhēng)的移植和接續(xù)。
“形象思維”作為詩或藝術(shù)定義,出現(xiàn)于1838-1840年間的俄羅斯思想界。前蘇聯(lián)文藝?yán)碚摻缫话阏J(rèn)為:俄羅斯批評(píng)家別林斯基發(fā)表于《莫斯科觀察家》1838年7月號(hào)上的(《<馮維辛全集>和扎果斯金的<猶里·米洛斯拉夫斯基>》一文里,首次提出“詩是寓于形象的思維”這個(gè)定義。實(shí)際上,他在前一個(gè)月發(fā)表于同一刊物的書評(píng)《伊凡·瓦年科講述的<俄羅斯童話>》里已經(jīng)提到這個(gè)定義了。兩年后,別林斯基在《藝術(shù)的觀念》(1840年)中對(duì)這個(gè)定義展開論述,將“詩”改為“藝術(shù)”,即“藝術(shù)是寓于形象的思維”。別林斯基還曾加注說明,在俄文中是他第一個(gè)使用這個(gè)定義。[1]
別林斯基藝術(shù)定義的思想之源,可以追蹤到黑格爾關(guān)于藝術(shù)是理念的感性顯現(xiàn)的美學(xué)思想。黑格爾認(rèn)為:“就藝術(shù)美來說的理念,并不是專就理念本身來說的理念,而是化為符合現(xiàn)實(shí)的具體形象,而且與現(xiàn)實(shí)結(jié)合成為直接的妥貼的統(tǒng)一體的那種理念。”[2]因此,黑格爾關(guān)于美的基本定義就是一句話:“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xiàn)。”研究別林斯基的學(xué)者認(rèn)為:1836年末到1840年這段時(shí)期,是別林斯基的精神探索期。這期間他崇拜黑格爾。[3]所以別林斯基1838到1840年間把“形象思維”作為詩乃至藝術(shù)定義,可以理解為德國哲學(xué)家黑格爾美學(xué)思想的俄文版本。
“形象思維”觀念誕生后整整一個(gè)世紀(jì)的時(shí)間里,沒有引起非議。但是,本世紀(jì)50年代末60年代初,前蘇聯(lián)文藝界在創(chuàng)作上出現(xiàn)了粉飾現(xiàn)實(shí)的傾向,相應(yīng)的在理論上提出了“無沖突論”的觀點(diǎn)。這種創(chuàng)作上和理論上的錯(cuò)誤傾向和觀點(diǎn),促使當(dāng)時(shí)的蘇聯(lián)美學(xué)家和文藝?yán)碚摷宜伎迹壕烤故裁词俏膶W(xué)藝術(shù)的特性正是在思考和闡釋文學(xué)藝術(shù)的根本性質(zhì)問題,尋找藝術(shù)區(qū)別于其他意識(shí)形式的主要特征,使藝術(shù)沿著藝術(shù)自身規(guī)律健康發(fā)展的時(shí)候,前蘇聯(lián)文化界圍繞別林斯基關(guān)于“形象思維”的觀點(diǎn),展開了一場(chǎng)深入持久的理論論爭(zhēng)。
文學(xué)畢業(yè)論文-民間文學(xué)的特征
畢業(yè)論文
畢業(yè)論文
民間文學(xué)作為一個(gè)學(xué)術(shù)名詞,是“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之后才出現(xiàn)和流行的。它指的是:廣大勞動(dòng)人民的語言藝術(shù)──人民的口頭創(chuàng)作。這種文學(xué),包括散文的神話、民間傳說、民間故事,韻文的歌謠、長(zhǎng)篇敘事詩以及小戲、說唱文學(xué)、諺語、謎語等體裁的民間作品。
民間文學(xué)一般認(rèn)為有下列幾種特征:
一、口頭性
由于在過去漫長(zhǎng)的歷史時(shí)期中,廣大勞動(dòng)人民,包括他們的專業(yè)藝人或半專業(yè)藝人,被排斥在文字使用之外,因此,他們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一般只能用口頭語言,甚至還用地方土語方言去構(gòu)思、表現(xiàn)(包括演出)和傳播。現(xiàn)在新社會(huì)的人民,雖然大多數(shù)已經(jīng)認(rèn)識(shí)文字,并且有的還能使用它,但不少的場(chǎng)合,他們?nèi)匀灰每陬^語言歌詠或講述,而且,它要取得民間文學(xué)(新民間文學(xué))的資格,必須基本上采用廣大人民熟悉的、千百年來民間傳承的文學(xué)形式,如故事、歌謠等,并且能夠在群眾口頭上流傳。因此,口頭性──用口頭語言創(chuàng)作和傳播是民間文學(xué)的一個(gè)主要特征。
文學(xué)場(chǎng)邏輯與文學(xué)觀分析論文
要討論當(dāng)代西方思想家,對(duì)于治文學(xué)的人來說可能有著更便利的條件。因?yàn)楫?dāng)代西方許多哲人,在提出一個(gè)個(gè)自成一格的話語系統(tǒng)的同時(shí),總是不約而同地傾向于把文學(xué)或藝術(shù)當(dāng)成自己的殖民地。伊格爾頓不無譏諷地說:"當(dāng)哲學(xué)家變成實(shí)證哲學(xué)家的工具時(shí),美學(xué)就可以用來拯救思想了。哲學(xué)強(qiáng)有力的主題被某種具體、純粹、斤斤計(jì)較的理論所排遣,現(xiàn)在正變得無家可歸,四處漂泊,它們尋求著一片蔽身的瓦頂,終至在藝術(shù)的話語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這當(dāng)然是事情的一方面。但從策略的角度來看,至少對(duì)于我們即將要討論的布迪厄來說,文學(xué)藝術(shù)之所以容易成為思想家所關(guān)注的寵兒,可能還因?yàn)樽鳛榫瘳F(xiàn)象,文學(xué)藝術(shù)具有更普遍的可通約性。一種理論,倘若能在對(duì)文學(xué)藝術(shù)的分析中站得住腳,在其他領(lǐng)域中也許就顯得是不言而喻的了。更何況文學(xué)藝術(shù)在人類社會(huì)中又有類乎廣告效應(yīng)那么強(qiáng)大的影響力。
盡管主要身份是社會(huì)學(xué)家的布迪厄在原則上反對(duì)建立一種普遍性元話語,然而,他的確在事實(shí)上創(chuàng)造了一整套話語系統(tǒng),并將它令人咋舌地運(yùn)用在農(nóng)民、失業(yè)、教育、法律、科學(xué)、階級(jí)、政治、宗教、體育、語言、住房、婚姻、知識(shí)分子、國家制度等極為廣闊的領(lǐng)域里,而他特別留意的對(duì)象之一,似乎是文學(xué)藝術(shù)。他不僅在許多著作中屢屢提及文學(xué)藝術(shù),而且還專門寫了幾部專著如《區(qū)隔:趣味判斷的社會(huì)批判》、《藝術(shù)之戀:歐洲藝術(shù)博物館及其觀眾》、《藝術(shù)的法則:文學(xué)場(chǎng)的發(fā)生和結(jié)構(gòu)》、《文化生產(chǎn)場(chǎng):論藝術(shù)和文學(xué)》等等。要紹介布迪厄的文學(xué)理論,我們可能會(huì)有一種浩浩茫茫不知從何處說起的慨嘆,因?yàn)椴际蠋缀鯖]有遺漏文學(xué)社會(huì)學(xué)的任何一個(gè)重要領(lǐng)域,但是,正如上述書名所暗示的那樣,文學(xué)場(chǎng)顯然是布迪厄文學(xué)理論的一個(gè)關(guān)鍵詞。正是通過文學(xué)場(chǎng)的概念,布迪厄的文學(xué)理論才得以清楚的表述。所以,不妨讓我們從文學(xué)場(chǎng)開始說起。
一、為什么是文學(xué)場(chǎng)?
布迪厄自認(rèn)獨(dú)擅勝場(chǎng),并得到了一些學(xué)者贊同的學(xué)術(shù)閃光點(diǎn)之一是,他超越了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經(jīng)驗(yàn)研究和理論研究、內(nèi)部閱讀與外部閱讀、存在主義與結(jié)構(gòu)主義等之間的二元對(duì)立。具體到文學(xué)研究領(lǐng)域,布迪厄認(rèn)為,主觀主義或本質(zhì)主義的文學(xué)分析方法,諸如浪漫主義者基于卡理斯瑪意識(shí)形態(tài),將作者視為獨(dú)創(chuàng)者;新批評(píng)派之類的形式主義者沉迷于文本的形式之中,將陌生化等形式因素視為文學(xué)性的一般特質(zhì);實(shí)證主義者相信經(jīng)驗(yàn)數(shù)據(jù)的科學(xué)性,把賴以統(tǒng)計(jì)的分類范疇當(dāng)成文學(xué)事實(shí)的自在范疇;薩特在傳記材料中尋求作者的個(gè)人特性,并將它與文學(xué)作品中所呈現(xiàn)的特性混為一談;弗洛伊德或榮格借助于俄狄浦斯情結(jié)或集體無意識(shí)來解釋文學(xué)的本質(zhì);而福科則拒絕在話語場(chǎng)之外發(fā)現(xiàn)文學(xué)發(fā)生的解釋原則;……凡此種種,都不同程度地把文學(xué)觀念、文學(xué)實(shí)踐和文學(xué)作品當(dāng)作理所當(dāng)然的現(xiàn)實(shí)加以接受,而完全忽視了這種現(xiàn)實(shí)在人的頭腦中賴以構(gòu)成的社會(huì)條件和歷史條件。另一方面,一些馬克思主義者,例如盧卡契或者以發(fā)生學(xué)結(jié)構(gòu)主義者自命的戈德曼,則完全無視文學(xué)自身相對(duì)獨(dú)立的形式特性,無視作家作為能動(dòng)者在文學(xué)生產(chǎn)中對(duì)于文學(xué)意義的塑造,而將作者簡(jiǎn)化為某個(gè)社會(huì)集團(tuán)的無意識(shí)人,將文學(xué)的發(fā)生發(fā)展簡(jiǎn)化為政治經(jīng)濟(jì)力量的直接作用。
布迪厄超越二元對(duì)立的理論工具是場(chǎng)域、資本和習(xí)性(habitus,或譯慣習(xí))諸概念。就文學(xué)而言,布迪厄使用了文學(xué)場(chǎng)或者文化生產(chǎn)場(chǎng)的概念。一方面,文學(xué)場(chǎng)在作為元場(chǎng)域的權(quán)力場(chǎng)中居于被支配地位,也就是說,歸根到底,還是要受到政治經(jīng)濟(jì)因素的制約;另一方面,文學(xué)場(chǎng)可以被描述為獨(dú)立于政治、經(jīng)濟(jì)之外,具有自身運(yùn)行法則,具有相對(duì)自主性的封閉的社會(huì)宇宙。這說起來很有點(diǎn)類似于阿爾都塞對(duì)于經(jīng)濟(jì)基礎(chǔ)和上層建筑之間關(guān)系的表述。但是,對(duì)于布迪厄來說,文學(xué)場(chǎng)的隱喻不僅僅是對(duì)于文學(xué)與宏觀的社會(huì)世界之間互動(dòng)關(guān)系的一個(gè)闡釋工具,重要的是,它還是超越上述二元對(duì)立、反對(duì)本質(zhì)主義文學(xué)觀的一種敘事框架,同時(shí)也是理解文學(xué)的本質(zhì)、文學(xué)作品的形式與內(nèi)容,文學(xué)家的文學(xué)觀與創(chuàng)作軌跡,文學(xué)史的發(fā)展與變革,文學(xué)的生產(chǎn)和消費(fèi)等等幾乎重大的文學(xué)理論的問題。當(dāng)然,還需要提上一筆的是,他的文學(xué)場(chǎng)的理論主要關(guān)注的文學(xué)事實(shí)是近世以來逐漸獲得文學(xué)自主性的文學(xué)現(xiàn)象,換句話說,前資本主義的文學(xué)實(shí)踐基本上不在他考察的范圍之內(nèi)。
二、什么是文學(xué)場(chǎng)?
文學(xué)硬譯研究論文
聽說《新月》月刊團(tuán)體里的人們?cè)谡f,現(xiàn)在銷路好起來了。這大概是真的,以我似的交際極少的人,也在兩個(gè)年青朋友的手里見過第二卷第六七號(hào)的合本。順便一翻,是爭(zhēng)“言論自由”的文字和小說居多。近尾巴處,則有梁實(shí)秋先生的一篇《論魯迅先生的“硬譯”》,以為“近于死譯”。而“死譯之風(fēng)也斷不可長(zhǎng)”,就引了我的三段譯文,以及在《文藝與批評(píng)》的后記里所說:“但因?yàn)樽g者的能力不夠,和中國文本來的缺點(diǎn),譯完一看,晦澀,甚而至于難解之處也真多;倘將仂句拆下來呢,又失了原來的語氣。在我,是除了還是這樣的硬譯之外,只有束手這一條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讀者還肯硬著頭皮看下去而已”這些話,細(xì)心地在字旁加上圓圈,還在“硬譯”兩字旁邊加上套圈,于是“嚴(yán)正”地下了“批評(píng)”道:“我們‘硬著頭皮看下去’了,但是無所得。‘硬譯’和‘死譯’有什么分別呢?”新月社的聲明中,雖說并無什么組織,在論文里,也似乎痛惡無產(chǎn)階級(jí)式的“組織”,“集團(tuán)”這些話,但其實(shí)是有組織的,至少,關(guān)于政治的論文,這一本里都互相“照應(yīng)”;關(guān)于文藝,則這一篇是登在上面的同一批評(píng)家所作的《文學(xué)是有階級(jí)性的嗎?》的余波。在那一篇里有一段說:“……但是不幸得很,沒有一本這類的書能被我看懂。……最使我感得困難的是文字,……簡(jiǎn)直讀起來比天書還難。……現(xiàn)在還沒有一個(gè)中國人,用中國人所能看得懂的文字,寫一篇文章告訴我們無產(chǎn)文學(xué)的理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字旁也有圓圈,怕排印麻煩,恕不照畫了。總之,梁先生自認(rèn)是一切中國人的代表,這些書既為自己所不懂,也就是為一切中國人所不懂,應(yīng)該在中國斷絕其生命,于是出示曰“此風(fēng)斷不可長(zhǎng)”云。別的“天書”譯著者的意見我不能代表,從我個(gè)人來看,則事情是不會(huì)這樣簡(jiǎn)單的。第一,梁先生自以為“硬著頭皮看下去”了,但究竟硬了沒有,是否能夠,還是一個(gè)問題。以硬自居了,而實(shí)則其軟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種特色。第二,梁先生雖自來代表一切中國人了,但究竟是否全國中的最優(yōu)秀者,也是一個(gè)問題。這問題從《文學(xué)是有階級(jí)性的嗎?》這篇文章里,便可以解釋。Proletary這字不必譯音,大可譯義,是有理可說的。但這位批評(píng)家卻道:“其實(shí)翻翻字典,這個(gè)字的涵義并不見得體面,據(jù)《韋白斯特大字典》,Proletary的意思就是:Acitizenofthelowestclasswhoservedthestatenotwithproperty,butonlybyhavingchildren。……普羅列塔利亞是國家里只會(huì)生孩子的階級(jí)!(至少在羅馬時(shí)代是如此)”其實(shí)正無須來爭(zhēng)這“體面”,大約略有常識(shí)者,總不至于以現(xiàn)在為羅馬時(shí)代,將現(xiàn)在的無產(chǎn)者都看作羅馬人的。這正如將Chemie譯作“舍密學(xué)”,讀者必不和埃及的“煉金術(shù)”混同,對(duì)于“梁”先生所作的文章,也決不會(huì)去考查語源,誤解為“獨(dú)木小橋”竟會(huì)動(dòng)筆一樣。連“翻翻字典”(《韋白斯特大字典》!)也還是“無所得”,一切中國人未必全是如此的罷。二但于我最覺得有興味的,是上節(jié)所引的梁先生的文字里,有兩處都用著一個(gè)“我們”,頗有些“多數(shù)”和“集團(tuán)”氣味了。自然,作者雖然單獨(dú)執(zhí)筆,氣類則決不只一人,用“我們”來說話,是不錯(cuò)的,也令人看起來較有力量,又不至于一人雙肩負(fù)責(zé)。然而,當(dāng)“思想不能統(tǒng)一”時(shí),“言論應(yīng)該自由”時(shí),正如梁先生的批評(píng)資本制度一般,也有一種“弊病”。就是,既有“我們”便有我們以外的“他們”,于是新月社的“我們”雖以為我的“死譯之風(fēng)斷不可長(zhǎng)”了,卻另有讀了并不“無所得”的讀者存在,而我的“硬譯”,就還在“他們”之間生存,和“死譯”還有一些區(qū)別。我也就是新月社的“他們”之一,因?yàn)槲业淖g作和梁先生所需的條件,是全都不一樣的。那一篇《論硬譯》的開頭論誤譯勝于死譯說:“一部書斷斷不會(huì)完全曲譯……部分的曲譯即使是錯(cuò)誤,究竟也還給你一個(gè)錯(cuò)誤,這個(gè)錯(cuò)誤也許真是害人無窮的,而你讀的時(shí)候究竟還落個(gè)爽快。”末兩句大可以加上夾圈,但我卻從來不干這樣的勾當(dāng)。我的譯作,本不在博讀者的“爽快”,卻往往給以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氣悶,憎惡,憤恨。讀了會(huì)“落個(gè)爽快”的東西,自有新月社的人們的譯著在:徐志摩先生的詩,沈從文,凌叔華先生的小說,陳西瀅(即陳源)先生的閑話,梁實(shí)秋先生的批評(píng),潘光旦先生的優(yōu)生學(xué),還有白璧德先生的人文主義。所以,梁先生后文說:“這樣的書,就如同看地圖一般,要伸著手指來尋找句法的線索位置”這些話,在我也就覺得是廢話,雖說猶如不說了。是的,由我說來,要看“這樣的書”就如同看地圖一樣,要伸著手指來找尋“句法的線索位置”的。看地圖雖然沒有看《楊妃出浴圖》或《歲寒三友圖》那么“爽快”,甚而至于還須伸著手指(其實(shí)這恐怕梁先生自己如此罷了,看慣地圖的人,是只用眼睛就可以的),但地圖并不是死圖;所以“硬譯”即使有同一之勞,照例子也就和“死譯”有了些“什么區(qū)別”。識(shí)得ABCD者自以為新學(xué)家,仍舊和化學(xué)方程式無關(guān),會(huì)打算盤的自以為數(shù)學(xué)家,看起筆算的演草來還是無所得。現(xiàn)在的世間,原不是一為學(xué)者,便與一切事都會(huì)有緣的。然而梁先生有實(shí)例在,舉了我三段的譯文,雖然明知道“也許因?yàn)闆]有上下文的緣故,意思不能十分明了”。在《文學(xué)是有階級(jí)性的嗎?》這篇文章中,也用了類似手段,舉出兩首譯詩來,總評(píng)道:“也許偉大的無產(chǎn)文學(xué)還沒有出現(xiàn),那么我愿意等著,等著,等著。”這些方法,誠然是很“爽快”的,但我可以就在這一本《新月》月刊里的創(chuàng)作——是創(chuàng)作呀!——《搬家》第八頁上,舉出一段文字來——“小雞有耳朵沒有?”“我沒看見過小雞長(zhǎng)耳朵的。”“它怎樣聽見我叫它呢?”她想到前天四婆告訴她的耳朵是管聽東西,眼是管看東西的。“這個(gè)蛋是白雞黑雞?”枝兒見四婆沒答她,站起來摸著蛋子又問。“現(xiàn)在看不出來,等孵出小雞才知道。”“婉兒姊說小雞會(huì)變大雞,這些小雞也會(huì)變大雞么?”“好好的喂它就會(huì)長(zhǎng)大了,像這個(gè)雞買來時(shí)還沒有這樣大吧?”也夠了,“文字”是懂得的,也無須伸出手指來尋線索,但我不“等著”了,以為就這一段看,是既不“爽快”,而且和不創(chuàng)作是很少區(qū)別的。臨末,梁先生還有一個(gè)詰問:“中國文和外國文是不同的,……翻譯之難即在這個(gè)地方。假如兩種文中的文法句法詞法完全一樣,那么翻譯還成為一件工作嗎?……我們不妨把句法變換一下,以使讀者能懂為第一要義,因?yàn)椤仓^皮’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并且‘硬譯’也不見得能保存‘原來的精悍的語氣’。假如‘硬譯’而還能保存‘原來的精悍的語氣’,那真是一件奇跡,還能說中國文是有‘缺點(diǎn)’嗎?”我倒不見得如此之愚,要尋求和中國文相同的外國文,或者希望“兩種文中的文法句法詞法完全一樣”。我但以為文法繁復(fù)的國語,較易于翻譯外國文,語系相近的,也較易于翻譯,而且也是一種工作。荷蘭翻德國,俄國翻波蘭,能說這和并不工作沒有什么區(qū)別么?日本語和歐美很“不同”,但他們逐漸添加了新句法,比起古文來,更宜于翻譯而不失原來的精悍的語氣,開初自然是須“找尋句法的線索位置”,很給了一些人不“愉快”的,但經(jīng)找尋和習(xí)慣,現(xiàn)在已經(jīng)同化,成為己有了。中國的文法,比日本的古文還要不完備,然而也曾有些變遷,例如《史》《漢》不同于《書經(jīng)》,現(xiàn)在的白話文又不同于《史》《漢》;有添造,例如唐譯佛經(jīng),元譯上諭,當(dāng)時(shí)很有些“文法句法詞法”是生造的,一經(jīng)習(xí)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現(xiàn)在又來了“外國文”,許多句子,即也須新造,——說得壞點(diǎn),就是硬造。據(jù)我的經(jīng)驗(yàn),這樣譯來,較之化為幾句,更能保存原來的精悍的語氣,但因?yàn)橛写谛略欤栽鹊闹袊氖怯腥秉c(diǎn)的。有什么“奇跡”,干什么“嗎”呢?但有待于“伸出手指”,“硬著頭皮”,于有些人自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不過我是本不想將“爽快”或“愉快”來獻(xiàn)給那些諸公的,只要還有若干的讀者能夠有所得,梁實(shí)秋先生“們”的苦樂以及無所得,實(shí)在“于我如浮云”。但梁先生又有本不必求助于無產(chǎn)文學(xué)理論,而仍然很不了了的地方,例如他說,“魯迅先生前些年翻譯的文學(xué),例如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還不是令人看不懂的東西,但是最近翻譯的書似乎改變風(fēng)格了。”只要有些常識(shí)的人就知道:“中國文和外國文是不同的”,但同是一種外國文,因?yàn)樽髡吒魅说淖龇ǎ帮L(fēng)格”和“句法的線索位置”也可以很不同。句子可繁可簡(jiǎn),名詞可常可專,決不會(huì)一種外國文,易解的程度就都一式。我的譯《苦悶的象征》,也和現(xiàn)在一樣,是按板規(guī)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譯的,然而梁實(shí)秋先生居然以為不能看懂者,乃是原文原是易解的緣故,也因?yàn)榱簩?shí)秋先生是中國新的批評(píng)家了的緣故,也因?yàn)槠渲杏苍斓木浞ǎ潜容^地看慣了的緣故。若在三家村里,專讀《古文觀止》的學(xué)者們,看起來又何嘗不比“天書”還難呢。三但是,這回的“比天書還難”的無產(chǎn)文學(xué)理論的譯本們,卻給了梁先生不小的影響。看不懂了,會(huì)有影響,雖然好像滑稽,然而是真的,這位批評(píng)家在《文學(xué)是有階級(jí)性的嗎?》里說:“我現(xiàn)在批評(píng)所謂無產(chǎn)文學(xué)理論,也只能根據(jù)我所能了解的一點(diǎn)材料而已。”這就是說:因此而對(duì)于這理論的知識(shí),極不完全了。但對(duì)于這罪過,我們(包含一切“天書”譯者在內(nèi),故曰“們”)也只能負(fù)一部分的責(zé)任,一部分是要作者自己的胡涂或懶惰來負(fù)的。“什么盧那卡爾斯基,蒲力汗諾夫”的書我不知道,若夫“婆格達(dá)諾夫之類”的三篇論文和托羅茲基的半部《文學(xué)與革命》,則確有英文譯本的了。英國沒有“魯迅先生”,譯文定該非常易解。梁先生對(duì)于偉大的無產(chǎn)文學(xué)的產(chǎn)生,曾經(jīng)顯示其“等著,等著,等著”的耐心和勇氣,這回對(duì)于理論,何不也等一下子,尋來看了再說呢。不知其有而不求曰胡涂,知其有而不求曰懶惰,如果單是默坐,這樣也許是“爽快”的,然而開起口來,卻很容易咽進(jìn)冷氣去了。例如就是那篇《文學(xué)是有階級(jí)性的嗎?》的高文,結(jié)論是并無階級(jí)性。要抹殺階級(jí)性,我以為最干凈的是吳稚暉先生的“什么馬克斯牛克斯”以及什么先生的“世界上并沒有階級(jí)這東西”的學(xué)說。那么,就萬喙息響,天下太平。但梁先生卻中了一些“什么馬克斯”毒了,先承認(rèn)了現(xiàn)在許多地方是資產(chǎn)制度,在這制度之下則有無產(chǎn)者。不過這“無產(chǎn)者本來并沒有階級(jí)的自覺。是幾個(gè)過于富同情心而又態(tài)度褊激的領(lǐng)袖把這個(gè)階級(jí)觀念傳授了給他們”,要促起他們的聯(lián)合,激發(fā)他們爭(zhēng)斗的欲念。不錯(cuò),但我以為傳授者應(yīng)該并非由于同情,卻因了改造世界的思想。況且“本無其物”的東西,是無從自覺,無從激發(fā)的,會(huì)自覺,能激發(fā),足見那是原有的東西。原有的東西,就遮掩不久,即如格里萊阿說地體運(yùn)動(dòng),達(dá)爾文說生物進(jìn)化,當(dāng)初何嘗不或者幾被宗教家燒死,或者大受保守者攻擊呢,然而現(xiàn)在人們對(duì)于兩說,并不為奇者,就因?yàn)榈伢w終于在運(yùn)動(dòng),生物確也在進(jìn)化的緣故。承認(rèn)其有而要掩飾為無,非有絕技是不行的。但梁先生自有消除斗爭(zhēng)的辦法,以為如盧梭所說:“資產(chǎn)是文明的基礎(chǔ)”,“所以攻擊資產(chǎn)制度,即是反抗文明”,“一個(gè)無產(chǎn)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誠誠實(shí)實(shí)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當(dāng)?shù)馁Y產(chǎn)。這才是正當(dāng)?shù)纳疃窢?zhēng)的手段。”我想,盧梭去今雖已百五十年,但當(dāng)不至于以為過去未來的文明,都以資產(chǎn)為基礎(chǔ)。(但倘說以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為基礎(chǔ),那自然是對(duì)的。)希臘印度,都有文明,而繁盛時(shí)俱非在資產(chǎn)社會(huì),他大概是知道的;倘不知道,那也是他的錯(cuò)誤。至于無產(chǎn)者應(yīng)該“辛辛苦苦”爬上有產(chǎn)階級(jí)去的“正當(dāng)”的方法,則是中國有錢的老太爺高興時(shí)候,教導(dǎo)窮工人的古訓(xùn),在實(shí)際上,現(xiàn)今正在“辛辛苦苦誠誠實(shí)實(shí)”想爬上一級(jí)去的“無產(chǎn)者”也還多。然而這是還沒有人“把這個(gè)階級(jí)觀念傳授了給他們”的時(shí)候。一經(jīng)傳授,他們可就不肯一個(gè)一個(gè)的來爬了,誠如梁先生所說,“他們是一個(gè)階級(jí)了,他們要有組織了,他們是一個(gè)集團(tuán)了,于是他們便不循常軌的一躍而奪取政權(quán)財(cái)權(quán),一躍而為統(tǒng)治階級(jí)。”但可還有想“辛辛苦苦誠誠實(shí)實(shí)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當(dāng)?shù)馁Y產(chǎn)”的“無產(chǎn)者”呢?自然還有的。然而他要算是“尚未發(fā)財(cái)?shù)挠挟a(chǎn)者”了。梁先生的忠告,將為無產(chǎn)者所嘔吐了,將只好和老太爺去互相贊賞而已了。那么,此后如何呢?梁先生以為是不足慮的。因?yàn)椤斑@種革命的現(xiàn)象不能是永久的,經(jīng)過自然進(jìn)化之后,優(yōu)勝劣敗的定律又要證明了,還是聰明才力過人的人占優(yōu)越的地位,無產(chǎn)者仍是無產(chǎn)者”。但無產(chǎn)階級(jí)大概也知道“反文明的勢(shì)力早晚要被文明的勢(shì)力所征服”,所以“要建立所謂‘無產(chǎn)階級(jí)文化’,……這里面包括文藝學(xué)術(shù)”。自此以后,這才入了文藝批評(píng)的本題。四梁先生首先以為無產(chǎn)者文學(xué)理論的錯(cuò)誤,是“在把階級(jí)的束縛加在文學(xué)上面”,因?yàn)橐粋€(gè)資本家和一個(gè)勞動(dòng)者,有不同的地方,但還有相同的地方,“他們的人性(這兩字原本有套圈)并沒有兩樣”,例如都有喜怒哀樂,都有戀愛(但所“說的是戀愛的本身,不是戀愛的方式”),“文學(xué)就是表現(xiàn)這最基本的人性的藝術(shù)”。這些話是矛盾而空虛的。既然文明以資產(chǎn)為基礎(chǔ),窮人以竭力爬上去為“有出息”,那么,爬上是人生的要諦,富翁乃人類的至尊,文學(xué)也只要表現(xiàn)資產(chǎn)階級(jí)就夠了,又何必如此“過于富同情心”,一并包括“劣敗”的無產(chǎn)者?況且“人性”的“本身”,又怎樣表現(xiàn)的呢?譬如原質(zhì)或雜質(zhì)的化學(xué)底性質(zhì),有化合力,物理學(xué)底性質(zhì)有硬度,要顯示這力和度數(shù),是須用兩種物質(zhì)來表現(xiàn)的,倘說要不用物質(zhì)而顯示化合力和硬度的單單“本身”,無此妙法;但一用物質(zhì),這現(xiàn)象即又因物質(zhì)而不同。文學(xué)不借人,也無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還在階級(jí)社會(huì)里,即斷不能免掉所屬的階級(jí)性,無需加以“束縛”,實(shí)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樂,人之情也”,然而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那會(huì)知道北京檢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饑區(qū)的災(zāi)民,大約總不去種蘭花,像闊人的老太爺一樣,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汽笛呀!”“列寧呀!”固然并不就是無產(chǎn)文學(xué),然而“一切東西呀!”“一切人呀!”“可喜的事來了,人喜了呀!”也不是表現(xiàn)“人性”的“本身”的文學(xué)。倘以表現(xiàn)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學(xué)為至高,則表現(xiàn)最普遍的動(dòng)物性——營養(yǎng),呼吸,運(yùn)動(dòng),生殖——的文學(xué),或者除去“運(yùn)動(dòng)”,表現(xiàn)生物性的文學(xué),必當(dāng)更在其上。倘說,因?yàn)槲覀兪侨耍砸员憩F(xiàn)人性為限,那么,無產(chǎn)者就因?yàn)槭菬o產(chǎn)階級(jí),所以要做無產(chǎn)文學(xué)。其次,梁先生說作者的階級(jí),和作品無關(guān)。托爾斯泰出身貴族,而同情于貧民,然而并不主張階級(jí)斗爭(zhēng);馬克斯并非無產(chǎn)階級(jí)中的人物;終身窮苦的約翰孫博士,志行吐屬,過于貴族。所以估量文學(xué),當(dāng)看作品本身,不能連累到作者的階級(jí)和身分。這些例子,也全不足以證明文學(xué)的無階級(jí)性的。托爾斯泰正因?yàn)槌錾碣F族,舊性蕩滌不盡,所以只同情于貧民而不主張階級(jí)斗爭(zhēng)。馬克斯原先誠非無產(chǎn)階級(jí)中的人物,但也并無文學(xué)作品,我們不能懸擬他如果動(dòng)筆,所表現(xiàn)的一定是不用方式的戀愛本身。至于約翰孫博士終身窮苦,而志行吐屬,過于王侯者,我卻實(shí)在不明白那緣故,因?yàn)槲也恢烙膶W(xué)和他的傳記。也許,他原想“辛辛苦苦誠誠實(shí)實(shí)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當(dāng)?shù)馁Y產(chǎn)”,然后再爬上貴族階級(jí)去,不料終于“劣敗”,連相當(dāng)?shù)馁Y產(chǎn)也積不起來,所以只落得擺空架子,“爽快”了罷。其次,梁先生說,“好的作品永遠(yuǎn)是少數(shù)人的專利品,大多數(shù)永遠(yuǎn)是蠢的,永遠(yuǎn)是和文學(xué)無緣”,但鑒賞力之有無卻和階級(jí)無干,因?yàn)椤拌b賞文學(xué)也是天生的一種福氣”,就是,雖在無產(chǎn)階級(jí)里,也會(huì)有這“天生的一種福氣”的人。由我推論起來,則只要有這一種“福氣”的人,雖窮得不能受教育,至于一字不識(shí),也可以賞鑒《新月》月刊,來作“人性”和文藝“本身”原無階級(jí)性的證據(jù)。但梁先生也知道天生這一種福氣的無產(chǎn)者一定不多,所以另定一種東西(文藝?)來給他們看,“例如什么通俗的戲劇,電影,偵探小說之類”,因?yàn)椤耙话銊诠谵r(nóng)需要娛樂,也許需要少量的藝術(shù)的娛樂”的緣故。這樣看來,好像文學(xué)確因階級(jí)而不同了,但這是因鑒賞力之高低而定的,這種力量的修養(yǎng)和經(jīng)濟(jì)無關(guān),乃是上帝之所賜——“福氣”。所以文學(xué)家要自由創(chuàng)造,既不該為皇室貴族所雇用,也不該受無產(chǎn)階級(jí)所威脅,去做謳功頌德的文章。這是不錯(cuò)的,但在我們所見的無產(chǎn)文學(xué)理論中,也并未見過有誰說或一階級(jí)的文學(xué)家,不該受皇室貴族的雇用,卻該受無產(chǎn)階級(jí)的威脅,去做謳功頌德的文章,不過說,文學(xué)有階級(jí)性,在階級(jí)社會(huì)中,文學(xué)家雖自以為“自由”,自以為超了階級(jí),而無意識(shí)底地,也終受本階級(jí)的階級(jí)意識(shí)所支配,那些創(chuàng)作,并非別階級(jí)的文化罷了。例如梁先生的這篇文章,原意是在取消文學(xué)上的階級(jí)性,張揚(yáng)真理的。但以資產(chǎn)為文明的祖宗,指窮人為劣敗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資產(chǎn)家的斗爭(zhēng)的“武器”,——不,“文章”了。無產(chǎn)文學(xué)理論家以主張“全人類”“超階級(jí)”的文學(xué)理論為幫助有產(chǎn)階級(jí)的東西,這里就給了一個(gè)極分明的例證。至于成仿吾先生似的“他們一定勝利的,所以我們?nèi)ブ笇?dǎo)安慰他們?nèi)ァ保f出“去了”之后,便來“打發(fā)”自己們以外的“他們”那樣的無產(chǎn)文學(xué)家,那不消說,是也和梁先生一樣地對(duì)于無產(chǎn)文學(xué)的理論,未免有“以意為之”的錯(cuò)誤的。又其次,梁先生最痛恨的是無產(chǎn)文學(xué)理論家以文藝為斗爭(zhēng)的武器,就是當(dāng)作宣傳品。他“不反對(duì)任何人利用文學(xué)來達(dá)到另外的目的”,但“不能承認(rèn)宣傳式的文字便是文學(xué)”。我以為這是自擾之談。據(jù)我所看過的那些理論,都不過說凡文藝必有所宣傳,并沒有誰主張只要宣傳式的文字便是文學(xué)。誠然,前年以來,中國確曾有許多詩歌小說,填進(jìn)口號(hào)和標(biāo)語去,自以為就是無產(chǎn)文學(xué)。但那是因?yàn)閮?nèi)容和形式,都沒有無產(chǎn)氣,不用口號(hào)和標(biāo)語,便無從表示其“新興”的緣故,實(shí)際上也并非無產(chǎn)文學(xué)。今年,有名的“無產(chǎn)文學(xué)底批評(píng)家”錢杏邨先生在《拓荒者》上還在引盧那卡爾斯基的話,以為他推重大眾能解的文學(xué),足見用口號(hào)標(biāo)語之未可厚非,來給那些“革命文學(xué)”辯護(hù)。但我覺得那也和梁實(shí)秋先生一樣,是有意的或無意的曲解。盧那卡爾斯基所謂大眾能解的東西,當(dāng)是指托爾斯泰做了分給農(nóng)民的小本子那樣的文體,工農(nóng)一看便會(huì)了然的語法,歌調(diào),詼諧。只要看臺(tái)明•培特尼(DemianBednii)曾因詩歌得到赤旗章,而他的詩中并不用標(biāo)語和口號(hào),便可明白了。最后,梁先生要看貨色。這不錯(cuò)的,是最切實(shí)的辦法;但抄兩首譯詩算是在示眾,是不對(duì)的。《新月》上就曾有《論翻譯之難》,何況所譯的文是詩。就我所見的而論,盧那卡爾斯基的《被解放的堂•吉訶德》,法兌耶夫的《潰滅》,格拉特珂夫的《水門汀》,在中國這十一年中,就并無可以和這些相比的作品。這是指“新月社”一流的蒙資產(chǎn)文明的余蔭,而且衷心在擁護(hù)它的作家而言。于號(hào)稱無產(chǎn)作家的作品中,我也舉不出相當(dāng)?shù)某煽?jī)。但錢杏邨先生也曾辯護(hù),說新興階級(jí),于文學(xué)的本領(lǐng)當(dāng)然幼稚而單純,向他們立刻要求好作品,是“布爾喬亞”的惡意。這話為農(nóng)工而說,是極不錯(cuò)的。這樣的無理要求,恰如使他們凍餓了好久,倒怪他們?yōu)槭裁礇]有富翁那么肥胖一樣。但中國的作者,現(xiàn)在卻實(shí)在并無剛剛放下鋤斧柄子的人,大多數(shù)都是進(jìn)過學(xué)校的智識(shí)者,有些還是早已有名的文人,莫非克服了自己的小資產(chǎn)階級(jí)意識(shí)之后,就連先前的文學(xué)本領(lǐng)也隨著消失了么?不會(huì)的。俄國的老作家亞歷舍•托爾斯泰和威壘賽耶夫,普理希文,至今都還有好作品。中國的有口號(hào)而無隨同的實(shí)證者,我想,那病根并不在“以文藝為階級(jí)斗爭(zhēng)的武器”,而在“借階級(jí)斗爭(zhēng)為文藝的武器”,在“無產(chǎn)者文學(xué)”這旗幟之下,聚集了不少的忽翻筋斗的人,試看去年的新書廣告,幾乎沒有一本不是革命文學(xué),批評(píng)家又但將辯護(hù)當(dāng)作“清算”,就是,請(qǐng)文學(xué)坐在“階級(jí)斗爭(zhēng)”的掩護(hù)之下,于是文學(xué)自己倒不必著力,因而于文學(xué)和斗爭(zhēng)兩方面都少關(guān)系了。但中國目前的一時(shí)現(xiàn)象,當(dāng)然毫不足作無產(chǎn)文學(xué)之新興的反證的。梁先生也知道,所以他臨末讓步說,“假如無產(chǎn)階級(jí)革命家一定要把他的宣傳文學(xué)喚做無產(chǎn)文學(xué),那總算是一種新興文學(xué),總算是文學(xué)國土里的新收獲,用不著高呼打倒資產(chǎn)的文學(xué)來爭(zhēng)奪文學(xué)的領(lǐng)域,因?yàn)槲膶W(xué)的領(lǐng)域太大了,新的東西總有它的位置的。”但這好像“中日親善,同存共榮”之說,從羽毛未豐的無產(chǎn)者看來,是一種欺騙。愿意這樣的“無產(chǎn)文學(xué)者”,現(xiàn)在恐怕實(shí)在也有的罷,不過這是梁先生所謂“有出息”的要爬上資產(chǎn)階級(jí)去的“無產(chǎn)者”一流,他的作品是窮秀才未中狀元時(shí)候的牢騷,從開手到爬上以及以后,都決不是無產(chǎn)文學(xué)。無產(chǎn)者文學(xué)是為了以自己們之力,來解放本階級(jí)并及一切階級(jí)而斗爭(zhēng)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就拿文藝批評(píng)界來比方罷,假如在“人性”的“藝術(shù)之宮”(這須從成仿吾先生處租來暫用)里,向南面擺兩把虎皮交椅,請(qǐng)梁實(shí)秋錢杏邨兩位先生并排坐下,一個(gè)右執(zhí)“新月”,一個(gè)左執(zhí)“太陽”,那情形可真是“勞資”媲美了。五到這里,又可以談到我的“硬譯”去了。推想起來,這是很應(yīng)該跟著發(fā)生的問題:無產(chǎn)文學(xué)既然重在宣傳,宣傳必須多數(shù)能懂,那么,你這些“硬譯”而難懂的理論“天書”,究竟為什么而譯的呢?不是等于不譯么?我的回答,是:為了我自己,和幾個(gè)以無產(chǎn)文學(xué)批評(píng)家自居的人,和一部分不圖“爽快”,不怕艱難,多少要明白一些這理論的讀者。從前年以來,對(duì)于我個(gè)人的攻擊是多極了,每一種刊物上,大抵總要看見“魯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則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學(xué)家。但我看了幾篇,竟逐漸覺得廢話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彈所擊之處,也不是致命傷。例如我所屬的階級(jí)罷,就至今還未判定,忽說小資產(chǎn)階級(jí),忽說“布爾喬亞”,有時(shí)還升為“封建余孽”,而且又等于猩猩(見《創(chuàng)造月刊》上的“東京通信”);有一回則罵到牙齒的顏色。在這樣的社會(huì)里,有封建余孽出風(fēng)頭,是十分可能的,但封建余孽就是猩猩,卻在任何“唯物史觀”上都沒有說明,也找不出牙齒色黃,即有害于無產(chǎn)階級(jí)革命的論據(jù)。我于是想,可供參考的這樣的理論,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胡涂。對(duì)于敵人,解剖,咬嚼,現(xiàn)在是在所不免的,不過有一本解剖學(xué),有一本烹飪法,依法辦理,則構(gòu)造味道,總還可以較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話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為竊火給人,雖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堅(jiān)忍正相同。但我從別國里竊得火來,本意卻在煮自己的肉的,以為倘能味道較好,庶幾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較多的好處,我也不枉費(fèi)了身軀:出發(fā)點(diǎn)全是個(gè)人主義,并且還夾雜著小市民性的奢華,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來,反而刺進(jìn)解剖者的心臟里去的“報(bào)復(fù)”。梁先生說“他們要報(bào)復(fù)!”其實(shí)豈只“他們”,這樣的人在“封建余孽”中也很有的。然而,我也愿意于社會(huì)上有些用處,看客所見的結(jié)果仍是火和光。這樣,首先開手的就是《文藝政策》,因?yàn)槠渲泻懈髋傻淖h論。鄭伯奇先生現(xiàn)在是開書鋪,印Hauptmann和Gregory夫人的劇本了,那時(shí)他還是革命文學(xué)家,便在所編的《文藝生活》上,笑我的翻譯這書,是不甘沒落,而可惜被別人著了先鞭。翻一本書便會(huì)浮起,做革命文學(xué)家真太容易了,我并不這樣想。有一種小報(bào),則說我的譯《藝術(shù)論》是“投降”。是的,投降的事,為世上所常有。但其時(shí)成仿吾元帥早已爬出日本的溫泉,住進(jìn)巴黎的旅館了,在這里又向誰去輸誠呢。今年,說法又兩樣了,在《拓荒者》和《現(xiàn)代小說》上,都說是“方向轉(zhuǎn)換”。我看見日本的有些雜志中,曾將這四字加在先前的新感覺派片岡鐵兵上,算是一個(gè)好名詞。其實(shí),這些紛紜之談,也還是只看名目,連想也不肯想的老病。譯一本關(guān)于無產(chǎn)文學(xué)的書,是不足以證明方向的,倘有曲譯,倒反足以為害。我的譯書,就也要獻(xiàn)給這些速斷的無產(chǎn)文學(xué)批評(píng)家,因?yàn)樗麄兪怯胁回潯八臁保涂鄟硌芯窟@些理論的義務(wù)的。但我自信并無故意的曲譯,打著我所不佩服的批評(píng)家的傷處了的時(shí)候我就一笑,打著我的傷處了的時(shí)候我就忍疼,卻決不肯有所增減,這也是始終“硬譯”的一個(gè)原因。自然,世間總會(huì)有較好的翻譯者,能夠譯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時(shí)我的譯本當(dāng)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來填這從“無有”到“較好”的空間罷了。然而世間紙張還多,每一文社的人數(shù)卻少,志大力薄,寫不完所有的紙張,于是一社中的職司克敵助友,掃蕩異類的批評(píng)家,看見別人來涂寫紙張了,便喟然興嘆,不勝其搖頭頓足之苦。上海的《申報(bào)》上,至于稱社會(huì)科學(xué)的翻譯者為“阿狗阿貓”,其憤憤有如此。在“中國新興文學(xué)的地位,早為讀者所共知”的蔣光Z先生,曾往日本東京養(yǎng)病,看見藏原惟人,談到日本有許多翻譯太壞,簡(jiǎn)直比原文還難讀……他就笑了起來,說:“……那中國的翻譯界更要莫名其妙了,近來中國有許多書籍都是譯自日文的,如果日本人將歐洲人那一國的作品帶點(diǎn)錯(cuò)誤和刪改,從日文譯到中國去,試問這作品豈不是要變了一半相貌么?……”(見《拓荒者》)也就是深不滿于翻譯,尤其是重譯的表示。不過梁先生還舉出書名和壞處,蔣先生卻只嫣然一笑,掃蕩無余,真是普遍得遠(yuǎn)了。藏原惟人是從俄文直接譯過許多文藝?yán)碚摵托≌f的,于我個(gè)人就極有裨益。我希望中國也有一兩個(gè)這樣的誠實(shí)的俄文翻譯者,陸續(xù)譯出好書來,不僅自罵一聲“混蛋”就算盡了革命文學(xué)家的責(zé)任。然而現(xiàn)在呢,這些東西,梁實(shí)秋先生是不譯的,稱人為“阿狗阿貓”的偉人也不譯,學(xué)過俄文的蔣先生原是最為適宜的了,可惜養(yǎng)病之后,只出了一本《一周間》,而日本則早已有了兩種的譯本。中國曾經(jīng)大談達(dá)爾文,大談尼采,到歐戰(zhàn)時(shí)候,則大罵了他們一通,但達(dá)爾文的著作的譯本,至今只有一種,尼采的則只有半部,學(xué)英德文的學(xué)者及文豪都不暇顧及,或不屑顧及,拉倒了。所以暫時(shí)之間,恐怕還只好任人笑罵,仍從日文來重譯,或者取一本原文,比照了日譯本來直譯罷。我還想這樣做,并且希望更多有這樣做的人,來填一填徹底的高談中的空虛,因?yàn)槲覀儾荒芟袷Y先生那樣的“好笑起來”,也不該如梁先生的“等著,等著,等著”了。六我在開頭曾有“以硬自居了,而實(shí)則其軟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種特色”這些話,到這里還應(yīng)該簡(jiǎn)短地補(bǔ)充幾句,就作為本篇的收?qǐng)觥!缎略隆芬怀鍪溃椭鲝垺皣?yán)正態(tài)度”,但于罵人者則罵之,譏人者則譏之。這并不錯(cuò),正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雖然也是一種“報(bào)復(fù)”,而非為了自己。到二卷六七號(hào)合本的廣告上,還說“我們都保持‘容忍’的態(tài)度(除了‘不容忍’的態(tài)度是我們所不能容忍以外),我們都喜歡穩(wěn)健的合乎理性的學(xué)說”。上兩句也不錯(cuò),“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和開初仍然一貫。然而從這條大路走下去,一定要遇到“以暴力抗暴力”,這和新月社諸君所喜歡的“穩(wěn)健”也不能相容了。這一回,新月社的“自由言論”遭了壓迫,照老辦法,是必須對(duì)于壓迫者,也加以壓迫的,但《新月》上所顯現(xiàn)的反應(yīng),卻是一篇《告壓迫言論自由者》,先引對(duì)方的黨義,次引外國的法律,終引東西史例,以見凡壓迫自由者,往往臻于滅亡:是一番替對(duì)方設(shè)想的警告。所以,新月社的“嚴(yán)正態(tài)度”,“以眼還眼”法,歸根結(jié)蒂,是專施之力量相類,或力量較小的人的,倘給有力者打腫了眼,就要破例,只舉手掩住自己的臉,叫一聲“小心你自己的眼睛!”
文學(xué)場(chǎng)邏輯學(xué)研究論文
要討論當(dāng)代西方思想家,對(duì)于治文學(xué)的人來說可能有著更便利的條件。因?yàn)楫?dāng)代西方許多哲人,在提出一個(gè)個(gè)自成一格的話語系統(tǒng)的同時(shí),總是不約而同地傾向于把文學(xué)或當(dāng)成自己的殖民地。伊格爾頓不無譏諷地說:"當(dāng)家變成實(shí)證哲學(xué)家的工具時(shí),美學(xué)就可以用來拯救思想了。哲學(xué)強(qiáng)有力的主題被某種具體、純粹、斤斤計(jì)較的所排遣,現(xiàn)在正變得無家可歸,四處漂泊,它們尋求著一片蔽身的瓦頂,終至在藝術(shù)的話語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這當(dāng)然是事情的一方面。但從策略的角度來看,至少對(duì)于我們即將要討論的布迪厄來說,文學(xué)藝術(shù)之所以容易成為思想家所關(guān)注的寵兒,可能還因?yàn)樽鳛榫瘳F(xiàn)象,文學(xué)藝術(shù)具有更普遍的可通約性。一種理論,倘若能在對(duì)文學(xué)藝術(shù)的中站得住腳,在其他領(lǐng)域中也許就顯得是不言而喻的了。更何況文學(xué)藝術(shù)在人類中又有類乎廣告效應(yīng)那么強(qiáng)大的力。
盡管主要身份是社會(huì)學(xué)家的布迪厄在原則上反對(duì)建立一種普遍性元話語,然而,他的確在事實(shí)上創(chuàng)造了一整套話語系統(tǒng),并將它令人咋舌地運(yùn)用在農(nóng)民、失業(yè)、、、、階級(jí)、、宗教、、語言、住房、婚姻、知識(shí)分子、國家制度等極為廣闊的領(lǐng)域里,而他特別留意的對(duì)象之一,似乎是文學(xué)藝術(shù)。他不僅在許多著作中屢屢提及文學(xué)藝術(shù),而且還專門寫了幾部專著如《區(qū)隔:趣味判斷的社會(huì)批判》、《藝術(shù)之戀:歐洲藝術(shù)博物館及其觀眾》、《藝術(shù)的法則:文學(xué)場(chǎng)的發(fā)生和結(jié)構(gòu)》、《文化生產(chǎn)場(chǎng):論藝術(shù)和文學(xué)》等等。要紹介布迪厄的文學(xué)理論,我們可能會(huì)有一種浩浩茫茫不知從何處說起的慨嘆,因?yàn)椴际蠋缀鯖]有遺漏文學(xué)社會(huì)學(xué)的任何一個(gè)重要領(lǐng)域,但是,正如上述書名所暗示的那樣,文學(xué)場(chǎng)顯然是布迪厄文學(xué)理論的一個(gè)關(guān)鍵詞。正是通過文學(xué)場(chǎng)的概念,布迪厄的文學(xué)理論才得以清楚的表述。所以,不妨讓我們從文學(xué)場(chǎng)開始說起。
一、為什么是文學(xué)場(chǎng)?
布迪厄自認(rèn)獨(dú)擅勝場(chǎng),并得到了一些學(xué)者贊同的學(xué)術(shù)閃光點(diǎn)之一是,他超越了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經(jīng)驗(yàn)和理論研究、內(nèi)部閱讀與外部閱讀、存在主義與結(jié)構(gòu)主義等之間的二元對(duì)立。具體到文學(xué)研究領(lǐng)域,布迪厄認(rèn)為,主觀主義或本質(zhì)主義的文學(xué)分析,諸如浪漫主義者基于卡理斯瑪意識(shí)形態(tài),將作者視為獨(dú)創(chuàng)者;新批評(píng)派之類的形式主義者沉迷于文本的形式之中,將陌生化等形式因素視為文學(xué)性的一般特質(zhì);實(shí)證主義者相信經(jīng)驗(yàn)數(shù)據(jù)的科學(xué)性,把賴以統(tǒng)計(jì)的分類范疇當(dāng)成文學(xué)事實(shí)的自在范疇;薩特在傳記材料中尋求作者的個(gè)人特性,并將它與文學(xué)作品中所呈現(xiàn)的特性混為一談;弗洛伊德或榮格借助于俄狄浦斯情結(jié)或集體無意識(shí)來解釋文學(xué)的本質(zhì);而福科則拒絕在話語場(chǎng)之外發(fā)現(xiàn)文學(xué)發(fā)生的解釋原則;……凡此種種,都不同程度地把文學(xué)觀念、文學(xué)實(shí)踐和文學(xué)作品當(dāng)作理所當(dāng)然的現(xiàn)實(shí)加以接受,而完全忽視了這種現(xiàn)實(shí)在人的頭腦中賴以構(gòu)成的社會(huì)條件和條件。另一方面,一些馬克思主義者,例如盧卡契或者以發(fā)生學(xué)結(jié)構(gòu)主義者自命的戈德曼,則完全無視文學(xué)自身相對(duì)獨(dú)立的形式特性,無視作家作為能動(dòng)者在文學(xué)生產(chǎn)中對(duì)于文學(xué)意義的塑造,而將作者簡(jiǎn)化為某個(gè)社會(huì)集團(tuán)的無意識(shí)人,將文學(xué)的發(fā)生簡(jiǎn)化為政治力量的直接作用。
布迪厄超越二元對(duì)立的理論工具是場(chǎng)域、資本和習(xí)性(habitus,或譯慣習(xí))諸概念。就文學(xué)而言,布迪厄使用了文學(xué)場(chǎng)或者文化生產(chǎn)場(chǎng)的概念。一方面,文學(xué)場(chǎng)在作為元場(chǎng)域的權(quán)力場(chǎng)中居于被支配地位,也就是說,歸根到底,還是要受到政治經(jīng)濟(jì)因素的制約;另一方面,文學(xué)場(chǎng)可以被描述為獨(dú)立于政治、經(jīng)濟(jì)之外,具有自身運(yùn)行法則,具有相對(duì)自主性的封閉的社會(huì)宇宙。這說起來很有點(diǎn)類似于阿爾都塞對(duì)于經(jīng)濟(jì)基礎(chǔ)和上層建筑之間關(guān)系的表述。但是,對(duì)于布迪厄來說,文學(xué)場(chǎng)的隱喻不僅僅是對(duì)于文學(xué)與宏觀的社會(huì)世界之間互動(dòng)關(guān)系的一個(gè)闡釋工具,重要的是,它還是超越上述二元對(duì)立、反對(duì)本質(zhì)主義文學(xué)觀的一種敘事框架,同時(shí)也是理解文學(xué)的本質(zhì)、文學(xué)作品的形式與,文學(xué)家的文學(xué)觀與創(chuàng)作軌跡,文學(xué)史的發(fā)展與變革,文學(xué)的生產(chǎn)和消費(fèi)等等幾乎重大的文學(xué)理論的。當(dāng)然,還需要提上一筆的是,他的文學(xué)場(chǎng)的理論主要關(guān)注的文學(xué)事實(shí)是近世以來逐漸獲得文學(xué)自主性的文學(xué)現(xiàn)象,換句話說,前資本主義的文學(xué)實(shí)踐基本上不在他考察的范圍之內(nèi)。
二、什么是文學(xué)場(chǎng)?
文學(xué)形象本質(zhì)研究論文
摘要:文學(xué)的本質(zhì)是形象。因?yàn)榈谝?文學(xué)語言的特性是它的構(gòu)象性,本身并不是自足的,而是指向外部世界,目的在塑造形象,表現(xiàn)生活的感性形態(tài),因此語言不能成為文學(xué)的本質(zhì)。第二,文學(xué)的外在表現(xiàn)形式和內(nèi)在存在形式都是形象。認(rèn)為文學(xué)的本質(zhì)是形象,可能遇到來自兩個(gè)方面的反駁。一是認(rèn)為形象沒有普遍性,一是認(rèn)為形象沒有特殊性。但認(rèn)真分析,這兩種說法都是站不住腳的。
近些年來,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理論界不大談文學(xué)的本質(zhì)問題,有的學(xué)者干脆回避或否認(rèn)文學(xué)的本質(zhì)問題,然而本質(zhì)問題卻依然存在。文學(xué)理論不是雜多觀點(diǎn)的偶然堆積,而是系列觀念的有機(jī)組合。在這種組合中,總有幾塊基石存在,整個(gè)理論體系便建立在這些基石之上。文學(xué)本質(zhì)便是這樣的基石之一。對(duì)文學(xué)本質(zhì)的不同看法,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文學(xué)理論的基本走向,而且決定著文學(xué)理論的具體內(nèi)容。因此,在對(duì)文學(xué)本質(zhì)的看法日益模糊、混亂的今天,重新探討文學(xué)的本質(zhì)問題,不能說是沒有意義的。
一
討論文學(xué)的本質(zhì),首先有一個(gè)討論的角度和出發(fā)點(diǎn)的問題。因?yàn)槲膶W(xué)是復(fù)雜的,任何復(fù)雜的事物其本質(zhì)也不會(huì)是單一的。不同的角度和出發(fā)點(diǎn),得出的結(jié)論也肯定不會(huì)一樣。國內(nèi)一般從意識(shí)形態(tài)的角度探討文學(xué)的本質(zhì),從而得出文學(xué)是一種審美的意識(shí)形態(tài),更具體地說,是一種用語言來塑造形象的審美的意識(shí)形態(tài)的結(jié)論。這種學(xué)說著眼的主要是從人類的整個(gè)活動(dòng)中將文學(xué)區(qū)分出來,進(jìn)行的是一種形而上的探討,未能深入到作品之中。而文學(xué)作品乃至整個(gè)文學(xué)活動(dòng)作為一個(gè)具體、復(fù)雜、系統(tǒng)的整體,對(duì)其本質(zhì)的探討不能僅僅著眼于整個(gè)的人類活動(dòng),滿足于將它與人類的其他活動(dòng)區(qū)分開來,更應(yīng)著眼于其本身,從中探索出更為符合其本性的結(jié)論。由此可見,意識(shí)形態(tài)說雖然正確,但也不是沒有局限,它透視了文學(xué)本質(zhì)的一個(gè)方面,卻忽視了其他的方面,而且就文學(xué)本身來看,有些甚至是更重要的方面。
筆者以為,探討文學(xué)本質(zhì)的最重要的角度與出發(fā)點(diǎn),應(yīng)當(dāng)是也只能是文學(xué)作品。這不僅是因?yàn)樵谖膶W(xué)四要素中,作品處于核心的地位,也是因?yàn)樽髌肥俏膶W(xué)的思想、形式、功能等唯一的具有物化形式的載體,還因?yàn)樵诠┪覀冄芯康奈膶W(xué)材料中,作品是最為可靠、最為準(zhǔn)確、最為長(zhǎng)久、也最便于操作的一個(gè)組成部分。可以說,文學(xué)的本質(zhì),歸根到底是由文學(xué)作品的本質(zhì)決定的。因此從作品切入,是把握文學(xué)本質(zhì)的最好的途徑。
二
古典文學(xué)研究論文
關(guān)于古典文學(xué)研究與當(dāng)代意識(shí)問題,在我看來,本不成為問題。因?yàn)檠芯窟^去,總是為了現(xiàn)在和將來。不管哪個(gè)時(shí)代,誰也知道,著書立說,是給當(dāng)代和后代的人看的。問題是自覺與否。
例如王國維,他通過對(duì)甲骨文的研究,改正了殷商先王的世序,從而糾正了《史記·殷本紀(jì)》的錯(cuò)誤,使后人研究“兄終弟及”的王位承襲制度時(shí),更準(zhǔn)確地理解了“國賴長(zhǎng)君”的道理。
這看起來似乎和我們當(dāng)代無關(guān),是純學(xué)術(shù)的研究。其實(shí)不然,它正反映了人類社會(huì)進(jìn)化的邏輯:奴隸主政權(quán)為了統(tǒng)治的鞏固、秩序的穩(wěn)定,它深思熟慮,設(shè)計(jì)出當(dāng)時(shí)認(rèn)為合理的王位繼承方案。這一方案直到春秋時(shí)期,吳國還在繼續(xù)實(shí)行這一制度;余波所及,北宋的杜太后還曾囑咐宋太祖死后應(yīng)傳位于弟趙匡義即后來的宋太宗。那么,這一制度后來怎么又讓位于父?jìng)髯拥氖酪u制呢?原來兄終弟及制多次發(fā)生搶班奪權(quán)、兄弟相殘的現(xiàn)象,因此認(rèn)為索性確定立嫡長(zhǎng)子,以免旁支的覬覦。當(dāng)然,如無嫡長(zhǎng)子,則立賢。而所謂賢,全憑“父皇”的認(rèn)定,這就必然產(chǎn)生偽裝,如隋煬帝之蒙騙其父隋文帝。這一繼承人問題,紛紛擾擾,不但苦惱了中國,也苦惱了外國;不但苦惱了古人,也苦惱了今人。迄今為止,民主國家的總統(tǒng)直選制,勉強(qiáng)為這一紛擾畫上了一個(gè)句號(hào)。
我們現(xiàn)當(dāng)代人懂得這些,就既明白歷史是這樣過來的,一切存在過的都有合理性;但又知道它不斷地在走向它的反面,由合理的轉(zhuǎn)化為不合理的,最后,皇權(quán)的專制必然為民主的政治所取代。所以,研究過去的一切,首先是求“真”,即求得歷史的真相。
但,一切過去的“真”,既有善的,也有惡的。我們繼承發(fā)揚(yáng)善的,批判揚(yáng)棄惡的,無論正反面,都可給后人以裨益:懲惡而勸善。
求“真”與“善”,是哲學(xué)和科學(xué)(包括自然科學(xué)和社會(huì)科學(xué))的任務(wù),而文學(xué)則在“真”、“善”基礎(chǔ)之上更追求“美”。孔子早就指出“言之無文,行而不遠(yuǎn)”,可見文學(xué)藝術(shù)擁有“美”的專利。之所以出現(xiàn)“文”、“理”現(xiàn)象,背景或?qū)嵸|(zhì)是由于“情”與“理”的存在。求“真”與“善”,是理性的思維活動(dòng),而求“美”,則是感情的思維活動(dòng)。我們常說的邏輯思維即前者,而形象思維則指后者。
熱門標(biāo)簽
文學(xué)評(píng)論 文學(xué)鑒賞 文學(xué)批評(píng) 文學(xué)性 文學(xué)賞析 文學(xué)論文 文學(xué)評(píng)論論文 文學(xué)論文論文 文學(xué)創(chuàng)作 文學(xué)賞析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