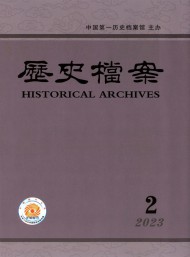明清商業(yè)發(fā)展的表現(xiàn)范文
時間:2024-01-26 17:27:12
導(dǎo)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明清商業(yè)發(fā)展的表現(xiàn),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xiàn),歡迎閱讀由公務(wù)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明清旅游旅游方式特色近現(xiàn)代化
中圖分類號K928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收稿日期2017-09-12
AbstractThetouristsinMingandQingdynastiescanbedividedintofourcategoriesaccordingtotheiroccupations:aristocraticbureaucrats,scholars,businessmenandordinarycivilianswhosetravelingcontent,waysandmotivesdiffersignificantly.TourisminMingandQingdynastieshasshownmoderncharacteristics.First,tourismofallclassespresentedatrendofdemocratization,andthetravelingmotivesindicateddiversification.Second,somescenicspotsbecamefamousandprofessionaltravelingservicemenappearedwithdevelopmentofmoderntouristindustry.Third,somepreliminaryprofessionaltravelingorganizationswereformed.Fourth,travelingbooksandfull-timetouristguidesturnedup.
KeywordtourisminMingandQingdynasties;travelingways;characteristic;modernized
在我國古代,“旅”和“游”是兩個相互獨(dú)立的概念,兩者之間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旅”主要是指商人或者是旅館,而“游”則主要是指今天的旅游者。實際上,古代著作《周易正義》《楚辭·遠(yuǎn)游》《尚書·皋陶漠》《廬山遙寄盧侍卿虛舟》等,其中均出現(xiàn)了有關(guān)“旅”或“游”的使用。但是旅游兩個字真正地組合一起,則出現(xiàn)于我國南北朝時期,南朝詩人沈約在其詩詞《悲哉行》中記載:“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此詩詞中旅游的含義已與現(xiàn)代旅游的含義相差無幾。而到了唐代以后,旅游一詞得到了廣泛的運(yùn)用,韋應(yīng)物在詩詞《送姚孫還河中》、白居易在詩詞《宿桐廬館同崔存度醉后作》中均體現(xiàn)了對旅游詞組的運(yùn)用,他們將旅游解釋成為一種出游或游覽方式。
由于歷史、文化、社會背景等方面的差異,古代的旅游與現(xiàn)代旅游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古代旅游所表現(xiàn)出來的文化活動類型主要是基于對古代社會生活的反映,因此古代的旅游往往表現(xiàn)出與時代相互適應(yīng)的特征或特色。在本文的研究中,以明清時期的旅游文化活動為研究對象,分析明清時期旅游文化所表現(xiàn)出來的特色,有利于后人對于明清時期旅游文化活動的深入了解。
一、明清時期的旅游者構(gòu)成及主要活動
明清時期的旅游者按照其職業(yè)劃分主要包含四大類,即貴族官僚、文人雅士、商人和市井鄉(xiāng)民,這四種旅游者的旅游內(nèi)容、旅游方式和旅游動機(jī)均有顯著的差異。
1.貴族官僚的旅游活動。從古至今,官職是體現(xiàn)一個人價值的重要杠桿,表現(xiàn)在古代旅游方面,官職其中之一的作用是,借助于公干的機(jī)會進(jìn)行旅游。官員在旅游的過程中不需要擔(dān)負(fù)旅游費(fèi)用即可游山玩水。明清時期,大量的官員憑借職位的便利進(jìn)行旅游,他們成為明清時期旅游的主要構(gòu)成者,宦游也成為明清時期最為主要的旅游方式之一。按照官員任職的差異,明清時期的官宦旅游主要劃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官員利用守衛(wèi)疆土的便利,在轄區(qū)之內(nèi)進(jìn)行游玩;二是官員利用上任、覲見、公派等長距離旅游的機(jī)會,借助于明清時期的國家驛站系統(tǒng),在沿途周邊進(jìn)行游覽;三是官員卸任之后,回本籍或者是在祖國的大好河山中游覽天下。其中,第一種旅游方式是明清時期官員守土的共有特征。
貴族官僚旅游的優(yōu)點(diǎn)在于使得明清時期的文化在旅游中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其劣勢在于官宦貴族利用旅游方式進(jìn)行結(jié)群,形成復(fù)雜的關(guān)系網(wǎng),影響著地方資源和利益的分配。另外,官宦旅游浪費(fèi)國家大量的財政資源,造成國家和當(dāng)?shù)匕傩諒?qiáng)大的財政負(fù)擔(dān),強(qiáng)烈擾亂了地方居民安定。
2.文人雅士的旅游活動。與官宦旅游有明顯的不同,文人雅士往往強(qiáng)調(diào)個人的獨(dú)韻,因此其旅游方式和旅游的內(nèi)容,往往是平常百姓和商人以及官員所不感興趣的。在史學(xué)界,關(guān)于文人雅士的界定也有很大的差異。從廣義的含義來講,文人雅士主要是指一些詩詞、小說、戲劇的作者,而本文則主要基于明清時期的社會現(xiàn)實,將文人雅士界定為一種狹義的群體,即一些考取功名的知識分子以及閑居世外的清逸雅士。
明清時期的考試制度,主要是采用了三年為一周期的鄉(xiāng)試和會試制度,考試地點(diǎn)均分布于各省或者是南北兩京,因此每年學(xué)子進(jìn)行考試需提前準(zhǔn)備,長途結(jié)伴而行,這也成為當(dāng)時學(xué)子趕考的特點(diǎn),而這一科舉考試制度對明清時期的文人雅士旅游產(chǎn)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一是表現(xiàn)為一部分趕考士子往往借助寺廟的形式進(jìn)行借讀,順便游覽廟宇風(fēng)光;二是趕考士子利用結(jié)伴而行的形式,在沿途尋芳訪勝;三是趕考完成之后,一部分士子往往會在應(yīng)考的城市宣泄放縱。這三種不同的旅游方式均對明清時期的旅游產(chǎn)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在學(xué)子趕考的過程中,通過長時間的準(zhǔn)備進(jìn)行沿途旅游,一方面可以增強(qiáng)自我游玩興趣,還可以增加士子個人的知識和見聞,為考試增添新的思路。而結(jié)伴而行的方式往往有利于增強(qiáng)旅游中學(xué)子之間的文思交流,尤其是一些常年拘束在鄉(xiāng)下的學(xué)子,初到京城繁華之地,創(chuàng)作的思路被打開;而考試結(jié)束以后,趕考士子往往是如釋重負(fù),其旅游方式則是通過游覽當(dāng)?shù)孛麆倩蛘呤菍せ▎柫绞竭M(jìn)行宣泄。
文人雅士聚集旅游是古代一種極為常見的旅游方式,很多志同道合的文人士子聚集在一起,圍繞感興趣的話題而展開討論,進(jìn)行集會或?qū)嵤蕵坊顒樱诤艽蟪潭壬洗龠M(jìn)了文化的交流和知識的傳遞。但同時一些文人雅士聚集在一起以文會友,有的為了某種政治目的進(jìn)行聯(lián)誼,這對古代的政權(quán)產(chǎn)生了較為重要的影響。
3.商人的旅游活動。明清時期,商品經(jīng)濟(jì)得到了快速發(fā)展,使得商人旅游也呈現(xiàn)出繁榮發(fā)展趨勢,商人成為明清時期旅游者的重要組成部分。很多商人往往在行商的過程中專門繞道旅游,販貨成為部分商人旅游的借口,這些商人或者是為人之色,或者是為景之色。在旅游過程中,商人是旅游活動的積極策劃者,也是旅游活動的積極推動者,他們往往帶著家眷,甚至帶著一群名妓進(jìn)行郊外訪游,美色成為商人旅游的調(diào)劑品。
明清時期商人在經(jīng)營過程中面臨著較大的商業(yè)風(fēng)險和商業(yè)時機(jī),因此,商人們愛好旅游是縱情娛樂的一種調(diào)整方式。尤其是商人到達(dá)外出經(jīng)商的一個陌生環(huán)境中,在外出門的商人往往會降低日常道德約束,因此有人批判明清時期商人旅游存在著道德弱化的傾向問題。例如,程春宇在《士商類要》中就對商人的夜游進(jìn)行規(guī)勸。由于商人經(jīng)營往往伴隨較高的風(fēng)險,因此明清時期商人旅游更傾向于對寺廟景觀的旅游,這促進(jìn)了明清時期寺廟文化的繁榮和發(fā)展。從整體來看,明清時期隨著商品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商業(yè)旅游已經(jīng)演變成為一種較為頻繁的旅游方式,商人旅游豐富了明清時期城市生活的內(nèi)容,同時也帶動了商業(yè)旅游的繁榮。
4.市井鄉(xiāng)民的旅游活動。明清時期的市民主要居住于城市,因此清新自然的近郊區(qū)成為他們旅游的常駐之地,尤其是在每年的清明節(jié)前后,踏青郊游成為市民旅游的主要活動;另外,城外莊園狩獵打圍是明清時期富豪們主要熱衷的項目,《醒世姻緣傳》中就對晁大舍邀請富豪賞雪飲酒的場景進(jìn)行了描述;受到城市文化和風(fēng)俗的影響,明清時期各地的旅游節(jié)日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但主要的節(jié)慶有上元節(jié)、清明節(jié)、端午節(jié)、中元節(jié)等。在明清市井鄉(xiāng)民的旅游者組成中,還有一部分特殊的旅游群體,即幫閑和老白賞,均是一些蹭人助自己游覽并騙取錢財,替游客招聚賭,與游客一起游覽風(fēng)景、飲酒作樂相湊同行的人群。
受制于社會經(jīng)濟(jì)條件、傳統(tǒng)觀念、風(fēng)俗習(xí)慣的影響,明清時期的鄉(xiāng)村居民旅游發(fā)展相對落后,一些鄉(xiāng)村居民主要是在節(jié)慶的時候進(jìn)城觀賞風(fēng)景,例如元宵節(jié)觀燈,或者是共賞城市煙花美景。而鄉(xiāng)村居民比較熱衷的游樂項目主要是觀社火、參加當(dāng)?shù)氐膹R會,或者是進(jìn)行燒香聚會等幾種常見形式。
二、明清時期旅游的近現(xiàn)代化發(fā)展特色
盡管明清時期的旅游活動受到社會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現(xiàn)實約束,具有其自身的現(xiàn)實特點(diǎn),但在明清時期,尤其是明清中期以后,已經(jīng)形成了類似于近現(xiàn)代化的旅游特色,主要表現(xiàn)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明清時期,各階層旅游呈現(xiàn)大眾化發(fā)展趨勢,表現(xiàn)為上至王室貴族下至市井鄉(xiāng)民、商人等多種階層。而旅游的動機(jī)呈現(xiàn)出多樣化特點(diǎn),主要為文化交流動機(jī)、山水探勝動機(jī)、社交訪友動機(jī)、宗教信仰動機(jī)等多種類型。這也是明清時期旅游近現(xiàn)代化的重要表現(xiàn)之一。
第二,明清時期已經(jīng)形成了一些著名的旅游景點(diǎn),并且伴隨著近代化的商業(yè)旅游業(yè)發(fā)展,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一些專業(yè)的旅游服務(wù)者。例如,王士性在《廣志繹》中就記載:“西湖業(yè)已為游地,則細(xì)民所藉為利,日不止千金,有司時禁止,固以易俗,但漁者、舟者、戲者、市者、酩者,咸失其本業(yè),反不便于此輩也。”可見,當(dāng)時的杭州西湖已經(jīng)成為一個商業(yè)旅游發(fā)展中心城市,商業(yè)旅游發(fā)展相當(dāng)繁榮,收入“日進(jìn)千金”,同時伴隨著旅游發(fā)展,西湖的飲食服務(wù)業(yè)也得到關(guān)聯(lián)發(fā)展,同時出現(xiàn)了一些旅游服務(wù)從業(yè)者。小說《豆棚閑話》中記載,虎丘是因為旅游而得以發(fā)展壯大的城市,隨著旅游業(yè)的發(fā)展,虎丘旅游業(yè)發(fā)展增加了百姓的收入,并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崗位需求。
第三,明清時期已經(jīng)形成了初步的專業(yè)旅游組織,這類似于現(xiàn)代的旅游組織團(tuán)體。明清時期,以宗教朝覲為名形成了專業(yè)組織,例如民間朝圣進(jìn)香的民間信仰組織香會,這與現(xiàn)代的進(jìn)香團(tuán)體或者旅行社有著相似之處。明清時期的香會在旅游前期會進(jìn)行一部分旅游策劃,同時還準(zhǔn)備各種旅途食宿,并配有固定的合作旅店,這與現(xiàn)代旅行社的功能有所類似。
第四,明清時期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服務(wù)于旅游活動的旅游書籍以及專職導(dǎo)游群體。明清時期,為了滿足社會各階層旅游活動的需要,出現(xiàn)了大量的旅游書籍,以指導(dǎo)大眾旅游活動,例如《天下水陸路程》、《天下路程圖引》、《客商一覽醒迷》、《新刻京本華夷風(fēng)物商程一覽》等等。這些書籍均對旅游交通、旅游資源、旅游地天氣等進(jìn)行了記載。具有旅游指南性質(zhì)的各種“路程”刊行,是明清旅游近代化的又一重要標(biāo)志。
參考文獻(xiàn):
[1]周海燕.明清徽州文人士大夫旅游研究[J].安徽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13(4).
[2]王子超.明清時期山水怡性旅游的自然回歸[J].南都學(xué)壇,2013(1).
[3]黃一斕.明晚期女性熱衷宗教節(jié)日旅游之原因——基于同期小說的考察[J].江蘇社會科學(xué),2011(6).
[4]徐永斌.《鏡花緣》與旅游文化[J].明清小說研究,2010(1).
[5]宋立中.明清江南婦女“冶游”與封建倫理沖突[J].婦女研究論叢,2010(1).
[6]宋立中.明清江南婦女游風(fēng)述論[J].福建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09(6).
[7]周建波,孫淮寧.明清時期的文化消費(fèi)[J].社會科學(xué)家,2009(8).
[8]魏向東.晚明旅游活動的經(jīng)濟(jì)滲透——關(guān)于晚明旅游近代化的商榷[J].社會科學(xué),2009(3).
[9]陳寶良.明代的商貿(mào)旅游[J].中州學(xué)刊,2007(5).
篇2
一、“本土化”視域下理論探索與實證研究有效結(jié)合
“中國傳統(tǒng)經(jīng)濟(jì)再評價”討論的基點(diǎn)是“反思”、“回應(yīng)”西方學(xué)界對中國傳統(tǒng)經(jīng)濟(jì)的認(rèn)識與評價。西方學(xué)界討論的核心問題是在西方資本主義進(jìn)入中國之前,中國傳統(tǒng)經(jīng)濟(jì)究竟是發(fā)展還是停滯的重大問題;認(rèn)識的角度無論是“西歐中心論”、“中國中心論”、“多中心論”、“無中心論”等,都是西方學(xué)者總結(jié)、批判與再批判的結(jié)果;研究的方法主要是中西比較的方法。這無疑開闊了中國學(xué)者的視野,對進(jìn)一步認(rèn)識中國傳統(tǒng)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有重大促進(jìn)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一些問題,并成為“再評價”爭論的焦點(diǎn):一是西方傳統(tǒng)與中國實際問題;二是評價的標(biāo)準(zhǔn)問題;三是核心概念問題。隨著討論的深入,有些學(xué)者認(rèn)識到有必要建立符合中國實際的評價標(biāo)準(zhǔn),應(yīng)從中國傳統(tǒng)文獻(xiàn)出發(fā)重新檢討、發(fā)掘相關(guān)理論與概念。在充分吸收國外先進(jìn)理論、概念與方法的基礎(chǔ)上,結(jié)合國內(nèi)外既有研究成果,走“本土化”研究之路成為必然。
“農(nóng)商社會”、“帝制農(nóng)商社會”與“富民社會”是北京師范大學(xué)特聘教授葛金芳先生、東北師范大學(xué)趙軼峰先生與云南大學(xué)林文勛先生吸收國內(nèi)外最新學(xué)術(shù)成果,結(jié)合中國實際建立起來的關(guān)于中國傳統(tǒng)經(jīng)濟(jì)發(fā)展問題的“本土化”解釋模式的嘗試。以上諸論對中國傳統(tǒng)經(jīng)濟(jì)是發(fā)展還是停滯,及發(fā)展的限制性因素等都有自己的評估。“農(nóng)商社會”說認(rèn)為,宋元明清江南區(qū)域商品經(jīng)濟(jì)得到很大的發(fā)展,形成了農(nóng)商并重的局面,但是受戰(zhàn)亂、生態(tài)及制度等的影響,中國傳統(tǒng)經(jīng)濟(jì)未能轉(zhuǎn)型為現(xiàn)代工業(yè)文明。“帝制農(nóng)商社會”說認(rèn)為,明清社會發(fā)生了諸如市場空前繁榮、社會分層體系簡單化等一系列“歷史性”的變遷,但受制于制度和傳統(tǒng)社會諸多結(jié)構(gòu)性要素,整個社會呈現(xiàn)出經(jīng)濟(jì)社會活性和政治集權(quán)共同增強(qiáng)的特點(diǎn),并不包含社會組織方式及科學(xué)技術(shù)的根本改進(jìn),這種社會是一種“帝制農(nóng)商社會”。“富民社會”認(rèn)為中唐特別是宋代以來崛起的“富民”階層,雖然從根本上改變了宋元明清諸朝的階級基礎(chǔ)和社會結(jié)構(gòu),但并沒有成為帝制社會的離心力量,而是通過科舉等途徑成功與“士”、“官”階層對接。以上諸說從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肯定了宋元明清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但是同時強(qiáng)調(diào)有諸多其他因素決定了中國社會作為整體,并未與西方社會處于同一演進(jìn)軌道上,所謂中國“工業(yè)革命”、“現(xiàn)代化”進(jìn)程的前景在當(dāng)時也尚渺茫。
在本次會議上,葛金芳先生、趙軼峰先生、林文勛先生、薛政超先生、張錦鵬女士、刁培俊先生等從不同視角進(jìn)一步論證了“農(nóng)商社會”、“帝制農(nóng)商社會”與“富民社會”。葛金芳先生從交易費(fèi)用的視角,重新解釋了南宋臨安工商業(yè)發(fā)展的原因,指出便利的交通運(yùn)輸、可靠的交易慣例和生產(chǎn)空間的相對集中在降低交易成本,促進(jìn)臨安工商業(yè)繁榮中具有重要作用。趙軼峰先生指出,明清時代的商業(yè)發(fā)展并沒有消解帝制國家權(quán)力,國家權(quán)力與商業(yè)相互滲透,衍生出一種帝制體系與商業(yè)發(fā)展基本契合的結(jié)構(gòu)形態(tài)。云南大學(xué)林文勛、薛政超先生認(rèn)為明清形成的“士紳社會”是中國古代“富民社會”的最高和最后階段。云南大學(xué)張錦鵬女士從投資、購買、售賣三個方面論述了“富民”是如何通過財富力量改變身份進(jìn)而成為重要社會力量的過程。廈門大學(xué)刁培俊先生著重探討了中國“富民”如何縱深發(fā)展的可能。
此外,與會學(xué)者還對傳統(tǒng)經(jīng)濟(jì)中商人群體、鄉(xiāng)村經(jīng)濟(jì)的商品化、市場等問題進(jìn)行了深入的探討。河北大學(xué)劉秋根先生通過對遺存的大量“山西商人書信”的深入研究,以“汾陽皮張商人”為個案,分析了明清“本土化”的商業(yè)概念與金融體系。北京師范大學(xué)陳濤先生以特定地區(qū)“甫里”為例,說明了唐代后期蘇州鄉(xiāng)村經(jīng)濟(jì)的商品化及其原因與特點(diǎn)。北京師范大學(xué)李志英女士從病蟲害的獨(dú)特視角考察了民國時期農(nóng)產(chǎn)品的商品化及其生態(tài)影響。刁培俊先生主要從文獻(xiàn)檢討、方法思考等方面入手,分析了史料中所呈現(xiàn)的對福建路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截然相反評價的原因,認(rèn)為宋元福建路經(jīng)濟(jì)雖有發(fā)展,但仍存在內(nèi)部發(fā)展不平衡等問題,應(yīng)深入檢驗、批判性審視歷史文獻(xiàn),避免陷入“選精”、“集粹”的陷阱。云南大學(xué)田曉忠先生綜述了20世紀(jì)以來學(xué)人對明以前中國古代傳統(tǒng)市場的研究。
二、斷代研究與貫通研究無所偏廢
對明清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的討論,一直是國內(nèi)外學(xué)術(shù)界的重要論題之一。“明清停滯論”和“宋代高峰論”是20世紀(jì)90年代以前非常有影響力的兩種學(xué)說。90年代以后,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經(jīng)濟(jì)研究所和美國“加州學(xué)派”,都反對“明清停滯論”和“宋代高峰說”,認(rèn)為清代是傳統(tǒng)中國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高峰。“中國傳統(tǒng)經(jīng)濟(jì)再評價”研討會的緣起也主要與西方學(xué)者與中國學(xué)者提出的對明清(主要是清前期)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的新論有關(guān),因此關(guān)于明清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的討論無疑成為歷次討論的焦點(diǎn)。本次會議打破了以明清停滯與發(fā)展、宋代與清代孰為高峰等既有論爭模式的局限,跳出了以研究明清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問題為主的核心圈子,用更加貫通的視角研究中國傳統(tǒng)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這應(yīng)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農(nóng)商社會”、“帝制農(nóng)商社會”和“富民社會”,雖說主要是針對唐宋以后中國社會政治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的認(rèn)識理論,但以上諸說都是建立在對中國傳統(tǒng)經(jīng)濟(jì)有一宏觀認(rèn)識的架構(gòu)之上的。葛金芳先生認(rèn)為中國古代經(jīng)歷了一個由“農(nóng)業(yè)社會”到“農(nóng)商社會”的發(fā)展歷程,并最終會走向現(xiàn)代的“工商社會”。趙軼峰先生認(rèn)為中華文明基本結(jié)構(gòu)形態(tài)可以區(qū)分為先秦時代的“王制”,秦至清的“帝制”以及民國以來的“共和制”。林文勛先生從社會群體對社會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階級結(jié)構(gòu)及政治結(jié)構(gòu)的影響出發(fā)”將古代社會概括為漢唐的“豪民社會”,唐宋以來的“富民社會”,以及近代的“市民社會”。
河南大學(xué)李振宏先生從貫通的角度,對秦至清皇權(quán)在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的專制作了系統(tǒng)性的剖析,認(rèn)為皇權(quán)在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具有獨(dú)占性,皇權(quán)對國土上的一切物產(chǎn)具有不容置疑的絕對權(quán)力,臣民沒有真正屬于自己的私有財產(chǎn)。山東大學(xué)劉玉峰先生認(rèn)為自春秋戰(zhàn)國“工商食官”格局被逐步打破后,中國古代工商業(yè)整體上形成了官營國有工商業(yè)和私營私有工商業(yè)并存的“官私二元結(jié)構(gòu)”,進(jìn)入封建帝制時代,私營私有工商業(yè)又可再分為貴族官僚私營工商業(yè)和民間私營工商業(yè),因此將其結(jié)構(gòu)形態(tài)概稱為“整體官私二元、實際組成三類”。
三、經(jīng)濟(jì)因素與非經(jīng)濟(jì)因素全面關(guān)照
傳統(tǒng)經(jīng)濟(jì)發(fā)展中的經(jīng)濟(jì)概念如勞動生產(chǎn)率、畝產(chǎn)量、墾田數(shù)、人口等一直是此前討論的重點(diǎn)。隨著討論的深入,必然要涉及政治、制度等非經(jīng)濟(jì)因素,這也被認(rèn)為是評估傳統(tǒng)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的另一個重要突破口,但治經(jīng)濟(jì)史的學(xué)者尤其是西方學(xué)者,他們對中國傳統(tǒng)政治體制與制度等認(rèn)識的準(zhǔn)確程度,卻是值得懷疑的。“加州學(xué)派”就有學(xué)者在考慮經(jīng)濟(jì)數(shù)據(jù)的同時,也將中國的各種體制、制度等考慮在內(nèi),這無疑是明顯的進(jìn)步,但得出的結(jié)論卻讓人詫異,認(rèn)為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政令和地方實施屬于不同的系統(tǒng),政府只要與地方精英們很好的結(jié)合起來,就能把國家治理好,并進(jìn)一步認(rèn)為中國絕不是專制主義。也有法國的漢學(xué)家認(rèn)為中國古代講“民本主義”,認(rèn)為中國政治沒有民主并不是問題。以上觀點(diǎn)包含對中國傳統(tǒng)政治的一些誤解,但影響很大,在國內(nèi)也有不少追隨者。因此,在研究中國傳統(tǒng)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過程中,加強(qiáng)對非經(jīng)濟(jì)因素的正確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本次會議對傳統(tǒng)經(jīng)濟(jì)發(fā)展中的非經(jīng)濟(jì)因素如國家權(quán)力、思想觀念等進(jìn)行了廣泛的討論。如前揭李振宏先生對秦至清皇權(quán)專制社會進(jìn)行了經(jīng)濟(jì)史方面的論證,指出皇權(quán)對國土上的一切物產(chǎn)具有不容置疑的絕對權(quán)力,臣民沒有真正屬于自己的私有財產(chǎn)。蘇州大學(xué)臧知非先生認(rèn)為國家力量在戰(zhàn)國秦漢時代私營工商業(yè)發(fā)展演變過程中起著關(guān)鍵作用,是國家力量導(dǎo)致了私營工商業(yè)跌宕起伏。首都師范大學(xué)李華瑞先生通過對宋代的商業(yè)和高利貸資本的形成、具體活動、投資方向及地主、官僚、商人三位一體關(guān)系形成的論述,說明了宋代社會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歷史走向。趙軼峰先生認(rèn)為,以往許多研究夸大了商業(yè)與帝制體系的矛盾性,權(quán)力與市場相互滲透,明清時代的商業(yè)與帝制國家體系是并同發(fā)展的。
對于經(jīng)濟(jì)發(fā)展中的思想觀念等因素,南京大學(xué)范金民先生從《史記?貨殖列傳》出發(fā),對司馬遷的商業(yè)思想,及其筆下的商人所表現(xiàn)出的商業(yè)智慧和商業(yè)倫理等進(jìn)行深入分析,指出這是值得深入總結(jié)的商業(yè)精神財富。李華瑞先生對中國古代“重本抑末”的傳統(tǒng)政策與經(jīng)濟(jì)觀念中的變與不變的因素進(jìn)行了深入分析,認(rèn)為周秦至隋唐根深蒂固的“重本抑末”政策,在宋代有所松弛,出現(xiàn)了認(rèn)可盈利的思想,但這仍很難突破帝制國家“重本抑末”的傳統(tǒng)政策,對這種“變”的因素不能估計過高,宋代商品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受到政治的強(qiáng)烈干預(yù),很大程度上是財政政策的衍生發(fā)展,不完全具有商品經(jīng)濟(jì)的獨(dú)立性質(zhì)。云南大學(xué)黃純艷先生則從宋人水上信仰及其變化的角度考察了宋代商品經(jīng)濟(jì)和海上貿(mào)易發(fā)展。
四、會議的成果、問題與啟示
本次會議名家云集,討論熱烈,成果斐然。這主要表現(xiàn)在:第一,通過熱烈討論,與會學(xué)者一致認(rèn)為,國家力量等非經(jīng)濟(jì)因素在中國傳統(tǒng)經(jīng)濟(jì)發(fā)展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第二,視野更加開闊,角度更加新穎。本次會議對傳統(tǒng)經(jīng)濟(jì)的評價突破了經(jīng)濟(jì)史的視野,用政治的、生態(tài)的和思想的更加開闊的視野去認(rèn)識傳統(tǒng)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就經(jīng)濟(jì)史本身而言,如交易費(fèi)用等概念的引入也對考察傳統(tǒng)經(jīng)濟(jì)發(fā)展有重要意義。第三,本次會議的與會學(xué)者都是各方名家,都有深厚的學(xué)養(yǎng),他們在對中國傳統(tǒng)政治、經(jīng)濟(jì)等的整體把握和史料的解讀上更加準(zhǔn)確,成果具有很強(qiáng)的信服力。
在取得可喜成果的同時,與會學(xué)者也指出了一些需要注意的問題。第一,不能忽略全球史的視野。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xué)平先生指出,傳統(tǒng)經(jīng)濟(jì)的研究應(yīng)有全球史的關(guān)懷,多注意與海外的聯(lián)系,研究國內(nèi)市場時不能忘了外部世界,明清新作物的引進(jìn)、白銀流入等都對中國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南開大學(xué)李治安先生也說,“農(nóng)商社會”的發(fā)展,絕對與海上絲綢之路的發(fā)展有莫大的關(guān)系。臺灣東吳大學(xué)徐泓先生也指出本次會議海外市場如朝貢貿(mào)易、海外貿(mào)易等談的不多。第二,不能過分強(qiáng)調(diào)非經(jīng)濟(jì)因素。對經(jīng)濟(jì)發(fā)展中的非經(jīng)濟(jì)因素的論述是本次會議的重要成果之一,但是劉秋根先生警示說,經(jīng)濟(jì)發(fā)展本身還是有客觀規(guī)律可循的,對經(jīng)濟(jì)發(fā)展中的非經(jīng)濟(jì)因素不能強(qiáng)調(diào)的太過,顯然,這應(yīng)是非常及時的提醒。針對兩種認(rèn)識傾向,葛金芳先生指出,雙方各有所據(jù),但論述時也一定要看到局部與整體,長期與短期的關(guān)系問題,要兼顧經(jīng)濟(jì)因素與非經(jīng)濟(jì)因素。
篇3
一、有關(guān)“反歐洲中心主義”及其對明清歷史重估的理解
歐美人看歷史中國的好與壞,撇開因人而異、從來就非鐵板一塊的復(fù)雜因素外,從主流意識上說,它是因時而變,重心多次發(fā)生變化。無論是在中世紀(jì)晚期、啟蒙時代或者“工業(yè)革命”時代,時高時低的評價,多般取決于他們自己的境遇,“以我為主”,為其所用。根本性的變化發(fā)生在18世紀(jì)中葉到19世紀(jì)中葉,評價的取向與重點(diǎn)發(fā)生重大轉(zhuǎn)移,才有了今天所說的“歐洲中心主義”居主流的中國觀。19世紀(jì)60年代后,中日兩國學(xué)界對此的反應(yīng)頗為不同。似乎日本學(xué)界也有“以我為主”的意識,在“明治維新”成功后,對“歐洲中心主義”有所抗?fàn)帲小皷|洋史”等等話題的提出。
同樣,20世紀(jì)后半期開始發(fā)生的對“歐洲中心主義”的批判,轉(zhuǎn)而對明清歷史有諸多好評,中國學(xué)者也首先應(yīng)當(dāng)設(shè)法尋求理解。這里,除了西方社會內(nèi)在的思想分化或思想變遷以外,20年來中國經(jīng)濟(jì)的高速發(fā)展,也極大地幫助了一些“反歐洲中心主義”者樹立信心。因此,由他們引起的眾多“問題意識”,除了歷史中國與資本主義世界的關(guān)聯(lián)外,也還包含了歷史中國與現(xiàn)實中國、現(xiàn)實世界的關(guān)聯(lián)。對后一點(diǎn),有些史家注意不夠。
“反歐洲中心主義”史學(xué)的代表性的人物、多卷本《現(xiàn)代世界體系》的作者華勒斯坦,在《中國與歷史資本主義》一書里,通過其寫作的長文,發(fā)出了對現(xiàn)實的強(qiáng)烈反詰:“西方是否真的興起過?或者說西方事實上是衰退的?它是否曾是一個奇跡,或者是一個沉重的病癥?它是一項成就,或者是嚴(yán)重的失誤?是理性的,或者是非理性的實現(xiàn)?是不尋常的突破,或者是不尋常的崩潰?我們是否需要了解其他文明以及其它歷史系統(tǒng)何以會對現(xiàn)代資本主義的出現(xiàn)加以限制?而這是預(yù)先設(shè)定好的狀態(tài),或者純粹是意料之外的?(注:卜正民、Blue主編:《中國與歷史資本主義:漢學(xué)知識的系譜學(xué)》,第二章“西方、資本主義與現(xiàn)代世界體系”(華勒斯坦),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最后一句,特別提醒:對于抑制資本主義出現(xiàn)的文明系統(tǒng)(華氏顯然首先是指中國),要另眼相看。這里,華勒斯坦要表達(dá)的是有沒有可能走出與西方資本主義不同的另一條歷史通道。至今為止,國內(nèi)贊同“反歐洲中心主義”對中國歷史重新評價的人,沒有注意到這一思想背后的思想傾向,似是不應(yīng)有的疏忽。因為,它關(guān)系到我們對這種史學(xué)思潮可能產(chǎn)生的現(xiàn)實導(dǎo)向,有沒有清醒的認(rèn)識,以及如何明智地應(yīng)對。
我們對“反歐洲中心主義”的應(yīng)對,也可以從兩個層面來進(jìn)行研討。
第一,基于事實的層面:“反歐洲中心主義”有強(qiáng)烈的重新解讀歷史的沖動,因此他們在重新解讀甚至想顛覆歐洲史舊體系的時候,特別注意吸收近年歐洲史研究對其有用的新成果。同樣,他們也對中國歷史的光明面、積極的成果非常敏感,很想把被“歐洲中心主義”遮蔽了的東西,展示于陽光之下。這兩者對我們都有歷史認(rèn)識方面糾偏補(bǔ)全的沖擊作用。由此啟發(fā),若要全面地進(jìn)行明清史再認(rèn)識,則需要中國歷史與歐洲歷史的雙向互動,難度將大大增加。
由于“反歐洲中心主義”的提醒,我們確實有必要重新反思,力求更全面地看待中國的歷史與文化。但是,應(yīng)該引起警惕的是,不能以一偏糾一偏。對“反歐洲中心主義”背景下出現(xiàn)的許多新的歷史判斷,我們從歷史的經(jīng)驗事實層面上需要獨(dú)立地省視,應(yīng)該有自己的主見,注重實證,拿出我們自己的東西。在實證方面,我們應(yīng)該擁有西人難以替代的本土優(yōu)勢。這種新的西潮,應(yīng)該成為激勵我們更細(xì)致全面考察國史的強(qiáng)大動力,而決不是跟風(fēng)而進(jìn),單純變成另一聲音的消極代言人。
第二,基于價值認(rèn)同的層面:無論叫“資本主義”還是叫“現(xiàn)代性”,都不是完美的,它本身已經(jīng)帶來的社會病癥,或者可能有的未來隱患,“反歐洲中心主義”者的棒喝,并非全然是危言聳聽。但正如有的學(xué)者所驚嘆的,“反歐洲中心主義”斷然丟棄長期學(xué)術(shù)積淀形成的歷史比較“規(guī)則”,我們對歷史發(fā)展的把握,會不會變得無所適從?至于更宏觀的道德訴求,諸如物質(zhì)與精神、效率與公平等等的不和諧,恐怕是一個永恒性的難題。在史學(xué)上過度的執(zhí)著,會不會再度激活出新的“烏托邦”傾向?例如效率與公平的問題,后來有些國家找到了較好的內(nèi)部解決辦法,但它往往又是以把貧困包袱甩給別的國家為代價,轉(zhuǎn)換成國際性的困局,從人類歷史全局來看,仍然是一個大難題。因此,當(dāng)我們進(jìn)入歷史評估時,往往需要有歷史主義與價值觀的平衡,而非執(zhí)著一端。
歷史學(xué)的特點(diǎn)之一就是需要冷峻地“秉筆直書”,需要有一種超乎情感之上的,實證地描述歷史變遷的職業(yè)意識——不論中西,任何歷史都是連續(xù)的,是連續(xù)中的發(fā)展。歷史軌跡的明晰,是每個國家發(fā)展自己的基礎(chǔ)。在這一意義上,歷史學(xué)獨(dú)立的認(rèn)識價值,就在于它是為“現(xiàn)在”而提供“過去”的情景,過分注重對“未來”的設(shè)計,會使歷史學(xué)走向“過度詮釋”的歧途。但我們也無法否認(rèn),價值觀的分歧,必然有形無形地影響著史家對歷史描述特別是評估的主觀取向,這是史學(xué)上的一個吊詭。學(xué)術(shù)上如何處理,也需要史學(xué)界進(jìn)一步研討。
二、關(guān)于明清歷史再認(rèn)識視角的變化
1840年開始,中國一再受挫于列強(qiáng)的“船堅炮利”,原有“天朝優(yōu)越”的自信力終于遭遇到了嚴(yán)重的動搖。史學(xué)家從“物競天擇,優(yōu)勝劣汰”的法則中,感受到了中華民族有難以自存以至亡國滅種的危險。在這樣的情景下,回溯明清歷史,關(guān)注對政治史的批判,認(rèn)定明清已經(jīng)走到“前現(xiàn)代”的盡頭,處于“長期停滯”的狀態(tài),占據(jù)著主流的地位。現(xiàn)在的“反歐洲中心主義”,恰恰是針對著這種史學(xué)傾向而來的挑戰(zhàn)。
當(dāng)前,我們對明清史進(jìn)行再認(rèn)識,自然就會產(chǎn)生許多新的檢討角度。擇其要者,大致有兩方面的觀點(diǎn)值得注意:
首先,對“革命”做法的檢討,覺得它對自己國家的歷史缺乏同情地理解的態(tài)度——一個國家,不要說是一個有數(shù)千年歷史的大國,它的存在,總有一種“歷史精神”在支持;它曾經(jīng)采取的治國方略,總有它存在的一定“合理性”,也包括當(dāng)時不得不如此做的原因。否則,它的存在,就成為不可理解的怪物,而想要前進(jìn),要擺脫困局,也不容易找準(zhǔn)入手的路向。推倒一切重來的“革命”不是好辦法,后遺癥嚴(yán)重。受此苦痛,史家意識到有必要秉著實事求是的精神,更全面、更深入、更細(xì)致地鑒別分析明清歷史的實際運(yùn)作狀態(tài),特別是挖掘這些運(yùn)作的“歷史土壤”有否改良的可能,而非脫胎換骨,“只爭朝夕”。這種時候,久被壓抑的歷史連續(xù)性問題,與過去總期望歷史突變不同,成為了考察歷史不可或缺的另一視點(diǎn)。
這里,思考的難點(diǎn),是如何把“合理性”變成動態(tài)的概念,由此回答連續(xù)性與社會變革的契合關(guān)系在哪里?否則,“長期停滯論”很難以從根本上被驅(qū)趕出去。易言之,當(dāng)變革實際上還沒有獲得根本性的突破之前,“長期停滯”的提示,在思考中國長時段歷史上,會不會仍然有其認(rèn)識論上的價值?
其次,與前述相聯(lián)系,歷史考察的視域必然地要有所擴(kuò)展。近20年來,這方面的進(jìn)步還是比較快的。原來史學(xué)的重心始終是政治史和人物史,現(xiàn)在經(jīng)濟(jì)史、文化史、社會生活史等等,都逐漸在深入展開。站在歷史前臺的是事件和人物,但事件與人物背后,或者說海平面以下的,是所有人與人相處關(guān)系的社會規(guī)則,以及由規(guī)則“叢林”構(gòu)成的結(jié)構(gòu)性歷史。因此在研討“前現(xiàn)代”或向現(xiàn)代過渡的時候,經(jīng)濟(jì)史與社會史的作用必然要被突出起來。總體上說,在中國,目前專史、斷代研究的力量較強(qiáng),成果多,而跨朝代的、連貫的研究難度高,一時還跟不上來。但少了這種延續(xù)性的通貫研究,就很難準(zhǔn)確定位斷代史,更難把握中國歷史自身的發(fā)展脈絡(luò),以及它連續(xù)而非斷裂式發(fā)展產(chǎn)生的路向。
在“現(xiàn)代化進(jìn)程”的討論中,曾經(jīng)有一種意見很受大家重視,那就是“整體的、全面的、協(xié)調(diào)的同步發(fā)展”。其實有哪個國家,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三者的“轉(zhuǎn)型”過程(請注意,這里說的是過程,而非最終結(jié)果)真正全面協(xié)調(diào)得那么順利?西方專家提出的靜態(tài)“現(xiàn)代化理論”不僅太理想,而且也與各國歷史實景不是很吻合。在各國現(xiàn)代化的實際運(yùn)行過程中,大凡經(jīng)濟(jì)推進(jìn)的欲求最強(qiáng),共通性也最大;其次是政治,政治與經(jīng)濟(jì)的匹配,恐怕有許多繞不過去的相關(guān)性,但其間不僅滯后是經(jīng)常有的,而且也表現(xiàn)出某種為許多理論家不可思議的妥協(xié)性與靈活性,兩者的匹配有本土的特點(diǎn);意識形態(tài)的通約程度就更要低一些,民族文化的特色往往會表現(xiàn)得最為強(qiáng)烈。因此,同是走向現(xiàn)代,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各種因子的匹配,具體的對應(yīng)組合方式,實際是相當(dāng)機(jī)靈和多樣的,是隨機(jī)性的,也可以說是創(chuàng)造性的。
現(xiàn)在我們已經(jīng)可以這樣說:現(xiàn)代化沒有標(biāo)準(zhǔn)模式。只有在各種模式的整體效果上,是可以比較甚至評判的。但即使效果最佳,其他國家也往往很難“克隆”,往往也是“一次性”的。因此,放到“前現(xiàn)代”中國歷史的考察中,學(xué)界提出了一個問題:在中國“前現(xiàn)代”社會中,有沒有應(yīng)該被發(fā)掘出來的“現(xiàn)代化資源”?假若有,是哪些?但從實際歷史運(yùn)行來觀察,又會糾纏于前述三者互動節(jié)奏的“合理性”在哪里?實際上卻缺乏明晰的判別依據(jù)。因為討論到突破的環(huán)節(jié),什么時候以什么最佳,史家多般無從主觀下斷。在這里,我們只能隱約地感到,歷史從來很難服從理論,而理論卻必須依據(jù)歷史來修正。這樣,問題又回到需要對中國歷史進(jìn)程進(jìn)行全盤性的總體思考上來。
三、關(guān)于明清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與不發(fā)展
如果回到長達(dá)五六百年明清經(jīng)濟(jì)史敘事的角度,確有相當(dāng)多的史料能夠證明,中國的經(jīng)濟(jì)主體——無論是工商業(yè)者還是農(nóng)民、手工業(yè)者——不缺乏經(jīng)濟(jì)理論的考量,也沒有停止過它自身的經(jīng)濟(jì)上升運(yùn)動,所謂“長期停滯”是一種受“歐洲中心主義”影響的偏見。但即使是“反歐洲中心主義”的史學(xué)家,也都認(rèn)為19世紀(jì)之后,中西歷史發(fā)生了“大分流”,中國淪入了真正的“停滯”。對于后一說法,我們似乎把它忽略了,未能認(rèn)真地予以正面回應(yīng)(注:參見王家范:《中國社會經(jīng)濟(jì)史面臨的挑戰(zhàn)——回應(yīng)〈大分流〉的“問題意識”》,《史林》,2004年第4期。)。
筆者以為,由于各斷代經(jīng)濟(jì)史微觀研究深入的結(jié)果,事實上已經(jīng)把“長期停滯論”撕成了碎片,傷痕累累。由宋入元,由元入明,由明入清,由前清至晚清,乃至晚清至民國,經(jīng)濟(jì)都不曾有過真正的停滯。微觀或斷代研究不足的地方,就是各代說各代的,不能顧此及彼,把連續(xù)發(fā)展在時段上系統(tǒng)化,用以論證中國經(jīng)濟(jì)發(fā)展整體狀態(tài)的趨向,揭示它的發(fā)展以及不發(fā)展兩面。但是,明清經(jīng)濟(jì)史的考察,即使發(fā)掘的光明面再多,也無法繞過一個巨大的障礙:如何通解過去說的“中國近代的落后”?這是與西方國家、與日本比,要否認(rèn)也很難。那么這種“落后”與“前現(xiàn)代”的歷史有沒有關(guān)聯(lián)?可以把這種原因仍然單純地歸咎于“列強(qiáng)侵略”(“反歐洲中心主義”就有類似暗示性的傾向)嗎?恐怕很少有人會這樣認(rèn)為。
對明清經(jīng)濟(jì)發(fā)展?fàn)顟B(tài)的估量,應(yīng)該說是比較困難的,主要談兩個問題:
其一,在歷史上,討論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水準(zhǔn),最容易成為觀察“社會進(jìn)步”與歷史分期標(biāo)志的是工具、能源以及由此帶來的資源開發(fā)、物質(zhì)增長的速率。它們都是非常醒目的標(biāo)志,判別上最不容易出現(xiàn)歧見。“前現(xiàn)代”與現(xiàn)代,在這方面的分水嶺便是以煤為能源的蒸汽機(jī)的使用(所謂“煤鐵聯(lián)合”)。中國“前現(xiàn)代”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主要是靠人力資源與手工機(jī)械。為什么它向現(xiàn)代“煤鐵聯(lián)合”的機(jī)械化生產(chǎn)轉(zhuǎn)變反應(yīng)慢而效率低?這是很需要費(fèi)心回答的大關(guān)節(jié)。
與此相關(guān)聯(lián),筆者以為許多學(xué)者對“人口”的正面效應(yīng)估計不足,不顧國情的不同,片面執(zhí)著于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人口多,當(dāng)然容易造成生產(chǎn)與消費(fèi)相沖的危機(jī);但人口多,強(qiáng)大的生存欲求,也能促發(fā)各種經(jīng)濟(jì)開發(fā)的努力,出現(xiàn)許多意想不到的發(fā)展總量的增長。因此,直到清亡為止,從“前現(xiàn)代”經(jīng)濟(jì)的特性上衡量,中國是不是到達(dá)了“人口危機(jī)”的臨界點(diǎn),變成了消極的因素,還是相反,勞動力豐厚與密集恰恰是宋以來經(jīng)濟(jì)能長期連續(xù)發(fā)展的基礎(chǔ)?這需要討論。當(dāng)然更關(guān)鍵的,被西方視為現(xiàn)代經(jīng)濟(jì)轉(zhuǎn)變標(biāo)志的那種技術(shù)進(jìn)步,為什么不能發(fā)生在中國,以及即使后來學(xué)到的、使用了,發(fā)展得也很慢,比日本都差得太多(我曾經(jīng)比較了19—20世紀(jì)中日棉紡織業(yè)的不同發(fā)展態(tài)勢(注:參見王家范:《發(fā)展與憂患:明清史再認(rèn)識》,《解放日報》,2004年8月8日“思想者”專版。))?這就啟示我們需要從經(jīng)濟(jì)總量以外的角度思考問題,需要關(guān)注促進(jìn)經(jīng)濟(jì)增長方式改變的其他要素。
其二,不管“反歐洲中心主義”如何顛覆傳統(tǒng)的中西比較,也不可能取消中西歷史比較作為方法論存在的意義。他們中有些人一直認(rèn)為,那種把經(jīng)濟(jì)發(fā)展與政治制度聯(lián)系起來的分析,意義不大。例如在向現(xiàn)代轉(zhuǎn)變的過程中,歐洲國家對經(jīng)濟(jì)的干預(yù)很強(qiáng),國家對工商的掠奪也很突出。甚至也可以這樣發(fā)問:發(fā)展經(jīng)濟(jì)的效率,能說集權(quán)制國家一定比分權(quán)制國家差嗎?但,這些能否構(gòu)成把政治制度與經(jīng)濟(jì)變革截然分開的充足理由?顯然站不住腳。
把政治與經(jīng)濟(jì)聯(lián)系起來考察時,兩者互相作用的聯(lián)接點(diǎn)在哪里?國家財政政策的考察是個突破口。說具體些,財政政策,會影響到經(jīng)濟(jì)資源的支配與使用狀態(tài),國民生產(chǎn)總量的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以及它造成的最終利益格局,特別是政治主體與經(jīng)濟(jì)主體的利益分配格局,這些都會反過來制約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速度與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持續(xù)性。
篇4
關(guān)鍵詞:明清時期;商品經(jīng)濟(jì);近現(xiàn)代;全面拓展
中圖分類號:J205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3)02-0187-01
一、明清時期的繪畫功能
明清時期已經(jīng)進(jìn)入了封建社會的末期,各種社會矛盾都已經(jīng)發(fā)展到非常尖銳的地步,社會基礎(chǔ)與社會制度受到挑戰(zhàn)而風(fēng)雨飄搖,而且在封建社會內(nèi)部催生出新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資本主義生產(chǎn)關(guān)系,“物質(zhì)生活的生產(chǎn)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從《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批判?序言》,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82頁) ,因此明清兩代的繪畫在整體沉寂停滯中又呈現(xiàn)出了進(jìn)步與發(fā)展。在此期間出現(xiàn)了像董其昌、吳門四家、揚(yáng)州八怪、石濤、等藝術(shù)大家,他們在新的文化思想與審美趣尚以及日趨頻繁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推陳出新,故而明清繪畫既具備了時代所賦予的獨(dú)特面貌,又彰顯出中國繪畫由古代向現(xiàn)代轉(zhuǎn)型的趨勢與特征。
以往時代的畫家把創(chuàng)作作品當(dāng)成一種表現(xiàn)自我、情感宣泄的產(chǎn)物,而明清時期的最大的也是區(qū)別于以往任何時代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商品經(jīng)濟(jì)進(jìn)入繪畫領(lǐng)域內(nèi)部同時也深入影響了繪畫藝術(shù)本體的其它環(huán)節(jié)。明代初期,政治上中央集權(quán),思想和文化上實行專制統(tǒng)治,宮廷繪畫占主導(dǎo)地位,統(tǒng)治階級的干涉束縛讓畫家完全投其所好,總體藝術(shù)成就不高。明代中晚期以來,伴隨著工商業(yè)經(jīng)濟(jì)的迅速發(fā)展,巨大的社會需要和利潤空間使一向被視為自娛寄興的繪畫作品通過多種交易渠道進(jìn)入流通領(lǐng)域,染上濃厚的商品化色彩。
繪畫領(lǐng)域商品經(jīng)濟(jì)的盛行在一定程度改善了畫家的生活環(huán)境,使其能更好的從事繪畫創(chuàng)作,而且它也豐富了中國畫的表現(xiàn)形式,促使文人畫家的“書卷氣”與職業(yè)畫家的“匠氣”融合,但是它的弊端也是不容忽視的,這一時期的畫作大都粗制濫造,有些畫家完全用經(jīng)濟(jì)的手段和規(guī)律對待藝術(shù)的創(chuàng)作,就十分荒唐了,甚至有可能造成繪畫整體水平的下降。文人畫家的宗旨是自娛、寄興,而在明清商品經(jīng)濟(jì)的刺激下,許多畫家不顧藝術(shù)操守和作為一個商人的誠信,這不能不說商品經(jīng)濟(jì)給繪畫藝術(shù)帶來了很大的負(fù)面影響。中國繪畫史上的真正藝術(shù)家,即使處于怎樣的社會背景下,也決不會因商品利益的引誘而放棄對于藝術(shù)本位追求。
二、近現(xiàn)代的繪畫功能
近現(xiàn)代中國經(jīng)歷了從逐漸衰落到衰敗至及再至民族復(fù)興的艱苦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延續(xù)數(shù)千年的封建專制制度被徹底,中國社會呈現(xiàn)出前所未有的激烈變革,社會思想也發(fā)生著劇烈的沖突與斗爭,革命思潮與運(yùn)動風(fēng)起云涌,為適應(yīng)新的社會化模式、行為模式,此時中國的近現(xiàn)代美術(shù)也產(chǎn)生了前所未有的變革。“海派”在這一時期表現(xiàn)的尤為突出,在藝術(shù)傳統(tǒng)上,“海派”畫家繼承了“揚(yáng)州八怪”的世俗化傳統(tǒng),同時由于面對更廣闊的文化視野、更紛繁復(fù)雜的社會生活和更激烈的矛盾沖突,他們的繪畫創(chuàng)作及其世俗化特征向著更開闊、深入、成熟的方向發(fā)展,他們將詩書畫印融為一爐并且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賞,在中國近現(xiàn)代美術(shù)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更令人稱贊的是“海派”的畫家們在國家遭受天災(zāi)人禍時一次又一次的書畫賑災(zāi)活動。
20世紀(jì)20年代以后的中國畫壇由于受到的影響,中國畫向現(xiàn)代轉(zhuǎn)型的趨勢日益增強(qiáng),在肯定中國畫傳統(tǒng)價值的同時更著重于在傳統(tǒng)中求變求新,把師造化的獨(dú)特感受與傳統(tǒng)中最有價值的部分有機(jī)結(jié)合,從而開拓出一片新的天地,這一時期繪畫的功能得到逐漸完善。20世紀(jì)三四十年代,中國畫面對傳承與發(fā)展,徐悲鴻主張“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絕者繼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畫之可采入者融之”,提倡寫實主義;20世紀(jì)四五十年代,這一時期的畫家主張繪畫應(yīng)該是意義功能與客觀再現(xiàn)功能的統(tǒng)一;繪畫功能全面拓展的時代是上世紀(jì)70年代末,我國進(jìn)入改革開放的偉大時期,隨著社會主義物質(zhì)文明的迅速繁榮,中國文化亦開始走向全面的復(fù)興,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也得到全面發(fā)展,因此,當(dāng)代繪畫功能得到了全面的拓展,歸納起來有:教育功能,審美功能,自娛功能,文化交流功能,科學(xué)研究功能,經(jīng)濟(jì)建設(shè)功能,商品功能,環(huán)境美化功能等等。
三、結(jié)語
在世界繪畫史上,還沒有哪一個畫種比中國畫更為古老,更具有精美、深邃而綿延不斷的傳統(tǒng)。因而“歷史”在中國畫領(lǐng)域,不僅僅是圖像傳承和風(fēng)格興替,更是一種精神象征。就當(dāng)今中國畫的發(fā)展?fàn)顩r來說,我們現(xiàn)在正處在一個瞬息萬變的信息時代,多元化已經(jīng)成為中國畫發(fā)展的必然趨勢,在當(dāng)代社會中,藝術(shù)已經(jīng)逐漸被商業(yè)魅影附了身,已經(jīng)逐漸喪失藝術(shù)功能本來的面目,現(xiàn)當(dāng)代的藝術(shù)家在順應(yīng)時代潮流的過程中,也有責(zé)任和義務(wù)重塑繪畫的本土文化,以使繪畫的功能得到更加全面的發(fā)展。
篇5
一、市場資源配置與全國性地理布局的重組
唐代以前,全國農(nóng)作物與手分布呈現(xiàn)強(qiáng)烈的均衡狀態(tài),各地的作物構(gòu)成都具有較強(qiáng)的自給自足特征,遠(yuǎn)距離的物資交流很大一部分通過政府調(diào)撥手段來實現(xiàn)。商品流通在品種上多局限于名特產(chǎn)品,在時間上局限于豐歉調(diào)劑,在空間上地域延展度不大,尤其是大宗商品的遠(yuǎn)距離貿(mào)易稀疏。“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史記·貨殖列傳》所載的這一民諺,直到唐代仍為商人恪守不逾,因為運(yùn)輸成本的巨大耗費(fèi)會抵銷商品地區(qū)差價所帶來的商業(yè)利潤。
宋代多種商品的遠(yuǎn)距離貿(mào)易有了長足發(fā)展,幾個地區(qū)之間的商品糧流通突破了豐歉調(diào)劑的模式就是其顯著的表征。最大的商品糧基地太湖平原米谷供給杭州、浙東以至福建,長江中游各地的商品糧順江而下銷江淮,兩廣米谷供給福建及浙東,北宋時南方米谷通過官府及私商運(yùn)至汴京。同時與全國市場相配合的專業(yè)化商品生產(chǎn)在一些局部嶄露頭角。如紡織品有,河北東路、京東西路一帶蠶絲傳統(tǒng)產(chǎn)區(qū),成都平原的蜀錦,兩浙路的湖州、杭州、越州的絹與羅,江西撫州的紗,福建、蜀川等地的麻布,都開始跨區(qū)域流通。此外,洞庭山等地的柑桔、福建的荔枝、四川遂寧的糖霜、江州的魚苗等各地的特產(chǎn),都形成專門化的商品生產(chǎn),遠(yuǎn)銷四方。[②a]但總體而言,市場作用下的資源配置及其對全國范圍內(nèi)經(jīng)濟(jì)地理布局的相當(dāng)微弱。
這些變化在明清繼續(xù)深化和擴(kuò)大,在作物引種推廣、產(chǎn)區(qū)重組優(yōu)化的過程中,各地農(nóng)作物的商品生產(chǎn)、手工業(yè)品的加工制作,經(jīng)過優(yōu)勝劣汰的市場競爭的作用,自然均衡分布狀況被打破,全國范圍內(nèi)的區(qū)域性商品基地出現(xiàn)。這種變化以蠶桑絲織業(yè)、陶瓷業(yè)、稻米業(yè)最為突出。
蠶桑絲織業(yè)是我國的傳統(tǒng)作物,唐宋以前全國各地都普遍存在,明清則發(fā)生了深刻變化。最為悠久、產(chǎn)品質(zhì)量上乘的華北蠶絲區(qū)已基本上退出商品生產(chǎn)領(lǐng)域,陜西、山西絕少存在,河北、河南及山東僅稀落殘存于少數(shù)地區(qū),如山東部分州縣的山蠶。另一大傳統(tǒng)產(chǎn)區(qū)川西平原清代也在相當(dāng)程度上衰落了。而江南蠶絲業(yè)則一枝獨(dú)秀,并集中于湖州、嘉興及杭州府的狹小的地域內(nèi),湖絲以其優(yōu)良質(zhì)地廣布全國市場,鮮有競爭對手。珠江三角洲是明中葉以后新興的蠶桑區(qū),但其質(zhì)量遠(yuǎn)遜于湖絲,即使在當(dāng)?shù)匾膊粩澈z。絲綢織作,也是江南技壓群芳,產(chǎn)品覆蓋全國,集中于蘇州、杭州、江寧和湖州、嘉興等府的城鎮(zhèn)。
陶瓷,唐末至兩宋金元時全國各地名窯遍布,百花齊放,從元代開始至明清景德鎮(zhèn)一枝獨(dú)秀,逐漸壟斷了全國市場,其他除了江蘇宜興紫砂、廣東石灣瓷器等少數(shù)窯場外紛紛凋零,尤其是北方的窯址退化為低級陶窯,其產(chǎn)品僅在當(dāng)?shù)匦》秶鷥?nèi)流通。[①b]
以稻谷為代表的糧食作物,雖然各大區(qū)域都有生產(chǎn),但有的已不成為主業(yè),幾大商品糧基地形成。長江中上游的四川、湖南、江西及安徽大部分地區(qū),珠江中上游的廣西,華北的河南、山東等地,都成為重要的商品糧基地,河套、、東北等新興的商品糧基地崛起。與此同時,江南太湖平原,由宋代的最大商品糧基地一變而為明清全國最大的商品糧市場,珠江三角洲亦由商品糧的輸出地轉(zhuǎn)變?yōu)檩斎氲亍?/p>
其他作物與產(chǎn)品大都發(fā)生了類似的產(chǎn)地集中與布局優(yōu)化過程。棉花種植集中于江南、華北、湖北三大產(chǎn)地,明代華北棉花南運(yùn)江南,清代江南棉花部分海運(yùn)福建等地,湖北棉花西入四川。棉布織作以江南最盛,其市場明代廣布南北各地,清代有所縮小,但高質(zhì)量棉布仍暢銷全國。清代華北棉布在當(dāng)?shù)丶拔鞅闭紦?jù)優(yōu)勢,并輻及東北市場,湖北、四川棉布則占領(lǐng)西南市場。苧麻與麻布產(chǎn)地局限于南方的江西、湖南、廣西、及閩粵部分州縣,市場化不顯著。此外,蔗糖以臺灣、廣東、四川及福建為集中產(chǎn)區(qū);果品基地以閩粵的亞熱帶水果和華北的溫帶水果為主,市場除本區(qū)域外,均以江南最大;鐵器以廣東佛山、山西澤潞的產(chǎn)品市場最廣;造紙以贛閩浙皖山區(qū)為最大基地,產(chǎn)品運(yùn)銷四方。
經(jīng)濟(jì)地理布局的變動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場資源配置的結(jié)果。在有限的土地上,如果以原有自然狀態(tài)下的低效率生產(chǎn),那么總產(chǎn)量無疑不能養(yǎng)活日益增多的人口,必須借助于市場手段進(jìn)行全國范圍內(nèi)的資源配置。根據(jù)各地的自然條件,優(yōu)先發(fā)展能夠充分利用地力與自然資源的農(nóng)業(yè)物與手工業(yè),從而使各自的生產(chǎn)效率提高,社會總產(chǎn)量相應(yīng)增加。以最大商品糧基地湖南和最大棉桑基地江南而論,湖南自然條件宜于水稻種植,而人口密度遠(yuǎn)遠(yuǎn)低于江南,人均占地遠(yuǎn)多于江南。湖南相對粗放經(jīng)營取得了明顯的經(jīng)濟(jì)效益,水稻生產(chǎn)勞動生產(chǎn)率大大高于江南,每戶可出米40—90石,比松江等地高出數(shù)倍。同時湖南等地生產(chǎn)投資少,生產(chǎn)成本較低,即使在湖南水稻生產(chǎn)集約化上升后,湖南米價仍大大低于江南,從而可以不遠(yuǎn)千里來到江南與當(dāng)?shù)孛渍归_競爭。競爭的結(jié)果,使得江南水稻生產(chǎn)中勞動生產(chǎn)率最低而生產(chǎn)成本最高的松江、太倉等大批不宜稻的沙地、及太湖南部不甚宜稻的低洼地退出水稻種植。這些土地用于種棉植桑,則獲得更好的經(jīng)濟(jì)效益。[②b]這就形成湖南水稻種植區(qū)、江南桑棉種植區(qū)的勞動分工,而這種分工促進(jìn)了各地勞動生產(chǎn)率與經(jīng)濟(jì)效益的共同提高。
市場對資源的配置發(fā)生導(dǎo)向作用,價格機(jī)制開始有效地調(diào)節(jié)全國商品的地區(qū)平衡,這在商品糧市場中較為明顯。乾隆曾說,“浙西一帶地方所產(chǎn)之米,不足供本地食米之半,全藉江西、湖廣客販米船,由蘇州一路接濟(jì)。向來米船到浙,行戶接貯棧房,陸續(xù)發(fā)糶,鄉(xiāng)市藉以轉(zhuǎn)輸。即客販偶稀,而棧貯乘時出售,有恃無恐。是以非遇甚欠之歲,米價不致騰涌。向來情形如此。”[①c]從這段話可以看出,蘇州米運(yùn)至浙西,無論在城市還是鄉(xiāng)村,都形成了一個有機(jī)的銷售,完成向最終消費(fèi)者分散的功能。米谷販運(yùn)常年穩(wěn)定,貨源充足,因此行戶能夠“有恃無恐”。即使在偶然稀落的情況下,也不致造成價格的大變動。康熙五十五年的一個奏折也反映道:“蘇州八月初旬,湖廣、江西客米未到,米價一時偶貴,后即陸續(xù)運(yùn)至,價值復(fù)平”。[②c]李煦此語表明,蘇州米價深受長江中游米谷輸入的影響,而米谷運(yùn)輸較穩(wěn)定,米價的大起大落通常只是偶發(fā)現(xiàn)象。不僅銷地市場如此,產(chǎn)區(qū)亦然。嘉慶《善化縣志》說,“湖南米谷最多。然不以一歲之豐歉為貴賤,而以鄰省之搬運(yùn)為低昂”。這就是說,湖南產(chǎn)地的米價,決定性的因素主要不是自然豐歉原因,而是市場狀況。
經(jīng)濟(jì)地理布局的優(yōu)化,又促進(jìn)了全國范圍內(nèi)的商品流通和資源配置。如高唐州有“水陸之便,故繒綺自蘇杭應(yīng)天至,鉛鐵自山陜至,竹木自湖廣至,瓷漆諸器自饒、徽至,楮幣自浙至”。[③c]乾隆《安邑縣運(yùn)鹽城志·風(fēng)俗》所記,也典型地反映了全國市場對各地方市場影響。山西解州運(yùn)鹽城,唯產(chǎn)食鹽,然“商賈取處,百貨駢集,珍饋羅列,凡于無物不有,是合五方物產(chǎn),即為運(yùn)城物產(chǎn)”。商品在全國范圍內(nèi)的周流,以蘇杭等地棉布、絲綢及日用雜貨等各種手工業(yè)制品最為顯著,可謂無遠(yuǎn)弗屆。在明清各地方志中,蘇杭雜貨的記載,俯拾皆是。江西“民間所用細(xì)布,悉從蘇松蕪湖商販貿(mào)易”。清代山東兗州府,“服食器用,鬻自江南者十之六七矣”。廣東英德縣墟市,“蘇杭雜貨齊備”。遠(yuǎn)至塞北,亦不例外,宣化府大市中,南京羅緞鋪、蘇杭羅緞鋪為商賈競相爭占;寧夏的蘇杭雜貨集于毓秀坊內(nèi)。……[④c]唯其如此,蘇杭各類手工業(yè)產(chǎn)品的生產(chǎn)具備有利的市場刺激。“吳制服而華,以為非是弗文也;吳制器而美,以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吳服,而吳益工于服;四方貴吳器,而吳益工于器。”[⑤c]顯然,市場是江南商品生產(chǎn)持續(xù)發(fā)展和進(jìn)步的動力,推而廣之,也是全國經(jīng)濟(jì)地理布局的誘因。商品糧產(chǎn)地、經(jīng)濟(jì)作物種植區(qū)、經(jīng)濟(jì)作物加工區(qū)、手工業(yè)品產(chǎn)區(qū)之間的商品對流,互為產(chǎn)品市場,彼此依賴,相互促進(jìn)。當(dāng)然,至傳統(tǒng)末期,市場機(jī)制在社會經(jīng)濟(jì)中作用的局限性仍然是顯而易見的,在此基礎(chǔ)上的資源配置也沒有成為全國經(jīng)濟(jì)地理布局的主導(dǎo)因素。
二、中心地體系與區(qū)域市場格局的調(diào)整
城鄉(xiāng)經(jīng)濟(jì)往來并不一定要通過市場紐帶來維系,可以通過賦稅與地租的形式直接運(yùn)抵城市,唐以前供給城市的農(nóng)產(chǎn)品相當(dāng)數(shù)量并非經(jīng)由市場渠道。在城鄉(xiāng)對立的普遍存在下,一些治所城市也曾獲得較大,鄉(xiāng)村集市也能萌發(fā),但城鄉(xiāng)市場沒有形成結(jié)構(gòu)性的體系,這種狀況直到宋以來市鎮(zhèn)的普遍興起才改變。一批鎮(zhèn)市在商道要沖、城市附郭、農(nóng)副產(chǎn)品集中產(chǎn)地及少數(shù)商品生產(chǎn)專業(yè)區(qū)內(nèi)崛起。一些較大的鎮(zhèn)上升為與縣治同級的經(jīng)濟(jì)中心地,并對縣城形成挑戰(zhàn)之勢,其中不少在規(guī)模與市場功能上超過了縣城,個別進(jìn)而超過了州府城市。
宋代的多數(shù)地區(qū),都已形成以府、州、軍等治所城市為核心的“州府市場”網(wǎng)絡(luò),它的地理范圍往往以一個州府行政區(qū)或其部分地區(qū)為主體,也可以包括鄰近州府的轄區(qū),有的則由兩三個州府組成。在州府治所(少數(shù)也以大縣巨鎮(zhèn))之下,有縣鎮(zhèn)溝通城鄉(xiāng)市場聯(lián)系,網(wǎng)絡(luò)的底層則是由集市、墟市、村市等構(gòu)成的基層市場。
宋代的等級市場體系中,各級中心地多與行所吻合,因為傳統(tǒng)政治因素對市場的愈往前愈強(qiáng)烈,經(jīng)濟(jì)的封閉性與地方性也很嚴(yán)重,宋代出現(xiàn)松動,但仍有限。這種突破至明清加強(qiáng),中心地等級與行政治所等級分離。明清市鎮(zhèn)的發(fā)展更為迅速,尤其是在經(jīng)濟(jì)作物和工礦業(yè)的刺激下,宋代還很稀疏的專業(yè)市鎮(zhèn)日趨普遍和壯大,商道市鎮(zhèn)也在各地商品周流擴(kuò)大的過程中強(qiáng)化和膨脹。新興市鎮(zhèn)的突出發(fā)展使之在市場規(guī)模與功能上出現(xiàn)等級分化,不再只是與縣治同級的中心地,超過縣城、超過州府治所的市鎮(zhèn)比比皆是。還有十來個巨鎮(zhèn),甚至超越省府治所或與之并駕齊驅(qū),成長為省級乃至更大范圍的經(jīng)濟(jì)中心地。清人述嶺南、華中、中原等地巨鎮(zhèn)在商品流通中的作用,有一段話非常典型:“食貨富于南而輸于北,由廣東佛山鎮(zhèn)到湖廣漢口鎮(zhèn),則不止廣東一路矣。由湖廣漢口鎮(zhèn)到河南朱仙鎮(zhèn),又不止湖廣一路矣。”[①d]
區(qū)域市場是一個自然地域內(nèi)中心地體系發(fā)育和市場聯(lián)系加強(qiáng)的產(chǎn)物。在唐以前,還很難清晰地描繪出自成一體的區(qū)域市場網(wǎng)絡(luò)。宋代的發(fā)達(dá)地區(qū),由一定數(shù)量的州府市場網(wǎng)絡(luò)整合而成的區(qū)域市場已開始形成。以成都為中心、川西平原為區(qū)域核心帶的蜀川區(qū)域市場,北宋時以汴京為中心的華北區(qū)域市場,南宋時以杭州為中心的兩浙區(qū)域市場,都已形成了這種自成一體的內(nèi)部有機(jī)聯(lián)系的網(wǎng)絡(luò)格局。明清時期全國主要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區(qū)大都形成有機(jī)的區(qū)域市場,并出現(xiàn)耐人尋味的現(xiàn)象,各區(qū)域市場和省級市場的最高中心地,往往不是省會,或不為省會獨(dú)任之。作為區(qū)域市場的最高中心地,它必須是一個綜合性大城市,它不僅是一個商品集散中心,還應(yīng)該是初級產(chǎn)品加工中心;它不僅對本區(qū)域內(nèi)部具有強(qiáng)大的吸納力,而且是有足夠的輻射力將本區(qū)域產(chǎn)品引向外地和遠(yuǎn)方市場。
例如嶺南區(qū)域市場,由廣州和佛山共同組成最高中心地,組織廣東廣西的商品流通,并擔(dān)負(fù)該區(qū)域與省外、國外的交往。[②d]在廣西,商業(yè)中心功能由梧州府城及隔江不遠(yuǎn)的戎墟完成。湖廣區(qū)域市場,漢口鎮(zhèn)的中心地位自明晚期后遠(yuǎn)駕于兩省會之上。在湖南,清中葉以前湘潭是最大的米市和商業(yè)中心。江西,省內(nèi)外的物資周流以樟樹、吳城為樞紐,超過省會南昌。[③d]
華北和江南,因為政治沿革的原因,表面上有些特殊,實質(zhì)上和全國的普遍情形相似。北京乃京師所在,是華北平原的最高中心地。而作為清代直隸治所的保定府,其市場中心功能遠(yuǎn)次于后來居上的天津。山東,商業(yè)中心城市為臨清,而省會濟(jì)南在省內(nèi)外商品流通中的作用,湮然無聞,不僅遠(yuǎn)遜于臨清、濟(jì)寧,在某種程度上甚至不知該府鄒平縣下的周村一店。河南,開封和朱仙鎮(zhèn)是最高中心地,清前期則幾乎由朱仙鎮(zhèn)獨(dú)任其職。江南最高中心地在蘇州,它可以稱為江蘇的第二省會,但在區(qū)域市場的中心地等級中高于南京和浙江省會杭州。
此外,山西的區(qū)域核心帶在南部的潞安、澤州及絳州一帶,與省會太原相距尚遠(yuǎn)。以福建為主體的東南沿海區(qū)域,由于自然地理的影響,自流入海的各條江河,以入海口的城鎮(zhèn)為中心,分別自成一個地方市場,與國內(nèi)外的聯(lián)系密切,而區(qū)域內(nèi)尚未整合為一個有機(jī)的區(qū)域市場。云南、貴州等省至清代尚未形成區(qū)域市場。
由此看來,明清的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區(qū)內(nèi),真正由省會城市承當(dāng)市場中心城市者,大概只有陜西的西安、浙江的杭州、四川的成都,而四川商業(yè)中心在傳統(tǒng)時代末也開始由成都向重慶轉(zhuǎn)移了。
雖然至清中葉沒有出現(xiàn)如近代上海一樣的凌駕于各大城市之上的中心城市,但全國范圍內(nèi)仍然形成幾大超區(qū)域的中心城鎮(zhèn),如華北的北京,華東的蘇州,華南的廣佛,華中的漢口,有效地發(fā)揮著全國市場中心的功能。全國性統(tǒng)一市場在經(jīng)濟(jì)中心地體系的建立與變動過程中,在各大區(qū)域市場的重組與整合之下已趨形成。
省級市場、區(qū)域市場格局的形成過程,同時又是它們調(diào)整與重組的整合過程,并由于各地市場的相應(yīng)配合與促進(jìn),傳統(tǒng)時代的全國性統(tǒng)一市場形成。這突出表現(xiàn)于湖北、四川、廣西商業(yè)重心的轉(zhuǎn)移,這種轉(zhuǎn)移既是區(qū)域經(jīng)濟(jì)擺脫政治紐帶趨向市場軸心的結(jié)果,也是配合全國市場整合進(jìn)程的必然變化。
唐宋以前,湖北、四川的政治經(jīng)濟(jì)中心分別在荊襄、成都,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它們與政治中心長安及洛陽聯(lián)系更為便利的緣故,廣西的政治經(jīng)濟(jì)中心在東北部的桂林,同樣是因為北向地與中原王朝聯(lián)系的緣故。盡管川陜商道難于上青天,靈渠不過一人造小渠而已,顯然它們無法承載溝通區(qū)域間市場聯(lián)系所必需的大規(guī)模商品流通的容量——它們不可能成為全國市場聯(lián)系的大規(guī)模通道,但足以勝任中央與地方政令的傳輸,并且是當(dāng)時條件下與全國政治中心聯(lián)系的便捷途徑,因此區(qū)域政治經(jīng)濟(jì)中心亦隨之分布。這種格局無疑更多地是政治因素作用的產(chǎn)物,而與市場因素不甚相關(guān),甚至背道而馳。在市場發(fā)展的作用下,尤其是區(qū)域間市場聯(lián)系的增強(qiáng)、全國性統(tǒng)一市場的整合等因素的作用下,明清時這種區(qū)域格局發(fā)生或完成了轉(zhuǎn)移。
湖北的經(jīng)濟(jì)重心,自宋以來開始由荊襄一帶向今武漢附近轉(zhuǎn)移,至明中葉以后最高中心地穩(wěn)定于漢口,并將湖南引入其市場吸納與輻射范圍之內(nèi),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湖南決定性的主要輸出商品米谷及木材與鐵等重要輸出品、重要輸入品鹽等都必須以漢口為樞紐。廣西則由于珠江航運(yùn)的迅速發(fā)展和廣州、佛山的中心功能與輻射功能的擴(kuò)大,被整合入嶺南區(qū)域市場之中,其經(jīng)濟(jì)中心亦隨之由東北部的桂林轉(zhuǎn)移到東南部的梧州及戎墟。[①e]元明時衰落不振的四川區(qū)域市場至清代復(fù)蘇,并在長江航運(yùn)的帶動下,商業(yè)中心自嘉道時期開始由成都轉(zhuǎn)移至重慶。[②e]隨著各地市場聯(lián)系的加強(qiáng)、主要河道主干線承擔(dān)的作用越來越大,區(qū)域經(jīng)濟(jì)格局的變動融入全國市場的整合過程之中。
此外,邊疆民族地區(qū)經(jīng)濟(jì),雖然與內(nèi)地仍存在相當(dāng)差距,但明清時經(jīng)濟(jì)已大有起色,云南、西藏、新疆、蒙古地區(qū)、東北,東南的寶島與海南都得到程度不同的開發(fā),與內(nèi)地市場的交往緊密關(guān)聯(lián)。正是這種日趨密切的商旅與貨物往來,將各邊疆民族市場納入全國統(tǒng)一市場體系之中,不過它們大多不是以統(tǒng)一市場內(nèi)自成一體的區(qū)域市場的形式出現(xiàn)。
三、內(nèi)河航運(yùn)貿(mào)易的變動與傳統(tǒng)市場的整合
運(yùn)輸條件與物流設(shè)施的改善,縮短商品空間距離,降低商品交易成本,先進(jìn)的倉儲技術(shù)手段提高商品養(yǎng)護(hù)能力,從而延長作為使用價值的存在時間,是市場的重要條件。承載使用價值時空轉(zhuǎn)移的交通運(yùn)輸在市場整合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宋元明清內(nèi)河航運(yùn)的變動,就突出地反映了市場整合的軌跡。在化交通出現(xiàn)之前,水運(yùn)的開發(fā)利用程度是市場發(fā)展的重要標(biāo)志。水運(yùn)具有陸運(yùn)無可比擬的優(yōu)越性,航運(yùn)迅速,運(yùn)載量大,運(yùn)輸成本低。[①f]因此本文以內(nèi)河航運(yùn)貿(mào)易為重點(diǎn)進(jìn)行考察。
長江航運(yùn)貿(mào)易漢唐之世就已存在,宋代進(jìn)一步得到開發(fā)。東出長江在四川對外聯(lián)系中的重要性加強(qiáng),“順流而下,委輸之利,通西蜀之寶貨,傳南土之泉谷,建帆高掛則越萬艘,連檣直進(jìn)則倏逾千里。”[②f]長江中下游河面上,米谷、木材與食鹽等商品的對流運(yùn)動日益擴(kuò)大。在長江運(yùn)輸?shù)膸酉拢拇|部的渝州、夔州、萬州等地的落后局面有了起色,中游的荊州附近崛起了沙市,這個附郭草市很快后來居上。鄂州地理位置的優(yōu)越性因長江流域市場交往的擴(kuò)大而得到充分發(fā)揮,宋代以后逐漸取代了江陵的中心地位。
明清時期長江已成為黃金水道,清代僅長江中上游的商品糧東運(yùn),已蔚為壯觀,木材、藥材、生鐵、豆類等亦順流而下;江南的絲棉織品及日用雜貨,淮南的鹽等,則大量逆流而上。長江航運(yùn)貿(mào)易最突出的表現(xiàn)就是漢口的迅速崛起并成為全國性中心城市。東西間商品交流的頻繁,正是漢口作為全國中心城市應(yīng)運(yùn)而生的根本原因。在宋代,雖然鄂城開始崛起,但由于長江航運(yùn)量的限制,它始終只是一個較大的商品轉(zhuǎn)運(yùn)站而已。四川商業(yè)重心開始東移重慶,也是長江上游與中下游聯(lián)系加強(qiáng)的產(chǎn)物。
長江沿線還興起一批中等城鎮(zhèn),自西而東主要有:敘州、沙市、岳州、九江、安慶、蕪湖等,并且它們的地位也在日益強(qiáng)化。各大支流沿岸的省級和地方性中心城市或商品運(yùn)輸中轉(zhuǎn)城市為數(shù)更多。岷江上有古城成都,涪江上有新興的商品糧市鎮(zhèn)太和鎮(zhèn),嘉陵江上有閬絲貿(mào)易中心蒼溪縣城,湘江上有湖南商業(yè)中心湘潭及長沙、衡陽,資江上有益陽,漢江上有“南船北馬”轉(zhuǎn)運(yùn)站老河口、棉運(yùn)輸中轉(zhuǎn)地云夢縣城。贛江上有江西商業(yè)中心樟樹鎮(zhèn)、吳城鎮(zhèn),撫河上有滸灣鎮(zhèn),信江上有河口鎮(zhèn),鄱江上有瓷都景德鎮(zhèn)……。
明清長江航運(yùn)的開發(fā)是全國性統(tǒng)一市場整合的重要表征,說明東西各區(qū)域間市場聯(lián)系的加強(qiáng),而在此前這種聯(lián)系相當(dāng)有限,遠(yuǎn)遜于南北間的物資交流。南北向的交通運(yùn)輸歷來是商品流通的主要流向,這是北方中心地位對物資運(yùn)輸?shù)乃隆T趥鹘y(tǒng)市場整合的過程中,南北向交通的重要性逐漸減退。唐代繁榮的湘江水道,至宋漸衰;贛江水道,宋代盛極一時,到清代其重要性相對下降;陸路的川陜商道,在宋代是四川區(qū)域市場鼎盛的生命線,也是陜西軍事重地的軍需供給線,南宋以后一蹶不振。清中葉后千年輝煌的大運(yùn)河也退出了舞臺。
珠江流域類似于長江,明清時以米、鹽為代表的原料與手品的對流運(yùn)動使西江運(yùn)輸趨于繁榮,廣西商業(yè)重心東移梧州及戎墟,佛山成長為嶺南區(qū)域和全國性中心城鎮(zhèn),都是珠江流域商品運(yùn)輸擴(kuò)大的直接表征。黃河、淮河、海河各大河流都涌現(xiàn)出區(qū)域性或地方性中心城市與商品轉(zhuǎn)運(yùn)樞紐。淮河支流上的朱仙鎮(zhèn),黃河與運(yùn)河相交處的淮安,海河各大支流相匯處的天津,以及衛(wèi)河上的河南清化鎮(zhèn)、河北小灘鎮(zhèn),汾河上的山西絳州,等等,都是各水系河道運(yùn)輸帶動下成長起來的。
以長江為代表的大河是東西交通的天然大動脈,其開發(fā)程度是傳統(tǒng)市場整合的重要標(biāo)志。一個明顯的事實是,隋唐以來歷代政府對天然的長江航運(yùn)未加利用,卻要耗費(fèi)巨大財力開掘修浚人工的南北大運(yùn)河,這正是南北物資交流的重要性使然,而這種重要性很大程度又是北方政治中心有賴于南方經(jīng)濟(jì)力量的支撐所驅(qū)動的,而不是由純經(jīng)濟(jì)、純市場的因素決定。
隋開運(yùn)河,完成了中國經(jīng)濟(jì)史上影響最為深遠(yuǎn)的偉大工程,自此歷宋元明清,大運(yùn)河都成為南北交通運(yùn)輸?shù)氖咨埔馈1彼毋旰颖苯狱S河,南入江淮,是京師的生命線,廣濟(jì)河?xùn)|通京東、河北,蔡河南入淮南。其運(yùn)輸量,僅官運(yùn)漕米,常年即達(dá)五六百萬石,高時達(dá)800萬石。汴河正所謂“橫亙中國,首承大河,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并山澤百貨,悉由此路而進(jìn)”。[①g]元代新開的會通河的載容量限于150料船,但商賈三四百料乃至500料船亦能行駛。不僅每年漕運(yùn)江淮米500萬石至大都,而且,“江淮、湖廣、四川、海外諸番土貢糧運(yùn)、商旅懋遷,畢達(dá)京師”。[②g]北宋的汴京、元朝的大都,全賴運(yùn)河的滋潤。在運(yùn)河沿岸,淮南以真、揚(yáng)、楚、泗為代表的商業(yè)城市得到持續(xù)發(fā)展。真州位于長江與運(yùn)河相接之處,唐代為白沙鎮(zhèn),北宋升為州治,號為“萬商之淵”,元代其商稅額僅次于大都和杭州,位列全國各大城市第三。在江南段則有鎮(zhèn)江、常州、蘇州、杭州等大中城鎮(zhèn)。
明清時大運(yùn)河仍充當(dāng)南北大動脈。明代運(yùn)河北上的商品;以棉布、綢緞為大宗,其次為茶葉、紙張、磁器、鐵器等;運(yùn)河南下的商品以棉花為主,次為豆貨、干鮮果品。清代,南貨北上主要是綢、布、姜、茶、紙、糖及各項雜貨;北貨南下則以糧食為主,棉花、梨棗、煙葉、油麻等貨亦為大宗。此外,長蘆、兩淮鹽場經(jīng)運(yùn)河南下或轉(zhuǎn)運(yùn)的運(yùn)輸量,明代一億多斤,清代約有二三億多斤。明代鈔關(guān)除九江外都位于運(yùn)河上,即崇文門、河西務(wù)(清移天津)、臨清、淮安、揚(yáng)州、滸墅、北新關(guān),其中運(yùn)河七關(guān)在鈔關(guān)商稅總額中所占百分比,萬歷時為92.7%,天啟時為88%。清代運(yùn)河七關(guān)在全國關(guān)稅總額中的百分比有所下降,康熙二十年為50.5%,雍正三年40.9%,乾隆十八年33.1%,嘉慶十七年29.3%,道光二十一年33.5%。[③g]明清時期運(yùn)河沿線一系列城市的興起,與南北物資交流緊密相關(guān)。臨清,可以說是大運(yùn)河“創(chuàng)造”的商業(yè)城市的典型代表。元代新開運(yùn)河使臨清獲得天獨(dú)厚的地理優(yōu)勢而崛起,楊效曾《臨清小紀(jì)》描述道:臨清每屆漕運(yùn)時期,帆檣林立,百貨山集,當(dāng)其盛時,綿亙數(shù)十里,市肆櫛比。明清時臨清一直是山東最大的商業(yè)城市,并曾為華北最大的紡織品貿(mào)易中心和糧食交易中心之一。天津也因運(yùn)河的接引而由明代的一個普通軍事衛(wèi)所躍升為清代河北重要中心地,江蘇的淮安成南北商品糧對流的中轉(zhuǎn)地,揚(yáng)州的繁榮,最主要也是得益于其作為淮鹽總匯和運(yùn)河樞紐的地位。蘇州更得益于運(yùn)河之助,成為明清最大的全國性中心城市之一。
清中葉后,海運(yùn)的重要性逐漸超過運(yùn)河,這是中國傳統(tǒng)市場新的生命力與牽引力之所在。運(yùn)河的運(yùn)輸能力畢竟有限,隨著南北商品運(yùn)動的深化,它逐漸不堪負(fù)荷。如果把運(yùn)河的運(yùn)輸作為傳統(tǒng)市場的某種象征,那么,它又是傳統(tǒng)市場的局限性與滯后性的突出體現(xiàn)。海運(yùn)取代運(yùn)河,則為全國市場的發(fā)展開辟了新的道路。隨著海運(yùn)的日益擴(kuò)大,天津進(jìn)一步成為華北最重要的對外聯(lián)系港口,而上海的崛起更具有劃的歷史意義。在西方列強(qiáng)入侵并強(qiáng)迫通商以前,上海的發(fā)展勢頭實際上已顯露無余,它不僅早已超過松江府城,而且漸有取代蘇州成為全國性中心城市之勢。史稱“自從康熙年間,大開海道,始有商賈經(jīng)過登州海面,直趨天津、奉天。萬商輻輳之盛,亙古未有”。[①h]到了近代,上海更成為中國最大的工商業(yè)中心。
最初的商業(yè)行為,集交易過程、運(yùn)輸、倉儲等環(huán)節(jié)于一體,或者說,集價值運(yùn)動、使用價值運(yùn)動于一體。后來,儲運(yùn)與商業(yè)分離,形成獨(dú)立的運(yùn)輸業(yè)、倉儲業(yè)乃至專門的信息業(yè);專門媒介交易而自己不介入商品所有權(quán)轉(zhuǎn)移過程的經(jīng)紀(jì)人、商亦趨活躍。
物流的倉儲環(huán)節(jié),宋代邸店遍布城鄉(xiāng),多集存儲與售賣于一身,既供商旅往宿,也有相應(yīng)的存貨、保管設(shè)施,專門化的倉儲設(shè)施也已出現(xiàn)。在運(yùn)河真、揚(yáng)、楚、泗一帶,有不少堆垛場,專供官運(yùn)與商運(yùn)物資長期存貨。多為官營,亦有民營,寄存商貨者交付垛地官錢或垛戶錢。在東南地區(qū),塌房存在于商業(yè)城鎮(zhèn)周圍。杭州的塌坊尤盛,據(jù)《都城紀(jì)勝》和《夢梁錄》的記載:城中北關(guān)水門內(nèi),有水?dāng)?shù)十里,曰白洋湖。其富家于水次起迭塌坊十?dāng)?shù)所,每所為屋千余間,小者亦數(shù)百間,以寄藏都城店鋪及客旅物貨。四維皆水,亦可防避風(fēng)燭,又免盜賊,甚為都城富室之便。這種大規(guī)模的倉儲令人驚訝,大概只有杭州一地,不過,具體而微者,各地亦可見到。湖州烏青鎮(zhèn)的鋪戶,其存貨塌坊就集中于數(shù)里之外的璉市,朝夕旋取以歸。[②h]明初南京商旅輻輳,貨物或止于舟,或貯于城外民居。官府“于三山門外瀕水處,為屋數(shù)十間,名曰塌坊。商人至者,俾悉貯貨其中,既納稅,從其自相貿(mào)易”。[③h]清代這樣的倉儲設(shè)施在中小型轉(zhuǎn)運(yùn)城鎮(zhèn)也普遍發(fā)展起來。湖北云夢縣城棉布倉儲的事例尤為典型,云夢是山陜商人販運(yùn)湖北棉布的中轉(zhuǎn)站,棉布北運(yùn)必須在此重加包裝捆載,才能“歷遠(yuǎn)不變色,若不由云城改捆,一至河南渡黃河,布多霉暗”。因此西商在此租賃寬間屋宇,設(shè)立了十?dāng)?shù)處店號。[④h]四川江津縣城也有這樣的倉儲設(shè)施,棉布由此分銷云南、貴州、川西,商人在城北中渡建有專門堆布店。湖南各地商人,在漢口、湘潭等中心城市設(shè)立本地貨物專用碼頭,攸縣商人在湘潭自建有碼頭,并時加修葺擴(kuò)充,漢口有寶慶碼頭、萍醴碼頭。運(yùn)輸環(huán)節(jié)還出現(xiàn)了相關(guān)的包裝服務(wù)業(yè)。在景德鎮(zhèn)瓷器出窯,都要分類揀選,分別包裝運(yùn)輸,以保證長途販運(yùn)無損。[⑤h]廣東干鮮果品經(jīng)梅嶺北運(yùn),也已形成高水平的包裝運(yùn)輸服務(wù)業(yè)。運(yùn)輸業(yè)的進(jìn)步,正是降低運(yùn)輸成本、延展商品市場的前提。
全國性經(jīng)濟(jì)地理布局自宋以來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動,明清時期的作物專業(yè)產(chǎn)區(qū)重組與優(yōu)化過程顯示出市場導(dǎo)向下資源配置的作用。經(jīng)濟(jì)中心地等級體系,自宋代歷明清逐漸與行政治所等級分離,各大地域的區(qū)域市場相繼形成,并配合全國市場的發(fā)展不斷調(diào)整與重組。以長江和大運(yùn)河為主的航運(yùn)網(wǎng)絡(luò)的消長變動,亦深刻地反映了傳統(tǒng)市場整合的軌跡。本文所述的這三個方面遠(yuǎn)不是中國傳統(tǒng)市場整合的全部,然而它們?nèi)郧逦仫@示出11—19世紀(jì)的發(fā)展歷程,在這種整合過程中,盡管市場機(jī)制沒有成為全國經(jīng)濟(jì)運(yùn)行的軸心,但傳統(tǒng)時代下全國性統(tǒng)一市場已趨形成。
注釋
①a 唐宋市場的革命性變化,簡略而言就是:城市市場突破坊市制和城墻的時空限制,市場涌現(xiàn)出一批功能性的新興市鎮(zhèn),市場在整個中的作用加強(qiáng)。
②a 本文具體引證多從略,可參閱拙著《宋代東南市場》第二章、第三章,云南大學(xué)出版社1994年版;《傳統(tǒng)市場的》第三篇、第四篇,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①b 參見《中國陶瓷》第五編第二章、第三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②b 李伯重:《“桑爭稻田”與明清江南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集約程度的提高》,載《中國農(nóng)史》1985年第1期;《明清江南與外地經(jīng)濟(jì)聯(lián)系的加強(qiáng)及其對江南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載《中國經(jīng)濟(jì)史研究》1986年第2期。
①c 《清高宗實錄》卷304,乾隆十三年五月乙酉。
②c 《李煦奏折》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六日“蘇州米價并進(jìn)晴雨折”。
③c 嘉靖《高唐州志》卷3。
④c 《兩臺奏議》卷5;《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兗州府物產(chǎn)考;道光《英德縣志》卷6;萬歷《宣府鎮(zhèn)志》,嘉靖《寧夏新志》卷1。
⑤c 張翰《松窗夢語》卷4。
①d 乾隆《祥符縣志》卷6。
②d 參閱陳春聲:《市場機(jī)制與社會變遷》第二章第三節(jié),中山大學(xué)出版社1992年版;羅一星《試論清代前期嶺南市場中心地的分布特點(diǎn)》,載《廣州研究》1988年第9期。
③d 參閱梁洪生:《吳城商鎮(zhèn)及其早期商會》,載《中國經(jīng)濟(jì)史研究》1995年第1期;蕭放:《明清江西四大鎮(zhèn)的發(fā)展及其特點(diǎn)》,載《平淮學(xué)刊》第五輯下冊,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版。
①e 參閱黃濱:《明清時期廣西“無東不成市”布局研究》,載《廣西社會》1992年第3期。
②e 參閱龍登高:《四川區(qū)域市場的歷史變遷》,待刊于《思想戰(zhàn)線》1997年第4期;林成西:《清代乾嘉之際四川商業(yè)重心的東移》,載《清史研究》1994年第3期。
①f 北宋沈括《夢溪筆談》卷12運(yùn)鹽之法為,每斤100里,陸運(yùn)4文,船運(yùn)1文。《慶元條法事類》卷37載,南宋按每百斤100里計地里腳錢,陸運(yùn)100文,水路溯流30文,順流10文。水運(yùn)的運(yùn)輸成本僅當(dāng)陸運(yùn)的20%—25%左右。元代差別也相似,據(jù)明人丘浚《大學(xué)衍義補(bǔ)》,“河漕視陸運(yùn)之費(fèi),省計三四;海運(yùn)視陸運(yùn)之費(fèi),省計七八。”
②f 蘇德祥《新修江瀆廟記》,《全蜀藝文志》卷37。
①g 《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38。
②g 《元史·河渠志》。
③g 許檀:《明清運(yùn)河的商品流通》,載《歷史檔案》1992年第1期。
①h 謝占壬:《古今海運(yùn)異宜》,載《皇朝經(jīng)世文編》卷48。
②h 《宋會要·食貨》18之31。
③h 《明太祖實錄》卷211,洪武二十四年八月辛巳。
篇6
關(guān)鍵詞:大分流 原始工業(yè)化 資本主義萌芽
一、引言
中國近代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是一段持續(xù)的過程,并不是全部外國資本主義的滲透,也有中國本身原始工業(yè)化發(fā)展因素的影響。正如諾斯所說“工業(yè)革命并非與我們有時所認(rèn)為的那種與根本決裂,恰恰相反它是以一系列漸進(jìn)變化的積累”。在中國整個近代化中,江南地區(qū)起著領(lǐng)導(dǎo)的作用,也是中國經(jīng)濟(jì)最發(fā)達(dá)的地區(qū)之一。雖然沒有自發(fā)地進(jìn)入近代化,但江南早期的工業(yè)化在明清時期有著出色的表現(xiàn),也為20世紀(jì)江南工業(yè)現(xiàn)代化的迅猛發(fā)展提供了許多貢獻(xiàn)性的因素。對中國明清時期的早期工業(yè)化的研究也是追溯工業(yè)化的源泉,了解中國工業(yè)發(fā)展歷史積累的必要。同時也會對現(xiàn)代農(nóng)村工業(yè)的發(fā)展有很好的啟示作用。
二、原始工業(yè)化理論綜述
原始工業(yè)化理論是美國學(xué)者門德爾斯于1969年首次提出構(gòu)想的。最初門氏將其定義為主要分散于農(nóng)村的制造業(yè)活動。1972年將其擴(kuò)展為“主要分布在農(nóng)村中的工業(yè)的迅速發(fā)展,它伴隨著鄉(xiāng)村經(jīng)濟(jì)的空間組織的變化”。在對弗蘭斯區(qū)域經(jīng)濟(jì)史研究中門德爾斯發(fā)現(xiàn),原始工業(yè)化的最終動力為人口壓力。18世紀(jì)末在弗蘭斯出現(xiàn)了原始工業(yè)化的時代,即手工業(yè)區(qū)與沒有家庭手工業(yè)的商業(yè)性的農(nóng)耕地區(qū),都存在市場的影響。后來克里得特等學(xué)者又?jǐn)U大為“農(nóng)村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生活完全活在很大程度上的依靠為區(qū)域間的市場或國際市場而進(jìn)行的大眾化生產(chǎn)”。總之,構(gòu)成原始工業(yè)化的三個要素為:農(nóng)業(yè)工業(yè),外部市場,商業(yè)性的農(nóng)業(yè)。
原始工業(yè)化理論為進(jìn)一步了解近代工業(yè)的歷史基礎(chǔ)和近代以前的歐洲以外的工業(yè)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理論工具,提出以后在歐洲以外的國家和地區(qū)引起了廣泛的反響。因為這些地區(qū)伴隨著歐洲近代工業(yè)化而來的同時也存在著大量的農(nóng)村工業(yè)。其理論被廣泛地用于東亞地區(qū),如近年來對日本、印度的經(jīng)濟(jì)史研究中,歐洲的原始工業(yè)化理論研究已成為一種模式。王國斌還認(rèn)為與歐洲原始工業(yè)化相關(guān)的那些條件,在明清時期的中國可能比歐洲更為普遍。在中國的經(jīng)濟(jì)史研究中,與此相關(guān)的是明清原始工業(yè)化發(fā)展的問題。
三、明清時期江南地區(qū)的原始工業(yè)化基本狀況
1.當(dāng)?shù)亟?jīng)濟(jì)的商品化發(fā)展概況
其具體表現(xiàn)為:棉花的種植刺激了手工紡織業(yè)的繁榮,常熟、無錫成為長江三角洲第二、第三的棉布貿(mào)易中心,每年分別有1000萬和300萬匹的棉布輸出;桑蠶和絲綢在蘇州府經(jīng)濟(jì)增長中占主要地位。桑蠶業(yè)在迅猛發(fā)展,在這一過程中絲織業(yè)幾乎完全脫離了農(nóng)耕而成為專業(yè)化的生產(chǎn)。到了晚清時期,許多絲織業(yè)是靠城鎮(zhèn)作坊中的雇傭完成的。但原材料的生產(chǎn)如植桑,養(yǎng)蠶和棉布紡紗織布一樣全是在小農(nóng)的家庭生產(chǎn)中進(jìn)行的。植桑栽培的擴(kuò)展使這一地區(qū)成為缺糧地區(qū),糧食作物也逐漸地商品化。
2.當(dāng)?shù)剌p工業(yè)的發(fā)展,以最為繁華的紡織業(yè)為例
紡織業(yè)是明清江南工業(yè)中最大的部門,是江南僅次于農(nóng)業(yè)的第二大產(chǎn)業(yè),在明清時期出現(xiàn)了重大變化。其發(fā)展表現(xiàn)為:(1)手工紡織產(chǎn)量規(guī)模的擴(kuò)大。在對整個江南地區(qū)棉布產(chǎn)量的估算中,得出“在明后期江南的棉布產(chǎn)量為5000萬匹,清中期為10000萬匹”。(2)生產(chǎn)技術(shù)的進(jìn)步:①不斷改進(jìn)的生產(chǎn)工具。如斜身式花機(jī)的出現(xiàn)大大改進(jìn)了織機(jī)的性能,提高了產(chǎn)品的質(zhì)量,增強(qiáng)了工人操作的精確度。②生產(chǎn)工藝的發(fā)展。棉布制造中,紋絡(luò)花樣等工藝的發(fā)展;此外棉布的染色技術(shù)也有提高。(3)分工與專業(yè)化的加強(qiáng)。較為復(fù)雜的工序中,專門的生產(chǎn)部門產(chǎn)生。如在棉紡織業(yè)中最重要的分工為織和紡的兩大工序的分離,手工業(yè)生產(chǎn)與農(nóng)業(yè)的分離,家庭內(nèi)部的分工。(4)地區(qū)專業(yè)化也日益加強(qiáng)。江南的松江、蘇州、無錫為棉紡織基地。(5)市場的擴(kuò)大華北和海外銷售市場的擴(kuò)大使得當(dāng)?shù)卦脊I(yè)化發(fā)展迅速。
四、對江南原始工業(yè)基本狀況的研究現(xiàn)狀
對江南地區(qū)的原始工業(yè)化研究中也許人們提到最多的是過于膨脹的人口增長,有限的土地規(guī)模造成的土地資源的相對短缺,內(nèi)卷化增長及江南地區(qū)的斯密型增長。海內(nèi)外學(xué)者對此各有所見,對江南原始工業(yè)化為何沒有發(fā)展成為近代工業(yè)的原因解釋也不勝枚舉,主要有:
1.黃宗智在分析長江三角洲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的商品化時是按照菜雅諾夫的邏輯
他指出在人口壓力下農(nóng)村家庭農(nóng)場不會產(chǎn)生資本主義的行為。他認(rèn)為甚為發(fā)達(dá)的商品經(jīng)濟(jì)卻阻撓了長三角地區(qū)經(jīng)營式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從而阻礙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fā)展。經(jīng)營式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逐漸被小農(nóng)家庭式耕作所取代;認(rèn)為明清時期該地區(qū)手工業(yè)增長小農(nóng)作業(yè)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資本積累上,包買商人傾向于流通領(lǐng)域。江南地區(qū)商品經(jīng)濟(jì)發(fā)展是建立在勞動投入的無限制增長上的勞動邊際報酬遞減的基礎(chǔ)上,走上了一條內(nèi)卷化、生活水平停滯和可用資源的全面壓力日益增長所構(gòu)成的模式。
2.國內(nèi)學(xué)者李伯重在《江南的近代化》描繪了江南工業(yè)的基本框架,以紡織業(yè)為例則表現(xiàn)為江南地區(qū)經(jīng)濟(jì)的斯密型增長
江南工業(yè)是“超輕結(jié)構(gòu)”,注重能源與材料的節(jié)省,使江南不可能出現(xiàn)能源或材料革命。而明清紡織業(yè)和英國的紡織品市場,從容量上來看都相差無幾,也無怪乎江南的原始工業(yè)化走出了與英國的“煤炭主義”道路不同的以紡織輕工業(yè)為主的道路。
3.于秋華認(rèn)為,在現(xiàn)實生活中江南地區(qū)斯密性增長和過密性增長相互交織發(fā)展
篇7
消費(fèi)結(jié)構(gòu)包括消費(fèi)需求、消費(fèi)水平、消費(fèi)方式和消費(fèi)品的類別與比例等項,能從一個重要方面反映一定社會經(jīng)濟(jì)形態(tài)的性質(zhì)。
一、人口壓力與人口流動所造成的消費(fèi)需求結(jié)構(gòu)對商品經(jīng)濟(jì)的作用
一切經(jīng)濟(jì)活動的最終動因是消費(fèi)的需要,人口作為社會生產(chǎn)活動的主體,既是生產(chǎn)力的構(gòu)成因素和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體現(xiàn)者,又是物質(zhì)資料的生產(chǎn)者和消費(fèi)者,一個社會、一個地區(qū)的人口,一方面依存于經(jīng)濟(jì),為經(jīng)濟(jì)水平所制約,另一方面也對經(jīng)濟(jì)發(fā)展產(chǎn)生作用。其中人口的消費(fèi)需求與生產(chǎn)結(jié)構(gòu)的性能密切相關(guān)。
在生產(chǎn)工具簡陋的古代農(nóng)業(yè)社會,生產(chǎn)的增長一般依靠充足勞動力的投入,即勞動密度的增加,因此經(jīng)濟(jì)繁榮往往以人丁興旺為標(biāo)尺。江南地區(qū)的開發(fā)得力于西晉末年開始的具有先進(jìn)勞動技能的北人南下。隨著勞動生產(chǎn)率的提高和外地人口的涌入,江南人口急劇膨脹,北宋時人稠地狹的矛盾已初露端倪,逮至明清階段人地關(guān)系的緊張愈演愈烈。就全國范圍看,明代人口最多時達(dá)一億左右。清乾隆在位的60年間連續(xù)突破兩億、三億大關(guān),道光年間竟增至四億。而偏處東南一隅的江南地區(qū)人口高度集中,雄居全國之冠,據(jù)推算:明代全國平均每平方公里人口數(shù)為19人,而浙江是114人(相當(dāng)于全國人口平均密度的600%),南直隸為48人(相當(dāng)于全國密度的250%);其中,蘇、松、嘉三府,每人平均占田數(shù)僅4畝左右,存在首大量的剩余人口。①]在前資本主義社會里,人口或勞動力過剩不是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必需,且成為經(jīng)濟(jì)和社會運(yùn)行的拖累,往往需要通過移民、擴(kuò)充軍隊、興辦公共工程等非生產(chǎn)方式來暫時消化一部分過剩勞動力。明清時期,北方的過剩人口很難解決,而江南地區(qū)由于商品經(jīng)濟(jì)的充分發(fā)展,較為成功地化解了這一難題,避免了因人口過剩而導(dǎo)致的流民動亂。
江南地區(qū)的可耕土地在北宋時即已開發(fā)殆盡。可是,一定量的土地能夠養(yǎng)活的人口量有一定的界限。在以機(jī)器、化肥、大規(guī)模的農(nóng)場經(jīng)營為標(biāo)志的近代農(nóng)業(yè)興起以前,挖掘土地潛力的主要方式是強(qiáng)化精耕細(xì)作,提高單位面積收益。但勞動投入的增加也并不單意味著使用更多的勞動力,相反由于勞動技能的熟練和改進(jìn)使生產(chǎn)率得到提高,將大量農(nóng)業(yè)勞動力從固定數(shù)額的土地上排擠出去。江南農(nóng)產(chǎn)之利,全在水田,因此江南人民千方百計地提高稻作集約化程度,如推廣雙季稻、稻麥連作、棉豆間作等,發(fā)展了多元性的農(nóng)業(yè)結(jié)構(gòu)。由于中國小農(nóng)經(jīng)濟(jì)以農(nóng)業(yè)和家庭手的結(jié)合為特征,提供手工業(yè)原料的經(jīng)濟(jì)作物得以迅速推廣——當(dāng)然也與經(jīng)濟(jì)作物的收益高于糧食作物有關(guān)。集約化耕作需要一定的農(nóng)業(yè)投資,又往往須現(xiàn)金支付,而清代江南農(nóng)家耕種十畝,還要“雇工以助之”,更需相當(dāng)數(shù)額的資金,所以不得不依賴家庭手工業(yè)收入來補(bǔ)充。與生產(chǎn)經(jīng)營的多樣化相適應(yīng),專業(yè)化亦有所提高。個體小生產(chǎn)者基于生產(chǎn)條件的差異和個人技能的專長、或?qū)iT從事糧食生產(chǎn),或?qū)iT種植經(jīng)濟(jì)作物(種棉、植桑等),還有的離開土地后專職人事絲、棉等家庭手工生產(chǎn)。生產(chǎn)經(jīng)營的多樣化與專業(yè)化帶有為“交換價值”而生產(chǎn)的性質(zhì)。與商品性生產(chǎn)相適應(yīng),并且由于人口依然大量過剩,眾多無地或少地以及土地瘠薄的人棄農(nóng)就商,或兼事貨殖作為副業(yè),如徐光啟所云:“南人大眾,耕懇無田,仕進(jìn)無路,則去而為末富、奸富者多矣。”②]
上面所述都加劇了江南工商業(yè)人口和半工商業(yè)人口比重的上升,這類人口多向新型的工商業(yè)市鎮(zhèn)集中。城鎮(zhèn)中的工商業(yè)者與市場聯(lián)系密切,他們隊伍的擴(kuò)大無疑促進(jìn)了商品交換與生產(chǎn)的發(fā)展,而且江南城居地主、官紳數(shù)量的龐大及其高消費(fèi)的生活方式,也成為商品市場經(jīng)濟(jì)高漲的一個動因。
二、消費(fèi)主體、消費(fèi)水平對商品經(jīng)濟(jì)的
明清江南地區(qū)的生活消費(fèi)水平較前有很明顯的提高,平均水平也高于同時期其它地區(qū)。然而,在商品市場經(jīng)濟(jì)的旋渦中,各個消費(fèi)主體由于本身經(jīng)濟(jì)能力與所處的經(jīng)濟(jì)環(huán)境不同,其消費(fèi)水平呈現(xiàn)出顯著的差異,這種差異與生產(chǎn)結(jié)構(gòu)、經(jīng)營相關(guān)聯(lián)。
實際上,明清江南人口的絕大多數(shù)仍然附在土地上,即便那些游離出來的工商業(yè)者,也與土地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guān)系,割不斷與土地聯(lián)系的臍帶。個體農(nóng)戶的多種經(jīng)營還是以種植糧食作物的農(nóng)耕生產(chǎn)為主體,尤其在肥美的水田地區(qū),主要種植稻作,兼種棉、桑等經(jīng)濟(jì)作物,糧食基本自給自足或半自足。少數(shù)以種植經(jīng)濟(jì)作物為主的農(nóng)家,口糧也多取自本地,交換行為基本在市鎮(zhèn)這類地方小市場完成。以糧食種植為中心、以糊口為目的的生產(chǎn)規(guī)定了消費(fèi)水平的低下和簡單。一般人家大都以織助耕,家庭手工業(yè)的大小直接關(guān)系到消費(fèi)水平的高低,“女工勤者,其家必興,女工游惰,其家必落;正與男事相類……且夫匹夫匹婦,男治田可十畝,女養(yǎng)蠶可十筐,日成布可二匹,或紡紗八兩,寧復(fù)憂饑寒乎?”③]這種配合緊密的男耕女織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的商品化發(fā)展,不僅解決了龐大人口的基本生活消費(fèi)問題,而且多余產(chǎn)品大量進(jìn)入交換領(lǐng)域,輸出埠外。但是,商品化生產(chǎn)的發(fā)達(dá)并沒有使江南人民突破“低消費(fèi)”的界定。就連植桑、養(yǎng)蠶、繅絲、織造專業(yè)化、商品化程度很高的湖州來說,廣大專事副業(yè)或手工業(yè)的個體家庭,仍然是靠換取糧食以維持生計和交納租賦以保障簡單再生產(chǎn)的進(jìn)行。鮮有財富的大量積累,故時人有曰:“湖絲雖遍天下,而湖民身無一縷,可慨!④]
當(dāng)然,與單純的經(jīng)濟(jì)下“低消費(fèi)”不同,明清江南地區(qū)的“低消費(fèi)”具有相對性。況且,消費(fèi)本身及其影響已逾出本區(qū)域,從而加強(qiáng)了小農(nóng)經(jīng)濟(jì)對市場的依賴性。
農(nóng)村以小農(nóng)經(jīng)濟(jì)為中心的商品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不可能完全解決嚴(yán)重的勞動力過剩問題,大量剩余勞動力轉(zhuǎn)化為比較固定的工商業(yè)者,并洶洶涌入城鎮(zhèn),成為市鎮(zhèn)勃興的重要因素。明清時期密如星斗的市鎮(zhèn),聚集了以工商者為主體的大量人口。基于農(nóng)工產(chǎn)品比價的“剪刀差”以及前資本主義商業(yè)的高額利潤,城鎮(zhèn)居民的消費(fèi)水平高于四鄉(xiāng)。隨著市鎮(zhèn)多方面的城市功能的增強(qiáng),特別是零售商業(yè)、鋪坊手工業(yè)、飲食業(yè)和酒樓、茶肆、妓院等行業(yè)的蜂起,加上大量地主、士紳的遷入,使得市鎮(zhèn)行政管理復(fù)雜化,官吏隊伍遽速壯大。這些達(dá)官貴人、富商巨賈憑藉經(jīng)濟(jì)、實力,消費(fèi)水準(zhǔn)高得驚人,高檔奢侈性消費(fèi)品的猛增促進(jìn)了商業(yè)的繁榮。但中小工商業(yè)者的生活用品基本來自本土所產(chǎn),他們所從事的商品性生產(chǎn)的發(fā)展主要緣自外地市場的需求。市鎮(zhèn)市場繁華絢麗,零售店鋪鱗次櫛比。可是,城市零售商業(yè)并非執(zhí)行流通任務(wù)的職能商人資本,而是一種“不執(zhí)行職能或半執(zhí)行職能”的“雜種”⑤],僅能說明消費(fèi)服務(wù)環(huán)節(jié)的流暢而已。至于飲食、服務(wù)、娛樂業(yè)更與社會再生產(chǎn)過程無緣。市鎮(zhèn)居民消費(fèi)水平的差異所造成的多重導(dǎo)向促使江南經(jīng)濟(jì)商品生產(chǎn)的種類多樣化。
蘇、杭等江南大城市的消費(fèi)水平總體上又高于市鎮(zhèn)。因其城市功能在明清時出現(xiàn)有利于商品經(jīng)濟(jì)的轉(zhuǎn)化,在較大程度上克服了政治中心官宦性消費(fèi)的弊端,所以消費(fèi)水平上升的重要意義表現(xiàn)為占有城市人口多數(shù)的一般工商業(yè)者經(jīng)濟(jì)能力的提高。明代蘇州西北閶門至楓橋是進(jìn)入蘇州的主干通道,這里列肆二十余里,居民數(shù)萬計。東北半城皆居機(jī)戶,“比戶皆工織作”。生產(chǎn)技能和生產(chǎn)率遠(yuǎn)遠(yuǎn)高于市鎮(zhèn)和鄉(xiāng)村的工商業(yè)者。較為豐厚的經(jīng)濟(jì)收入是消費(fèi)水平上升的基礎(chǔ)。清人錢詠追記明代蘇州商貿(mào)盛景:“吳中五方雜處,為東南一大都會,群貨聚集,何啻數(shù)十萬家。”⑥]這些來自外地和本地的富商大賈累資數(shù)萬、十萬、百萬計,由于商業(yè)資本在江南極難轉(zhuǎn)向產(chǎn)業(yè)資本,便大量消耗在奢侈性消費(fèi)中,由此刺激了商業(yè)的過度繁榮,也有利于販運(yùn)貿(mào)易的興旺、高檔商品生產(chǎn)的增長,并進(jìn)而為廣大的手工生產(chǎn)者和小商人提供了大量生存、經(jīng)營機(jī)會。商業(yè)和服務(wù)行業(yè)的繁榮消化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從而使社會秩序較為安定,使工商業(yè)的發(fā)展獲得了良好的社會環(huán)境。
另外,一些原來官宦性消費(fèi)極強(qiáng)的江南行政城市即府治、縣治的平均消費(fèi)水平也源于商品經(jīng)濟(jì)發(fā)展所導(dǎo)致的城市功能變動而得到提高。首先,工商業(yè)人口的數(shù)量增加,改變了人口的比例,擴(kuò)大了城市規(guī)模。如松江舊城狹窄,方圓不及九里。明隆慶、萬歷間,人口驟增,居民稠密。來自四鄉(xiāng)、外地的農(nóng)村過剩人口匯集在府城周圍。四郊十里左右,人口不下二十萬,大多數(shù)從事工商職業(yè)。府城東、西門是商業(yè)、手工業(yè)麋集區(qū)。萬歷年間,東城“男人制鞋”“輕俏精美”,“率以五六人為群”,“列肆郡中,幾百余家。”西門外,有暑襪店百余號,遠(yuǎn)方客商爭來購買。這些工商業(yè)人口的多樣性、復(fù)雜化的較高消費(fèi)來自市場,交換的擴(kuò)大又反過來刺激生產(chǎn)結(jié)構(gòu)的商品化程度。這樣的消費(fèi)顯然與官僚、軍隊、士紳、城居地主及其仆從的龐大消費(fèi)有別。此外,還有一個因素不能忽略,即當(dāng)時租稅折銀現(xiàn)象也促進(jìn)了市場交換的繁榮,盡管其中因商品作為租、賦轉(zhuǎn)化物的不純性而使交換摻雜著大量水份。
與物質(zhì)消費(fèi)提高相適應(yīng),江南城鄉(xiāng)不同層次的文化消費(fèi)也有了相當(dāng)可觀的提高和轉(zhuǎn)變,當(dāng)另文述及。
三、消費(fèi)品結(jié)構(gòu)、消費(fèi)行為結(jié)構(gòu)對商品的
依照“物的有用性”即使用價值在人類生活中的作用,消費(fèi)行為可大致劃分為一般性的日常生活消費(fèi)與奢侈性高消費(fèi)。
在消費(fèi)品總量中,一般日常消費(fèi)品質(zhì)量的提高和比重的增加,意味著社會經(jīng)濟(jì)正常、健康的和進(jìn)步。在前資本主義社會,雖然物質(zhì)生產(chǎn)水平低,但由于階級、等級、職業(yè)差別和財富差別的懸殊,享有特權(quán)或財富的“非生產(chǎn)者”的奢侈性消費(fèi)畸型地膨脹,其對市場的依賴性尤其促使長距離販運(yùn)貿(mào)易的片面發(fā)展,由此影響到生產(chǎn)結(jié)構(gòu)里勞動、資金的投入集中于奢侈性用品的生產(chǎn),從而相對削弱了日常生活用品的生產(chǎn)。高侈奢消費(fèi)行為還使勞動和資金流入商業(yè)、服務(wù)、娛樂業(yè)領(lǐng)域,浪費(fèi)了大量財富,在一定程度上堵塞了擴(kuò)大再生產(chǎn)的各種機(jī)會。
奢侈性消費(fèi)品與一般日常用品的界線不是一成不變的。明清江南地區(qū)某些原屬高檔消費(fèi)品的商品降為普及性的一般生活用品,這是一個可喜的征兆。如棉布衣飾在唐時僅為權(quán)貴服用,迄及,“凡棉布御寒,貴賤同之。”⑦]至清時,“江南一帶,康熙間,常服尚多用布。”到嘉慶間,已是“以布為恥,綾緞綢紗爭新色新洋。”⑧]棉布作為日常用品,其龐大的消費(fèi)需求有力地推動了棉花等經(jīng)濟(jì)作物的種植和棉紡織業(yè)的發(fā)展。絲織業(yè)中也存在相似的情形,如包頭絹行、改機(jī)行,都是生產(chǎn)與民間消費(fèi)有關(guān)的日常服飾品,包頭絹為創(chuàng)織細(xì)軟的紗代替高級品的精紗,而改機(jī)則是把原屬高級品的緞或紗改織成較堅實的綢,以利在民間擴(kuò)大銷路。這類日常用品范圍的擴(kuò)大、數(shù)額的增加、質(zhì)量的提高,有利于產(chǎn)品結(jié)構(gòu)擺脫前資本主義的性質(zhì)。
但明清江南地區(qū)消費(fèi)行為的兩極分化依舊嚴(yán)重,并且隨著商品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奢侈性消費(fèi)益發(fā)熾盛。康熙“盛世”之時,唐甄根據(jù)在蘇州一帶親歷,描繪了城鄉(xiāng)、貧富人家消費(fèi)和經(jīng)濟(jì)水平的巨大差距,“行于都市,列肆焜耀,冠服華朊,入其(農(nóng)家)家室,朝則熄無煙,寒則蜎體不申。”⑨]廣大生產(chǎn)主體的消費(fèi)能力低下,表明他們?nèi)狈?jīng)濟(jì)實力進(jìn)行擴(kuò)大再生產(chǎn)。
明清江南奢侈性高消費(fèi)是在商品經(jīng)濟(jì)廣泛發(fā)展的背景下形成的,這究竟與市場交換和生產(chǎn)結(jié)構(gòu)有什么關(guān)系呢?
四、奢侈性高消費(fèi)風(fēng)氣對商品經(jīng)濟(jì)的影響
在日常消費(fèi)品商品性生產(chǎn)增長的同時,明清江南的奢侈性高消費(fèi)品也與日俱增。消費(fèi)行為的“尚奢”風(fēng)習(xí)迷漫于大、中、小城鎮(zhèn)以至鄉(xiāng)村,見諸當(dāng)時士大夫充滿憤慨和憂患的議論,張瀚寫到:“至于民間風(fēng)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過于三吳,自昔吳俗奢華,樂奇異,人情皆赴焉……”⑩]尚奢恥儉還引起社會道德風(fēng)尚的變化,徐獻(xiàn)忠認(rèn)為:“今天下風(fēng)俗,惟江之南靡而尚華侈,人情乖薄,視本實者,競嗤鄙之。”[(11)]
以尚奢、薄情為特征的消費(fèi)、道德風(fēng)氣的嬗變大抵以嘉、萬時期作為一個轉(zhuǎn)折點(diǎn),“正、嘉以前,南都最為醇厚。”[(12)]許多“百不見一二之”的現(xiàn)象伴著明中葉江南商品經(jīng)濟(jì)的高漲層見疊出。“傳者謂:弘治時,世臣富;正德時,內(nèi)臣富;嘉靖時,商賈富;隆萬時,游俠富。”[(13)]商品經(jīng)濟(jì)的發(fā)達(dá)引動了奢侈性消費(fèi)的膨脹和社會風(fēng)氣的商品化。
產(chǎn)自江南的直接與商品生產(chǎn)有關(guān)的高檔商品主要是精致昂貴的絲織品。高檔絲織品工藝復(fù)雜,不僅需要手工精細(xì)的熟練操作,而且需要勞動分工和協(xié)作,這裨益于生產(chǎn)的集中化,因而絲織行業(yè)中的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場相對多一些,還出現(xiàn)了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某些變動。但大體上還是依靠熟練勞動力的勞動投入,精益求精,如此緊密的內(nèi)部組織結(jié)構(gòu)抑制了生產(chǎn)分工和協(xié)作的社會化。這種生產(chǎn)奉行質(zhì)量競爭的原則,不同于實行價格競爭的“合理化”生產(chǎn)——后者以改進(jìn)技術(shù)、擴(kuò)大產(chǎn)量、提高勞動效率為標(biāo)志,是近代資本主義生產(chǎn)的競爭、經(jīng)營方式。悠久的絲織業(yè)日益變?yōu)樯a(chǎn)高、精、尖產(chǎn)品的產(chǎn)業(yè),不能促使整個生產(chǎn)結(jié)構(gòu)的革命性變動。如同英國傳統(tǒng)的毛紡業(yè)一樣,既有強(qiáng)大的生命力(絲綢在近代國際市場仍有極強(qiáng)的競爭力),也有頑強(qiáng)的惰性。在歷史上,生產(chǎn)技術(shù)、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變革總是出現(xiàn)在新的產(chǎn)業(yè)上,如近代英國是在新興的棉紡工場里最先使用蒸汽機(jī),從而揭開了產(chǎn)業(yè)革命的序幕。
江南以絲織品為主的高層次消費(fèi)品遠(yuǎn)銷全國及海外,同時各地及海外的珍稀產(chǎn)品也大量的匯入江南市場。這決不僅僅在于富貴人家消費(fèi)水平即購買力的提高,亦與尚奢競侈的普遍風(fēng)尚相關(guān)。城鄉(xiāng)中、小人家很多貸錢購買金銀首飾,競為華侈。在蘇州,“不論富貴貧賤,在鄉(xiāng)在城,男人俱是輕裘,女人俱是錦繡。”[(14)]
奢侈性消費(fèi)刺激了商業(yè)、服務(wù)業(yè)的發(fā)達(dá),可以消化大批過剩勞動人口,從某種意義上說有一定的益處,清人顧公燮,體察到了這點(diǎn),“自古風(fēng)俗移人,賢者不免。山陜之人,富而若貧,江粵之人,貧而若富。即以吾蘇而論,洋貨、皮貨、綢緞、衣飾、金玉、珠寶、參藥諸鋪,戲園、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幾千萬人。有千萬人之奢華,即有千萬人之生理。若欲變千萬人之奢華而返于淳,必將使千萬人之生理,亦幾于絕,此天地間損益流通,不可轉(zhuǎn)移之局也。”又議論道:“治國之道,在于安頓窮人。……蘇郡五方雜處,如寺院、戲館、游船、賭博、青樓、蟋蟀、鵪鶉等局,皆窮人大養(yǎng)濟(jì)院。一旦令其改業(yè),則必至失業(yè),且流為游棍,為乞丐,為盜賊,害無底矣。”[(15)]然而,這種前資本主義性質(zhì)的“第三產(chǎn)業(yè)”脫離了物質(zhì)生產(chǎn)力水平。盛宴酒會、住宅園林、珠光寶器、陳設(shè)裝置、納妾宿妓、婚喪嫁娶的揮霍鋪張,以及過度的民間信仰、風(fēng)俗節(jié)日等方面的消費(fèi)對生產(chǎn)和商品生產(chǎn)的意義幾乎都是消極的。其對商品經(jīng)濟(jì)和社會生活的負(fù)面作用主要表現(xiàn)以下方面:
加劇市場畸型繁榮,浪費(fèi)巨大社會財富。高消費(fèi)的主體多為享有特權(quán)的官僚貴族、城居地主、富商大賈及其奴仆隊伍。他們的資財源于生產(chǎn)者的剩余產(chǎn)品,多是租稅的轉(zhuǎn)化形態(tài),如官俸即取自政府征收的田賦雜稅,以及各種法外收入。他們所購置的高檔奢侈性產(chǎn)品不管是本地所產(chǎn)還是靠長途販運(yùn)進(jìn)來的,價格都遠(yuǎn)遠(yuǎn)高于價值;加之他們的收入很多不是來自親身生產(chǎn),必然不甚計較商品的真實價值,如此一來一般生活用品的價格與高檔消費(fèi)品的價格之差距大得驚人。況且龐大的仆從隊伍也是消耗社會財富的重要因素。明清奴婢制度十分發(fā)達(dá),男優(yōu)女婢、青樓妓、輿夫傭仆,數(shù)量壯觀,“大家僮仆,多至萬指。”[(16)]“人奴人多,今吳中仕宦之家,有至一、二千人者。”[(17)]這些奴婢或半婢身份的“雇工人”多用于家內(nèi)服役,屬寄生性消費(fèi)人口。另外,活動在江南的外地商人和高利貸者為了抬高自己的社會身份,更為窮奢極侈,揮霍無度,時稱:“大抵吳人濫觴,而徽入導(dǎo)之。”[(18)]因本土地貧瘠、田賦沉重而難投資地產(chǎn)的徽商,其自身的家庭生活頗為節(jié)儉,但卻在盛宴酒會、納妾宿妓、娛樂游戲等社會化的消費(fèi)上不惜揮金如土。這也限制了商業(yè)、高利貸資本可能向產(chǎn)業(yè)資本轉(zhuǎn)化的量額。由各色富貴人家及其附從人口所造成的奢侈性高生活消費(fèi),使明清江南市場帶有畸型膨脹的病態(tài),尚奢風(fēng)氣滋長、蔓延、輻射到一般庶民地主和中小人家的日常消費(fèi)習(xí)俗上,即便外出打工糊口的行幫中,許多人也把血汗錢糟蹋在酒肆、賭場與戲館中。這種靡然風(fēng)行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短期消費(fèi)方式,嚴(yán)重?fù)p害了擴(kuò)大再生產(chǎn)所必需的資本積累。
江南本地富戶中,地主型居多,生活消費(fèi)主要來自田產(chǎn),有的也兼營商業(yè)、高利貸業(yè)。但由于地權(quán)可移動性的“軟化性格”,土地買賣在商品貨幣發(fā)達(dá)的氣候里更為頻繁,因此穩(wěn)定的田產(chǎn)收入得以權(quán)力所帶來的財富收入作保障,故而最終強(qiáng)有力維持奢侈生活的后盾是權(quán)力。江南士大夫如林如云,享有官銜和功名的士紳,包括現(xiàn)任官僚、致仕吏員以及生員、監(jiān)生,各恃自己的權(quán)勢,兼并土地。宦海沉浮,風(fēng)云變幻,故江南田地多易其主。因此,科舉入仕、破財捐官,用超經(jīng)濟(jì)的手段以保征經(jīng)濟(jì)利益的現(xiàn)象在江南地區(qū)尤其普遍。在這方面,殊為矚目的是占據(jù)明清江南商人資本市場最大份額的徽商、晉商等商幫的“政治性消費(fèi)”。許多徽商雖以微本起家,恪守職業(yè)道德,兢兢業(yè)業(yè),慘淡經(jīng)營,可一旦擁有一定的資財后便不惜血本勾通官府,謀求特權(quán)以賺取更多的利潤和減少經(jīng)濟(jì)的與非經(jīng)濟(jì)的搔擾、盤扣。大一些的徽商大都經(jīng)營受官府扶持和控制的鹽、茶販運(yùn)業(yè)和典當(dāng)業(yè),頗具官商色彩。政治性消費(fèi)的另一目的是抬高社會地位,炫耀門第。徽商還積極參予江南地區(qū)修路筑壩、賑災(zāi)救貧等公益、福利、慈善事業(yè),博取盛譽(yù)。此外,徽商等外地商人效法江南仕宦人家,將大量資財用于捐官和扶植鄉(xiāng)族子弟科舉入仕,不獨(dú)因為權(quán)力是財富的礦藏,還如汪道昆所言:“夫賈為厚利,儒為名高,夫人畢事儒不效,則馳儒而張賈,既側(cè)身飧其利矣,及為子孫計,寧弛賈而張儒。一張一弛,迭相為用。”[(19)]本來可以作為有力的經(jīng)濟(jì)力量的大量資財消耗在政治性的無謂投資上,這種物質(zhì)財富的“異化”消費(fèi)遏制了向產(chǎn)業(yè)資本轉(zhuǎn)化的欲望。
五、全國及海外消費(fèi)結(jié)構(gòu)與明清江南商品的互動
從明清江南市場的超區(qū)域輻射功能的視角,可以看到江南商品經(jīng)濟(jì)的及其特點(diǎn)與全國的消費(fèi)需求、消費(fèi)結(jié)構(gòu)互為制動、密切關(guān)聯(lián)。由于各地的生產(chǎn)、生活水平普遍低于江南地區(qū),使得江南以棉布、絲帛為主的農(nóng)、副、工產(chǎn)品遍銷全國及海外,而銷售路線的不斷轉(zhuǎn)移避開了某些地區(qū)生產(chǎn)發(fā)達(dá)后阻滯江南產(chǎn)品進(jìn)入的障礙。這就使得江南日常用品商品化生產(chǎn)因為有廣泛的市場需求而具備了持久的生命力,可同時也抹煞了生產(chǎn)技術(shù)突破性革新的要求。
國家維系龐大的官僚、軍隊等財政供給除來自賦稅外,也部分地與江南市場發(fā)生直接、間接的聯(lián)系,如“領(lǐng)織”、“市買”即是如此。特別是軍隊所用的棉布多是購自江南市場。封建國家這種巨大的軍政消費(fèi)需求對江南商品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另外,皇室、貴族、官僚和各地的地主、富商以及少數(shù)民族首領(lǐng)的奢侈性高消費(fèi)需求,了消費(fèi)結(jié)構(gòu)的比例和性質(zhì),對明清江南商品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發(fā)揮了不容低估的作用,這種作用如同前面的江南富貴階層消費(fèi)需求所產(chǎn)生的效果一樣,弊大于利。此外,海外市場對江南產(chǎn)品的消費(fèi)需求,基于明清政府對海外貿(mào)易的禁止和限制,以及以農(nóng)立國的大陸國家的特點(diǎn),對江南商品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的影響是偶發(fā)的、扭曲的、微小的。而不似近世之初的西歐國家由于海外市場對高檔消費(fèi)品需求的擴(kuò)大引起日用消費(fèi)品生產(chǎn)的增長,由此出現(xiàn)商品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的革命性變革。
六、小結(jié)
通觀明清時期以江南地區(qū)為主的全國消費(fèi)結(jié)構(gòu)在江南商品經(jīng)濟(jì)運(yùn)動中的地位和影響,可以得出帶有性的觀點(diǎn)。
人口密集的壓力是促使商品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最初、最直接的消費(fèi)動因。生產(chǎn)的日益商品化、工商業(yè)人口的增加和集中,使生活消費(fèi)愈來愈依賴市場。但消費(fèi)結(jié)構(gòu)的內(nèi)部比例依舊不合理。馬克斯·韋伯指出:“走向資本主義的決定性作用,只能出自一個來源,即廣大群眾的市場需求,這種需求只能通過需求的大眾化,尤其是遵循生產(chǎn)上層階級奢侈品的代用品路線,而出現(xiàn)于一小部分奢侈品中,這種現(xiàn)象以價格競爭為特征,而為宮廷進(jìn)行生產(chǎn)的奢侈品工業(yè)則遵循質(zhì)量競爭的手工業(yè)原則。”[(20)]固然與中國傳統(tǒng)商品生產(chǎn)相比,明清江南日常生活用品的商品化生產(chǎn)得到廣泛的、長足的發(fā)展,然而從質(zhì)量競爭變?yōu)閮r格競爭的新型消費(fèi)經(jīng)濟(jì)沒有形成一股不可阻擋的潮流,反因富貴階層消費(fèi)能力的提高和尚奢風(fēng)氣的普遍化,奢侈品的商品性生產(chǎn)惡性膨脹,并進(jìn)而加劇了交換的過度發(fā)達(dá)和市場的畸型繁榮。
通過對消費(fèi)結(jié)構(gòu)的剖析,可以看到明清江南商品經(jīng)濟(jì)的種種規(guī)定。城鄉(xiāng)普通人家尤其是農(nóng)戶的消費(fèi)水平相對低下,這主要是因為生產(chǎn)結(jié)構(gòu)里小農(nóng)業(yè)與家庭手工業(yè)結(jié)合的個體小農(nóng)經(jīng)濟(jì)的生產(chǎn)力伸張度有量與質(zhì)的限定。由于城鄉(xiāng)渾然一體,經(jīng)濟(jì)對流極不充分,城鄉(xiāng)交換仍舊限于地方小市場上的鹽、鐵、茶和糧食。城鎮(zhèn)市場的繁榮縱然與手工業(yè)的壯大有關(guān),但交換重于生產(chǎn)的前資本主義性質(zhì)一仍舊貫,較大規(guī)模的手工作坊、手工工場極為稀少,反映出生產(chǎn)分工與生產(chǎn)力依舊不發(fā)達(dá)。相反,城鎮(zhèn)珍稀奢侈品貿(mào)易、土特產(chǎn)貿(mào)易以及零售商業(yè)、飲食業(yè)、娛樂業(yè)的發(fā)達(dá)和市民文化的糜費(fèi)腐化,說明這種不合理的消費(fèi)結(jié)構(gòu)受到特定經(jīng)濟(jì)形態(tài)的制約。在這樣的背景下,商品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就難以出現(xiàn)質(zhì)的突破,以前的江南商品經(jīng)濟(jì)還是沒有自行走出中世紀(jì)。
注:
①參見從翰香《論明代江南地區(qū)的人口密度及其對的》,載于《史》1984年第3期。
②[明]徐光啟《農(nóng)政全書》卷9“農(nóng)事·開墾下”。
③[明]張履祥《補(bǔ)農(nóng)書》卷下。
④[明]宋雷《西吳里語》卷3。
⑤參見《資本論》第3卷320、327頁。
⑥[清]錢泳《履園叢話》卷24下“雜記下”。
⑦[明]宋應(yīng)星《天工開物》上卷,“乃服第二卷”。
⑧[清]黃印《錫金識小錄》卷1。
⑨[清]唐甄《潛書》下篇上,“存言”。
⑩[明]張瀚《松窗夢語》卷4,“百工紀(jì)”。
(11)[明]徐獻(xiàn)忠《吳興掌故集》卷13“風(fēng)土”。
(12)[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卷1。
(13)[清]孫之騄《二申野錄》卷4。
(14)[清]錢詠《履園叢話》卷7“臆論”。
(15)[清]顧公燮《消夏閑記摘抄》上。
(16)萬歷《嘉定縣志》卷2“疆域志·風(fēng)俗”。
(17)[清]顧炎武《日知錄》卷13,“奴仆”。
(18)[明]王世貞《觚不觚集》。
篇8
關(guān)鍵詞:貴州 明清 東西干線 文化線路
中圖分類號:K203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0-8705(2013)04-107-110
文化線路是近年來國際遺產(chǎn)保護(hù)界新興的一種開放的、動態(tài)的遺產(chǎn)類型。在中國,此項保護(hù)工作啟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是2009年中國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無錫論壇上發(fā)表的《無錫倡議》。《倡議》中,來至國內(nèi)外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領(lǐng)域的專家學(xué)者共同呼吁,以科學(xué)的態(tài)度重新審視和保護(hù)中國的線路文化遺產(chǎn)。所謂驛道文化線路是將陸路、水路或其他交通線路用一種有歷史聯(lián)系和文化關(guān)聯(lián)的動態(tài)方式集中起來,其中涵蓋了較多的遺產(chǎn)種類,除與驛道本身有關(guān)的文化遺產(chǎn)之外,還包含了線路在發(fā)展和演變過程中所帶來的人口流動、商貿(mào)往來、文化傳播、教育觀念改變等共同體現(xiàn)在物質(zhì)和非物質(zhì)上的歷史文化遺產(chǎn)。
貴州驛道文化線路遺產(chǎn)資源尤為豐富。明清時期,統(tǒng)治者十分重視貴州的戰(zhàn)略地位。明洪武十四年,為了控制云南,加強(qiáng)對西南邊疆的統(tǒng)治,明朝在元朝已開通的東西干線基礎(chǔ)上進(jìn)行整修,并在岳州至貴州(今貴陽)沿線設(shè)置了25驛,“一驛儲糧三千石,小旗一人領(lǐng)軍十人守之”以傳遞軍情,備足糧草,為討伐云南作準(zhǔn)備。在貴州境內(nèi),明朝沿線自西向東設(shè)亦資孔驛(今盤縣亦資孔)、湘滿驛(今盤縣西北)、新興驛(今普安縣)、尾灑驛(今晴隆縣)、渣城驛(今關(guān)嶺永寧)、關(guān)嶺驛、安莊驛(今鎮(zhèn)寧安莊坡)、普利驛(今安順市)、平壩驛、威清驛(今清鎮(zhèn)縣城)、貴陽驛、龍里驛(今龍里縣城)、新添驛(今貴定縣城)、平越驛(今福泉縣城)、清平驛(今凱里清平)、偏橋驛(今施秉縣城)、鎮(zhèn)遠(yuǎn)驛(今鎮(zhèn)遠(yuǎn)縣城)、水馬驛(今鎮(zhèn)遠(yuǎn)清溪西)、清浪驛(今鎮(zhèn)遠(yuǎn)清溪)、平溪驛(今玉屏),共20驛,其間還另設(shè)有12站。這條連接今云南、貴州、湖南的東西干線即為文獻(xiàn)所載的明清滇黔和湘黔主驛道。
一、線路上多維度的交流和對話
對貴州而言,交通線到達(dá)什么地區(qū),就會給當(dāng)?shù)貛戆l(fā)展的動力,改善交通條件是改變當(dāng)?shù)厣鐣顩r的重要方式。明清東西干線的暢通,使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得以多維度、大尺度的交流和互惠,溝通了貴州與鄰省及中原內(nèi)地多元化的文明對話,并由此發(fā)展和擴(kuò)散開來,極大地促成了西南民族地區(qū)與中原內(nèi)地文化的融合,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中原先進(jìn)農(nóng)耕技術(shù)的傳人。自洪武以來,明朝大舉推行屯田制,史載:“于時,東至遼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肅,南盡滇蜀,極于交趾,中原則大河南北,在在興屯矣。”貴州衛(wèi)所屯田數(shù)量十分可觀,據(jù)史記載,僅貴州都司所屬18衛(wèi)2所屯田近100萬畝。如此大面積的土地開發(fā),得益于隨軍屯、民屯而傳人的先進(jìn)的中原農(nóng)業(yè)耕種技術(shù),如耕牛的使用,水利的興修、育種的推廣、土質(zhì)的改良等。《明史食貨志載》:“每軍授田五十畝為一分,給耕牛農(nóng)具,教植樹”。大片的中原式農(nóng)田,在滇黔、湘黔驛道兩邊的壩子中與當(dāng)?shù)匕傩盏奶锿料嗷ソ诲e,漢、夷共同交流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經(jīng)驗,推動了貴州社會經(jīng)濟(jì)的大發(fā)展。
第二,沿線城鎮(zhèn)經(jīng)濟(jì)交往頻繁。自洪武年問貴州開設(shè)衛(wèi)所以后,永樂時期又增設(shè)了府、州、縣,它們大多散布在滇黔和湘黔驛道上,最初僅僅是軍事防御據(jù)點(diǎn)和官府所在地,由于地處交通線邊緣,附近又有密集的屯堡,便逐漸形成商業(yè)活動頻繁的集市。隨著貿(mào)易的不斷增加,一些大集市附近發(fā)展成為聚落區(qū),進(jìn)而演變成沿線重要的古城鎮(zhèn)。而城鎮(zhèn)經(jīng)濟(jì)發(fā)展也與交通條件的改善相輔相成,在湖廣通往云南的主干線上,每年過往馬匹不下三四千匹,往來商旅、運(yùn)夫不計其數(shù),沿線城鎮(zhèn)自然成為溝通不同區(qū)域、不同民族之間的經(jīng)濟(jì)聯(lián)系的紐帶。如湘黔驛道入黔門戶鎮(zhèn)遠(yuǎn),素有“水陸驛站”之稱,城內(nèi)有來至江西、湖廣和南京的商人,云南的銅、錫從普安入黔后,經(jīng)過二十余站到達(dá)鎮(zhèn)遠(yuǎn),再改走水路運(yùn)至湖南常德。又如滇黔驛道上的普定和普安,城內(nèi)商賈云集,物產(chǎn)富饒,市場內(nèi)尤以大宗牲畜交易較為發(fā)達(dá),大量馬匹交易在此產(chǎn)生,馬匹一部分是進(jìn)貢京城。《明實錄》記載:“洪武十七年十二月甲寅,貴州都司送所市馬四百匹至京師”,又“洪武十八年正月癸酉,四川、貴州二都司送所市馬一萬一千六百匹至京師”,另一部分則是販賣給云南。東西省際干線的的暢通,為所有城鎮(zhèn)的商業(yè)活動和貿(mào)易往來提供了便利的前提保障。
第三,極具地域特色的屯堡文化形成。隨著明朝“調(diào)北征南”、“調(diào)北填南”等一系列軍事政治和后續(xù)開發(fā)西南邊疆的舉措,大批來至自安徽、江蘇、江西、浙江、河南等地的軍事和半軍事移民及其家眷入駐貴州,主要居住在東西驛道沿線周圍,尤其是安順普定、安莊、平壩三個衛(wèi),一般每百戶為一屯或堡。這些屯堡移民不僅改變了當(dāng)?shù)孛褡褰Y(jié)構(gòu),還從某種程度上影響了貴州多元文化的格局,并形成極具地域特色的“屯堡文化”現(xiàn)象。六百年來,明朝在全國各地設(shè)置的屯堡早已消失殆盡,而貴州東西省際干線上的屯堡村寨卻始終堅守著中原和江南地區(qū)漢民族的禮俗文化、建筑文化、服飾文化、飲食文化、娛樂文化、宗教文化和民間信仰。尤其是屯堡娛樂文化中的“地戲”,源于明朝軍隊里盛行“軍儺”,是屯堡人獨(dú)有的民間戲劇,“借以演習(xí)武事,不使生疏,含有寓兵于農(nóng)之深意。”后與中原民間傳承的儺戲結(jié)合而成為貴州獨(dú)特的文化遺存。
第四,儒學(xué)教育的推廣。明代是貴州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歷史時期。儒學(xué)勃然興起,一方面與明朝“治國以教化為先,教化與學(xué)校為本”有關(guān),另一方面也與驛道沿線的衛(wèi)所有關(guān)。明代衛(wèi)所中的軍事移民大多來至于文化較發(fā)達(dá)的江蘇、江西、安徽、浙江、河南等地,到貴州后普遍要求興辦儒學(xué),使其后代有讀書習(xí)禮的機(jī)會。故儒學(xué)教育首先在衛(wèi)所住地發(fā)展起來,并成為貴州教育的先導(dǎo)。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普定衛(wèi)儒學(xué)率先建立,為全省樹立了榜樣,隨后在東西驛道沿線上,凡有條件的衛(wèi)都建立了衛(wèi)學(xué),有州學(xué)的衛(wèi)寄學(xué)于州學(xué)。貴州衛(wèi)學(xué)在明代官學(xué)中占的比重較大,數(shù)量相當(dāng)于官學(xué)總數(shù)的一半以上。這些學(xué)校,不但為貴州培養(yǎng)了人才,還向國子監(jiān)輸送了一批監(jiān)生。從這個角度來說,東西干線促成了儒學(xué)教育在貴州的大力推廣。
二、沿線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現(xiàn)狀
1、沿線文化遺產(chǎn)的特點(diǎn)
東西驛道是貴州較早開通的交通線之一,也是明清以來貴州最主要的省際干線,至今保存著許多反映喀斯特地區(qū)高原山地、丘陵盆地地貌特征的驛道、橋梁、關(guān)隘、碼頭、渡口等交通設(shè)施,以及沿線古驛站、古村落、古城垣等遺跡和書院、茶店、會館、寺廟、民居等古建筑遺址,還有寓于其中豐富的社會風(fēng)情、文學(xué)作品、歷史傳說等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極大的豐富了文化遺產(chǎn)類型,是一條較為典型的歷史文化線路。明清東西干線從不同角度反映了歷史上貴州與中原以及周邊地區(qū)的商品、思想、知識及價值的互惠和持續(xù)不斷的交流,生動地展現(xiàn)出貴州文化的歷史脈絡(luò),闡釋了作為驛道文化線路的內(nèi)涵,為研究滇、黔、湘古代社會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民族關(guān)系、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實物佐證。
2、物質(zhì)和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現(xiàn)狀
1)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
貴州明清東西干線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指與驛道有關(guān)或因為驛道而帶來的古建筑、古遺址。干線自西向東先后穿過今天的盤縣、普安、晴隆、關(guān)嶺、安順、平壩、清鎮(zhèn)、貴陽、龍里、貴定、福泉、黃平、施秉、鎮(zhèn)遠(yuǎn)、玉屏15個縣市,根據(jù)調(diào)查和統(tǒng)計,沿線具有代表性的古遺址86處,其中國家級1處,省級6處,縣級38處,其他41處;古建筑152處,其中國家級7處,省級38處,縣級49處,其他58處;摩崖、碑刻11處,共計249處。以上有形文化遺產(chǎn)通過確定不同級別的文物保護(hù)單位來加以保護(hù),其中國家級的文物保護(hù)單位占總數(shù)的3.21%,省級的占17.7%,縣級的占34.9%,可見沿線古遺址、古建筑保存現(xiàn)狀十分令人擔(dān)憂,各級政府相關(guān)部門保護(hù)的力度還有待加強(qiáng)。
2)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
根據(jù)文化線路遺產(chǎn)內(nèi)容的劃定,除相關(guān)的有形文化遺存外,還包括反映該線路多維度對話交流所帶來的無形文化遺存。東西干線沿線至今仍然保存著許多以非物質(zhì)形態(tài)存在的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guān)、世代相承的傳統(tǒng)文化,其表現(xiàn)形式尤為豐富,如口頭傳誦、傳統(tǒng)表演藝術(shù)、民俗活動、禮儀與節(jié)慶、民間傳統(tǒng)知識和實踐、傳統(tǒng)手工藝技能等。沿線17項國家級、99項省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中,有9個傳承人獲批國家級傳承人,占表中總數(shù)的52.9%,37個傳承人獲批省級傳承人,占總數(shù)的37.4%,說明政府有關(guān)部門已經(jīng)充分認(rèn)識到保護(hù)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必須首先保護(hù)傳承人的重要性。
三、沿線文化遺產(chǎn)價值評估
作為文化遺產(chǎn)載體的驛道及其附屬設(shè)施,以及因驛道的修建、開通而積淀下來的無形文化遺產(chǎn),首先具有的是久遠(yuǎn)的歷史價值。從相關(guān)的文獻(xiàn)資料記載中可知,明清以前貴州就已經(jīng)與鄰省云南、四川、湖南存在多渠道的溝通和交流了。從秦漢至明清,歷朝歷代的統(tǒng)治者為治理西南邊疆,無一不注重驛道的開辟和郵驛制度的完善。貴州乃至整個西南地區(qū),及至明清在時間和空間上完全延續(xù)和繼承了古代傳統(tǒng)的驛道線路文化遺產(chǎn),并不斷的加以完善,形成了以湘黔、滇黔及其他主干線路網(wǎng),并積淀了眾多的因驛道而帶來的歷史文化遺產(chǎn)族群。從這個角度來說,貴州明清東西干線承載了上千年的傳統(tǒng)驛道文化,具有厚重的歷史價值。
其次是具有不可復(fù)制的文化遺產(chǎn)價值。從明清東西干線采集的物質(zhì)和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信息看,不僅涵蓋了與驛道有直接關(guān)系的不可移動文化遺產(chǎn),如橋梁、道路、關(guān)隘、渡口、碼頭等,以及沿線基礎(chǔ)設(shè)施和文化交流所帶來的不同區(qū)域風(fēng)格的古建筑,如館舍、馬店、書院、寺廟、古井等古遺址,而且還涵蓋了建立在與云南及中原內(nèi)地動態(tài)的、持續(xù)的、多維度的文化、教育、科技領(lǐng)域交流理念上的無形文化遺產(chǎn),集中表現(xiàn)在沿線名城古鎮(zhèn)的興起;商品貨物持續(xù)的交換;多民族文化的再融合;教育理念及社會風(fēng)氣的轉(zhuǎn)變;宗教的傳入和儒家思想的傳播,以及文學(xué)作品的產(chǎn)生、制度文化的完善等等。無論是物質(zhì)的,還是非物質(zhì)的,均充分體現(xiàn)了沿線文化遺產(chǎn)的豐富性,具有不可復(fù)制的文化遺產(chǎn)資源價值。
第三是驛道賴以存在的生態(tài)價值。貴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和豐富的木材資源,為驛道、橋梁的修筑和搭建提供了取之不盡建筑材料。貴州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驛道、橋梁是當(dāng)?shù)厥慕ㄔ斓模瑘怨痰氖氖构诺馈蛄旱靡员4嬷两瘛6S富的木材資源,使驛道沿線驛站、會館、馬店、民居、書院、寺廟、道觀等古建筑呈現(xiàn)以木材建造為主的特色。此外,喀斯特地貌也為貴州驛道打上山地文化特色的烙印。根據(jù)調(diào)查,無論是湘黔、滇黔、川黔,還是黔桂驛道,所經(jīng)之地地形復(fù)雜多變,山川盆地,懸崖河谷,森林平原,無所不有,這樣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滋養(yǎng)著驛道空間構(gòu)造上的特殊性。反過來,它的暢通,也給賴以存在的環(huán)境積淀了豐厚的文化底蘊(yùn)。
第四是潛在的旅游開發(fā)價值。作為一種線性文化遺產(chǎn)載體,貴州驛道文化線路聚集了沿途眾多的文化景觀,串聯(lián)起人文與自然、有形與無形、可移動與不可移動的文化遺產(chǎn)資源,具有不可估量的旅游價值。它拓展了當(dāng)今人們對人文生態(tài)旅游的理解,提高了文化線路旅游的品位,讓游客既學(xué)習(xí)了驛道文化的歷史知識,又能享受和體驗驛道上的自然人文景觀,以及沿線的傳統(tǒng)文化、民族風(fēng)情。開發(fā)明清東西干線文化線路,對于填補(bǔ)當(dāng)今文化旅游的空白,打造貴州旅游大省,形成特色旅游品牌,繁榮地方經(jīng)濟(jì),提高驛道沿線人民生活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四、小結(jié)
明清東西省際干線是集沿途古聚落、古建筑及交通附屬設(shè)施等文化遺存要素在內(nèi)的一種線形文化遺產(chǎn)的集合,既有線路本身的物質(zhì)文化價值,又有依賴于山川、河谷生態(tài)價值,還有因線路而帶來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價值。歷史上,貴州社會的開發(fā)與進(jìn)步與四通八達(dá)的省際干線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加強(qiáng)對線路文化遺產(chǎn)的研究和保護(hù),有利于進(jìn)一步整合線路文化遺產(chǎn)資源、提升文化遺產(chǎn)價值,確立今后保護(hù)文化遺產(chǎn)的新視野,同時,保護(hù)和復(fù)活驛道線路文化遺產(chǎn),可拓展當(dāng)代人文化旅游的內(nèi)涵和外延,促進(jìn)文化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實現(xiàn)貴州地方經(jīng)濟(jì)、社會的可持續(xù)和諧發(fā)展。
參考文獻(xiàn):
[1]《明實錄·太祖洪武實錄》卷157[M].
[2]《明史》卷77,《食貨志》[M],中華書局,1974年版.
篇9
明清時期,歷代統(tǒng)治者也不斷強(qiáng)調(diào),將備荒倉儲建設(shè)置于重要的位置,如朱元璋曾說:“務(wù)農(nóng)重谷,王政所先。古者民勤耕稼之業(yè),故三年耕則余一年之食,九年耕則余三年之食,二十七年耕則余九年之食,是以歲或不登,民無饑色,以儲蓄有素故也。朕屢敕有司勸課農(nóng)桑,而儲蓄之豐未見其效,一遇水旱,民即饑?yán)А9蕠L令河南等處郡縣,各置倉庾,于豐歲給價糴谷,就擇其地民人年高而篤實者主之,或遇荒歉,即以賑給,庶使民得足食,野無餓夫。其有未備之處,宜皆舉行。”他先是“令天下立預(yù)備倉,糴谷收貯以備賑濟(jì)”,后來又感到常平倉平抑糧價的作用不可低估,遂下詔:“今后宜令各府州縣設(shè)常平倉。每遇秋成,官出錢鈔收糴入倉。如遇歉歲,平價出糶。蓋米價不踴則物價自平,如此則官不失得,民受其惠矣。”其后歷朝皇帝也多有強(qiáng)調(diào),如嘉靖三年,“令各處府按官督該司處置預(yù)備倉,以積糧多少為考績殿最”。清朝建立后,也仿照歷代舊制,推行倉儲建設(shè)。順治十七年,戶部議定常平倉每年春夏出糶,秋冬糴還,平價生息,兇歲則按數(shù)給散貧戶。后歷代清帝也屢頒詔旨,要求各地推行,如康熙二十九年正月詔諭:“重念食為民天,必蓋藏素裕而后水旱無虞。曾經(jīng)特頒諭旨:著各地方大吏督率有司,曉諭小民,務(wù)令多積米糧,俾俯仰有資,兇荒可備,已經(jīng)通行。其各省遍設(shè)常平及義倉、社倉,勸諭捐輸米谷,亦有諭旨允行。后復(fù)有諭旨:常平等倉積谷,關(guān)系最為緊要。見今某省實心奉行,某省奉行不力,著再行各該督撫,確察具奏。朕于積貯一事,申飭不啻再三。藉令所在官司能俱體朕心,實有儲蓄……嗣后直省總督、巡撫及司道府州縣官員,務(wù)宜恪遵屢次偷旨,切實舉行,俾家有余糧、倉庾充牣,以副朕愛養(yǎng)生民至意。如有仍前玩愒、茍圖塞責(zé)、漫無積貯者,將該管官員及總督巡撫,一并從重治罪。爾部即遵諭通行。”[1]雍正帝尤其強(qiáng)調(diào)倉儲的積谷備荒作用,指出:“積貯倉谷,關(guān)系民生,最為緊要。”在各種倉儲中,他特別重視社倉建設(shè),認(rèn)為“備荒之倉莫便于近民,而近民莫便于社倉”,即位不久即諭令各省建立社倉,并要求“有司善為倡導(dǎo)于前,留心稽核于后,使地方有社倉之宜,無社倉之害”[3]。由于皇帝的重視,各地社倉建設(shè)捷報頻傳,雍正二年時,各省已“漸行社倉之法”,并最終形成了“省會以至州郡俱建常平倉,鄉(xiāng)村則建社倉,市鎮(zhèn)則設(shè)義倉,而近邊有營倉之制,所以預(yù)為之備者,無處不周矣”的局面,建立起較為完備的備荒倉儲體系。
二、宗族社會保障的發(fā)展
宗族是以父系血緣關(guān)系為紐帶的人類生活共同體。在歷史發(fā)展的不同階段,宗族制度的表現(xiàn)形式與性質(zhì)也不相同。宋代以后,宗族制度發(fā)生了顯著變化。針對人們血緣觀念淡薄的現(xiàn)象,官僚士大夫發(fā)起重整宗族制度的活動,一方面通過提倡孝悌倫常,加強(qiáng)對族人思想的控制,另一方面設(shè)置族田、建立義莊,通過保障或改善宗族成員生活的手段,維護(hù)子孫的生存,達(dá)到“敦本收族”的目的。最早的宗族義莊制度可以追溯到北宋范仲淹創(chuàng)立的范氏義莊。1049年任知杭州時,盡出自己多年積余的俸祿,在故鄉(xiāng)蘇州買田千畝,捐為范氏宗族公產(chǎn),稱為“義莊”,其所得租米,分與全體宗族成員“,供給衣食及婚嫁喪葬之用”。為了保證義莊的運(yùn)營和持續(xù),范仲淹還親自制定《義莊規(guī)矩》,對義莊收入的分配作了具體安排,對于所有宗族成員都給予定量的糧食布匹,對婚嫁喪葬等給予補(bǔ)助,表現(xiàn)出普遍福利的性質(zhì)。其后又對宗族子弟的讀書就學(xué)以及參加科舉進(jìn)行物質(zhì)激勵。正因為如此,范氏宗族成員的生活不只能基本維持,而是得到較大改善,普通族人自不待言“,雖至貧者,不復(fù)有寒餒之憂”[6]。范氏義莊起了開導(dǎo)風(fēng)氣、模范后世的作用。明清時期,宗族制度的發(fā)展進(jìn)入了新的階段。為了重整封建宗法關(guān)系,明代各個宗族紛紛建祠修譜、創(chuàng)立族田義莊,族田義莊的數(shù)量由是大為增加,所謂“蘇郡自宋范文正公建立義莊,六七百年世家巨族踵其法而行者,指不勝屈”[7]“;自明以來,代有仿行之(范氏義莊)者,而江以南尤盛”[8]。據(jù)李文治、江太新先生的粗略統(tǒng)計,明代276年間,各地族田義莊資料約有200宗左右,遠(yuǎn)遠(yuǎn)超過宋元兩代的總和(400年間約70余宗)[9]。進(jìn)入清代以后,由于皇帝的重視和倡導(dǎo),加上社會環(huán)境的變化,宗族勢力日益膨脹,如康熙帝頒行“圣諭”十六條,首條即“敦孝弟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雍正帝積極闡揚(yáng)康熙帝的“圣諭”十六條,鼓勵宗族“立家廟以薦蒸嘗,設(shè)家塾以課子弟,置義莊以贍貧乏,修族譜以聯(lián)疏遠(yuǎn)”。皇帝的詔諭得到地主士紳的積極響應(yīng)。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xiàn)了設(shè)立義莊的,以致有“義莊之設(shè)遍天下”的說法。據(jù)范金民的統(tǒng)計,至清代末年,僅蘇州府的義莊數(shù)即達(dá)到200個之多[10]。適應(yīng)宗族人口增加、規(guī)模擴(kuò)大等情況,明清時期宗族社會保障主要表現(xiàn)為周貧、濟(jì)困的特點(diǎn)。范氏義莊的變遷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diǎn)。義莊初設(shè)時,范氏族人僅90余口,歲入租米800斛,故“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余而無窮”[1]。由于宗族成員不斷增加,生齒日繁,而義田數(shù)量所增有限,且賦課繁重,普遍福利的原則雖未打被,但已窒礙難行,逐漸向以救助族中之貧困成員為主轉(zhuǎn)變。為此清朝康熙十七年《續(xù)申義莊規(guī)矩》中規(guī)定:“體貧勸學(xué)以示教養(yǎng)。祖澤本以周急不以繼富,嗣后子孫寡婦貧無子老至六十、貧有子老至七十者,俱計年遞加優(yōu)給;其家殷者,雖老無子,例不加給。”喪葬撫恤亦以貧富為實施原則[2]。其后主奉范能滸再次增改,規(guī)定:子孫年滿16歲,經(jīng)審核后可以本名支取一份米糧,“年至六十以上加優(yōu)老一戶,七十以上加二戶,八十以上加三戶,九十以上加四戶,如內(nèi)有無子孫者再加一戶,如有廢疾不能自營衣食者再加一戶。加給之?dāng)?shù)通不得過五戶。如有家道殷實不愿支給者聽”;“寡婦守節(jié)滿三年者,本房房長及親支保明,批給本名一戶米,五年以上加一戶,十年以上加二戶,十五年以上加三戶,二十年以上加四戶,過此不加給。”[3]在后來的《增定廣義莊規(guī)矩》中,明確“濟(jì)貧”宗旨,對貧困族人予以特別照顧,規(guī)定:“謹(jǐn)考先規(guī),子孫不論貧富均沾義澤,遇有極貧,量加周贍,似可無庸再益。但有貧病交加,實在不能自存者,允誼矜念,以廣先仁。每歲房支長報名,執(zhí)事核實,每名給米一戶,稍資澶粥,極困者量加。”[4]由此可見,時代愈后,范氏義莊愈是強(qiáng)調(diào)濟(jì)貧功能。從各宗族義莊所訂的規(guī)則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周貧、濟(jì)困的特點(diǎn)。江蘇無錫膠山《安氏家乘》載有立于萬歷二十三年的“贍族條件”,其中規(guī)定:“族人年力已衰、家無恒產(chǎn)、不能經(jīng)營生理者,極貧月給米六斗、冬夏布銀五錢,次貧月給米三斗、冬夏布銀三錢,其能自給者,夏送醬麥五斗、夏布銀二錢,冬送糕米一石、布銀三錢”;“族有孀居無子,或子幼貧不能養(yǎng)者,極貧月給米五斗、冬夏布銀五錢,次貧月給米三斗、冬夏布銀三錢,其子成立,住月給米,仍給冬夏布銀”;“族人年幼父母俱亡、無兄長撫育者,許近屬收養(yǎng),月給米三斗,歲給布銀三錢”;“族有孤貧不能自婚者,極貧助銀五兩,次三兩,又次二兩;女不能嫁者,如之……”;“族人有喪貧不能斂葬者,極貧而年高有行者,助銀八兩,次五兩,又次三兩”;“族人有臥病危迫、貧不能自醫(yī)藥者,其近屬為之延醫(yī)診視,助醫(yī)藥之費(fèi)”;“族中子弟有讀書向進(jìn)而家貧者,縣試給紙筆銀三錢正案,府試給紙筆路費(fèi)銀五錢,院試給紙筆路費(fèi)銀壹兩,進(jìn)學(xué)助巾衫銀壹兩五錢。鄉(xiāng)試助路費(fèi)銀二兩”。可見,安氏家族重點(diǎn)對“族人年力已衰、家無恒產(chǎn)、不能經(jīng)營生理者”、“族有孀居無子,或子幼貧不能養(yǎng)者”“、族人年幼父母俱亡、無兄長撫育者”“、族有孤貧不能自婚者”“、族人有喪貧不能斂葬者”“、族人有臥病危迫、貧不能自醫(yī)藥者”、“族中子弟有讀書向進(jìn)而家貧者”等幾種情況進(jìn)行資助,明顯表現(xiàn)出“周貧濟(jì)困”的特點(diǎn)[5]。浙江蕭山來氏于康熙五十年所訂“來氏賑米條款”中指出:“宗祠給米,本為孤寡老疾四項極貧無靠而設(shè),其中稍可自存活與親屬可依倚者,便在可以與可以無與之間。夫米止有此數(shù),可以無與而與,則不可不與者與之反少,非哀煢獨(dú)惠鰥寡之道,故不得不有所分別而稍靳之也”。據(jù)此作出具體規(guī)定,對于“幼而無父”“、老而無子”“、無夫守志”、“瞽盲瘻痖駝背折肢為廢疾父母不能養(yǎng)贍”、“癩瘺癆損鼓脹黃胖為痼疾親戚無可依靠”等幾類族人,分別給米救助[6]。大阜潘氏自徽州遷入蘇州,人才輩出,顯宦迭現(xiàn),漸成文化名族,本著“所以專祭祀而恤宗族”之旨,自道光十二年創(chuàng)辦“松鱗莊”,對“貧乏者量加赒贈”。道光十七年,制定“松鱗莊贍族規(guī)條”,要求對“貧老無依及孤寡廢疾不能自養(yǎng)者,自當(dāng)酌籌矜恤”,具體矜恤對象包括“貧老無依者”“、寡婦貧乏者”、“幼孤男女貧乏者”“、廢疾無人養(yǎng)恤者”“、喪葬嫁娶無力者”等[7]。由此可見,明清兩代的宗族義莊普遍注意到了對同族成員的生活保障問題,并且在宗族社會保障方面表現(xiàn)出以“周貧”、“濟(jì)困”為宗旨的特點(diǎn)。
三、民間慈善事業(yè)的興盛
明清時期的社會保障事業(yè)雖曾得到政府的大力提倡,但其規(guī)模及設(shè)施等似未必能超過宋代。而明清時期的最大亮點(diǎn),無疑是民間慈善活動的興盛。中國歷史上的慈善活動早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但其成為一種由團(tuán)體機(jī)構(gòu)主持的社會事業(yè)則始自明代后期。明代中晚期,隨著商品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出現(xiàn)了地主城居化的趨勢,城鎮(zhèn)成為財富和人口的聚集地,為民間慈善組織的產(chǎn)生奠定了經(jīng)濟(jì)基礎(chǔ)。明代是“結(jié)社”風(fēng)氣盛行的時代,社會各個階層尤其是文人士大夫慣于結(jié)成“會”、“社”之類的團(tuán)體,從事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等各種活動,為善會善堂的出現(xiàn)作了組織準(zhǔn)備。以規(guī)勸民眾“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為宗旨的勸善書,如《太上感應(yīng)篇》、《功過格》、《陰騭文》之類,在民間得到廣泛傳播,對宣揚(yáng)慈善風(fēng)氣、促進(jìn)慈善組織興起也起到了積極作用。應(yīng)該強(qiáng)調(diào)的是,晚明時期的官僚士大夫針對社會弊陋叢生、危機(jī)四伏的現(xiàn)狀,力圖通過端正人心、整頓風(fēng)俗的方法,重建傳統(tǒng)道德和社會秩序。其中崇奉陽明心學(xué)者與佛、道合流,強(qiáng)調(diào)行善積德、因果報應(yīng),擴(kuò)大了勸善運(yùn)動的社會基礎(chǔ);而堅持程朱理學(xué)者則維護(hù)儒學(xué)正統(tǒng),從宣傳皇帝圣諭、宣講鄉(xiāng)約入手,將救助貧困視為改良社會的有效手段。兩股力量殊途同歸,共同推動了民間慈善事業(yè)的興起與發(fā)展。如學(xué)者所指出的:“晚明以來善書開始大量涌現(xiàn),標(biāo)志著一場新的思想運(yùn)動正在配釀形成,我們可以稱之為‘勸善運(yùn)動’。這場‘運(yùn)動’既有心學(xué)家的參與,更有一般儒家士人的積極推動。其目標(biāo)則是通過行善積德以求得最大限度的福祉,進(jìn)而重建理想的社會秩序。用儒家的傳統(tǒng)說法,亦即通過‘遷善改過’、‘與人為善’以實現(xiàn)‘善與人同’的理想社會”[1]。因此之故,明末清初以后,善會善堂等民間慈善組織在全國各地廣泛涌現(xiàn)。明代后期出現(xiàn)的民間慈善組織主要有同善會、放生會、掩骼會、一命浮圖會、救生會(局)、育嬰會等。放生指釋放、救護(hù)被捕捉或?qū)⒈辉讱⒌膭游铮瑛B獸蟲魚之類。這種善舉在中國有著悠久歷史,且在宋代較為盛行。從明末開始,受高僧云棲袾宏《戒殺放生文》的影響,放生善舉得以復(fù)興,放生會、放生社之類的民間慈善組織隨之出現(xiàn)。明末清初的杭州、紹興、南京、常熟、吳江、昆山、桐城、北京、番禺等地都設(shè)有放生會或放生社,放生事業(yè)十分興盛。掩骼會的職能為收集掩埋暴露的無名尸骨。對強(qiáng)調(diào)入土為安的傳統(tǒng)中國社會而言,掩骼是倍受重視的善舉,但在明末以前,專以掩埋無名尸骨為職能的民間慈善組織并不多見。至明末崇禎年間,北京和紹興等地相繼出現(xiàn)了掩骼會。崇禎十四年,江蘇太倉州遭遇嚴(yán)重旱災(zāi),知州錢肅樂組織一命浮圖會。其救助辦法為:事先編纂《察舉饑戶冊》,冊中每頁分三段,上段記施主姓名,中段書寫“認(rèn)救一命”,下段記錄被救濟(jì)者的姓名及救濟(jì)日期。參加一命浮圖會的人,根據(jù)財力,可一人救濟(jì)多人,也可多人合救一人。從當(dāng)年六月到九月,會員每隔十天向被救濟(jì)者提供米五升和錢一百文,使其得以維持基本生活。救濟(jì)活動結(jié)束前的九月十五日,參加者召開法會,誦讀佛經(jīng),向佛祖報告施主和被救濟(jì)者的姓名。一命浮圖會也流行于明末的浙江寧波、紹興一帶。救生會(局)的基本運(yùn)營模式,是由民間或政府出資雇傭水手,置備救生船,在容易發(fā)生事故的水面巡視。一旦發(fā)生船舶傾覆或有人落水的事故,救生船應(yīng)迅速前往打撈。遇難者被救后,由救生機(jī)構(gòu)發(fā)給衣被,提供食物和醫(yī)藥,并給予返家路費(fèi);若不幸死亡,提供棺木和墓地掩埋,并進(jìn)行登記,以便家屬前來認(rèn)領(lǐng)。育嬰社(會)是以收養(yǎng)棄嬰為職能的慈善組織。救助棄嬰的活動在中國出現(xiàn)很早,但大都由政府主持。嚴(yán)格意義上的民間育嬰組織出現(xiàn)于明末。崇禎初年揚(yáng)州即設(shè)有育嬰社(會)。據(jù)稱,這個由商人蔡璉舉辦的育嬰機(jī)構(gòu),聚集愛心人士,收容路邊棄嬰,每人每月出銀一錢五分,雇招乳婦,養(yǎng)育嬰兒,以三年為期,屆時招人領(lǐng)養(yǎng)[2]。育嬰社在明末清初的戰(zhàn)亂中毀敗,清初順治年間,仍由蔡璉在揚(yáng)州小東門復(fù)建。揚(yáng)州育嬰社對各地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約略與揚(yáng)州育嬰社同時,浙江紹興人錢元登創(chuàng)辦了名為保嬰局的慈善團(tuán)體,收養(yǎng)遺棄嬰孩,雇老婦和乳婦喂養(yǎng)照顧嬰孩,并準(zhǔn)許家境貧寒的夫婦將子女寄養(yǎng)于局。被遺棄嬰孩準(zhǔn)人抱養(yǎng),無人抱養(yǎng)者長成后,由局中代為女子擇配婚嫁,為男子提供教育機(jī)會和生活出路。不過,明末慈善組織中影響最大的當(dāng)屬同善會。萬歷十八年,退休官僚楊東明在河南虞城縣最早創(chuàng)立同善會,其后不久便被移植到江南地區(qū)。從萬歷后期到崇禎年間,江蘇武進(jìn)、無錫、昆山、蘇州、松江、華亭、太倉,浙江的嘉善、杭州均設(shè)立了同善會。其中,高攀龍等創(chuàng)立的無錫同善會和陳龍正創(chuàng)立的嘉善同善會影響最大,最具典型。從高攀龍制定的無錫《同善會規(guī)例》和陳龍正所作《同善會式》中可以看出,勸善是同善會最主要的目的。這一方面表現(xiàn)為每當(dāng)同善會聚會之際,都要由主會人公開講演,向聽眾進(jìn)行道德說教;另一方面表現(xiàn)為同善會的救濟(jì)對象除貧困這一物質(zhì)標(biāo)準(zhǔn)外,還有道德方面的要求,具體而言,貧困無依的孝子、節(jié)婦,屬于優(yōu)先救濟(jì)的對象,至于“不孝不悌、賭博健訟、酗酒無賴,及年少強(qiáng)壯、游手游食以致赤貧者”則不在救助之列[1]。清代的民間慈善事業(yè)出現(xiàn)了興盛局面,這主要表現(xiàn)在:第一,慈善組織數(shù)量眾多。明代各地的慈善組織機(jī)構(gòu)的數(shù)量尚屬有限,而清代的數(shù)量則大為增加。第二,慈善組織種類齊全。從施濟(jì)內(nèi)容看,有對貧民的施衣、施米、施粥等,有對病人的施藥、診治,有對死者的施棺、代葬及義塚;從施濟(jì)對象看,有收容孤老貧病者的安濟(jì)堂,有收容流浪者的棲流所,有收養(yǎng)嬰兒的育嬰堂、保嬰堂、恤孤局等,有救濟(jì)貞女節(jié)婦的恤嫠會、清節(jié)堂、儒寡會等,有管束不肖子弟的洗心局、歸善局、遷善局等,有綜合性實施救濟(jì)的芹香堂、同仁堂、博濟(jì)堂等。可以說,清代的慈善組織機(jī)構(gòu)種類齊全、應(yīng)有盡有,涉及到了慈善事業(yè)的各個方面。第三,慈善組織財力充足。明代的同善會經(jīng)費(fèi)極少,主要依靠會員的捐助,能用于救濟(jì)貧困的金額極為有限。到了清代,慈善組織的經(jīng)費(fèi)來源擴(kuò)大,金額大為增加,除了地方官員發(fā)起募金以外,他們還把沒官田地劃歸善堂,許多士紳也捐建土地、房屋,從而使得慈善組織的不動產(chǎn)數(shù)量大增,經(jīng)費(fèi)較為充裕。第四,參與慈善事業(yè)的社會階層更為廣泛。清代以前,社會救助活動大多是由地方士紳主持的。隨著商品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和工商業(yè)的發(fā)達(dá),工商業(yè)者開始成為慈善事業(y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辦理善舉成為會館、公所的重要職能[2]。第五,慈善活動的經(jīng)常化。明代的同善會都是定期舉行救濟(jì)活動,或一年二次,或一年四次。而清代的慈善組織則不受時間的限制,隨時施行救濟(jì),活動趨于經(jīng)常化了[3]。
四、明清社會保障事業(yè)的特點(diǎn)及其啟示
篇10
一、韋伯對宗教的評論給予中國問題的啟示
本文所謂的中國特殊的環(huán)境,是專指相對于馬克斯·韋伯所言的西歐發(fā)展資本主義時期,宗教改革給人們思想上帶來的新的沖擊而言的。當(dāng)然,中國與西方的發(fā)展不同,有多方面復(fù)雜的原因,遠(yuǎn)不是一兩種觀點(diǎn)所能解說清楚的,各家學(xué)者對此問題都有獨(dú)到見解。本文只想從支配商人行為的價值觀或是宗教信仰入手,探討中國商人從自身傳統(tǒng)文化中汲取營養(yǎng),形成其誠信觀的演變過程。鑒于明清之際正是中國商人階層力量逐步發(fā)展壯大,直至打破傳統(tǒng)四民秩序的特殊歷史階段,我們特意將眼光放在這一階段展開探討。
馬克斯·韋伯在其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提出一個引起世人矚目的觀點(diǎn),即文化因素如思想,可以推動經(jīng)濟(jì)形態(tài)的改變。余英時在談到韋伯《新教倫理》的特殊貢獻(xiàn)時說,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的興起,除了經(jīng)濟(jì)本身的因素之外,還有一層文化的背景,即"新教倫理"或"入世苦行"。西方宗教改革中"加爾文派"的"入世苦行"特別有助于資本主義的發(fā)展。韋伯研究了新英格蘭的情況,發(fā)現(xiàn)這種"入世苦行"精神的出現(xiàn)先于資本主義秩序的建立。富蘭克林把"資本主義精神"概括為勤、儉、誠實和有信用等,韋伯認(rèn)為此種精神先于資本主義出現(xiàn),因此,它實際上是資本主義興起的一個重要原因。
韋伯提出,思想意識會在歷史的實際進(jìn)程中產(chǎn)生推動的作用。這種觀點(diǎn)啟發(fā)我們:中國古代商人階層的發(fā)展壯大,除了經(jīng)濟(jì)原因外,是不是同樣可以在文化思想上找到某種解釋呢?中國傳統(tǒng)文化博大精深,本文只想從中國商人的誠信重諾這一點(diǎn),研究傳統(tǒng)文化對商人的影響作用。
二、中國近世商人階層的出現(xiàn)及其特點(diǎn)
既然要從文化入手,不妨先來考察文化熏陶的對象--人。商人階層在16世紀(jì)至18世紀(jì)中國明清時代的家世背景是我們首先關(guān)注的問題。余英時在其所著《士與中國文化》一書中提到清代沈yáo@①對宋代以來商人社會功能變遷的觀察:
"宋太祖乃盡收天下之利權(quán)歸于官,于是士大夫始必兼農(nóng)桑之業(yè),方得贍家,一切與古異矣。仕者既與小民爭利,未仕者又必先有農(nóng)桑之業(yè)方得給朝夕,以專事進(jìn)取,于是貨殖之事益急,商賈之事益重。非父兄先營事業(yè)于前,子弟即無由讀書以致身通顯。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為士。此宋、元、明以來變遷之大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則纖嗇之風(fēng)益甚。然而睦姻任恤之風(fēng)往往難見于士大夫,而轉(zhuǎn)見于商賈,何也?則以天下之勢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焉。其業(yè)則商賈也,其人則豪杰也。為豪杰則洞悉天下之物情,故能為人所不為,不忍人所忍。是故為士者轉(zhuǎn)益纖嗇,為商者轉(zhuǎn)敦古誼。此又世道風(fēng)俗之大較也(《落帆樓文集》卷二十四)。"
這段引文頗能說明宋元以后商人地位的變化,具體說是讀書人與商人之間發(fā)生了微妙的聯(lián)系,讀書人出身于商人家庭以及商人子弟復(fù)又讀書博取功名已是常有的事情。另外,隨著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商業(yè)愈加重要,有才智的、習(xí)讀詩書的人也轉(zhuǎn)而從事商業(yè)活動。處于四民排序兩端的士與商發(fā)生了密切的聯(lián)系,這一現(xiàn)象最有利于我們觀察商人經(jīng)營活動的理念和價值觀。無疑,知識分子(在古代就是那些熟讀儒家經(jīng)典的讀書人)應(yīng)該是最能體現(xiàn)文化熏陶的人群。雖然文化一詞含義廣泛,社會學(xué)者對此各有定義,但大致說來,可將其視為"成套的行為系統(tǒng)",而文化的內(nèi)核則由"一套傳統(tǒng)觀念,尤其是價值系統(tǒng)所構(gòu)成"。這個定義是20世紀(jì)50年代美國人類學(xué)家克羅伯與克拉孔檢視了160多個關(guān)于"文化"的定義之后對文化的概括(杜維明,1987)。中國文化的主流發(fā)端于孔孟的儒家學(xué)說,雖經(jīng)千余年來的演進(jìn)變化,其基本特點(diǎn)依舊根植于孔孟的經(jīng)典著作。歷代統(tǒng)治者為了鞏固和加強(qiáng)自己的統(tǒng)治,必然在意識形態(tài)上加以引導(dǎo),他們最終選擇了儒家文化。嚴(yán)格來說,儒家思想不能與韋伯所考察的西方世界的宗教思想等量齊觀,它沒有專門的公共機(jī)構(gòu)(教堂),沒有明確的入教儀式。承認(rèn)自己是儒家的一名信徒,雖不能說毫無意義,但總比不上信奉伊斯蘭教或基督教那樣要明確承擔(dān)一定的義務(wù)。但是,切不可認(rèn)為傳統(tǒng)中國就沒有影響國民意識的一套價值體系。這個任務(wù)恰恰是由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文化來完成的。就此一點(diǎn)來說,其功效之巨,拋卻宗教信仰所規(guī)定的清規(guī)戒律不談,與韋伯認(rèn)為的"入世苦行"思想庶幾仿佛。
這里特別要注意的是儒家經(jīng)典中對于人與人之間關(guān)系的闡述及其提出的各種主張,因為商人的誠信歸根結(jié)底是人際關(guān)系的反映。儒家文化的指向是積極入世的,所以它把注意力放在人生活于其中的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在中國一直被稱為"人倫",包括父子、君臣、夫妻、兄弟以及朋友五種類型。儒家思想具有內(nèi)傾的性格,強(qiáng)調(diào)個人的尊嚴(yán)。內(nèi)在力量主要表現(xiàn)在儒家的"求諸己"、"盡其在我"等精神上。對于這個世界的認(rèn)知,儒家強(qiáng)調(diào)個人自身的修煉,這種觀點(diǎn)影響到對于自身之外事物尤其是對于其他個體人的態(tài)度。可以看出,五倫關(guān)系的順次安排恰是強(qiáng)調(diào)個體自身的一個反映。對于自身之外的其他人如何分別親疏遠(yuǎn)近,這實在是一個內(nèi)傾性格的文化難以處理的問題,然而又必須面對。也許沒有比將血緣關(guān)系視作解決這個問題更好和更方便的工具了。因此,"五倫"之首便是"父子"。至于君臣僅次于父子排在第二位,則應(yīng)視作統(tǒng)治者改造儒家思想為我所用所必有的措施。事實上,曾有過父子與君臣之義發(fā)生矛盾時,何者更為重要的有趣討論,結(jié)果仍是父子之義占了上風(fēng)。順著這樣的思路,就不難理解家庭這個單位在中國文化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它也是理解信任在人們中間發(fā)生作用的一把鑰匙。 三、儒家倫理中"家庭觀念"與商人"誠信"的內(nèi)在聯(lián)系
家庭在中國人心目中的特點(diǎn)具體是什么呢?我們的著眼點(diǎn)是放在家庭成員中各自的地位上。上文說到父子為五倫中第一倫,父輩對下一代的權(quán)威在家庭中的影響力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說,儒家早已把對父輩絕對服從的觀念灌輸給千萬個傳統(tǒng)的中國家庭。地位尊崇的"父親"作為一家之主,對于自己的職責(zé)也決不含糊。他接受了儒家文化給他的絕對權(quán)威,也承擔(dān)這個文化要求他的職責(zé)。也可以說,沒有對自己職責(zé)的承當(dāng),不能完成任務(wù),就不可能樹立自身的權(quán)威,畢竟獲得尊重是要別人心服的。那么,這個職責(zé)是什么?前面說過,儒文化是積極入世的文化,它不同于道家哲學(xué)的順其自然或是無為而治,它強(qiáng)調(diào)個人應(yīng)做出一番事業(yè),甚至要"知其不可而為之"。從前的讀書人要博取功名,學(xué)而優(yōu)則仕,統(tǒng)治者的科舉取仕政策恰好給修習(xí)儒家著作的人提供了一條建功立業(yè)的道路。
隨著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中國的人口數(shù)量在明清之際已有極大的增長,而科舉取仕的名額較前代并沒有明顯增長。同時,經(jīng)商的巨大成功引起了世人的關(guān)注,讀書人漸漸發(fā)現(xiàn)不能對此現(xiàn)象無動于衷。后來,許多讀書不成的知識分子便轉(zhuǎn)而經(jīng)商。商業(yè)活動畢竟不同于一般簡單的手工勞動或是農(nóng)業(yè)活動,至少需要識文斷字。于是,讀書人(或可說是知識分子)就不可能不與商賈發(fā)生必然的聯(lián)系了。
以上分析可以幫助我們認(rèn)識儒家文化與中國商人(明清之際)之間的關(guān)系。本來,儒文化是極具世俗性的,它與人們的社會生活息息相關(guān)。不論是儒學(xué)宗師抑或是粗識文字的普通百姓,無不從中汲取精神上的養(yǎng)分。在商人這一群體中,頗有飽讀詩書的知識分子,或者與雖不從商但與商賈有特殊聯(lián)系的知識分子保持密切的交往,史料中不乏這樣的記載。
商人本人如果是儒家文化的接受者,他在家庭中便是家長,便要做出一番事業(yè)。他的做事哲學(xué)是來自于儒學(xué)的,他的行商原則也是這個文化的反映。當(dāng)然,不可否認(rèn),也有人從事商業(yè)活動遵從另一種道德規(guī)范,但在明清時代的中國,可以說沒有任何哪個文化力量比儒文化的影響更大,能給人們提供另一種精神憑借。
儒文化強(qiáng)調(diào)勤儉,其次便是誠信了,這些都在儒家倫理中占據(jù)中心位置。范仲淹以為"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八)。司馬光解釋:"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至臻其道則一也。"致"誠"之道必須自"不妄語人"即"不欺"始,經(jīng)過長久的修養(yǎng),一個人才能達(dá)到"言行一致,表里相應(yīng),遇事坦然有余地"的境界。"誠"與"不欺"上通"天之道",這為此世的道德找到了宗教性的超越根據(jù)。儒家思想的長期宣說,把這些觀念深深印刻在商人心中,所以商人對誠信二字的重視已是順理成章的事。
不過,僅有誠信的思想源流還不足以說明問題,外界的因素同樣在起作用,或者使人恪守自己的道德信仰,或者使人背離之。明清之際的中國社會對商人重視誠信有什么樣的影響呢?我們注意到,在封建的官僚機(jī)制維持統(tǒng)治的千余年中,政府這個系統(tǒng)早已變得極具腐朽性,中央以及地方的政府從來沒有真正地把向商人階層提供服務(wù)看作是應(yīng)盡的義務(wù)。中國那時的工商業(yè)者從未有過的而政府理應(yīng)加以倡導(dǎo)建設(shè)的,包括以下幾點(diǎn)內(nèi)容:一是籌集資金的制度(除合伙經(jīng)營、共有資產(chǎn)的繼承、合營海運(yùn)貿(mào)易以外的集資辦法,而這幾種集資辦法都無法律保護(hù),也不能及時得到司法調(diào)解和仲裁);二是能夠促進(jìn)資本由商業(yè)轉(zhuǎn)向工業(yè),保護(hù)資金合理流動的法律機(jī)構(gòu)、財政機(jī)構(gòu)和貿(mào)易機(jī)構(gòu)(如銀行、證券交易所、保險公司、經(jīng)濟(jì)人、法律專家等);三是一種可以信賴的通貨;四是在國家的內(nèi)地舉行的、能促進(jìn)思想觀念交流的大規(guī)模的集市。
士大夫官僚階層的地位無疑是凌駕于商人階層之上的,他們對于商人的盤剝與壓榨是歷史上實有的記載。這種社會背景自然干預(yù)和影響了商人階層的行為。外界因素的這種不利影響,使商人的心理總被不安全的預(yù)期干擾著。他們不知道凌駕于自己頭上的那個官僚機(jī)構(gòu)會做出什么樣不利于自己經(jīng)營的舉動,這導(dǎo)致了他們自身的行為調(diào)整。或許這種影響還不會馬上使商人對誠信的遵守產(chǎn)生背離,但他們對于自己事業(yè)的前景已不樂觀。畢竟,人是趨利避害的,超越自身利益的道德操守不會永久地具有生命力。外界環(huán)境給行為主體造成的不安全影響,摧毀了對于誠信的鞏固和維持。這是文化的力量無法挽救的。
參考文獻(xiàn)
[1]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2]杜維明.文化:中國與世界[M].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7.
[3]高韋定.海外華人企業(yè)家的管理思想[M].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3.
[4]弗朗西斯·福山.信任[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5]高兆明.信任危機(jī)的現(xiàn)代性解釋[J].學(xué)術(shù)研究,2002,(4).
[6]儲小平.儒家倫理與海外華人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J].汕頭大學(xué)學(xué)報(人文科學(xué)版),1997,(5).
- 上一篇:土地地價評估方法
- 下一篇:管理科學(xué)的特點(diǎ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