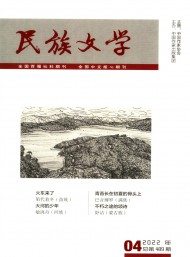民族意識覺醒的表現范文
時間:2023-10-26 17:33:06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民族意識覺醒的表現,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摘要:城市民族工作是民族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現階段,城市少數民族出現了一些新情況,城市少數民族工作面臨著一些新挑戰。做好新形勢下的城市民族工作,要推動民族工作社會化,處理好政府、民族社團、民族成員三者之間的關系。
關鍵詞:城市民族工作;城市;少數民族;民族工作社會化
中圖分類號:D6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6269(2013)01-0057-04
城市民族工作是民族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事關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一項重要工作。現階段,我國城市民族工作的總體狀況是好的。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口流動的加快及現代化進程的推進,城市民族工作面臨著新形勢。分析城市民族工作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研究加強城市民族工作的對策和措施,是當前城市民族工作的一個重要課題。
一、城市少數民族的新情況
城市民族工作是以城市少數民族問題為對象的工作。城市少數民族是指居住在國家按行政建制設立的直轄市、市內,由國家正式認定的漢族以外的各民族[1]。由于城市是一個地區對外開放的窗口,是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對周邊地區具有輻射和帶動作用,再加上民族問題的敏感性和連帶性,城市民族問題往往會演變成整個民族和某一民族地區的問題。城市民族工作的范圍和內容在不斷擴展。
(一)民族結構隨著少數民族人口的增加而多民族化
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并完善,城鎮化速度加快,原有城鄉界限被打破,中華民族迎來了空前的人口大流動大遷移。越來越多的少數民族群眾走出原居住區,進入了城市。以天津市為例,城市多民族化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少數民族人數增長。資料顯示,1953年天津市少數民族總人口有94121人。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時,天津市少數民族總數為131528人。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時,少數民族總人口為164262人。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時,少數民族總人口為202654人。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時,少數民族總人口為266871人。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時,少數民族總人口為331327人。
2.少數民族成分增多。天津市在1953年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時有少數民族19個;1964年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時有少數民族24個;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時,有少數民族29個;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時,有41個少數民族;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時,有49個少數民族;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時,有少數民族53個。
3.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激增。截止2010年底,天津市共登記有流動人口3024118人,其中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約有2萬人,并且表現出結構新、層次多等特點。天津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具有以下特點。從民族成分看,天津市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成分多樣,主要有回族、朝鮮族、土家族、蒙古族、滿族、維吾爾族近30個民族。在天津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中,滿族、朝鮮族、回族、蒙古族都在萬人以上。他們中的一些人在天津仍保留著本民族的風俗習慣和服飾特色。從來源地區看,他們主要來自東北、西北和西南地區,以新疆維吾爾族,四川藏族、羌族,青海、甘肅、寧夏回族,東北三省朝鮮族為多。從居住情況看,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生活條件一般較差,大多居住在打工單位內部、出租房、居民家中和工地現場。同時,因在語言、生活習慣等方面與當地居民有所不同,出現維吾爾族、藏族、朝鮮族相對聚居區20多片。從行業看,他們主要從事制造、建筑、餐飲、住宿、游商等10多個行業。來自不同地域的少數民族從事行業也有所不同,寧夏少數民族主要從事建筑行業,四川少數民族游商較多,甘肅、青海、新疆回族、撒拉族、維吾爾族經營餐飲生意較多。從年齡結構看,青壯年比較多。但是在來天津市創業較早的朝鮮族中,近年來老年人比例大大增加。這是由于許多到天津市工作的朝鮮族在事業取得一定進展、有一定經濟基礎后,紛紛將老人和孩子接到身邊。
(二)多元文化相互交融
文化是以象征符號為基礎,是人適應環境,并與他人分享意義、表達自我的符號體系。文化是群體特有的標志[2]。不同文化以自身價值觀和信仰為核心和基礎形成特定文化模式。這種文化模式“是一個地區文化中的文化特質按一定的內部關系構成的協調一致的體系”[3]。不同文化模式之間具有顯著的差異性,但文化也有整合的趨向。“人們從周圍地區可能的特質中選擇出可利用的東西,放棄不可利用的東西。人們還把其他的特質加以重新鑄造,使它們符合自己的需要。”[4]多民族化的城市民族格局帶來多元文化的交匯融合。作為文化載體的少數民族人口涌向城市,不僅活躍了城市經濟,加強了各民族之間的經濟交流與合作,同時將本民族的傳統文化帶入城市,豐富了城市文化的內涵,促進了城市文化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不同文化彼此適應、相互融合,在都市與傳統之間孕育著一種蘊含多種文化元素的城市文化,為城市的發展注入了新的生機和活力。
(三)民族意識逐漸增強
民族意識是特定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積累起來的對客觀世界的反映。民族意識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民族意識包括民族認同意識、分界意識、交往意識和發展意識等;廣義的民族意識是一切具有民族特點的各種觀點的總和[5]。現代化和城市化進程的推進促進了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的發展,人們的文化水平和素質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由于自然資源和技術水平等條件的限制,民族和地區間的經濟發展差距逐步拉大。少數民族進城務工人員普遍文化素質較低,就業技能差,其謀生手段具有明顯的本土性。從職業分布的角度來看,他們主要分布在以體力勞動為主的行業,收入水平較低[6]。窘迫的生活現狀使他們很難融入城市生活,處于城市生活的邊緣,形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以本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為主要內容的民族意識便逐漸增強,表現在更加關注民族間的發展差距,迫切要求發展本民族經濟,維護本民族形象,更加關注涉及本民族各種合法權益的保障等。“民族意識的增強,是民族差別、地區發展差距的一種反映。只要這個大環境繼續存在,只要發展差距繼續拉大,民族意識的增強也會繼續存在,并且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發展,可能對民族關系產生某種不良影響。”[7]如何使覺醒的民族意識回到理性的軌道上來是當前城市化進程中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務和目標。
二、城市民族工作的新挑戰
篇2
[關鍵詞]格林卡歌劇;詠嘆調;音樂特點
一、格林卡的生平及主要音樂創作
米哈伊爾?伊萬諾維奇?格林卡(1804-1857),俄羅斯作曲家。1804年6月1日生于俄羅斯斯摩棱斯克省葉爾寧縣的一個地主莊園家庭里。格林卡自幼酷愛音樂,尤其對俄羅斯民歌和農奴樂隊的演奏十分癡迷,他的童年是在民間音樂的熏陶下度過的。格林卡是俄羅斯民族樂派的奠基人,他為俄羅斯音樂進入世界音樂之林,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被世界人民譽為“俄羅斯民族音樂之父”的并對19世紀后半葉歐洲各國民族樂派的興盛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開創了屬于俄羅斯本民族所特有的音樂寫作風格和表現手法。
格林卡出生于一個受西方文化影響深厚的封建地主家庭里,在童年時接觸到很多民間歌手,從他們那里了解到更多的民間音樂,致使在格林卡日后的音樂中,隨處可見濃重的民間音樂的創作根基。隨著格林卡的漸漸長大以及1812年俄國抗擊拿破侖侵略的衛國戰爭的爆發,他在祖國的歷史沉浮中飽受激勵,使一種民族意識和民族精神在小格林卡的心中逐漸萌生。這些都為他后來的音樂創作奠定了堅實的民族情感基礎。
格林卡驚人的學習毅力以及超兒的音樂天賦,使他的多方面的音樂修養得到穩步的提高。在俄國十二月黨人運動時期,他的歌曲《不要誘惑》《貧窮的歌手》等,已經顯露出他的創作特點。在意大利學習時,他將民族抗爭和自我覺醒的強烈藝術思想大量地反映在他的作品中。1834年,格林卡開始創作他生平最重要的一部歌劇《伊凡?蘇薩寧》。這部歌劇創作是俄國第一部具有世界水平的真正的民族歌劇。這部歌劇被人稱作是“俄羅斯歌劇的曙光”。
《伊凡?蘇薩寧》創作的成功和演出所收獲的巨大反響給予格林卡很大的創作信心,他之后又深入地認識烏克蘭的民間音樂,將之體現在自己的創作當中。他生平的另外一部歌劇,根據普希金的同名長詩構思的神話歌劇《魯斯蘭與柳的米拉》中的《魔鬼進行曲》和《波斯合唱曲》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創作產生的。這部歌劇具有鮮明的民族民間音樂特色、高度的藝術技巧和英雄主義與樂觀主義的主題。它與《伊萬?蘇薩寧》一起,為俄國古典歌劇的兩個基本分支――神話史詩劇和人民歷史劇――奠定了基礎。隨后,格林卡除了完成了歌劇《魯斯蘭與柳的米拉》的其他部分之外,還創作了一系列的浪漫歌曲和管弦樂曲,都生動地描寫了俄羅斯的民間生活風俗。1844年,格林卡在西班牙采風之后創作產生的《阿拉貢?霍塔》和《馬德里之夜》,更成為俄羅斯作曲家以外國題材創作管弦樂作品的開端。格林卡1847年回國,成功地運用歐洲古典音樂的藝術成就,創造性地繼承和發展了俄羅斯音樂的民族傳統,將俄羅斯民歌交響化,在1848年寫出了交響幻想曲《卡瑪林斯卡亞》,孕育了整個俄羅斯的交響音樂。
格林卡在創作上雖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俄國貴族社會并沒有認識到他作品的真正的藝術價值和歷史貢獻。格林卡的作品經常遭到冷遇和惡意的誹謗,演出機會越來越少,有時甚至被完全擠掉。這極大地打擊了格林卡的創作熱情,他的創作意識一度停滯不前。幸好在他晚年的時候,身邊還聚集著一些與貴族社會持相反立場的年輕人,他們就是未來的俄羅斯民族音樂運動的中堅力量:五人強力集團。之后集團中的成員都成為格林卡所奠基的俄羅斯古典音樂的繼承者。格林卡在晚年的時候,經常在家里舉行家庭音樂晚會,與他周圍志同道合的音樂人共同分享彼此的音樂成果,這一度成為當時進步的重要的社會活動,同樣有效地推進了俄羅斯民族主義音樂的向前發展。1854年,在斯塔索夫的懇求下,格林卡寫了自傳體的《札記》,這本《札記》是研究格林卡創作思想和作品的最有價值的文獻。1856年,格林卡最后一次離別祖國,去鉆研前輩的音樂,發展俄羅斯的合唱藝術,研究古老的調式。然而他此次出國就再也沒能回來。1857年2月15日,他逝世于柏林。
二、格林卡歌劇創作的歷史地位
在格林卡的音樂創作當中,歌劇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雖然他一生只寫了兩部歌劇,但這兩部歌劇卻是他的作品中社會意義和藝術成就最大的兩部,有效地開辟了俄羅斯歌劇創作的發展道路。格林卡自幼就受到俄羅斯民間音樂的熏陶,在濃郁的民間藝術氛圍中成長,同時,他本身又極易受到藝術的感染并且自認為有著奔放不羈的藝術想象力,這使他水到渠成地開始學習音樂藝術,最終開創并引領了具有俄羅斯民族風格的音樂流派,并使俄羅斯民族樂派在世界音樂發展歷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歷史地位。格林卡在童年和青年時期,經歷過兩次讓他印象深刻的民族保衛戰爭,使他萌發并穩固了民族意識形態和愛國主義情懷。他的音樂創作和音樂表現無不充斥著對國家、民族、人民以及世事的感懷,堅定地運用民族音樂思想來進行藝術創造。格林卡多次出訪國外,學習其他民族的音樂創作手法,了解其他民族音樂的發展歷程,從而更深層次地感悟俄羅斯本土音樂的發展及未來。他非常喜愛意大利歌劇,他感動于意大利歌劇帶給他的音樂創作、歌唱表演等各方面的震撼。致使在他最初的創作中會帶有一些明顯的意大利歌劇的音樂創作痕跡。而漸漸的,格林卡意識到了意大利音樂與自己從小就熟知的俄羅斯音樂截然不同,他尤其不喜歡某些意大利歌唱家過分注意外在效果的作風。而他也在自己的音樂創作中逐漸理清了屬于自己的創作思路,那就是想要創作牢固扎根于俄羅斯民間音樂的土壤、汲取俄羅斯城市音樂文化的養分,借鑒西歐古典樂派和浪漫樂派的音樂成果而創作產生的帶有強烈俄羅斯民族文化氣息的歌劇作品。想要把俄羅斯民族音樂的發展像意大利歌劇的德奧藝術歌曲那樣,展現在世界面前,讓各國音樂界都了解并喜愛俄羅斯音樂,使俄羅斯民族樂派光大于世界。正如他自己說的“我自己并不想成為一個意大利人,因此,我漸漸認識到要以一個俄國人的感覺來作曲”。格林卡的兩部歌劇,采用了很多古老的俄羅斯民歌作為歌劇的旋律。這些俄羅斯民間音調已經在他幼年的時候就深深地融入格林卡的靈魂中去,結合他在戰爭與生活中的親身感悟,讓他的音樂創作無限地貼近人民生活,在欣賞情感上引起巨大的共鳴。這樣的創作手法不僅為他節省了好多時間,而且也使觀眾更容易吹著這些曲調離開劇場,這一點確保了作品的成功和廣泛的欣賞群體,有效地幫助格林卡的歌劇作品流傳發展。格林卡之后的一群作曲家看了他的歌劇后,認識到一種有益的東西,所以幾乎所有他們的音樂都包含一些俄羅斯民歌的片斷,也都有了那種特殊的民族 風味。這樣使俄羅斯民族音樂在格林卡音樂創作的帶領下能夠廣泛地流傳和長足地發展。這一點充分體現出了格林卡對于俄羅斯民族音樂所做出的巨大的歷史貢獻。
格林卡的創作是在俄羅斯人民生活斗爭的鼓舞下和民間音樂藝術的深刻影響下成長起來的,因此具有比較鮮明的民族特征和愛國主義思想。格林卡在開創俄羅斯音樂歷史和民族主義音樂創作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他在俄羅斯的音樂史上是一位承前啟后的關鍵性人物。他對此前的俄羅斯音樂成就進行了綜合和總結,將具有典型民族風格特點的音樂內容高度的提煉,同時為了開創一個嶄新的俄羅斯民族音樂發展新時期,他積極地學習借鑒國外的先進音樂成果,有效地豐富了俄羅斯音樂流派的音樂寫作技巧,并大膽地在其作品中的音樂創作、表現、配器等各方面進行濃烈的民族精神及民族情懷的渲染。他從內容上選擇民族主義題材進行創作,并從俄羅斯民間音樂中深刻領會其思想感情、性格特征及審美情趣等,積極地運用到民族主義音樂的創作中,致使他引領了俄羅斯音樂創作中個性鮮明的英雄主義色彩和愛國主義情懷。此后很長一段時間內,俄羅斯民族樂派的音樂創作都沿襲著這一音樂個性。同時,在格林卡的一生中,曾多次出訪國外,進行音樂創作的理論學習和深入研究,他吸收了很多國外的音樂創作之長。他深刻地認識到,只有將音樂寫作與本民族的文化歷史發展結合在一起,才能創作出撼動人心、意味深長的深層次的音樂作品。他將國外的許多優秀的配器、和聲、曲式以及表現手法等各方面與民族主義樂派的創作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極大地推進了俄羅斯民族音樂的創作發展,也使俄羅斯民族主義樂派逐漸在世界音樂發展的大環境中嶄露頭角,并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這無不彰顯著格林卡的民族主義思想對音樂發展的積極影響。格林卡被世界人民譽為“俄羅斯民族音樂之父”。不僅他的音樂創作受到世人的敬仰,而他對民族精神的追求與歌頌、為本民族音樂文化的發展所做出的努力,更是值得人們世代相頌,格林卡不愧為俄羅斯民族史上最為偉大的音樂家。
在19世紀出現的俄羅斯的民族樂派是世界音樂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它引領了音樂創作的一種新的感情基調的誕生,在音樂表現中宣揚了一種新的精神氣質。民族樂派的作曲家在音樂創作中著重以本民族的民歌、民間舞曲為素材,采用本民族的英雄史詩、神話傳說和人民解放斗爭事跡為題材,并且將民族音樂的鮮明特點和古典主義音樂的優秀傳統以及浪漫主義音樂的藝術風格緊密地結合起來,創作出大量既有獨特藝術個性和民族感情,又有強烈藝術生命力的作品。他們通過自己的音樂創作,熱情地歌頌自己偉大的祖國、民族和人民,反映了他們的愛國主義思想和內心強烈的民族責任感。俄羅斯作曲家格林卡就是這方面做出突出表現的代表人物。
[參考文獻]
[1] 賀錫德.365首外國古今名曲欣賞(下冊)[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9.
[2] 西洋百首名曲詳解[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5.
篇3
關鍵詞:關鍵詞:魏晉;生命悲劇;超越
一、 中國悲劇的特色
中國擁有自己獨特的悲劇模式,悲劇意識和悲劇精神自炎黃子孫誕生之日起直至現在也都未從心底消失過。有人說中國人沒有悲劇意識,意思是說中國人不像西方人那樣具有徹底的毀滅性的悲劇精神,這是用西方的判斷標準來判斷得出的結論,筆者并不這么認為。“夸父逐日”、“精衛填海”、“寶黛愛情”,都是在講述我們的先輩與自然、命運抗爭的悲劇。“①中國文化形成的奠基期-春秋戰國時期正是一個戰爭頻仍,禮崩樂壞的悲劇時代,老子,孔子,莊子比任何人都深刻地認識到人所面對的生之悲劇。“他們比古希臘的悲劇家更了解宇宙、自然、世界意志的不可戰勝,更了解人的力量的有限性,因而也有更強烈的悲劇意識。但是,他們的任務不是在意識到這一切之后去增加人類的苦難,而是要消解這種苦難。”②這正是中國悲劇與西方悲劇的本質區別,也是有些人認為中國沒有悲劇原因。但這正是中國悲劇的獨特性所在,由于產生的文化背景,哲學基礎不同,中國人面對悲劇的人生時所表現出的精神不同于西方那種歇斯底里式的走向毀滅性精神。中華民族在屬于自己的這塊土地上,過著自給自足的農耕生活。在上千萬年的為生存而進行的抗爭中,中國的哲人們一開始就認識到了人與自然、社會的對立性。老子莊子提出了人與宇宙、自然的關系問題,孔子提出了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他們的學說都是建立在天人分離的認識基礎上的。但是,他們都沒有因此而像西方哲人那樣與自然的極端對立面上,將戰勝自然作為自己學說的最終指向,而是轉向與天合一。他們從自己在自然的生存中發現,合于自然、天、宇宙之道才能最終實現人類在與自然對抗中的勝利。從法天則地的學習中,他們認識到了循環往復的自然之道,寒來暑往,生死輪回,一切都由始而終,由終而始,循環往復,周而不衰,于是便有了道家的齊物我,同生死,返歸自然的思想,便有了儒家的中庸、禮樂文化。先哲們在這樣的基礎上對待自己所生存的悲劇社會時,便不像西方那樣用毀滅、終結的方式去面對。他們不是讓人們無望于現實和自己,而是告訴人們一都是循環的,悲有始也會有終,有終自然有喜的開始,以此來消除人們的消極情緒達到心靈的凈化。西方是讓人們從徹底的毀滅中,領悟到崇高的含義而實現心靈的凈化,我們的先哲在認識到悲劇的同時也開始了為我們尋求解除悲劇的道路工作,讓我們走出悲劇。而西方在認識到悲劇后,將悲劇淋漓盡致展現給人們,通過此種方式來讓人們思考悲劇,他們也并不是告訴人們人生只是永恒的苦難,還是要展現給人尋求希望的榜樣。因此,它們是同歸殊途而已。
二、 魏晉時代的生命悲劇
漢朝,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繁榮的王朝。中國士人在儒術獨尊的文化大一統下,安享盛世,循規蹈矩了四百多年。隨著東漢王朝政治的日益腐朽、經學的日益僵化,久在壓抑中的士人們開始從這個封閉的文化中掙脫出來。他們開始發現自己無比豐富的內心世界,體認到人生的歡樂,生命的寶貴,意識到自我的價值,人生的意義。但與此同時,戰亂帶來的命運的無常,死亡的恐怖,信仰的崩塌,使他們第一次體驗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悲涼和孤獨。自我保存的生命本能讓他們渴望永生,不可抗拒的死亡又讓剛剛覺醒的他們一時“四顧何茫茫”。“常恐歲時盡,魂魄忽高飛,自知百年后,堂上生旅葵”(阮瑀 《七哀詩》)“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生命悲劇意識由此而產生了。《古詩十九首》正是一組抒發人生短促、生存之悲的詩。“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面對脆弱的生命,“忽若飆塵”的人生,他們首先選擇盡情享受這初獲而知的生命,用來麻痹自己。“蕩滌放情志,何為自結束”、“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而這種一直延續在魏晉南北朝。但這僅僅是排遣內心悲哀與孤獨的方式,而非解決生命問題的方法。
李澤厚在《美的歷程》中說到:“這種對生死存亡的重視,對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嘆,從建安直到晉宋,從中下層直到皇家貴族,在相當一段時間中和空間中彌漫開來,成為整個時代的典型音調。”③那么,如何面對死亡,如何解決生死存亡的問題也成為整個時代士人們思考的問題。它一日不得解決,悲劇意識一日不得消除。而悲劇從東漢開始正愈演愈烈,到魏晉時期達到了它的高峰,也找到了它的出路。這段生命悲劇的整個由始而終的發展過程,所體現的美學悲劇性正是中國悲劇美學的最典型代表,反映著中國悲劇精神的特色所在。
如果說東漢士人只是意識到人生之悲,那么魏晉士人則是開始尋找超越自然、命運所帶給他們悲劇的出路了,縱使尋找的過程不可避免是充滿血腥的。
三、小結
魏晉固然是個亂世,但對生命悲劇的深刻體認與超越也必需在這樣一個時代完成。悲劇意識從未間斷,但悲劇精神此時柔和了很多。面對宇宙、世界、自然的意志,人的力量是有限而微弱的,先前的抗爭無法取得勝利,這時就需要另一種方式來為后來的士人指出一條正確的途徑。而陶淵明無疑是這種方式的開創者。陶淵明是真正實現委運任化而沒脫離現實的人,他的人生觀是最終超越了生死困擾的,也正如此,他結束了玄學,超越了魏晉的生命悲劇。
邱紫華教授在他的《悲劇精神與民族意識》中指出悲劇的產生與人的生命有限性以及由此而來的人的本能反抗死亡的意識有關,死亡與生命同在,抗爭也與生命同在,因此,悲劇是人類永恒的歷史現象,魏晉時期產生的生命悲劇是對人類悲劇一次集中體現,士人用不同的形式與死亡進行抗爭,例如煉丹吃藥、建功立業、等等。在這個過程中,士人們充分表現了自己的獨立意志,生命之美。它為后人也指出了超越生死之悲的一種可能,開拓了人類自由的領地。
參考文獻:
[1]王富仁:《悲劇意識與悲劇精神》,《江蘇社會科學》,2001年第1期.
篇4
正是基于這種認識,由香港陳可辛導演的影片《中國合伙人》,以明星企業新東方的三位創始人為藍本,講述了一代青年如何發掘自我潛力,把握時代脈動,終于將“資本紅旗”插上華爾街,實現“中國夢”的故事。影片獨特價值在于,它將“中國夢”編織在當今全球化背景下的后殖民語境中來講述,凸顯了“中國”在表述自我時依然面臨的文化焦慮,和自我認同的無力。作品中的香港“顯影”更折射出處于東西文化“夾縫”中的港人身份的尷尬。影片為我們更準確定位“中國”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坐標,突破西方殖民話語霸權的束縛,建構民族表述話語和身份認同提供了有益啟示。
一、表述焦慮:西方鏡像里的自我與他者
后殖民理論關注的核心是,歷史上的東方國家和民族,是如何被西方殖民話語所“表述”的,以及東方如何擺脫“被表述”的命運。在相對和平的當今世界,西方并沒有放松對東方的話語控制,日益強大和覺醒的東方國家對此也早已警覺,并做出了反控制的努力。可以說,東西方一直在文化領域進行一場爭奪“表述”話語權的戰爭。作為曾飽受殖民之苦的東方大國,30年來,我們的經濟獲得空前發展,民族自信也得到極大提升,用民族話語“表述”一個偉大的“中國夢”成為人們的共同心聲。電影《中國合伙人》正是一部力求用民族話語“表述”這一夢想的文本,正如陳可辛對影片主題的闡釋:三個人做的是一個脆弱的“美國夢”,到最后其實是中國夢:踏踏實實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像竹筍一樣快速生長,所以電影最后,他們還是要回到這片土地上,實現中國夢。②
然而,當我們從追夢激情中冷靜下來會發現,影片并沒有真正找到源于民族內部的,足以獨立表述這一夢想的話語。“”摧毀了一代青年對民族未來的想象力,“80年代”初的人們一時找不到重新表述自己的方式。影片中,在許多青年看來,“美國夢”便成了“中國夢”的鏡像,唯有透過它,我們才能看清自己的不足,找到實現“中國夢”的途徑。這一潛在的殖民心態將自我擺在了“落后”,甚至“卑微”的地位。影片開頭,三個人簽證美國連續失敗,陰暗封閉的簽證處給整部影片投下一個龐大的陰影。影片反復出現青年熱衷考托福,排隊苦等簽證的場景,尤其一個學生多次簽證不力后失態,被保安強行拖了出去,嘴里竟高喊:“美國人民需要我!”而孟曉俊的簽證成功,竟然贏得眾人的歡呼喝彩。這一有點夸張的情節,暴露了編者在面對西方時復雜微妙的心態。不僅個人,影片還著意表現了“90年代”初,全民族的后殖民心態。最突出的就是對1993年,北京第一次申奧失利的文化反思。影片再現了失利當天晚上,北京街頭蕭索的人群,以及路邊無人問津的申奧標語:“給中國一個機會,還世界一個奇跡。”顯然,在當時的民族意識中,能否舉辦奧運會是一個民族能否為世界,尤其是西方社會所認可的重要標志。但“給……一個機會”的表述,則暴露出在面對西方強勢文化時,內心的極度“卑微”。正是在這一晚,遠在美國的蘇梅選擇和成東青分手。影片巧妙地將后殖民語境下民族與個人的命運聯系起來,從中可見西方霸權話語對整個東方民族和個人侵入之深。
影片“90年代”后的敘事也沒有擺脫西方霸權話語的陰影和控制。不妨以孟曉俊為個案做分析。由于家庭原因,開始的孟曉俊是一個十足的西方主義者,他一心推崇的是 “機會面前人人平等”的“美國夢”。然而,在美國的他被同是中國留學生的張曦擠走了,淪落到刷盤子度日。更令他失望的是,飯店里的美國雇員居然也克扣他的小費,所謂“公平”根本不存在,他的“美國夢”終于破滅!回國與成東青“合伙”創業后,他便堅定理想,即用“美國夢”的方式——“個人奮斗、公平自由”,在中國實現事業的成功,然后再重新“打回”美國。孟曉俊在反駁美國教育服務中心的指控時,便強調美國這一無理舉動“違背了美國精神”,從而讓對方啞口無言。可見,他是借助于西方話語(也許唯有如此),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將“中國夢”納入西方的話語場域,暫時屏蔽掉西方話語中作為“他者”的東方,也消弭了本土的文化語境。一個更吊詭的現象是,孟曉俊在新夢想所從事的“一對一”簽證面試輔導,其本質乃是西方價值理念的灌輸和美國思維的訓練。所謂“真實、自信、具體、合理”的簽證哲學,不啻為對東方傳統價值理念的規訓,面試時滔滔不絕的孟曉俊,仿佛西方話語的訓導者和代言人。他的夢想是通過幫助更多學生去美國從而壯大企業,而他自己卻恰恰正是“美國精神”的受害者,這是一個悖論而封閉的話語邏輯。
由此可見,身處西方霸權話語主導的世界,盡管東方也做了爭取話語權的努力,然而這一局面并沒有根本改變。東方已不覺認同了西方話語所建構的“東方化的東方”,而要想獲得西方話語的認可,就必須按照西方規定的游戲規則和話語邏輯做自我改編,有限的發聲也成為“表述的表述”。斯皮瓦克曾指出,“試圖通過借助于第三世界的背景而獲得一個清白的論述立場的想法是不現實的。”③這一論斷盡管遭受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反駁,但至少從目前來看,第三世界國家經常身陷表述的焦慮,建構民族表述話語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二、香港顯影:“夾縫”想象與“逆性幻想”
《中國合伙人》凸顯表述焦慮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香港視角的融入。香港導演陳可辛和編劇林愛華的參與,讓這個以大陸人為主角的創業故事呈現了許多香港顯影,從中分明可以感受到香港人對30年來的大陸和西方世界的獨特想象和復雜情感。盡管香港已經回歸15年了,但與長達150年的殖民經歷相比,這點時間遠不足以消弭其強烈的“夾縫”生存體驗。
一方面,香港并沒有完全適應更迭、文化轉換的歷史轉向。正如香港學者陳清僑所言:“眾所周知亦所難明的是,中英聯合聲明早經肯定的‘一國兩制’方案,始終未能舒解港人因回歸中國而牽動的情緒不安和腦波震蕩。”④這直接導致了對祖國大陸歷史缺少理解,甚至誤解,港人的大陸想象始終與歷史“隔”了一層。陳可辛原本以為,只要“動用香港的經驗,就可以拍出內地那個年代的心態;‘我在1970年代的香港成長,跟內地1980年代很像。內地1990年代到奧運前那種財大氣粗,又跟香港的1980年代一模一樣。’”⑤然而,改革30年,尤其是“80年代”與香港的“70年代”還是有本質區別的。影片中,“80年代”許多重要社會文化事件都沒有得到展現,原本寬廣深厚的文化場域被窄化、淺化了。陳可辛本人也認識到翻譯“國情”時的“信息缺失”,所以不得不請內地編劇二度操刀,以“普及細節”。即便是回歸之后的敘述,也可見對大陸歷史的偏頗,乃至“成見”。比如影片反映了1999年美國轟炸我駐南聯盟大使館這一歷史事件,群情激奮的青年學生暴力圍攻成東青,指責他是“賣國賊”。狼狽的成東青則斥責學生“只知窩里斗”“跟30年前有什么區別?”事實上,人物原型俞敏洪本人在新東方的危機時刻并無此過激言行,學生的情緒也比影片中的要微妙,甚至“更多的學生在白天游行結束后,晚上又到燈下復習‘托福’。”⑥可以說,這只是陳可辛強力“征用”這一歷史事件,曖昧地表達了對“國民性”和大陸“”歷史的反思和無法祛除的當下疑慮。
另一方面,面對以美英為代表的曾經的西方殖民力量,港人的內心情緒是很復雜的。正如一位香港學者所言:“香港電影在參與1997話語中,透過建立復雜的人情世態和符號結構,刻鏤了香港人在為自己重新設定文化位置時,那種夾帶著濃烈民族情感、但又對殖民政府欲拒還就的復雜心態。”⑦即是說,對于結束長期殖民統治,終于回歸祖國懷抱的香港而言,源于同族同宗、同一血脈的民族情感自然是極其濃烈的。影片的“中國夢”主題,以及主人公對美國教育服務中心的一一反駁、據理力爭,讓強烈的民族情感呼之欲出,其中分明可以聽到香港同胞的心聲。但是,長期隔絕所造成的經濟文化上的隔閡卻不是短時期可以彌合的。此時,長期的殖民經歷便在港人潛意識中發揮作用,即在文化上往往更容易認同曾經的,并且今天仍占主導地位的西方文化。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影片的民族意識和夢想激情從未真正脫離西方話語,西方往往成了東方自我確證甚至“羨慕”的對象。“東方好萊塢”這一美名,正是香港獲得西方話語認可的確證。因此,香港視角所造成的情緒曖昧和表述焦慮,在影片中是非常濃厚的。
這一身處大陸和西方之間的“夾縫”想象,對于之后文化身份的重建是不利的。因為“當被殖民者將痛恨與崇拜復制在殖民者這一個對象上時,始終貫穿著黑格爾意義的主仆互認心理,根本無暇顧及真切的‘在地經驗’與受挫的文化傳統。”這就是美籍華裔學者張英進所指出的“逆性幻想”現象,它讓香港“看不見眼前存在的東西——香港已有的商業文化。在建構文化身份時,香港文化難以從內部形成清晰的自我意識。”⑧這一分析可謂非常精辟。后殖民語境下的“逆性幻想”,使香港不僅對自己,而且對作為“雙重他者”的大陸和西方也存在嚴重的文化“游移”和“盲視”。這一獨特心態造成影片不可能深入發掘民族傳統,展現30年積淀逐步形成的民族商業文化,也不可能以相對客觀的視角審視“美國夢”。影片中,美國教育服務中心的幾位工作人員成了整個西方世界的代表,他們的狡黠、強硬乃至無理構成西方話語的本質,這樣的處理顯然過于簡單化了。這一精神困境使標題里的“中國”二字彰顯出獨特的文化內涵,它已經成為所有“中華政治實體”的代表,是一個抽象社群的符號,一個“想象的共同體”。唯有如此,它才可以容納各種不同,甚至矛盾的民族情緒和文化因子。
三、認同危機:全球化表征與“第三度空間”建構
霍爾曾深刻指出:“認同問題實際上是在其形成過程中(而非存在過程中)有關歷史、語言、文化等資源的使用問題:不是‘我們是誰’或‘我們來自何方’等問題,而是我們可能成為什么,我們是如何被再現的,是如何應付我們該怎樣再現自己的問題。”⑨即是說,“認同”絕非是對已經“存在”的文化身份的“相認”,而是通過運用各種“資源”對身份(自我他者)的一種建構,以及對這種建構方式的一種反思。在當今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范圍內各種政治、經濟和文化力量之間的沖突和融合是前所未有的。全球化一方面導致了傳統文化的危機,單質的文化身份已很難存在;另一方面也為重建本土文化身份的認同提供了契機,因為它可以激活和強化民族認同的自覺性,擺脫以前對民族文化的麻木和“盲視”狀態。電影《中國合伙人》將后殖民語境納入全球化背景中,從而更加凸顯了認同的危機和契機。
作品直觀呈現了全球化帶來的時空壓縮和本地位置感的消失。在現代交通和通訊工具的推動下,時間戰勝了空間,同時性和短暫性成為生活的常態。影片多次對機場的航線模型燈做了特寫,它隱喻中美兩國之間的空間距離,現在就像地圖上這依次亮至對岸的燈一樣,可以輕松跨越。這使得“遠距控制”(吉登斯語)成為現代生活的獨特景觀,正如影片所展現的,美國教育服務中心的一封“投訴信”,就可以直接影響國內教輔市場的走向。的確,傳統社會那種穩固的、變化緩慢的“在場”機制被摧毀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遠處所發生的事件對本地在場生活世界的深刻影響。⑩此外,影片展現了全球化帶來的文化混雜化,不同國家的文化因子可以在世界各地自由“旅行”。影片里中國學生可以隨時欣賞馬龍·白蘭度的經典之作《碼頭風云》,而在美國你也可以觀看香港導演吳宇森的代表作《英雄本色》。這種文化混雜化削弱了傳統文化中,特定空間的穩定性和同質性對于認同的建構功能。最后,影片還運用蒙太奇技術,使場景在中國和美國之間頻繁切換,談判室外的紐約城市景觀,與國內一些大城市已無本質區別。同樣,國內都市現代人的生活元素與美國也實無異處。這一全球同質化的進程越快,本地“位置感”的消失就越明顯,那么“需要發現或制造出某種存在于其中的永恒真理的壓力就越大。”如此,自我身份認同的危機感就越強。
上文已經指出,全球化不僅帶來身份認同的危機,也提供了建構認同的契機。霍米·巴巴提出的“第三度空間”(或譯為“中間狀態”)設想,是少數極富啟發性的認同建構思路。巴巴指出,在后殖民語境下形成的二元對立文化格局中,“關于差異的敘事和文化政治成了封閉的闡釋循環。他者失去了表意、否定、生發自己的歷史欲望、建立自己制度性的對立話語的權利。”因為,“它總是以分析的方式要求他者的文化內容是知識的好對象、差異的溫順載體。”而通過對二元之外“第三度空間”的建構,可以構成文化行為的新話語空間,即“確保文化的意義和象征沒有原本性的單一體或固定態,而且使同一符號能夠被占有、轉譯、重新歷史化和重新解讀”。這一設想是極其深刻而精彩的!它拒絕了敵我分明的二元格局,打開了廣泛協商的無限空間,使認同始終處于既聯系過于,又立足當下,且面向未來的“未完成”狀態。但影片對認同的認識遠未達到這一高度,主要存在以下兩方面不足。
其一,影片固守敵我二元文化格局,刻意將“中國夢”與“美國夢”表述為對立的文化形態,失去了打開“第三度空間”的可能。影片批評西方對東方的認識“一點沒有改變”,仍停留于西方話語表述的“文本中的東方”,的確有力回擊了西方霸權話語,應當肯定。但是,從根本上看,東西方之間的對話和交往,絕不應該是強化對立和相互“攻陷”,而是在遵守寬容原則和差異邏輯的前提下,建立寬容平等的互動關系。因為,差異邏輯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是在充斥著霸權話語的現實世界中,對一種自我身份及其文化合法化和對平等尊重的訴求;但另一方面,對差異的過度強調,則會造成“自我”對“他者”的盲目排斥,甚至暴力抗拒。影片對東西方差異的表現即有過度之嫌,這既妨礙了我們對西方的客觀認識,最終也不利于健全民族品格和真正認同的建立。畢竟“西方的‘東方主義’是危險的,東方的‘西方主義’同樣不可取。”
其二,影片對“中國夢”,這一民族夢想的認識和建構也存在很多不足,其根源是對民族傳統文化“基因”缺乏深入發掘。霍爾指出,認同“與傳統的發明以及傳統自身有關,從而迫使我們把傳統解讀為‘變化的相同物’(Gilroy,1994),而非無窮的重復:不是所謂的回歸本源,而是與我們的‘路徑’妥協”。即是說,只有發掘、含茹民族傳統,將傳統文化精髓傳承并轉換至現代生活中來,我們才能找準自我接納的“路徑”,實現自我認同。因為,“中國夢”區別于“美國夢”的一個根本特征是,“中國夢”是要再現我國歷史上曾長期呈現的東方大國、強國的恢弘氣象,是全民族一直夢寐以求的“復興”之夢,因此它具有“縱深的歷史感”(石毓智語)。而深厚的傳統文化正是傳遞這一夢想,接續這一“歷史感”的血脈。“美國夢”則不然,它孕育于短暫的美國歷史,且一直延續至今,美國人對它的感受停留于“現實的體驗”,因此它也鼓勵通過個人奮斗,獲得“現實”的成功。影片編者對此沒有深刻認識,盡管他也強調民族尊嚴,但是我們并沒有看到任何民族傳統因素在他創業過程中起到引領和推動作用,民族傳統文化“基因”并沒有真正介入影片的夢想敘事。它更多的只是,三個“合伙人”用“美國夢”的方式,實現“中國夢”的創業故事而已。它沒有提供返回傳統文化,認同民族身份的清晰“路徑”,缺乏應有的厚重和深度。需要指出,這也正體現了香港導演和編劇在想象大陸時,經常出現的“經驗貧乏”“信息缺失”和“文化盲視”的困境。
綜上所述,電影《中國合伙人》作為“社會文本”,為我們檢閱30年的改革歷程提供了獨特視角,作品塑造的幾位有代表性的企業家形象,可以說填補了影史空白。由于影片創作者身處獨特的文化語境,導致作品并沒有找到獨立表述的話語,從中可以感受到濃重的表述焦慮和身份認同危機。影片帶來的啟示是深刻的,即面對全球化背景下的后殖民語境,我們應首先保護、傳承和轉換優秀的傳統文化,將其作為向世界發聲的“基調”;此外,內地還需加強與港澳臺影視工作者的交流與合作,豐富他們關于大陸的“在地經驗”,增強港澳臺同胞對民族傳統文化的切身體驗和認同感;最后,在表現西方時,我們應在遵守差異性邏輯的前提下,更客觀地認識和了解西方文化,既不陷入殖民話語“陷阱”,也不將其“妖魔化”。唯有如此,我們才能運用源于民族內部的表述話語,真正編織一個能夠鼓勵一代青年,并能與“美國夢”平等對話的“中國夢”!
注釋:
① [美]尼·布朗著,齊頌譯:《電影與社會:分析的形式與形式的分析》(下),《世界電影》1987年第5期。
②⑤見《合伙到散伙:電影〈中國合伙人〉戲里戲外》,《南方周末》2013年5月17日。
③轉 引自趙稀方:《后殖民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86頁。
④ 見《文化想象的時空》,陳清僑主編:《文化想象與意識形態》,牛津大學出版社。
⑥ 吳曉波:《激蕩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2頁。
⑦ 邱靜美:《跨越邊界——香港電影中的大陸顯影》,見鄭樹森編:《文化批評與話語電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24頁。
⑧ 陳林俠:《港臺電影中的后殖民演繹:從“雙城故事”到“臺灣意識”》,《文藝研究》2009年第3期。
⑨{15}[英]斯圖亞特·霍爾著,周韻譯:《導論:誰需要“認同”?》,周憲主編:《文學與認同:跨學科的反思》,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6頁。
⑩ 周憲:《全球本土化中的認同危機與重建》,周憲主編:《文學與認同:跨學科的反思》,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229頁。
{11}[美]哈維著,閻嘉譯:《后現代狀況》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36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