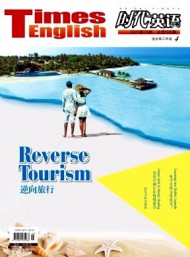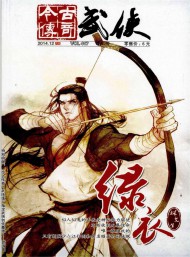類型人物范文10篇
時間:2024-02-22 11:30:21
導語:這里是公務員之家根據(jù)多年的文秘經驗,為你推薦的十篇類型人物范文,還可以咨詢客服老師獲取更多原創(chuàng)文章,歡迎參考。

類型人物研究論文
眾所周知,小說是一種文字藝術。它作用于人們的第二信號系統(tǒng),借助于讀者的生活經驗和想象力完成其藝術欣賞過程。盡管小說無法展現(xiàn)作用于第一信號系統(tǒng)的視覺場面,(即便是《老人與海》這樣的小說,我們也很難真正體驗到大海的視覺奇觀。)可是,觀眾的參與和想象活動是藝術審美的生命,小說擁有了這樣的特性便成為了一種高雅的文化產品。在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中,不僅人物命運能得到充分的展現(xiàn),而且人物豐富復雜得難以言狀的內心世界也能得到淋漓盡致的揭示。《奧勃洛莫夫》中的奧勃洛莫夫在床上一動不動地躺著,作者就能把他的豐富的內心活動展示給我們。也許,只有小說有這樣的魅力:一部小說的情節(jié)或細節(jié)描寫已經隨著時間的流逝被讀者淡忘了,然而那小說中眾多的成功塑造的人物卻在讀者心中長存甚至伴隨他們一生。我們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文字有利于塑造復雜的人物個性和千變萬化的內心世界。在小說之林里,即便是象西德尼.謝爾頓或瓊瑤這樣的通俗小說作家,也依然必須在人物個性的塑造上下一定的功夫。
再看戲劇。由于戲劇的空間表現(xiàn)的顯而易見的局限性,導致它不可能依靠視覺手段。因此戲劇的真正武器是對話。戲劇家們運用對話來展開情節(jié)和沖突,揭示人物關系和性格。如果對話過于膚淺,流于生活的表面,如果我們通過對話看不到人物心靈和性格中那些隱秘的層次,戲劇就會變成毫無戲劇性可言的淺薄的東西。所以,戲劇沒有選擇,既然它不能用視覺的奇觀來嘩眾取寵,就只能靠對人性深刻的揭示來將觀眾吸引到劇場里來。正因如此,戲劇便獲得了高雅的屬性。無論是莎士比亞或是易卜生,無論是斯特林堡還是奧尼爾,戲劇大師們所追求的永遠是性格的豐富性和對心靈的隱秘的揭示。正是戲劇的短處成就了戲劇的高雅。戲劇也羨慕過電影的通俗性所帶來的金錢,也有人希望能創(chuàng)作出類似于警匪片、驚險片或恐怖片這樣一些戲劇樣式。但如您之所見,到現(xiàn)在我們也沒看見有什么“警匪戲劇”、“恐怖戲劇”或“驚險戲劇”形成氣候。娘胎里生就的高雅何須作東施效顰呢?
可是電影呢?電影擁有無與倫比的時空表現(xiàn)力,它可以表現(xiàn)高山大海和千軍萬馬的古戰(zhàn)場,可以展現(xiàn)星際大戰(zhàn)和史前生物的肉搏。它擁有任何其它姊妹藝術所沒有的視聽武器。得天獨厚的能力對人是不是有絕對的好處呢?比如一個長得十分漂亮的女孩兒,也許就因為她比別人漂亮便無需作更多的努力即能取悅于人。電影藝術的“天生麗質”正是這樣地使它無需在人物塑造方面苦下功夫就能取悅于觀眾。它可以將冰海沉船、彗星撞擊地球、龍卷風和大白鯊……所有人類能夠想象到的驚心動魄場面都展現(xiàn)給觀眾,并且只靠了這些視覺的奇觀本身便可以將觀眾在兩個小時左右的時間里牢牢地吸引在影院的座位上。人物性格的塑造便成了可有可無的事情,更遑論性格的深度。稍有文化修養(yǎng)的人就能分辨出一部莎士比亞劇本與《泰坦尼克號》影片中人物塑造的高下,恐怕只有白癡才會把兩者放在一個天平上衡量。好萊塢那些高成本的大片中的人物性格的落套和淺俗幾乎成為那種影片的標致。不知是不是會有誰將一部影片在票房上的成功與該影片的文化品味看作是一回事兒?如果有,那一定是利用電影賺到了錢的人或渴望賺到錢的人,千萬不能相信他的話。電影也有佳作,在佳作里也有膾炙人口的人物性格,但你會發(fā)現(xiàn)那常常就是借助了對小說或戲劇作品的改編,電影編劇的原創(chuàng)人物寥寥無幾。而且您還會發(fā)現(xiàn),改變自小說和戲劇作品的電影作品,盡管有著比原作更廣泛的觀眾面,但看過原著的人往往會抱怨這些改編實在是糟改原著,至少失去了原著的深刻性和人生品味,充其量不過是原著的贗品。
在這里,也許應該為電影藝術說上兩句公道話。我們無權要求任何門類的藝術都必須達到同樣的人文深度。要求一部恐怖片也要深刻如契柯夫的《海鷗》顯然是滑稽可笑的。畢竟在這個世界上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把深刻作為自己的審美目標的。恐怖片就象我們坐翻滾過山車,一時的刺激便帶來了值得花錢的愉悅。以往我們總是要求電影藝術的任何樣式都要追求人物性格的豐富立體性其實是根本錯誤的。在商業(yè)樣式的影片中,我們根本無法做到也根本不必追求人物性格的復雜性。即如美國影片《生死時速》,在創(chuàng)作這樣的影片的時候,編劇最需要下功夫的是講好一個具有驚心動魄場面和讓人透不過氣來的故事,而導演的任務就是把文字提供的視覺奇觀設計圖逼真地展現(xiàn)在銀幕上。人物的類型化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這些電影樣式商業(yè)成功的因素之一。就象麥當勞的策略一樣,如果它的漢堡包和辣雞翅不作定型化的生產,就不會有那樣多的贏利。因為它必須用一種模式化的生產來培養(yǎng)人們固定的口味。最明顯的例子便是美國的西部片,其中的人物都是固定不變的類型,那些無法無天的牛仔、那些孤單闖入敵陣的英雄、那些野辣辣但善良的妓女……所有這些就象定型生產的漢堡包,早已經培養(yǎng)起了一大批觀眾的口味,所以至今仍然保持著西部片的常盛不衰的觀眾群。香港的功夫片得到了西部片經營之妙吷,于是也成為中國唯一能夠殺向好萊塢的電影樣式。人物性格的復雜和立體,人物內心生活的深層結構本論文由整理提供,這些都必然會帶來作品在主題思想上的艱深和多意,這也許從來就不是把票房看作生命的那些電影投資者的意愿。我認為好萊塢為代表的商業(yè)電影是很值得今天的中國電影人研究的文化現(xiàn)象。一天,有個電視臺的記者問我:“您認為張藝謀和馮小剛誰更棒?”我反問他道:“你認為跳高的朱建華和打乒乓球的鄧亞萍誰更棒?”我認為他們都不錯。不能在商業(yè)喜劇如《不見不散》這樣的作品上苛責馮小剛塑造的人物膚淺,這就好象我們不能聽了相聲抱怨它太不莊重一樣。我們應該看到他的機智和幽默和敘事節(jié)奏的流暢。今天中國大部分的商業(yè)片不是太不深刻的問題,而是太不懂商業(yè)規(guī)律太缺乏商業(yè)想象力的問題,甚至是一個如何創(chuàng)作好類型人物的問題。
什么是類型人物?戲劇理論家和教育家貝克在他的著作《戲劇技巧》中有所描述。他認為劇作中的人物可分為三種類型:一種是概念化人物,他說:“概念化人物是作者立場的傳聲筒,作者毫不把性格描寫放在心上。”第二種便是類型化人物,他說:“類型人物的特征如此鮮明,以至于不善于觀察的人也能從他周圍的人們中看出這些特征。”這種人物“每一個人都可以用某些突出的特征或一組密切相關的特征來概括”。第三種為圓整人物(RoundCharacter),也有人翻譯作“個性化人物”的。他說:“圓整人物在類型中把自己區(qū)別開來,大的區(qū)別或者細微的區(qū)別。”這種人物具有性格的多側面和復雜性。他們的性格復雜到無法用簡單的話語來概括和分析。貝克認為,類型人物在今天還大大地存在的原因如下:①人物性格特征有限并且鮮明,這樣就易于觀眾領會和把握。②這樣的人物容易創(chuàng)造,更容易編寫。③鬧劇和情節(jié)劇看重的是情節(jié)的戲劇性,這樣的劇本哪怕它缺乏人物的個性化,觀眾仍然對同樣的故事百看不厭(如羅馬和伊麗莎白時代的觀眾)。事實上,中國人的敘事傳統(tǒng)中更突出的是對類型人物的描寫。而中國人的審美習慣也相當?shù)毓潭ㄔ陬愋腿宋锷稀!都t樓夢》除外,我國古典章回小說中的人物和戲曲舞臺上的人物大多數(shù)便是類型化的人物(尚有一些概念化人物)。例如《三國演義》《西游記》和《水滸》中的人物:曹操性格突出的是一個“奸雄”,關羽則可以概括為“忠勇”,諸葛亮不過突出了一個“神”字。張飛性格全部集中在“直魯”上。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藝術最大的特點便是夸張,表現(xiàn)在人物塑造方面便是人物性格的夸張。這種夸張的方法可以總結為強化人物性格中的某一特征。這樣的方法能取得良好的劇場性,易于為更多的普通觀眾所接受。其實直到今天,中國觀眾的審美特點也沒有太大的改變。記得《鄉(xiāng)音》這部被專家看好的影片到湘西農村放映的時候,這部為農民創(chuàng)作的、表現(xiàn)農民的影片在農民中卻沒有產生預期的效果,他們抱怨說影片“分不出好賴人”來。中國農民喜歡人物立場和性格一目了然。就象中國戲曲舞臺上人物,臉譜本身就有了綜合地表述立場和性格的功能。這種審美習慣在電視劇中表現(xiàn)得就更加明顯。專家們對《還珠格格》獲得那樣大的轟動效果瞠目結舌,覺得不可思議。“小燕子”就人物塑造而言性格何其夸張簡單,簡單得幾乎有點二百五!可為了看“小燕子”竟然能夠萬人空巷!其實,瓊瑤是個聰明人,她明白中國人的審美習慣,所以對所有劇中人物都采取了類型化的處理原則。您回過頭去看看,《西廂記》里的那個?炷錚魴愿裎薹薔褪歉觥傲胬砂保歡幢蝗嗣強詒兩瘛O衷謨忠恢弧傲胬砂鋇摹靶⊙嘧印狽衫戳耍懿患矣骰穡咳綣閬趕阜治鼉突岱⑾鄭懇桓齟蠛齏笞系牡縭恿韁械娜宋鍥涫刀甲叩氖搶嘈腿宋锏穆肥紜犢釋泛汀渡┠鎩分械吶鶻侵倘韙褐亍⒁緣鹵ㄔ貢閌峭懷齙囊煥N頤羌負蹩梢遠涎裕綣桓鲇笆穎嗑綺換嶠宋鎰骼嘈突恚禿苣崖憒籩諼縛冢闖靄儺障舶淖髕防礎?BR>將劇中人物作類型化處理也不一定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生活中的現(xiàn)實性格通常都是模糊的和多成份的,因此也是說不清道不明的。現(xiàn)在,劇作家要從那個人物之性格的綜合成份里選出一個或兩個特征作夸張?zhí)幚恚陀幸欢ǖ碾y度。首先你必須決定選擇什么。如果你選擇的那個人物性格的特征是大家已經看煩了的,觀眾就會覺得太舊。比如,我們一些表現(xiàn)部隊生活的作品總是愛重復這樣一些類型:傻大黑粗的農村兵、調皮搗蛋的城市兵、好媽媽式的教導員、性情直魯?shù)倪B長……其實這在《霓虹燈下的哨兵》中出現(xiàn)的時候大家還是覺得挺好的。但現(xiàn)在這種類型幾乎便成了定型,就讓人覺得有些東施效顰了。描寫青年的類型人物也有很多的重復,例如以往寫所謂的好青年,總不外是說話木訥、見了異姓就臉紅;如果寫女記者一定是風風火火、瘋瘋癲癲、敢愛敢恨……這樣的人物看多了,就讓人覺得中國的影視編劇沒有想象力,光會跟在別人的后面克隆。可見,真正的問題還不是反對人物類型化的問題,而是一個反對人物定型化的問題。其實,在中外很多的優(yōu)秀作品中,優(yōu)秀的類型人物不但不會被觀眾厭棄,反而會得到大家的喜愛。例如卓別林創(chuàng)造的那個象鴨子一樣走路的紳士流浪漢便是個極好的例子。這個小人物除了永恒的善良本性以外,最突出的性格特征就是永恒的尊嚴。無論情況多么艱難窘迫,也無論對手多么強大可怕,他總是拼命地保持著自己的紳士風度和尊嚴。俗話說“人窮志短”,可卓別林卻把它反了過來,去表現(xiàn)了一個可憐滑稽的小人物超越常理的尊嚴,就十分具有創(chuàng)造性和獨特的想象力了。因為卓別林是流浪漢出身,他一定知道在每一個受欺侮的靈魂深處都有一種深藏的渴望:保持住作人的尊嚴。他正是聰明地抓住了這一點。再如,在日本山田洋次的《男人辛苦》系列影片里也有個家喻戶曉的類型人物寅次郎。在日本,幾乎沒有不知道阿寅的。這個將眼睛瞇作一條縫的胖子性格格外的單純鮮明:他善良仗義多情卻又懶散而不拘小節(jié)。每天大大咧咧、無所事事,卻常常大言不慚。山田洋次真是個聰明人,他在這個人物性格上的類型化處理可是十分有學問的。在日本這個高度現(xiàn)代化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大多數(shù)日本人被西方人形容作每天只知道工作的“藍螞蟻”。給人的感覺是,大多數(shù)日本人中規(guī)中矩、一絲不茍、性格壓抑、不茍言笑、感情輕易不外露,例如一個日本人向你點頭說著“哈依”并不一定就表示他同意你的意見,你很難知道他的真實想法是什么。然而,在高度緊張的工作和生活節(jié)奏中,其實很多的日本人心里都有與現(xiàn)實相反的渴望。他們渴望著能沖出刻?宓納罟旒d烊魎嬉獾厴睿芄煌墻鵯亞楦鋅吹帽仁裁炊賈兀芄徊蛔⒁饃纖凈蛉魏穩(wěn)說牧成乇澩鎰約旱娜魏吻楦小庖磺斜闈∏∈巧教镅蟠胃秤璋⒁摹H嗣譴影⒁砩峽吹攪俗約核淙黃詿丫謾⑾胱鋈從植荒蘢齷蠆桓易齙摹U餼湍壓職⒁餿擻姓庋玫墓壑讜盜耍∑涫擔土謚泄難飛先巳聳熘陌ⅲ巖彩歉隼嘈突宋锪ǎ≌飧魴愿竇瓤湔諾慕巧鍆懷齙男愿裉卣鞅閌恰熬袷だā薄N頤鞘翟謔遣荒芤蛭飧鋈宋锍鱟暈按蟮淖骷衣逞副氏戮蛻亟榻岬皆艙宋锏娜ψ永鍶ァK鄧搶嘈突娜宋鋝⒉灰馕蹲歐穸ㄋ納羈絳浴O嚳矗绱蠹宜彩兜哪茄詘ⅲ焉砩霞刑逑腫胖泄斯裥災械牡湫吞卣鰲S紗絲杉桓穌嬲壑謁舶睦嘈腿宋錛炔荒蓯遣環(huán)啞湍艿美吹模膊荒蓯強寺〉慕峁D潛囟ㄊ且淮尉哂懈魴緣拇叢歟嵌隕釕釙懈形虻慕峁@嘈腿宋鎘Ω檬且恢終嬲牡湫停哂猩緇嶸畹鈉氈樾院托愿竦南拭饜浴?BR>我認為,學會寫類型人物應該是編劇的影視基本功。其實人物塑造也象繪畫一樣,在學習繪畫的時候常常有兩種練習:一種是速寫,一種是素描。本論文由整理提供
速寫要求用極其簡練的筆法和線條甚至有些夸張地將人物勾勒下來,而素描則要求對人物作空間層次的細致描畫。類型人物就好比是速寫,如果你沒有抓住一個人物性格鮮明個性特征的能力,也很難對人物多重成份的性格作全面的描述。更何況,即便是在那些以圓整人物為主角的電影作品中,類型化人物依然是不可少的。劇作家用了這樣的技巧來描寫次要人物。要知道,在電影劇作中,畢竟敘事的時間有限,在兩個小時的甚至更短的篇幅里,你要想將所有的劇中人物的性格都作圓整化的處理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時,那樣也是根本就沒有必要的。因為沒有主次就意味著喧賓奪主。這時,你又不能將次要角色處理得個性全無,那樣的做法觀眾也不會接受。最好的辦法就是抓住這些次要角色的某一個突出的性格特征作夸張?zhí)幚怼@纾谌毡倦娪啊哆h山的呼喚》中,作者對主要角色耕作和民子都作為圓整人物來塑造,寫出了他們復雜的性格成份。這兩個人物細膩復雜的情感和內心世界使我們感到了人物性格的現(xiàn)實性。可是,影片中的虻田以及民子的弟弟和弟媳,就作了類型化的性格處理。這樣的方法不僅增強了戲劇性,也反襯了耕作和民子這對中年人的深沉情感和性格的圓整性。在國產影片《牧馬人》中,編劇對許靈均和李秀芝這兩個男女主角作了圓整性格的刻劃,但對郭PIA子卻作了類型化的性格處理,而這個人物卻使作品增色不少。獲得了東京電影節(jié)大獎的日本影片《談談情,跳跳舞》中那個舞蹈動作怪異的青木也是個很成功的類型人物。這個人物使影片在總體基調的嚴肅性上增添了幾分活潑和輕松。影片的編導者一定非常清楚,任何藝術所產生的效果都離不看對比,在一部影片中莊諧共在才能相映成趣。
類型人物研討論文
人們習慣于將藝術大家庭的成員稱作七姊妹,如果你問一些知識分子:“在‘七姊妹’中最粗俗的一位是誰?”他們中的很多人可能都會說:“電影。”確實,就藝術氣質而言,不管電影工作者多么不愿意承認,電影藝術在眾姐妹中確實存在著某種自卑感。同時從事過文學、戲劇和電影創(chuàng)作的老前輩夏衍在給北京電影學院的學生上課的時候,曾開宗明意地指出:“要記住,電影說到底是一種俗文化。”他的見解也許在很多人看來有些偏頗,但如果你考察一下電影的歷史和現(xiàn)狀就會覺得他說的確實有道理。作為嬰兒的電影降生的‘產房’是鎳幣影院。生活在最底層的勞工們辛苦一天之后帶著滿身的汗餿氣走進黑洞洞的倉庫,去看那廉價的、黑白光影顫抖的《工廠大門》。影院經營人在他們身邊來回走動著,將一個空罐頭盒伸到他們面前,他們便向里邊扔上幾個鎳幣,算作是電影票錢……看,電影的出身是多么貧寒,充其量不過是街頭把戲的地位。為了使電影成為一種能夠與文學、戲劇、舞蹈、音樂……這些高雅的姊妹等肩而立的藝術,很多電影工作者耗費了畢生的精力。愛森斯坦、伯格曼、雷諾阿、費里尼、安東尼奧尼……他們確實拍攝出了令知識分子不得不脫帽欣賞的作品。但是從數(shù)量上看,在百年來世界電影作品的海洋里,他們這些高雅之作所占的比例又能有多少呢?可以說是微乎其微!難怪英國小說家和小說理論家福斯特在他的影響世界的大作《小說面面觀》里,公開地表達了他對電影和電影觀眾的鄙視。他認為故事與情節(jié)相比,前者是一種粗俗的形式,后者則高雅得多。因此前者是給“原始的穴居野人和現(xiàn)代的電影觀眾”看的。你看,他將現(xiàn)代的電影觀眾與原始的穴居野人看作是一回事了。再有,你聽說過有誰來討論戲劇或者音樂或者舞蹈算不算藝術這樣的問題嗎?肯定沒有,因為它們天經地義就是藝術。然而伴隨著電影成長的整個過程,都有人在討論“電影是一門藝術嗎”這樣的問題。直到1933年魯?shù)婪颍異垡驖h姆還在他的著作《電影作為藝術》中討論這個問題。
我常常考慮這是為什么?為什么電影藝術在人們眼睛里就會比其它的藝術姊妹要低俗?是電影工作者的水平低于從事其它藝術的人們?恐怕還不能作出這樣簡單的結論。有一點可以肯定:這與電影藝術的特性有關,正是這樣的特性在很大的程度上使電影藝術成為夏衍說的“俗文化”的。
眾所周知,小說是一種文字藝術。它作用于人們的第二信號系統(tǒng),借助于讀者的生活經驗和想象力完成其藝術欣賞過程。盡管小說無法展現(xiàn)作用于第一信號系統(tǒng)的視覺場面,(即便是《老人與海》這樣的小說,我們也很難真正體驗到大海的視覺奇觀。)可是,觀眾的參與和想象活動是藝術審美的生命,小說擁有了這樣的特性便成為了一種高雅的文化產品。在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中,不僅人物命運能得到充分的展現(xiàn),而且人物豐富復雜得難以言狀的內心世界也能得到淋漓盡致的揭示。《奧勃洛莫夫》中的奧勃洛莫夫在床上一動不動地躺著,作者就能把他的豐富的內心活動展示給我們。也許,只有小說有這樣的魅力:一部小說的情節(jié)或細節(jié)描寫已經隨著時間的流逝被讀者淡忘了,然而那小說中眾多的成功塑造的人物卻在讀者心中長存甚至伴隨他們一生。我們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文字有利于塑造復雜的人物個性和千變萬化的內心世界。在小說之林里,即便是象西德尼.謝爾頓或瓊瑤這樣的通俗小說作家,也依然必須在人物個性的塑造上下一定的功夫。
再看戲劇。由于戲劇的空間表現(xiàn)的顯而易見的局限性,導致它不可能依靠視覺手段。因此戲劇的真正武器是對話。戲劇家們運用對話來展開情節(jié)和沖突,揭示人物關系和性格。如果對話過于膚淺,流于生活的表面,如果我們通過對話看不到人物心靈和性格中那些隱秘的層次,戲劇就會變成毫無戲劇性可言的淺薄的東西。所以,戲劇沒有選擇,既然它不能用視覺的奇觀來嘩眾取寵,就只能靠對人性深刻的揭示來將觀眾吸引到劇場里來。正因如此,戲劇便獲得了高雅的屬性。無論是莎士比亞或是易卜生,無論是斯特林堡還是奧尼爾,戲劇大師們所追求的永遠是性格的豐富性和對心靈的隱秘的揭示。正是戲劇的短處成就了戲劇的高雅。戲劇也羨慕過電影的通俗性所帶來的金錢,也有人希望能創(chuàng)作出類似于警匪片、驚險片或恐怖片這樣一些戲劇樣式。但如您之所見,到現(xiàn)在我們也沒看見有什么“警匪戲劇”、“恐怖戲劇”或“驚險戲劇”形成氣候。娘胎里生就的高雅何須作東施效顰呢?
可是電影呢?電影擁有無與倫比的時空表現(xiàn)力,它可以表現(xiàn)高山大海和千軍萬馬的古戰(zhàn)場,可以展現(xiàn)星際大戰(zhàn)和史前生物的肉搏。它擁有任何其它姊妹藝術所沒有的視聽武器。得天獨厚的能力對人是不是有絕對的好處呢?比如一個長得十分漂亮的女孩兒,也許就因為她比別人漂亮便無需作更多的努力即能取悅于人。電影藝術的“天生麗質”正是這樣地使它無需在人物塑造方面苦下功夫就能取悅于觀眾。它可以將冰海沉船、彗星撞擊地球、龍卷風和大白鯊……所有人類能夠想象到的驚心動魄場面都展現(xiàn)給觀眾,并且只靠了這些視覺的奇觀本身便可以將觀眾在兩個小時左右的時間里牢牢地吸引在影院的座位上。人物性格的塑造便成了可有可無的事情,更遑論性格的深度。稍有文化修養(yǎng)的人就能分辨出一部莎士比亞劇本與《泰坦尼克號》影片中人物塑造的高下,恐怕只有白癡才會把兩者放在一個天平上衡量。好萊塢那些高成本的大片中的人物性格的落套和淺俗幾乎成為那種影片的標致。不知是不是會有誰將一部影片在票房上的成功與該影片的文化品味看作是一回事兒?如果有,那一定是利用電影賺到了錢的人或渴望賺到錢的人,千萬不能相信他的話。電影也有佳作,在佳作里也有膾炙人口的人物性格,但你會發(fā)現(xiàn)那常常就是借助了對小說或戲劇作品的改編,電影編劇的原創(chuàng)人物寥寥無幾。而且您還會發(fā)現(xiàn),改變自小說和戲劇作品的電影作品,盡管有著比原作更廣泛的觀眾面,但看過原著的人往往會抱怨這些改編實在是糟改原著,至少失去了原著的深刻性和人生品味,充其量不過是原著的贗品在這里,也許應該為電影藝術說上兩句公道話。我們無權要求任何門類的藝術都必須達到同樣的人文深度。要求一部恐怖片也要深刻如契柯夫的《海鷗》顯然是滑稽可笑的。畢竟在這個世界上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把深刻作為自己的審美目標的。恐怖片就象我們坐翻滾過山車,一時的刺激便帶來了值得花錢的愉悅。以往我們總是要求電影藝術的任何樣式都要追求人物性格的豐富立體性其實是根本錯誤的。在商業(yè)樣式的影片中,我們根本無法做到也根本不必追求人物性格的復雜性。即如美國影片《生死時速》,在創(chuàng)作這樣的影片的時候,編劇最需要下功夫的是講好一個具有驚心動魄場面和讓人透不過氣來的故事,而導演的任務就是把文字提供的視覺奇觀設計圖逼真地展現(xiàn)在銀幕上。人物的類型化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這些電影樣式商業(yè)成功的因素之一。就象麥當勞的策略一樣,如果它的漢堡包和辣雞翅不作定型化的生產,就不會有那樣多的贏利。因為它必須用一種模式化的生產來培養(yǎng)人們固定的口味。最明顯的例子便是美國的西部片,其中的人物都是固定不變的類型,那些無法無天的牛仔、那些孤單闖入敵陣的英雄、那些野辣辣但善良的妓女……所有這些就象定型生產的漢堡包,早已經培養(yǎng)起了一大批觀眾的口味,所以至今仍然保持著西部片的常盛不衰的觀眾群。香港的功夫片得到了西部片經營之妙吷,于是也成為中國唯一能夠殺向好萊塢的電影樣式。人物性格的復雜和立體,人物內心生活的深層結構,這些都必然會帶來作品在主題思想上的艱深和多意,這也許從來就不是把票房看作生命的那些電影投資者的意愿。我認為好萊塢為代表的商業(yè)電影是很值得今天的中國電影人研究的文化現(xiàn)象。一天,有個電視臺的記者問我:“您認為張藝謀和馮小剛誰更棒?”我反問他道:“你認為跳高的朱建華和打乒乓球的鄧亞萍誰更棒?”我認為他們都不錯。不能在商業(yè)喜劇如《不見不散》這樣的作品上苛責馮小剛塑造的人物膚淺,這就好象我們不能聽了相聲抱怨它太不莊重一樣。我們應該看到他的機智和幽默和敘事節(jié)奏的流暢。今天中國大部分的商業(yè)片不是太不深刻的問題,而是太不懂商業(yè)規(guī)律太缺乏商業(yè)想象力的問題,甚至是一個如何創(chuàng)作好類型人物的問題。
什么是類型人物?戲劇理論家和教育家貝克在他的著作《戲劇技巧》中有所描述。他認為劇作中的人物可分為三種類型:一種是概念化人物,他說:“概念化人物是作者立場的傳聲筒,作者毫不把性格描寫放在心上。”第二種便是類型化人物,他說:“類型人物的特征如此鮮明,以至于不善于觀察的人也能從他周圍的人們中看出這些特征。”這種人物“每一個人都可以用某些突出的特征或一組密切相關的特征來概括”。第三種為圓整人物(RoundCharacter),也有人翻譯作“個性化人物”的。他說:“圓整人物在類型中把自己區(qū)別開來,大的區(qū)別或者細微的區(qū)別。”這種人物具有性格的多側面和復雜性。他們的性格復雜到無法用簡單的話語來概括和分析。貝克認為,類型人物在今天還大大地存在的原因如下:①人物性格特征有限并且鮮明,這樣就易于觀眾領會和把握。②這樣的人物容易創(chuàng)造,更容易編寫。③鬧劇和情節(jié)劇看重的是情節(jié)的戲劇性,這樣的劇本哪怕它缺乏人物的個性化,觀眾仍然對同樣的故事百看不厭(如羅馬和伊麗莎白時代的觀眾)。事實上,中國人的敘事傳統(tǒng)中更突出的是對類型人物的描寫。而中國人的審美習慣也相當?shù)毓潭ㄔ陬愋腿宋锷稀!都t樓夢》除外,我國古典章回小說中的人物和戲曲舞臺上的人物大多數(shù)便是類型化的人物(尚有一些概念化人物)。例如《三國演義》《西游記》和《水滸》中的人物:曹操性格突出的是一個“奸雄”,關羽則可以概括為“忠勇”,諸葛亮不過突出了一個“神”字。張飛性格全部集中在“直魯”上。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藝術最大的特點便是夸張,表現(xiàn)在人物塑造方面便是人物性格的夸張。這種夸張的方法可以總結為強化人物性格中的某一特征。這樣的方法能取得良好的劇場性,易于為更多的普通觀眾所接受。其實直到今天,中國觀眾的審美特點也沒有太大的改變。記得《鄉(xiāng)音》這部被專家看好的影片到湘西農村放映的時候,這部為農民創(chuàng)作的、表現(xiàn)農民的影片在農民中卻沒有產生預期的效果,他們抱怨說影片“分不出好賴人”來。中國農民喜歡人物立場和性格一目了然。就象中國戲曲舞臺上人物,臉譜本身就有了綜合地表述立場和性格的功能。這種審美習慣在電視劇中表現(xiàn)得就更加明顯。專家們對《還珠格格》獲得那樣大的轟動效果瞠目結舌,覺得不可思議。“小燕子”就人物塑造而言性格何其夸張簡單,簡單得幾乎有點二百五!可為了看“小燕子”竟然能夠萬人空巷!其實,瓊瑤是個聰明人,她明白中國人的審美習慣,所以對所有劇中人物都采取了類型化的處理原則。您回過頭去看看,《西廂記》里的那個紅娘,整個性格無非就是個“伶俐可愛”,然而卻被人們口碑至今。現(xiàn)在又一只“伶俐可愛”的“小燕子”飛來了,能不家喻戶曉嗎?如果你細細分析就會發(fā)現(xiàn),每一個大紅大紫的電視連續(xù)劇中的人物其實都走的是類型人物的路數(shù),例如《渴望》和《嫂娘》中的女主角之忍辱負重、以德報怨便是突出的一例。我們幾乎可以斷言,如果一個影視編劇不會將人物作類型化處理,就很難滿足大眾胃口,寫出百姓喜愛的作品來。將劇中人物作類型化處理也不一定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生活中的現(xiàn)實性格通常都是模糊的和多成份的,因此也是說不清道不明的。現(xiàn)在,劇作家要從那個人物之性格的綜合成份里選出一個或兩個特征作夸張?zhí)幚恚陀幸欢ǖ碾y度。首先你必須決定選擇什么。如果你選擇的那個人物性格的特征是大家已經看煩了的,觀眾就會覺得太舊。比如,我們一些表現(xiàn)部隊生活的作品總是愛重復這樣一些類型:傻大黑粗的農村兵、調皮搗蛋的城市兵、好媽媽式的教導員、性情直魯?shù)倪B長……其實這在《霓虹燈下的哨兵》中出現(xiàn)的時候大家還是覺得挺好的。但現(xiàn)在這種類型幾乎便成了定型,就讓人覺得有些東施效顰了。描寫青年的類型人物也有很多的重復,例如以往寫所謂的好青年,總不外是說話木訥、見了異姓就臉紅;如果寫女記者一定是風風火火、瘋瘋癲癲、敢愛敢恨……這樣的人物看多了,就讓人覺得中國的影視編劇沒有想象力,光會跟在別人的后面克隆。可見,真正的問題還不是反對人物類型化的問題,而是一個反對人物定型化的問題。其實,在中外很多的優(yōu)秀作品中,優(yōu)秀的類型人物不但不會被觀眾厭棄,反而會得到大家的喜愛。例如卓別林創(chuàng)造的那個象鴨子一樣走路的紳士流浪漢便是個極好的例子。這個小人物除了永恒的善良本性以外,最突出的性格特征就是永恒的尊嚴。無論情況多么艱難窘迫,也無論對手多么強大可怕,他總是拼命地保持著自己的紳士風度和尊嚴。俗話說“人窮志短”,可卓別林卻把它反了過來,去表現(xiàn)了一個可憐滑稽的小人物超越常理的尊嚴,就十分具有創(chuàng)造性和獨特的想象力了。因為卓別林是流浪漢出身,他一定知道在每一個受欺侮的靈魂深處都有一種深藏的渴望:保持住作人的尊嚴。他正是聰明地抓住了這一點。再如,在日本山田洋次的《男人辛苦》系列影片里也有個家喻戶曉的類型人物寅次郎。在日本,幾乎沒有不知道阿寅的。這個將眼睛瞇作一條縫的胖子性格格外的單純鮮明:他善良仗義多情卻又懶散而不拘小節(jié)。每天大大咧咧、無所事事,卻常常大言不慚。山田洋次真是個聰明人,他在這個人物性格上的類型化處理可是十分有學問的。在日本這個高度現(xiàn)代化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大多數(shù)日本人被西方人形容作每天只知道工作的“藍螞蟻”。給人的感覺是,大多數(shù)日本人中規(guī)中矩、一絲不茍、性格壓抑、不茍言笑、感情輕易不外露,例如一個日本人向你點頭說著“哈依”并不一定就表示他同意你的意見,你很難知道他的真實想法是什么。然而,在高度緊張的工作和生活節(jié)奏中,其實很多的日本人心里都有與現(xiàn)實相反的渴望。他們渴望著能沖出刻板的生活軌跡瀟灑隨意地生活,能夠忘記金錢而把情感看得比什么都重,能夠不注意上司或任何人的臉色而敞開地表達自己的任何情感……而這一切便恰恰是山田洋次賦予阿寅的。人們從阿寅身上看到了自己雖然期待已久、想做卻又不能做或不敢做的。這就難怪阿寅這人有這樣好的觀眾緣了!其實,就連在中國文學史上人人熟知的阿Q也是個類型化人物哩!這個性格極度夸張的角色之最突出的性格特征便是“精神勝利法”。我們實在是不能因為這個人物出自偉大的作家魯迅筆下就生生地將他歸結到圓整人物的圈子里去。說他是類型化的人物并不意味著否定他的深刻性。相反,正如大家所共識的那樣,在阿Q身上集中體現(xiàn)著中國人國民性中的典型特征。由此可見,一個真正為觀眾所喜愛的類型人物既不能是不費氣力就能得來的,也不能是克隆的結果。那必定是一次具有個性的創(chuàng)造,是對生活深切感悟的結果。類型人物應該是一種真正的典型,更具有社會生活的普遍性和性格的鮮明性。
淺談電視劇的人物布局
摘要:在影視劇中,人物是故事的主體。人物品質決定故事品性,人物布局就是故事布局。在創(chuàng)作中,人物布局應該考慮四個維度:一是人物的類型化設計;二是人物的主題性設計;三是人物的戲劇化設計;四是人物的功能性設計。由此,才能以精彩的人物布局創(chuàng)作出優(yōu)秀的電視劇作品。
關鍵詞:人物;類型化設計;主題性設計;戲劇化設計;功能性設計
故事是影視劇的主體。故事有兩個主要元素,一為人物,二為情境。情境即人物在具體事件中的處境,包括事件、人物關系及時空環(huán)境。根據(jù)故事中人物與事件之間的關系,電視劇故事有三種形態(tài),即以事件為主的大情節(jié)、以人物為主的小情節(jié)和兼顧人物與事件的中情節(jié)。無論故事形態(tài)怎樣,人物總是故事的核心,故事是靠人物和人物命運來吸引觀眾,人物的品質決定故事的品質。在題材故事確定后,電視劇創(chuàng)作通常是從人物設計開始的。如果說情節(jié)是故事的血肉,人物則是故事的骨架。骨架搭建好了,故事就有了自己的戲路,故事的發(fā)展也就順理成章。但如果人物設計有缺陷,故事也會有缺陷,故事的調整也總是從人物設計著手。本文將從類型、主題及故事的戲劇性和功能性等多個維度來論述電視劇人物布局的基本要求。
一、電視劇人物的類型化設計
電視劇也是按照產品類型來生產的。不同類型的電視劇面對不同的觀眾和不同的市場,也有著不同的敘事模式和不同的功能特征。編劇在進行劇本創(chuàng)作的時候,首先要思考的便是做什么類型的電視劇,然后根據(jù)題材故事的特征,按照預定類型的要求進行故事中的人物設計。不同類型的電視劇對人物有不同的要求。如表1所示,主旋律電視劇的主人公一般都是正面人物,偶像劇的人物一般都是俊男靚女,具有偶像身份和氣質,而勵志劇中的主人公一般都是小人物,且要讓他們歷經坎坷。悲劇中的主人公多為好人,好人遭受不應該有的毀滅或痛苦,才會引發(fā)共情。而喜劇中的主人公一般都是有缺點的人,但又不能是純粹的壞人,主人公身上的缺點往往會被夸張到有悖常理,達到可笑的地步。類似的題材,不同的人物設計,就會產生不同類型的電視劇。譬如電視劇《蟻族》和《蝸居》都寫的是外地年輕人在城市中的生活狀態(tài),《蟻族》寫的是以虎一帆為代表的年輕人追求愛情與夢想的故事,是一部典型的勵志劇,而《蝸居》中的郭海萍郭海藻姐妹在城市里的生存狀態(tài),她們并沒有通過個人的努力去追求幸福,從她們身上反映的是社會問題,所以它是一部社會問題劇。很多電視劇類型定位不明確,人物設計也不符合類型劇的要求,最終導致項目的失敗。電視劇《獵場》被定位為商戰(zhàn)劇,但商戰(zhàn)劇的主人公一般都為商界精英或企業(yè)老板,而鄭秋冬只是一個獵頭,他做的工作只是幫企業(yè)挖人,無法上到商界的層面。而且他事業(yè)上也不成功,最后也只是個小公司的小老板,沒有做出什么驚天動地的大事業(yè)。因而可以說這并不是一部勵志劇,鄭秋冬是個小人物,但他并沒有靠自己努力取得成功,他更像是個投機分子,為了賺錢,他先是做傳銷,后來又假借他人的身份坑蒙拐騙,他后來的成功也不是靠個人的努力,而是靠羅伊人的幫助。這也不是一部愛情劇,他與羅伊人以及熊青春及賈衣玫之間的所謂愛情既不美好也不純粹,這樣的愛情故事難以激起觀眾的興趣。當然,人物的類型化設計并不意味著人物設計的模式化和套路化,編劇不能墨守成規(guī)。人物的創(chuàng)新是類型創(chuàng)新的重要方面。了解電視劇類型化的特征正是為了在遵循基本創(chuàng)作規(guī)律的同時有所突破和創(chuàng)新。電視劇《暗算》是一部成功的諜戰(zhàn)劇。在以往的諜戰(zhàn)劇中,主人公都是大智大勇的英雄人物,而在這部電視劇中主人公阿炳是個傻子。另一個主人公黃依依則是數(shù)學天才,她破譯密碼不是為了祖國,而是為了拯救一個與她有私情的男人,這兩個人物的結局也是悲慘的,阿炳是自殺,黃依依也死得很卑微。這兩個人物都是以往諜戰(zhàn)劇中少有的人物形象,也是這部電視劇最有價值之所在。
二、電視劇人物的主題性設計
類型人物論
人們習慣于將藝術大家庭的成員稱作七姊妹,如果你問一些知識分子:“在‘七姊妹’中最粗俗的一位是誰?”他們中的很多人可能都會說:“電影。”確實,就藝術氣質而言,不管電影工作者多么不愿意承認,電影藝術在眾姐妹中確實存在著某種自卑感。同時從事過文學、戲劇和電影創(chuàng)作的老前輩夏衍在給北京電影學院的學生上課的時候,曾開宗明意地指出:“要記住,電影說到底是一種俗文化。”他的見解也許在很多人看來有些偏頗,但如果你考察一下電影的歷史和現(xiàn)狀就會覺得他說的確實有道理。作為嬰兒的電影降生的‘產房’是鎳幣影院。生活在最底層的勞工們辛苦一天之后帶著滿身的汗餿氣走進黑洞洞的倉庫,去看那廉價的、黑白光影顫抖的《工廠大門》。影院經營人在他們身邊來回走動著,將一個空罐頭盒伸到他們面前,他們便向里邊扔上幾個鎳幣,算作是電影票錢……看,電影的出身是多么貧寒,充其量不過是街頭把戲的地位。為了使電影成為一種能夠與文學、戲劇、舞蹈、音樂……這些高雅的姊妹等肩而立的藝術,很多電影工作者耗費了畢生的精力。愛森斯坦、伯格曼、雷諾阿、費里尼、安東尼奧尼……他們確實拍攝出了令知識分子不得不脫帽欣賞的作品。但是從數(shù)量上看,在百年來世界電影作品的海洋里,他們這些高雅之?魎嫉謀壤幟苡卸嗌倌兀靠梢運凳俏⒑跗湮ⅲ∧壓鐘⒐∷導液托∷道礪奐腋K固卦謁撓跋焓瀾緄拇笞鰲緞∷得婷婀邸防錚乇澩锪慫緣纈昂偷纈骯壑詰謀墑印K銜適掠肭榻諳啾齲罷呤且恢執(zhí)炙椎男問劍笳咴蚋哐諾枚唷R虼飼罷呤歉霸嫉難ň右叭撕拖執(zhí)牡纈骯壑凇笨吹摹D憧矗執(zhí)牡纈骯壑謨朐嫉難ň右叭絲醋魘且換厥鋁恕T儆校閭倒興刺致巰肪緇蛘咭衾只蛘呶璧桿悴凰鬩帳跽庋奈侍飴穡靠隙揮校蛭翹煬匾寰褪且?guī)歡樗孀諾纈俺沙さ惱齬蹋加腥嗽諤致邸暗纈笆且幻乓?guī)吗¢]庋奈侍狻V鋇?933年魯?shù)婪颍異垡驖h姆還在他的著作《電影作為藝術》中討論這個問題。
我常常考慮這是為什么?為什么電影藝術在人們眼睛里就會比其它的藝術姊妹要低俗?是電影工作者的水平低于從事其它藝術的人們?恐怕還不能作出這樣簡單的結論。有一點可以肯定:這與電影藝術的特性有關,正是這樣的特性在很大的程度上使電影藝術成為夏衍說的“俗文化”的。
眾所周知,小說是一種文字藝術。它作用于人們的第二信號系統(tǒng),借助于讀者的生活經驗和想象力完成其藝術欣賞過程。盡管小說無法展現(xiàn)作用于第一信號系統(tǒng)的視覺場面,(即便是《老人與海》這樣的小說,我們也很難真正體驗到大海的視覺奇觀。)可是,觀眾的參與和想象活動是藝術審美的生命,小說擁有了這樣的特性便成為了一種高雅的文化產品。在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中,不僅人物命運能得到充分的展現(xiàn),而且人物豐富復雜得難以言狀的內心世界也能得到淋漓盡致的揭示。《奧勃洛莫夫》中的奧勃洛莫夫在床上一動不動地躺著,作者就能把他的豐富的內心活動展示給我們。也許,只有小說有這樣的魅力:一部小說的情節(jié)或細節(jié)描寫已經隨著時間的流逝被讀者淡忘了,然而那小說中眾多的成功塑造的人物卻在讀者心中長存甚至伴隨他們一生。我們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文字有利于塑造復雜的人物個性和千變萬化的內心世界。在小說之林里,即便是象西德尼.謝爾頓或瓊瑤這樣的通俗小說作家,也依然必須在人物個性的塑造上下一定的功夫。
再看戲劇。由于戲劇的空間表現(xiàn)的顯而易見的局限性,導致它不可能依靠視覺手段。因此戲劇的真正武器是對話。戲劇家們運用對話來展開情節(jié)和沖突,揭示人物關系和性格。如果對話過于膚淺,流于生活的表面,如果我們通過對話看不到人物心靈和性格中那些隱秘的層次,戲劇就會變成毫無戲劇性可言的淺薄的東西。所以,戲劇沒有選擇,既然它不能用視覺的奇觀來嘩眾取寵,就只能靠對人性深刻的揭示來將觀眾吸引到劇場里來。正因如此,戲劇便獲得了高雅的屬性。無論是莎士比亞或是易卜生,無論是斯特林堡還是奧尼爾,戲劇大師們所追求的永遠是性格的豐富性和對心靈的隱秘的揭示。正是戲劇的短處成就了戲劇的高雅。戲劇也羨慕過電影的通俗性所帶來的金錢,也有人希望能創(chuàng)作出類似于警匪片、驚險片或恐怖片這樣一些戲劇樣式。但如您之所見,到現(xiàn)在我們也沒看見有什么“警匪戲劇”、“恐怖戲劇”或“驚險戲劇”形成氣候。娘胎里生就的高雅何須作東施效顰呢?
可是電影呢?電影擁有無與倫比的時空表現(xiàn)力,它可以表現(xiàn)高山大海和千軍萬馬的古戰(zhàn)場,可以展現(xiàn)星際大戰(zhàn)和史前生物的肉搏。它擁有任何其它姊妹藝術所沒有的視聽武器。得天獨厚的能力對人是不是有絕對的好處呢?比如一個長得十分漂亮的女孩兒,也許就因為她比別人漂亮便無需作更多的努力即能取悅于人。電影藝術的“天生麗質”正是這樣地使它無需在人物塑造方面苦下功夫就能取悅于觀眾。它可以將冰海沉船、彗星撞擊地球、龍卷風和大白鯊……所有人類能夠想象到的驚心動魄場面都展現(xiàn)給觀眾,并且只靠了這些視覺的奇觀本身便可以將觀眾在兩個小時左右的時間里牢牢地吸引在影院的座位上。人物性格的塑造便成了可有可無的事情,更遑論性格的深度。稍有文化修養(yǎng)的人就能分辨出一部莎士比亞劇本與《泰坦尼克號》影片中人物塑造的高下,恐怕只有白癡才會把兩者放在一個天平上衡量。好萊塢那些高成本的大片中的人物性格的落套和淺俗幾乎成為那種影片的標致。不知是不是會有誰將一部影片在票房上的成功與該影片的文化品味看作是一回事兒?如果有,那一定是利用電影賺到了錢的人或渴望賺到錢的人,千萬不能相信他的話。電影也有佳作,在佳作里也有膾炙人口的人物性格,但你會發(fā)現(xiàn)那常常就是借助了對小說或戲劇作品的改編,電影編劇的原創(chuàng)人物寥寥無幾。而且您還會發(fā)現(xiàn),改變自小說和戲劇作品的電影作品,盡管有著比原作更廣泛的觀眾面,但看過原著的人往往會抱怨這些改編實在是糟改原著,至少失去了原著的深刻性和人生品味,充其量不過是原著的贗品。
在這里,也許應該為電影藝術說上兩句公道話。我們無權要求任何門類的藝術都必須達到同樣的人文深度。要求一部恐怖片也要深刻如契柯夫的《海鷗》顯然是滑稽可笑的。畢竟在這個世界上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把深刻作為自己的審美目標的。恐怖片就象我們坐翻滾過山車,一時的刺激便帶來了值得花錢的愉悅。以往我們總是要求電影藝術的任何樣式都要追求人物性格的豐富立體性其實是根本錯誤的。在商業(yè)樣式的影片中,我們根本無法做到也根本不必追求人物性格的復雜性。即如美國影片《生死時速》,在創(chuàng)作這樣的影片的時候,編劇最需要下功夫的是講好一個具有驚心動魄場面和讓人透不過氣來的故事,而導演的任務就是把文字提供的視覺奇觀設計圖逼真地展現(xiàn)在銀幕上。人物的類型化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這些電影樣式商業(yè)成功的因素之一。就象麥當勞的策略一樣,如果它的漢堡包和辣雞翅不作定型化的生產,就不會有那樣多的贏利。因為它必須用一種模式化的生產來培養(yǎng)人們固定的口味。最明顯的例子便是美國的西部片,其中的人物都是固定不變的類型,那些無法無天的牛仔、那些孤單闖入敵陣的英雄、那些野辣辣但善良的妓女……所有這些就象定型生產的漢堡包,早已經培養(yǎng)起了一大批觀眾的口味,所以至今仍然保持著西部片的常盛不衰的觀眾群。香港的功夫片得到了西部片經營之妙吷,于是也成為中國唯一能夠殺向好萊塢的電影樣式。人物性格的復雜和立體,人物內心生活的深層結構,這些都必然會帶來作品在主題思想上的艱深和多意,這也許從來就不是把票房看作生命的那些電影投資者的意愿。我認為好萊塢為代表的商業(yè)電影是很值得今天的中國電影人研究的文化現(xiàn)象。一天,有個電視臺的記者問我:“您認為張藝謀和馮小剛誰更棒?”我反問他道:“你認為跳高的朱建華和打乒乓球的鄧亞萍誰更棒?”我認為他們都不錯。不能在商業(yè)喜劇如《不見不散》這樣的作品上苛責馮小剛塑造的人物膚淺,這就好象我們不能聽了相聲抱怨它太不莊重一樣。我們應該看到他的機智和幽默和敘事節(jié)奏的流暢。今天中國大部分的商業(yè)片不是太不深刻的問題,而是太不懂商業(yè)規(guī)律太缺乏商業(yè)想象力的問題,甚至是一個如何創(chuàng)作好類型人物的問題。
人物類型管理論文
人們習慣于將藝術大家庭的成員稱作七姊妹,如果你問一些知識分子:“在‘七姊妹’中最粗俗的一位是誰?”他們中的很多人可能都會說:“電影。”確實,就藝術氣質而言,不管電影工作者多么不愿意承認,電影藝術在眾姐妹中確實存在著某種自卑感。同時從事過文學、戲劇和電影創(chuàng)作的老前輩夏衍在給北京電影學院的學生上課的時候,曾開宗明意地指出:“要記住,電影說到底是一種俗文化。”他的見解也許在很多人看來有些偏頗,但如果你考察一下電影的歷史和現(xiàn)狀就會覺得他說的確實有道理。作為嬰兒的電影降生的‘產房’是鎳幣影院。生活在最底層的勞工們辛苦一天之后帶著滿身的汗餿氣走進黑洞洞的倉庫,去看那廉價的、黑白光影顫抖的《工廠大門》。影院經營人在他們身邊來回走動著,將一個空罐頭盒伸到他們面前,他們便向里邊扔上幾個鎳幣,算作是電影票錢……看,電影的出身是多么貧寒,充其量不過是街頭把戲的地位。為了使電影成為一種能夠與文學、戲劇、舞蹈、音樂……這些高雅的姊妹等肩而立的藝術,很多電影工作者耗費了畢生的精力。愛森斯坦、伯格曼、雷諾阿、費里尼、安東尼奧尼……他們確實拍攝出了令知識分子不得不脫帽欣賞的作品。但是從數(shù)量上看,在百年來世界電影作品的海洋里,他們這些高雅之作所占的比例又能有多少呢?可以說是微乎其微!難怪英國小說家和小說理論家福斯特在他的影響世界的大作《小說面面觀》里,公開地表達了他對電影和電影觀眾的鄙視。他認為故事與情節(jié)相比,前者是一種粗俗的形式,后者則高雅得多。因此前者是給“原始的穴居野人和現(xiàn)代的電影觀眾”看的。你看,他將現(xiàn)代的電影觀眾與原始的穴居野人看作是一回事了。再有,你聽說過有誰來討論戲劇或者音樂或者舞蹈算不算藝術這樣的問題嗎?肯定沒有,因為它們天經地義就是藝術。然而伴隨著電影成長的整個過程,都有人在討論“電影是一門藝術嗎”這樣的問題。直到1933年魯?shù)婪颍異垡驖h姆還在他的著作《電影作為藝術》中討論這個問題。
我常常考慮這是為什么?為什么電影藝術在人們眼睛里就會比其它的藝術姊妹要低俗?是電影工作者的水平低于從事其它藝術的人們?恐怕還不能作出這樣簡單的結論。有一點可以肯定:這與電影藝術的特性有關,正是這樣的特性在很大的程度上使電影藝術成為夏衍說的“俗文化”的。
眾所周知,小說是一種文字藝術。它作用于人們的第二信號系統(tǒng),借助于讀者的生活經驗和想象力完成其藝術欣賞過程。盡管小說無法展現(xiàn)作用于第一信號系統(tǒng)的視覺場面,(即便是《老人與海》這樣的小說,我們也很難真正體驗到大海的視覺奇觀。)可是,觀眾的參與和想象活動是藝術審美的生命,小說擁有了這樣的特性便成為了一種高雅的文化產品。在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中,不僅人物命運能得到充分的展現(xiàn),而且人物豐富復雜得難以言狀的內心世界也能得到淋漓盡致的揭示。《奧勃洛莫夫》中的奧勃洛莫夫在床上一動不動地躺著,作者就能把他的豐富的內心活動展示給我們。也許,只有小說有這樣的魅力:一部小說的情節(jié)或細節(jié)描寫已經隨著時間的流逝被讀者淡忘了,然而那小說中眾多的成功塑造的人物卻在讀者心中長存甚至伴隨他們一生。我們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文字有利于塑造復雜的人物個性和千變萬化的內心世界。在小說之林里,即便是象西德尼.謝爾頓或瓊瑤這樣的通俗小說作家,也依然必須在人物個性的塑造上下一定的功夫。
再看戲劇。由于戲劇的空間表現(xiàn)的顯而易見的局限性,導致它不可能依靠視覺手段。因此戲劇的真正武器是對話。戲劇家們運用對話來展開情節(jié)和沖突,揭示人物關系和性格。如果對話過于膚淺,流于生活的表面,如果我們通過對話看不到人物心靈和性格中那些隱秘的層次,戲劇就會變成毫無戲劇性可言的淺薄的東西。所以,戲劇沒有選擇,既然它不能用視覺的奇觀來嘩眾取寵,就只能靠對人性深刻的揭示來將觀眾吸引到劇場里來。正因如此,戲劇便獲得了高雅的屬性。無論是莎士比亞或是易卜生,無論是斯特林堡還是奧尼爾,戲劇大師們所追求的永遠是性格的豐富性和對心靈的隱秘的揭示。正是戲劇的短處成就了戲劇的高雅。戲劇也羨慕過電影的通俗性所帶來的金錢,也有人希望能創(chuàng)作出類似于警匪片、驚險片或恐怖片這樣一些戲劇樣式。但如您之所見,到現(xiàn)在我們也沒看見有什么“警匪戲劇”、“恐怖戲劇”或“驚險戲劇”形成氣候。娘胎里生就的高雅何須作東施效顰呢?
可是電影呢?電影擁有無與倫比的時空表現(xiàn)力,它可以表現(xiàn)高山大海和千軍萬馬的古戰(zhàn)場,可以展現(xiàn)星際大戰(zhàn)和史前生物的肉搏。它擁有任何其它姊妹藝術所沒有的視聽武器。得天獨厚的能力對人是不是有絕對的好處呢?比如一個長得十分漂亮的女孩兒,也許就因為她比別人漂亮便無需作更多的努力即能取悅于人。電影藝術的“天生麗質”正是這樣地使它無需在人物塑造方面苦下功夫就能取悅于觀眾。它可以將冰海沉船、彗星撞擊地球、龍卷風和大白鯊……所有人類能夠想象到的驚心動魄場面都展現(xiàn)給觀眾,并且只靠了這些視覺的奇觀本身便可以將觀眾在兩個小時左右的時間里牢牢地吸引在影院的座位上。人物性格的塑造便成了可有可無的事情,更遑論性格的深度。稍有文化修養(yǎng)的人就能分辨出一部莎士比亞劇本與《泰坦尼克號》影片中人物塑造的高下,恐怕只有白癡才會把兩者放在一個天平上衡量。好萊塢那些高成本的大片中的人物性格的落套和淺俗幾乎成為那種影片的標致。不知是不是會有誰將一部影片在票房上的成功與該影片的文化品味看作是一回事兒?如果有,那一定是利用電影賺到了錢的人或渴望賺到錢的人,千萬不能相信他的話。電影也有佳作,在佳作里也有膾炙人口的人物性格,但你會發(fā)現(xiàn)那常常就是借助了對小說或戲劇作品的改編,電影編劇的原創(chuàng)人物寥寥無幾。而且您還會發(fā)現(xiàn),改變自小說和戲劇作品的電影作品,盡管有著比原作更廣泛的觀眾面,但看過原著的人往往會抱怨這些改編實在是糟改原著,至少失去了原著的深刻性和人生品味,充其量不過是原著的贗品。
在這里,也許應該為電影藝術說上兩句公道話。我們無權要求任何門類的藝術都必須達到同樣的人文深度。要求一部恐怖片也要深刻如契柯夫的《海鷗》顯然是滑稽可笑的。畢竟在這個世界上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把深刻作為自己的審美目標的。恐怖片就象我們坐翻滾過山車,一時的刺激便帶來了值得花錢的愉悅。以往我們總是要求電影藝術的任何樣式都要追求人物性格的豐富立體性其實是根本錯誤的。在商業(yè)樣式的影片中,我們根本無法做到也根本不必追求人物性格的復雜性。即如美國影片《生死時速》,在創(chuàng)作這樣的影片的時候,編劇最需要下功夫的是講好一個具有驚心動魄場面和讓人透不過氣來的故事,而導演的任務就是把文字提供的視覺奇觀設計圖逼真地展現(xiàn)在銀幕上。人物的類型化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這些電影樣式商業(yè)成功的因素之一。就象麥當勞的策略一樣,如果它的漢堡包和辣雞翅不作定型化的生產,就不會有那樣多的贏利。因為它必須用一種模式化的生產來培養(yǎng)人們固定的口味。最明顯的例子便是美國的西部片,其中的人物都是固定不變的類型,那些無法無天的牛仔、那些孤單闖入敵陣的英雄、那些野辣辣但善良的妓女……所有這些就象定型生產的漢堡包,早已經培養(yǎng)起了一大批觀眾的口味,所以至今仍然保持著西部片的常盛不衰的觀眾群。香港的功夫片得到了西部片經營之妙吷,于是也成為中國唯一能夠殺向好萊塢的電影樣式。人物性格的復雜和立體,人物內心生活的深層結構,這些都必然會帶來作品在主題思想上的艱深和多意,這也許從來就不是把票房看作生命的那些電影投資者的意愿。我認為好萊塢為代表的商業(yè)電影是很值得今天的中國電影人研究的文化現(xiàn)象。一天,有個電視臺的記者問我:“您認為張藝謀和馮小剛誰更棒?”我反問他道:“你認為跳高的朱建華和打乒乓球的鄧亞萍誰更棒?”我認為他們都不錯。不能在商業(yè)喜劇如《不見不散》這樣的作品上苛責馮小剛塑造的人物膚淺,這就好象我們不能聽了相聲抱怨它太不莊重一樣。我們應該看到他的機智和幽默和敘事節(jié)奏的流暢。今天中國大部分的商業(yè)片不是太不深刻的問題,而是太不懂商業(yè)規(guī)律太缺乏商業(yè)想象力的問題,甚至是一個如何創(chuàng)作好類型人物的問題。
類型人物論
人們習慣于將藝術大家庭的成員稱作七姊妹,如果你問一些知識分子:“在‘七姊妹’中最粗俗的一位是誰?”他們中的很多人可能都會說:“電影。”確實,就藝術氣質而言,不管電影工作者多么不愿意承認,電影藝術在眾姐妹中確實存在著某種自卑感。同時從事過文學、戲劇和電影創(chuàng)作的老前輩夏衍在給北京電影學院的學生上課的時候,曾開宗明意地指出:“要記住,電影說到底是一種俗文化。”他的見解也許在很多人看來有些偏頗,但如果你考察一下電影的歷史和現(xiàn)狀就會覺得他說的確實有道理。作為嬰兒的電影降生的‘產房’是鎳幣影院。生活在最底層的勞工們辛苦一天之后帶著滿身的汗餿氣走進黑洞洞的倉庫,去看那廉價的、黑白光影顫抖的《工廠大門》。影院經營人在他們身邊來回走動著,將一個空罐頭盒伸到他們面前,他們便向里邊扔上幾個鎳幣,算作是電影票錢……看,電影的出身是多么貧寒,充其量不過是街頭把戲的地位。為了使電影成為一種能夠與文學、戲劇、舞蹈、音樂……這些高雅的姊妹等肩而立的藝術,很多電影工作者耗費了畢生的精力。愛森斯坦、伯格曼、雷諾阿、費里尼、安東尼奧尼……他們確實拍攝出了令知識分子不得不脫帽欣賞的作品。但是從數(shù)量上看,在百年來世界電影作品的海洋里,他們這些高雅之?魎嫉謀壤幟苡卸嗌倌兀靠梢運凳俏⒑跗湮ⅲ∧壓鐘⒐∷導液托∷道礪奐腋K固卦謁撓跋焓瀾緄拇笞鰲緞∷得婷婀邸防錚乇澩锪慫緣纈昂偷纈骯壑詰謀墑印K銜適掠肭榻諳啾齲罷呤且恢執(zhí)炙椎男問劍笳咴蚋哐諾枚唷R虼飼罷呤歉霸嫉難ň右叭撕拖執(zhí)牡纈骯壑凇笨吹摹D憧矗執(zhí)牡纈骯壑謨朐嫉難ň右叭絲醋魘且換厥鋁恕T儆校閭倒興刺致巰肪緇蛘咭衾只蛘呶璧桿悴凰鬩帳跽庋奈侍飴穡靠隙揮校蛭翹煬匾寰褪且?guī)歡樗孀諾纈俺沙さ惱齬蹋加腥嗽諤致邸暗纈笆且幻乓?guī)吗¢]庋奈侍狻V鋇?933年魯?shù)婪颍異垡驖h姆還在他的著作《電影作為藝術》中討論這個問題。
我常常考慮這是為什么?為什么電影藝術在人們眼睛里就會比其它的藝術姊妹要低俗?是電影工作者的水平低于從事其它藝術的人們?恐怕還不能作出這樣簡單的結論。有一點可以肯定:這與電影藝術的特性有關,正是這樣的特性在很大的程度上使電影藝術成為夏衍說的“俗文化”的。
眾所周知,小說是一種文字藝術。它作用于人們的第二信號系統(tǒng),借助于讀者的生活經驗和想象力完成其藝術欣賞過程。盡管小說無法展現(xiàn)作用于第一信號系統(tǒng)的視覺場面,(即便是《老人與海》這樣的小說,我們也很難真正體驗到大海的視覺奇觀。)可是,觀眾的參與和想象活動是藝術審美的生命,小說擁有了這樣的特性便成為了一種高雅的文化產品。在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中,不僅人物命運能得到充分的展現(xiàn),而且人物豐富復雜得難以言狀的內心世界也能得到淋漓盡致的揭示。《奧勃洛莫夫》中的奧勃洛莫夫在床上一動不動地躺著,作者就能把他的豐富的內心活動展示給我們。也許,只有小說有這樣的魅力:一部小說的情節(jié)或細節(jié)描寫已經隨著時間的流逝被讀者淡忘了,然而那小說中眾多的成功塑造的人物卻在讀者心中長存甚至伴隨他們一生。我們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文字有利于塑造復雜的人物個性和千變萬化的內心世界。在小說之林里,即便是象西德尼.謝爾頓或瓊瑤這樣的通俗小說作家,也依然必須在人物個性的塑造上下一定的功夫。
再看戲劇。由于戲劇的空間表現(xiàn)的顯而易見的局限性,導致它不可能依靠視覺手段。因此戲劇的真正武器是對話。戲劇家們運用對話來展開情節(jié)和沖突,揭示人物關系和性格。如果對話過于膚淺,流于生活的表面,如果我們通過對話看不到人物心靈和性格中那些隱秘的層次,戲劇就會變成毫無戲劇性可言的淺薄的東西。所以,戲劇沒有選擇,既然它不能用視覺的奇觀來嘩眾取寵,就只能靠對人性深刻的揭示來將觀眾吸引到劇場里來。正因如此,戲劇便獲得了高雅的屬性。無論是莎士比亞或是易卜生,無論是斯特林堡還是奧尼爾,戲劇大師們所追求的永遠是性格的豐富性和對心靈的隱秘的揭示。正是戲劇的短處成就了戲劇的高雅。戲劇也羨慕過電影的通俗性所帶來的金錢,也有人希望能創(chuàng)作出類似于警匪片、驚險片或恐怖片這樣一些戲劇樣式。但如您之所見,到現(xiàn)在我們也沒看見有什么“警匪戲劇”、“恐怖戲劇”或“驚險戲劇”形成氣候。娘胎里生就的高雅何須作東施效顰呢?
可是電影呢?電影擁有無與倫比的時空表現(xiàn)力,它可以表現(xiàn)高山大海和千軍萬馬的古戰(zhàn)場,可以展現(xiàn)星際大戰(zhàn)和史前生物的肉搏。它擁有任何其它姊妹藝術所沒有的視聽武器。得天獨厚的能力對人是不是有絕對的好處呢?比如一個長得十分漂亮的女孩兒,也許就因為她比別人漂亮便無需作更多的努力即能取悅于人。電影藝術的“天生麗質”正是這樣地使它無需在人物塑造方面苦下功夫就能取悅于觀眾。它可以將冰海沉船、彗星撞擊地球、龍卷風和大白鯊……所有人類能夠想象到的驚心動魄場面都展現(xiàn)給觀眾,并且只靠了這些視覺的奇觀本身便可以將觀眾在兩個小時左右的時間里牢牢地吸引在影院的座位上。人物性格的塑造便成了可有可無的事情,更遑論性格的深度。稍有文化修養(yǎng)的人就能分辨出一部莎士比亞劇本與《泰坦尼克號》影片中人物塑造的高下,恐怕只有白癡才會把兩者放在一個天平上衡量。好萊塢那些高成本的大片中的人物性格的落套和淺俗幾乎成為那種影片的標致。不知是不是會有誰將一部影片在票房上的成功與該影片的文化品味看作是一回事兒?如果有,那一定是利用電影賺到了錢的人或渴望賺到錢的人,千萬不能相信他的話。電影也有佳作,在佳作里也有膾炙人口的人物性格,但你會發(fā)現(xiàn)那常常就是借助了對小說或戲劇作品的改編,電影編劇的原創(chuàng)人物寥寥無幾。而且您還會發(fā)現(xiàn),改變自小說和戲劇作品的電影作品,盡管有著比原作更廣泛的觀眾面,但看過原著的人往往會抱怨這些改編實在是糟改原著,至少失去了原著的深刻性和人生品味,充其量不過是原著的贗品。
在這里,也許應該為電影藝術說上兩句公道話。我們無權要求任何門類的藝術都必須達到同樣的人文深度。要求一部恐怖片也要深刻如契柯夫的《海鷗》顯然是滑稽可笑的。畢竟在這個世界上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把深刻作為自己的審美目標的。恐怖片就象我們坐翻滾過山車,一時的刺激便帶來了值得花錢的愉悅。以往我們總是要求電影藝術的任何樣式都要追求人物性格的豐富立體性其實是根本錯誤的。在商業(yè)樣式的影片中,我們根本無法做到也根本不必追求人物性格的復雜性。即如美國影片《生死時速》,在創(chuàng)作這樣的影片的時候,編劇最需要下功夫的是講好一個具有驚心動魄場面和讓人透不過氣來的故事,而導演的任務就是把文字提供的視覺奇觀設計圖逼真地展現(xiàn)在銀幕上。人物的類型化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這些電影樣式商業(yè)成功的因素之一。就象麥當勞的策略一樣,如果它的漢堡包和辣雞翅不作定型化的生產,就不會有那樣多的贏利。因為它必須用一種模式化的生產來培養(yǎng)人們固定的口味。最明顯的例子便是美國的西部片,其中的人物都是固定不變的類型,那些無法無天的牛仔、那些孤單闖入敵陣的英雄、那些野辣辣但善良的妓女……所有這些就象定型生產的漢堡包,早已經培養(yǎng)起了一大批觀眾的口味,所以至今仍然保持著西部片的常盛不衰的觀眾群。香港的功夫片得到了西部片經營之妙吷,于是也成為中國唯一能夠殺向好萊塢的電影樣式。人物性格的復雜和立體,人物內心生活的深層結構,這些都必然會帶來作品在主題思想上的艱深和多意,這也許從來就不是把票房看作生命的那些電影投資者的意愿。我認為好萊塢為代表的商業(yè)電影是很值得今天的中國電影人研究的文化現(xiàn)象。一天,有個電視臺的記者問我:“您認為張藝謀和馮小剛誰更棒?”我反問他道:“你認為跳高的朱建華和打乒乓球的鄧亞萍誰更棒?”我認為他們都不錯。不能在商業(yè)喜劇如《不見不散》這樣的作品上苛責馮小剛塑造的人物膚淺,這就好象我們不能聽了相聲抱怨它太不莊重一樣。我們應該看到他的機智和幽默和敘事節(jié)奏的流暢。今天中國大部分的商業(yè)片不是太不深刻的問題,而是太不懂商業(yè)規(guī)律太缺乏商業(yè)想象力的問題,甚至是一個如何創(chuàng)作好類型人物的問題。
類型人物論
人們習慣于將藝術大家庭的成員稱作七姊妹,如果你問一些知識分子:“在‘七姊妹’中最粗俗的一位是誰?”他們中的很多人可能都會說:“電影。”確實,就藝術氣質而言,不管電影工作者多么不愿意承認,電影藝術在眾姐妹中確實存在著某種自卑感。同時從事過文學、戲劇和電影創(chuàng)作的老前輩夏衍在給北京電影學院的學生上課的時候,曾開宗明意地指出:“要記住,電影說到底是一種俗文化。”他的見解也許在很多人看來有些偏頗,但如果你考察一下電影的歷史和現(xiàn)狀就會覺得他說的確實有道理。作為嬰兒的電影降生的‘產房’是鎳幣影院。生活在最底層的勞工們辛苦一天之后帶著滿身的汗餿氣走進黑洞洞的倉庫,去看那廉價的、黑白光影顫抖的《工廠大門》。影院經營人在他們身邊來回走動著,將一個空罐頭盒伸到他們面前,他們便向里邊扔上幾個鎳幣,算作是電影票錢……看,電影的出身是多么貧寒,充其量不過是街頭把戲的地位。為了使電影成為一種能夠與文學、戲劇、舞蹈、音樂……這些高雅的姊妹等肩而立的藝術,很多電影工作者耗費了畢生的精力。愛森斯坦、伯格曼、雷諾阿、費里尼、安東尼奧尼……他們確實拍攝出了令知識分子不得不脫帽欣賞的作品。但是從數(shù)量上看,在百年來世界電影作品的海洋里,他們這些高雅之?魎嫉謀壤幟苡卸嗌倌兀靠梢運凳俏⒑跗湮ⅲ∧壓鐘⒐∷導液托∷道礪奐腋K固卦謁撓跋焓瀾緄拇笞鰲緞∷得婷婀邸防錚乇澩锪慫緣纈昂偷纈骯壑詰謀墑印K銜適掠肭榻諳啾齲罷呤且恢執(zhí)炙椎男問劍笳咴蚋哐諾枚唷R虼飼罷呤歉霸嫉難ň右叭撕拖執(zhí)牡纈骯壑凇笨吹摹D憧矗執(zhí)牡纈骯壑謨朐嫉難ň右叭絲醋魘且換厥鋁恕T儆校閭倒興刺致巰肪緇蛘咭衾只蛘呶璧桿悴凰鬩帳跽庋奈侍飴穡靠隙揮校蛭翹煬匾寰褪且?guī)歡樗孀諾纈俺沙さ惱齬蹋加腥嗽諤致邸暗纈笆且幻乓?guī)吗¢]庋奈侍狻V鋇?933年魯?shù)婪颍異垡驖h姆還在他的著作《電影作為藝術》中討論這個問題。
我常常考慮這是為什么?為什么電影藝術在人們眼睛里就會比其它的藝術姊妹要低俗?是電影工作者的水平低于從事其它藝術的人們?恐怕還不能作出這樣簡單的結論。有一點可以肯定:這與電影藝術的特性有關,正是這樣的特性在很大的程度上使電影藝術成為夏衍說的“俗文化”的。
眾所周知,小說是一種文字藝術。它作用于人們的第二信號系統(tǒng),借助于讀者的生活經驗和想象力完成其藝術欣賞過程。盡管小說無法展現(xiàn)作用于第一信號系統(tǒng)的視覺場面,(即便是《老人與海》這樣的小說,我們也很難真正體驗到大海的視覺奇觀。)可是,觀眾的參與和想象活動是藝術審美的生命,小說擁有了這樣的特性便成為了一種高雅的文化產品。在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中,不僅人物命運能得到充分的展現(xiàn),而且人物豐富復雜得難以言狀的內心世界也能得到淋漓盡致的揭示。《奧勃洛莫夫》中的奧勃洛莫夫在床上一動不動地躺著,作者就能把他的豐富的內心活動展示給我們。也許,只有小說有這樣的魅力:一部小說的情節(jié)或細節(jié)描寫已經隨著時間的流逝被讀者淡忘了,然而那小說中眾多的成功塑造的人物卻在讀者心中長存甚至伴隨他們一生。我們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文字有利于塑造復雜的人物個性和千變萬化的內心世界。在小說之林里,即便是象西德尼.謝爾頓或瓊瑤這樣的通俗小說作家,也依然必須在人物個性的塑造上下一定的功夫。
再看戲劇。由于戲劇的空間表現(xiàn)的顯而易見的局限性,導致它不可能依靠視覺手段。因此戲劇的真正武器是對話。戲劇家們運用對話來展開情節(jié)和沖突,揭示人物關系和性格。如果對話過于膚淺,流于生活的表面,如果我們通過對話看不到人物心靈和性格中那些隱秘的層次,戲劇就會變成毫無戲劇性可言的淺薄的東西。所以,戲劇沒有選擇,既然它不能用視覺的奇觀來嘩眾取寵,就只能靠對人性深刻的揭示來將觀眾吸引到劇場里來。正因如此,戲劇便獲得了高雅的屬性。無論是莎士比亞或是易卜生,無論是斯特林堡還是奧尼爾,戲劇大師們所追求的永遠是性格的豐富性和對心靈的隱秘的揭示。正是戲劇的短處成就了戲劇的高雅。戲劇也羨慕過電影的通俗性所帶來的金錢,也有人希望能創(chuàng)作出類似于警匪片、驚險片或恐怖片這樣一些戲劇樣式。但如您之所見,到現(xiàn)在我們也沒看見有什么“警匪戲劇”、“恐怖戲劇”或“驚險戲劇”形成氣候。娘胎里生就的高雅何須作東施效顰呢?
可是電影呢?電影擁有無與倫比的時空表現(xiàn)力,它可以表現(xiàn)高山大海和千軍萬馬的古戰(zhàn)場,可以展現(xiàn)星際大戰(zhàn)和史前生物的肉搏。它擁有任何其它姊妹藝術所沒有的視聽武器。得天獨厚的能力對人是不是有絕對的好處呢?比如一個長得十分漂亮的女孩兒,也許就因為她比別人漂亮便無需作更多的努力即能取悅于人。電影藝術的“天生麗質”正是這樣地使它無需在人物塑造方面苦下功夫就能取悅于觀眾。它可以將冰海沉船、彗星撞擊地球、龍卷風和大白鯊……所有人類能夠想象到的驚心動魄場面都展現(xiàn)給觀眾,并且只靠了這些視覺的奇觀本身便可以將觀眾在兩個小時左右的時間里牢牢地吸引在影院的座位上。人物性格的塑造便成了可有可無的事情,更遑論性格的深度。稍有文化修養(yǎng)的人就能分辨出一部莎士比亞劇本與《泰坦尼克號》影片中人物塑造的高下,恐怕只有白癡才會把兩者放在一個天平上衡量。好萊塢那些高成本的大片中的人物性格的落套和淺俗幾乎成為那種影片的標致。不知是不是會有誰將一部影片在票房上的成功與該影片的文化品味看作是一回事兒?如果有,那一定是利用電影賺到了錢的人或渴望賺到錢的人,千萬不能相信他的話。電影也有佳作,在佳作里也有膾炙人口的人物性格,但你會發(fā)現(xiàn)那常常就是借助了對小說或戲劇作品的改編,電影編劇的原創(chuàng)人物寥寥無幾。而且您還會發(fā)現(xiàn),改變自小說和戲劇作品的電影作品,盡管有著比原作更廣泛的觀眾面,但看過原著的人往往會抱怨這些改編實在是糟改原著,至少失去了原著的深刻性和人生品味,充其量不過是原著的贗品。
在這里,也許應該為電影藝術說上兩句公道話。我們無權要求任何門類的藝術都必須達到同樣的人文深度。要求一部恐怖片也要深刻如契柯夫的《海鷗》顯然是滑稽可笑的。畢竟在這個世界上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把深刻作為自己的審美目標的。恐怖片就象我們坐翻滾過山車,一時的刺激便帶來了值得花錢的愉悅。以往我們總是要求電影藝術的任何樣式都要追求人物性格的豐富立體性其實是根本錯誤的。在商業(yè)樣式的影片中,我們根本無法做到也根本不必追求人物性格的復雜性。即如美國影片《生死時速》,在創(chuàng)作這樣的影片的時候,編劇最需要下功夫的是講好一個具有驚心動魄場面和讓人透不過氣來的故事,而導演的任務就是把文字提供的視覺奇觀設計圖逼真地展現(xiàn)在銀幕上。人物的類型化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這些電影樣式商業(yè)成功的因素之一。就象麥當勞的策略一樣,如果它的漢堡包和辣雞翅不作定型化的生產,就不會有那樣多的贏利。因為它必須用一種模式化的生產來培養(yǎng)人們固定的口味。最明顯的例子便是美國的西部片,其中的人物都是固定不變的類型,那些無法無天的牛仔、那些孤單闖入敵陣的英雄、那些野辣辣但善良的妓女……所有這些就象定型生產的漢堡包,早已經培養(yǎng)起了一大批觀眾的口味,所以至今仍然保持著西部片的常盛不衰的觀眾群。香港的功夫片得到了西部片經營之妙吷,于是也成為中國唯一能夠殺向好萊塢的電影樣式。人物性格的復雜和立體,人物內心生活的深層結構,這些都必然會帶來作品在主題思想上的艱深和多意,這也許從來就不是把票房看作生命的那些電影投資者的意愿。我認為好萊塢為代表的商業(yè)電影是很值得今天的中國電影人研究的文化現(xiàn)象。一天,有個電視臺的記者問我:“您認為張藝謀和馮小剛誰更棒?”我反問他道:“你認為跳高的朱建華和打乒乓球的鄧亞萍誰更棒?”我認為他們都不錯。不能在商業(yè)喜劇如《不見不散》這樣的作品上苛責馮小剛塑造的人物膚淺,這就好象我們不能聽了相聲抱怨它太不莊重一樣。我們應該看到他的機智和幽默和敘事節(jié)奏的流暢。今天中國大部分的商業(yè)片不是太不深刻的問題,而是太不懂商業(yè)規(guī)律太缺乏商業(yè)想象力的問題,甚至是一個如何創(chuàng)作好類型人物的問題。
從《戰(zhàn)狼2》看電影商業(yè)化存在的問題
摘要:2017年7月,《戰(zhàn)狼2》電影上映,優(yōu)異的口碑與票房成績使其成為國產主旋律電影中商業(yè)化的成功典范,同時其商業(yè)化過程中也存在一些問題。本文從影片人物設置及情節(jié)表達等方面著手,發(fā)現(xiàn)個中不足。并從講好中國故事及立足國際化視野等角度提出改進策略。
關鍵詞:主旋律;商業(yè)化;《戰(zhàn)狼2》主旋律電影商業(yè)化
發(fā)展至今,剛剛步入類型化階段,《戰(zhàn)狼2》的成功不過是主旋律電影商業(yè)化初步成功的表現(xiàn),未來的發(fā)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主旋律電影在商業(yè)化過程中雖然在敘事情節(jié)、視覺呈現(xiàn)及技術應用等方面具有突飛猛進的進步,但在人物與劇情設置、國家形象建構及主旨精神表達等方面依然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間。
一、《戰(zhàn)狼2》商業(yè)化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一)程式化的人物設置。《戰(zhàn)狼2》為了打破傳統(tǒng)主旋律影片的說教性與喊口號的愛國宣言形式,融入了商業(yè)電影類型片的模式,在票房上大獲全勝,但是卻不可避免地具有類型片的一些缺陷,如人物設定扁平化等。這是因為,在量產的商業(yè)電影中,要想既滿足電影最短周期的拍攝計劃,又能最大限度地符合受眾審美需求,逐漸形成了一套程式化流水線生產模式。主旋律電影在借用類型片模式時,自然而然也存在同樣的問題。從人物塑造上看,《戰(zhàn)狼2》中張翰扮演的卓亦凡,套用了青春成長類型的人物設置,從年輕沖動、一無是處,到成熟可靠、有所擔當?shù)霓D變,也是美國英雄電影中常塑造的一類人物模型。另外,影片中的女性形象被符號化。通常情況下,英雄類型片中的女性形象只是影片中的陪襯,所以人物性格會被符號化,美麗的外表、堅強的性格、對男主人公從厭棄到喜歡的情感轉變等。單一的人物性格使影片英雄形象塑造更簡單便捷,同樣英雄救美的愛情故事能夠吸引受眾的眼球,然而類型化的東西并不能長久地發(fā)展下去。(二)過度化的民族主義表達。一些西方媒體批評《戰(zhàn)狼2》中存在過度民族主義的表達,甚至聲稱這是一場民族的自戀想象。這種評論雖然存在西方社會對中國發(fā)展的偏見,卻也暴露出國產主旋律電影的一大弊端。這主要是因為電影為了展現(xiàn)強大的國家實力,宣揚愛國主義精神而導致的過度情感表現(xiàn)。如《戰(zhàn)狼2》結尾處,當冷鋒帶領中國工人及非洲難民穿越紅巾軍的防線時,面對重重武裝對峙,冷鋒將中國國旗套在自己的胳膊上,并將其高高舉起,口中大喊“WeareChinese!”。紅巾軍看到中國國旗后,對同伴說:“是中國人,停止射擊!”此時鏡頭給了每位主演一個特寫,展現(xiàn)人物堅定的眼神,配上激情壯烈的背景音樂,車隊一路暢通,順利通過紅巾軍的包圍,而冷鋒自始至終都手舉國旗,以悲壯之姿一直堅持到中國維和基地,接受群眾的熱烈歡呼。對愛國熱情的渲染不一定要通過如此形式化的鏡頭來展現(xiàn),處理不當不但不會將觀眾帶入到情境中,反而會讓觀者產生不自在感。同時,這種情節(jié)的設置很難讓《戰(zhàn)狼2》擁有國際市場,西方觀眾并不能在影片中尋得情感共鳴,自然很難達到在國際上宣傳中國形象的理想效果。
二、相關問題的改進策略
國產現(xiàn)實題材電影的商業(yè)想象力研究
《我不是藥神》由真實事件改編,聚焦窮人因高額藥費失去生存權的問題,屬于典型的現(xiàn)實題材電影。這里所說的現(xiàn)實題材,主要指將比較尖銳的社會問題如青少年犯罪、貧窮、婚姻沖突、社會不公、種族偏見等戲劇化。《我不是藥神》的高票房和好口碑顯然與此有關。2014年陳可辛導演的《親愛的》也屬于這一類型的電影,電影以一起真實的拐帶兒童事件為題材,在票房和口碑上也獲得雙贏。這兩部電影的成功顯示出現(xiàn)實題材進入商業(yè)電影的巨大前景。但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只要觸及尖銳社會問題的商業(yè)電影就一定能得到觀眾認可,獲得高票房。個中一大原因就在于現(xiàn)實題材進入商業(yè)電影的方式。因為商業(yè)電影本身有其特點:首先,商業(yè)電影的觀影對象是數(shù)量極其巨大的普通觀眾,必須考慮他們的情感投入和觀影愉悅問題。如果觀眾沒有表現(xiàn)出這兩點,就不能稱為一部成功的商業(yè)電影。其次,商業(yè)電影因其巨大的受眾,必然具有不可估量的社會影響力,也不得不考慮意識形態(tài)效果的問題。商業(yè)電影的特性決定了它在處理現(xiàn)實題材時需要更多的技巧。本文聚焦《親愛的》和《我不是藥神》兩部電影,對上述問題進行探討。
一、現(xiàn)實題材商業(yè)電影的情感投入和觀影愉悅
商業(yè)電影的高票房來自于它對觀眾的重視。電影必須調動觀眾進行情感投入,讓觀眾獲得觀影愉悅,才有可能獲得票房的成功。好萊塢商業(yè)電影為獲得觀眾認同采取了很多手段,比如類型制度、明星制度、拍攝手法、敘事手段等。同理,現(xiàn)實題材商業(yè)電影在使用這些手段時可以發(fā)揮各種技巧。《親愛的》和《我不是藥神》在使用這些手段時既有相同點,又有區(qū)別之處。1.從引導觀眾的情感投入來說,《親愛的》借用傳統(tǒng)成熟類型的方法,《我不是藥神》則沒有很強的類型痕跡,而是采取嚴密的敘事和人物塑造手段。《親愛的》巧妙地使用了中國傳統(tǒng)苦情戲類型。苦情戲被學術界認為是中國商業(yè)電影的主流類型,“作為中國電影史上最重要的電影樣式之一,從最早第一代鄭正秋的《孤兒救祖記》《姊妹花》到第二代蔡楚生的《一江春水向東流》,直至第三代謝晉的《天云山傳奇》《芙蓉鎮(zhèn)》等影片,苦情戲作品的持續(xù)獲得成功令其盤踞中國商業(yè)電影主流地位近80年”。[1]這個類型在與觀眾的互動中不斷發(fā)展,形成成熟的敘事模式,建立了成熟的觀眾情感宣泄機制。所以,從對觀眾情感投入的引導來說,這個類型本身就具備良好的條件,將尖銳的現(xiàn)實問題放入其中來表現(xiàn)十分有利。影片使用了兩次尋子敘事,第一次的尋子在情節(jié)上借用了苦情戲的情節(jié)傳統(tǒng)。男主人公在兒子丟失之后,一直在堅持不懈地尋找兒子。既有騙子的阻擾,也有好心人的相助,最后終于家人團聚。第二次的尋子則借助了苦情戲的人物傳統(tǒng)。傳統(tǒng)的苦情戲更多以女性為主人公,李紅琴作為一個農村的家庭婦女,她本身就很容易喚起觀眾的同情。在電影的后半段,為了獲得吉芳的撫養(yǎng)權,她甚至付出了身體的代價,但她卻沒有放棄。這種堅韌和對苦難的承受與傳統(tǒng)苦情戲中的女主人公有相似的地方。兩次尋子都將苦情戲的傳統(tǒng)進行移植,使現(xiàn)實題材借助傳統(tǒng)類型將觀眾的情感力量成功激發(fā)出來。《我不是藥神》則沒有具體類型的借用痕跡,它致力于講述一個情節(jié)嚴謹?shù)暮霉适拢茉熳層^眾產生共鳴的主人公形象,在情節(jié)設計和人物形象塑造上很符合羅伯特•麥基在《故事》中所歸納的好萊塢經典劇本的設計。首先,從觀眾的情感投入來說,麥基認為,觀眾對影片產生情感投入并不是因為同情,而是因為移情。移情是“自我中心的,也是非常個人化的。當我們認同一位主人公及其生活的欲望時,事實上是在為我們自己的生活欲望喝彩。通過移情,即通過我們自己與一個虛構人物之間的同理感受,考驗并延伸了自己的人性”。[2]當觀眾移情于人物時,就會設身處地地去追尋人物的欲望。當觀眾對世界的期望基本上等同于人物的期望時,電影就成功地召喚起了觀眾的情感投入。《我不是藥神》前半部分對主人公程勇的塑造正是遵循這一原則。程勇因生活所迫開始走私印度仿制藥,影片對他的個人困境和逐利欲望都表達得十分清晰,使人物形象很容易獲得觀眾的認同。同時影片前半部分也通過細節(jié)將程勇性格中的重情重誼進行細致地鋪墊,均勻分布了三次他直面慢粒白血病人的場景,每個場景都以程勇充滿同情的面部特寫作為場景的收尾。第一次是他初次見到老呂,老呂告訴他自己等藥救命時;第二次是他與病友群的各群主見面,看到他們摘下口罩時;第三次是到黃毛的住所,看到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病人們時,為他后面的壯舉奠定了堅實的性格基礎。前半部分對程勇與老呂、黃毛、思慧的友情刻畫也十分重要。當主人公程勇以朋友的身份進入到這些慢粒白血病人的生活中時,他與他們的關系是在個體層面上建構起來的。他在電影后半部分所作出的選擇首先是基于對朋友情誼的珍重。以程勇與老呂的關系為例,程勇與老呂在前半部分共同賣藥的過程中已經建立起扎實的朋友情誼,目睹朋友因為缺藥而死去,程勇的再次賣藥在情節(jié)安排和人物性格上都是入情入理的事情。以上這些對程勇性格的細膩刻畫讓觀眾對他產生移情并建立起了“觀眾紐帶”。麥基將觀眾紐帶作為一部成功商業(yè)電影的核心,“如果作者未能在觀眾和主人公之間接上一根紐帶,那么我們就會坐在影片之外,感覺不到任何東西”。[1]電影后半部分在人物塑造上最成功的是將人物陷入了麥基所說的“兩難之擇”,“真正的選擇是兩難之擇。它發(fā)生于兩種情境。一是不可調和的兩善取其一的選擇:從人物的視點來看,兩個事物都是他所欲者,他兩者都要,但環(huán)境迫使他只能二選一。二是兩惡取其輕的選擇:從人物的視點來看,兩個事物都是他所不欲者,而且他一個也不想要,但環(huán)境迫使他必須二者擇一。在這種真正的兩難之境中,一個人物如何選擇便是對其人性以及他所生活的世界的一個強有力的表達。”[2]影片正是充分利用了這種兩難之擇來展現(xiàn)主人公從普通人變成英雄的過程。程勇一方面有老父與兒子,他并不想坐牢,另一方面朋友因缺藥而死去也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在這種兩難選擇中,麥基所說的“人物弧光”就出現(xiàn)了,“最優(yōu)秀的作品不但揭示人物性格真相,而且還在其講述過程中展現(xiàn)人物內在本性中的弧光或變化,無論變好還是變壞”。[3]當人物面臨著越來越艱難的選擇時,這些痛苦的選擇就已經開始深刻地改變人物的人性,程勇最后的蛻變也讓觀眾跟隨他完成了一次精神的升華。情節(jié)設計與人物設計在《我不是藥神》中相輔相成。情節(jié)的作用就是為人物的兩難之擇不斷提供壓力,迫使人物作出越來越艱難的抉擇和行動,從而揭示出其真實的自我。人物的塑造制造起結實的觀眾紐帶,讓觀眾始終追隨主人公的選擇和改變。《我不是藥神》正是通過對情節(jié)和人物的精細把握使觀眾移情到主人公身上,產生強烈的情感投入。可見,現(xiàn)實題材進入商業(yè)電影可以采取成熟類型,也可以不采取。但是故事與人物的扎實到位是其核心,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引導觀眾對影片的情感投入。2.從提供觀眾的觀影愉悅方面,《親愛的》主要采用單一類型愉悅的方法,《我不是藥神》則是采用多種類型愉悅混合的方法。好萊塢類型研究者里克•奧爾特曼提出了類型愉悅的觀點。他認為好萊塢類型電影中會設置很多類型的十字路口,往往提供兩條截然對立的路徑,一條路徑提供文化價值或懲罰,另一條路徑則提供逃離這些文化價值的類型愉悅。類型愉悅往往意味著一種過度和越規(guī),“比如黑幫片中的暴力、間諜片中的間諜行為、愛情片中的愛情激情、冒險片中的危險等都屬于類型愉悅”。[1]觀眾在類型中獲得暴力、激情、狂歡等和現(xiàn)實生活的循規(guī)蹈矩相沖突的體驗。觀眾在觀看類型電影的過程中,電影劇情不斷加強電影主角和類型效果,引導觀眾朝類型愉悅邁進。而且,“在類型電影中,類型愉悅的設置是優(yōu)于社會正確的”。[2]也就是說,類型電影首先應該讓觀眾體會到類型愉悅。在電影的最后階段,再讓觀眾安全地返回到社會價值規(guī)范之中。我們以《親愛的》為例,它借助的苦情戲是通過過度的痛苦體驗來實現(xiàn)類型愉悅的,即讓觀眾哭個痛快。有學者精辟地總結苦情戲的觀影機制:“在這種觀看心理機制中,觀眾在體驗一次虛構而夸大的苦難過程中,自身的積怨和潛意識里的自憐自傷被戲劇化的情節(jié)所喚醒,完成了一次由淚水代表的情緒宣泄。另一方面,故事里苦難的虛構性和夸大性,又引發(fā)了一種不真實的感受,加上結尾常常是happyending,就算再虛幻,問題總歸也得到了解決,觀眾的體驗得以安全著陸,壓抑不至于進入生活本身。”[3]按照以上總結,苦情戲先是通過提供夸大的苦難經歷,引導觀眾完成以痛苦為體驗的情感宣泄,然后通過苦難的解決讓觀眾的觀影安全回歸現(xiàn)實。過度的苦難正是奧爾特曼所說的類型愉悅來源。《親愛的》通過田文軍尋找兒子和李紅琴尋求女兒的曲折悲慘的遭遇為觀眾提供了體驗痛苦的機會,隨著主人公苦難的加深,觀眾的痛苦體驗不斷加強,這正是《親愛的》提供的類型愉悅所在。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比起傳統(tǒng)苦情戲,《親愛的》對主人公苦難經歷的描述還是節(jié)制的,這與它是現(xiàn)實題材有很大關系。《我不是藥神》沒有明顯的類型定位,采取的是將不同類型中的類型愉悅元素進行綜合應用。這些元素基本分布在影片的前半段,比如夜店橋段的性感元素、砸賣假藥場橋段的狂歡元素、追逐黃毛橋段的動作元素、會見牧師橋段的喜劇元素等,為觀眾的觀影增添了很多的愉悅,也是將觀眾吸引到影片中的重要手段。影片將這些類型愉悅的元素點綴在流暢的劇情發(fā)展之中,有如在現(xiàn)實題材上點綴著的糖豆,讓觀眾在緊張和松弛之間獲得了某種平衡。影片對類型愉悅的使用也是比較節(jié)制的,當影片下半部分走入悲壯的正劇情節(jié)后,這些類型愉悅的成分基本就不再出現(xiàn)了。從以上分析可見,單一類型愉悅和多類型愉悅對現(xiàn)實題材的商業(yè)電影來說都需要掌握一種度,因為過度強烈的類型愉悅會削弱現(xiàn)實題材電影的現(xiàn)實內容和真實感。但如果能夠將類型愉悅合理地注入到現(xiàn)實題材商業(yè)電影之中,就能夠更好地讓觀眾更容易沉浸在電影之中,調整現(xiàn)實題材給觀眾帶來的壓抑感受,為現(xiàn)實題材的商業(yè)電影帶來更好的觀影體驗。
二、現(xiàn)實題材商業(yè)電影的意識形態(tài)效果
商業(yè)電影因為其巨大的受眾,往往受到更嚴格的審查。商業(yè)電影制作商也會盡量考慮各種文化勢力的平衡。所以商業(yè)電影一般來說不太會直接冒犯一個社會的主導意識形態(tài),但也并不代表它在意識形態(tài)上無所作為。很多研究好萊塢商業(yè)電影的學者都發(fā)現(xiàn)了好萊塢商業(yè)電影在意識形態(tài)上的復雜性和曖昧性。理查德•麥克白認為,“一部電影最好是被理解成一處由很多(常常是沖突的)意圖和邏輯貫穿其中并發(fā)生作用的地方,每一種力量或多或少明顯地、也或多或少有效地改變著它。”[1]麥克白這里強調了商業(yè)電影是多種意識形態(tài)力量作用下的產物,所以它的意識形態(tài)效果需要更加細致的分析。奧爾特曼則干脆將好萊塢商業(yè)電影作為哈貝馬斯所提出的公共空間的當代替代品。[2]因為各種社會文化力量都有可能進入到其中,商業(yè)電影有可能成為一個象征性的社會議題的討論場所。對于現(xiàn)實題材商業(yè)電影來說,這種作為社會議題討論場的功能顯得更加突出。比如《我不是藥神》中討論的窮人吃不起高價藥的問題就是一個重要的社會議題。這部電影本身并沒有對這些復雜的社會力量進行討論,而是主要提供了一個英雄挺身而出為窮人采購廉價藥的故事。2018年7月5日電影上映之后,圍繞這個社會議題的討論變得十分熱鬧,比如仿制藥是否合法與合理?專利權與生命權哪個更大?諸多敏感的社會議題被紛紛提出。討論的高潮出現(xiàn)在7月18日,國家高層領導就這部電影引發(fā)的輿論熱議作出批示,要求有關部門加快落實抗癌藥降價保供等相關措施。《我不是藥神》上映所引發(fā)的這些嚴肅的社會討論甚至政府高層的直接政策決定,生動地展示出現(xiàn)實題材商業(yè)電影作為社會公共空間和社會議題討論場的可能性。商業(yè)電影不僅可以作為社會議題的討論場,還承擔著象征性地化解社會文化矛盾的功[1]能。現(xiàn)實題材商業(yè)電影因為直接觸及社會的尖銳矛盾與沖突,其是否能夠實現(xiàn)化解社會文化矛盾的功能顯得更加重要。美國學者托馬斯•沙茨將類型電影作為社會文化沖突的儀式解決途徑,認為類型主要承擔兩種不同的儀式功能:一種是秩序儀式,另一種是融合儀式。秩序儀式解決的是文化社群所面對的外在威脅;融合儀式處理的則是文化社群的內在矛盾與沖突。融合儀式作為結局的電影類型涉及的是個體或群體接受集體價值和態(tài)度的過程。當這個類型片中的主人公們相互矛盾的態(tài)度和價值最終聚合為一個單一的社會單位時,沖突解決。[1]按照沙茨的這個分類,現(xiàn)實題材商業(yè)電影既可能采取融合儀式,將尖銳的社會問題通過融合儀式象征性地解決;也有可能采取秩序儀式將社會尖銳矛盾通過正義戰(zhàn)勝邪惡的方式進行象征性地解決。《親愛的》就是巧妙地采取了融合儀式,而《我不是藥神》采取的則是秩序儀式。1.《親愛的》:弱者融合儀式。《親愛的》選取的是傳統(tǒng)苦情戲中的尋親題材,并借助這個傳統(tǒng)類型進行一種巧妙的意識形態(tài)布局,從而使現(xiàn)實題材成為實現(xiàn)文化融合儀式的有力工具。其中核心就是尋子,對無辜弱小的孩子的尋找反而成為了一種強大的融合力量,將矛盾重重和四分五裂的社會人群重新融合在一起。我將這種意識形態(tài)操作手段稱為弱者融合儀式。為了完成這種弱者融合儀式,電影利用了苦情戲的類型傳統(tǒng)。托馬斯•沙茨認為,“觀眾對類型越是熟悉,那么它的成規(guī)也就扎得越牢,于是它那獨特的敘事邏輯就更能壓倒真實世界的邏輯,從而不僅創(chuàng)造一個人為的風景線,而且還創(chuàng)造出人為的價值系統(tǒng)和信念系統(tǒng)。”[2]所以,使用傳統(tǒng)類型本身就是一種成功的意識形態(tài)手段,尋找孩子和家庭團圓就是苦情戲有力的價值系統(tǒng),完全可以被借用過來。另一方面,電影又大量地改造苦情戲,使其能夠容納更豐富的當代社會內容,完成新的意識形態(tài)任務。首先,《親愛的》既利用又突破了苦情戲的情節(jié)設置。前半部分以田文軍為中心,以他尋找被拐走的兒子鵬鵬為線索,直到兒子終于找到,展現(xiàn)了一個家庭從失散到重合的過程。這部電影比較有特色的情節(jié)在后半段,主人公變成了拐走田鵬的人犯妻子李紅琴。這個人物形象在后半部分成為主角,就是影片既利用又突破傳統(tǒng)苦情戲的意圖所在。利用苦情戲的女性作為主人公的傳統(tǒng)我們在前面已經分析過,這里我們著重分析一下電影突破苦情戲的內容。同為尋親,影片前半段田文軍的尋親還是基于血緣親情,后半段李紅琴的尋親則突破了狹隘的血緣親情倫理,變成了一種更博愛的社會化親情。這就讓《親愛的》突破了一般尋親題材以血緣家庭為表現(xiàn)對象,讓尋親承擔起更艱巨的社會融合儀式的功能。其次,《親愛的》的人物也突破了苦情戲的人物設置。電影中所有的人物都或多或少承擔著某種社會符號的作用。影片開頭展現(xiàn)的是一個破碎的家庭,主人公田文軍在丟失孩子前就和妻子魯曉娟離了婚。家庭破碎的原因也并不能從家庭內部的邏輯上去解答,只能放在一個更大的社會時空中才能看清他們離婚的真相。這對夫妻是城鄉(xiāng)劇烈變化、人口遷徙頻繁的中國當代背景下夫妻關系的典型代表。妻子是有著更大追求的事業(yè)女性,來到繁華都市后,渴望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由此離開原來的底層家庭,組建了新的中產階層的家庭。但兒子的失蹤讓她立刻從獨立自主的女性變?yōu)槭ニ腥松非蠛蜆啡ど踔料萑胍环N精神恍惚狀況的可憐母親,并在尋子過程中與前夫再次建立起了親密關系,最終與現(xiàn)任丈夫離婚。這種對人物形象的機械化呈現(xiàn)恰恰是影片意識形態(tài)操作的策略:這個不安分的試圖擺脫家庭、追求個人幸福的女人最終因為兒子的走丟受到“懲罰”并“回歸”家庭。電影通過這個女性形象的塑造隱形地對當代都市新女性進行著規(guī)訓。韓德忠的形象顯然是一個新富階層的代表。如果不是因為尋子,他與田文軍的貧富差距讓他們不太可能建立起親密聯(lián)系。影片以韓為中心,建立了一個跨越貧富與階層的尋子共同體,這本身就是借親情來試圖融合起貧富差距日益顯著的城市居民。高夏在電影下半段的出現(xiàn)也是精心設計的一個文化符號。這是一個在大城市努力打拼,拼命向上爬,甚至有些不擇手段的年輕人。他與農村婦女李紅琴本來不會有任何交集,但李紅琴收養(yǎng)吉芳的努力讓他受到觸動,并對她產生真正的同情。這可以說是親情對城鄉(xiāng)隔膜的一種彌合。由此,這部電影以尋親為紐帶,以孩子為中心,完成了多重層面的社會融合儀式:破碎家庭的重新融合,以及貧富、階層、城鄉(xiāng)等的融合,將親情作為社會的粘合劑,使四分五裂的社會個體得以重新聯(lián)合起來。現(xiàn)實題材借助類型的情感力量,通過巧妙的意識形態(tài)操作,達到對社會進行干預與重建的文化功能。2.《我不是藥神》:英雄秩序儀式。《我不是藥神》采取的是英雄秩序儀式。影片以吃不起高價藥的慢粒白血病人群體作為正義的一方,而將賣高價藥的跨國制藥公司作為邪惡的一方。主人公程勇承擔的是秩序儀式中的英雄角色。電影十分重要的一個操作手段是將現(xiàn)實事件中作為慢粒白血病患者的主人公變成了一個健康人。如果程勇本人作為患者,他就會因為爭取個體生存權的急迫,成為一個抗爭者,將個人的生存權作為首要的考慮要素。當程勇作為一個健康人進入到白血病患者的生活中時,他對他們由同情到甘愿犧牲自己的過程,使其英雄性得到極大提升。電影另一個操作手段是降低說理的內容,而是著重寫情。關于正品藥物與仿制藥物之間的問題十分復雜,《我不是藥神》雖然將程勇作為英雄,但是他與代表邪惡一方的制藥公司之間在影片中沒有構成直接的沖突。影片著重刻畫的是程勇與病人之間的情。程勇周圍聚集的都是處于社會底層的慢粒白血病患者。老呂代表的是普通知識分子,思慧是跳色情舞蹈的單親媽媽,黃毛是農村到城市打工的青年,他們的生存本就艱難,昂貴的藥價幾乎讓他們失去了生存的可能性。程勇的重情重義就是他英雄氣質的核心。老呂的死亡是將程勇內心的英雄氣質完全激發(fā)出來的重要情節(jié)設置,最終讓他作出了犧牲自己的決定。這也是程勇這個中國式的英雄與好萊塢秩序儀式電影中的英雄最大的區(qū)別。好萊塢在秩序儀式電影中喜歡塑造孤獨的邊界英雄,比如西部片、黑色偵探片。這類英雄往往處于正義與邪惡的中間位置,不完全屬于正義一方,他們雖然會與邪惡勢力進行斗爭,但最后的結局也不是回歸到社會正義的一方,反而是遠離人群。《我不是藥神》中的程勇則完全站在正義的一方,即影片中的慢粒白血病人的群體,隨著他與慢粒白血病人之間情誼的建立,同情心推動著他逐漸向英雄的形象靠近。影片第三個操作手段是對代表政府的警察形象的設置,尤其是警官曹斌的形象設置。他一方面作為政府公職人員,需要追查賣仿制藥的嫌疑人,一方面影片又讓他具有與程勇一樣的同情心,同情那些貧窮的病人,最終他與程勇和病人們站在一起。電影最后也是由他作為政府代言人告訴程勇,政府已將這種抗白血病的藥納入醫(yī)保。由此,以程勇、曹斌為紐結點,政府與病人一起站在了正義的一方。《我不是藥神》的這種英雄秩序儀式是一個將正義一方的力量不斷匯聚的過程。《我不是藥神》的英雄秩序儀式以情感作為正義戰(zhàn)勝邪惡的力量。電影中的英雄具有強烈的同情心,英雄的犧牲又能夠喚起更多人的同情心,最終情感的力量讓正義的一方不斷壯大并取得勝利。這種英雄秩序儀式沒有如好萊塢秩序儀式電影中對秩序本身的懷疑,而且?guī)椭柟塘松鐣刃颉?/p>
三、結語:國產現(xiàn)實題材的商業(yè)想象力
讀解小說人物形象透析
(一)人物理論觀念
十九世紀后期,浪漫主義、自然主義、唯美主義的某些觀點在現(xiàn)代主義小說及其理論中都有明顯的投影,一些現(xiàn)實主義小說家和小說論者,還有處于臨界點的小說家和小說論者的小說理論與創(chuàng)作,也在一些方面對現(xiàn)代主義產生影響。如福樓拜強調“取消私人性格主義”,主張不偏不倚地再現(xiàn)生活,要求小說家與其小說主人公保持一定的距離。陀斯妥耶夫斯基聯(lián)系客觀現(xiàn)實描寫人物內心的同時,主張通過夢幻、意識流等手法,開闊人的深層意識,表現(xiàn)人物的變態(tài)心理、雙重人格;他創(chuàng)作的“復調小說”的主人公具有獨立意識,獨立性,被看作是一個自身的充分思想觀念的創(chuàng)造者,已經“不是作者言論的客體”,“也不是作者意識的傳聲筒”,與作者的關系是一種平等的“對話”關系。契科夫淡化情節(jié)。康拉德在小說中追求風格的完美,著力從心理深度上刻畫人物,他時而讓小說中的人物擔任敘述者,與“我”對話,時而又由幾個人充當敘述者,而且他認為展示人物,不應按時間先后平鋪直敘,打破敘述時間的順序。這些小說理論和小說創(chuàng)作的衍化、發(fā)展,進一步表現(xiàn)從外部世界遁入內心世界的“心理真實”,小說家退出小說等理論觀點。這種情況,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亨利•詹姆斯的小說理論中,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在結構分析興起來后,對人物的理解就形成了兩種意見:“純粹派”的論點——如今在批評家中占優(yōu)勢——指出,人物只是作為使他們得以產生并使他們的行動作為各種形象和事件的一部分而存在,除此之外,他們根本就不存在。倘若費盡心機想把他們從特定的上下文中抽取出來,把他們當作真實的人加以導輪,那就是感情用事地誤解了文學的性質。各種現(xiàn)實主義的觀點傾向于在某種“還原性”的參照中來理解人物,把人物視為某種人性、個性、心理本質、性格類型等等。“非還原”的觀點認為人物的具體特征是屬于語言的,而非再現(xiàn)的或實體的。“在符號學批評的庇護下,人物失去了他們的特權,他們的中心地位,以及他們的定義。……他們被文本化了。和一篇封閉的文本中的片斷一樣,人物充其量只是重復的模式,只是不斷地被置于其他主題構成的上下文的問題。在符號學批評中人物被融化了”(威英。謝麥爾《人物理論》)
(二)人物典型化的原則
人物性格的塑造,在菲爾丁看來,應該遵守可信性的原則,同時也不可超出蓋然性的范圍。他認為,小說家應當注意人物的概括性。他強調“我描寫的不是某甲、某乙,我描寫的是性格,不是某個人,而是類型。”他曾就“類型”作過這樣的解釋:讀者不要一聽見驛車中律師的聲音,便說這是某某人,應該懂得“那位律師不僅現(xiàn)在活著,而且四千年來他一直活著,我希望上帝容忍他再活上四千年。”(《約瑟夫。安德魯斯》)狄德羅十分強調人物的差異。并欣賞理查遜的長篇小說《克拉利莎》,說在這部作品里:“有如春天的大自然一樣,看不到同樣翠綠的兩片葉子。”在《理查遜贊》里,他贊賞道:“每個人都有他的思想、他的表情、他的語調”。歌德對于古典主義理論家津津樂道的類型說,則持否定說,他宣稱:“類型概念使我們漠然無動于衷。”繼而指出:“我們還不滿足于此,我們要求回到個別的東西進行充分的欣賞。”這“個別的東西”即顯示個性特征的東西。黑格爾在歐美文論中第一次明確地提出“性格就是理想藝術表現(xiàn)的真正中心”的論點。他認為“理想就是從一大堆個別偶爾的東西之中所揀回來的現(xiàn)實,因為內在因素在這種與抽象普遍性相對立的外在形象里顯現(xiàn)為活的個性。”巴爾扎克在典型化的基礎上提出了“人物再現(xiàn)的原則”。他認為,小說應通過人物形象把“一個系代呈現(xiàn)出來”。有鑒于此,光憑一兩個典型人物是無法實現(xiàn)這一要求的,必須有兩三千個出色的人物,林林總總的人物畫廊,而且人物,包括典型人物也可以在各部小說中反復出現(xiàn),互相穿插,以反映出正在發(fā)展的時代的面貌。這一原則,能使各部小說勾連起來,具有極強的整體感,從而更真實、更概括地再現(xiàn)歷史的衍化,和時代的變遷。別林斯基則將典型概括為:“熟悉的陌生人”。并強調指出了典型人物與環(huán)境的內在聯(lián)系:因此,“我們的作家在描寫人的同時,便自然地描繪了社會”。
(三)人物典型化的方法
怎樣創(chuàng)造典型呢?托爾斯泰在談到《戰(zhàn)爭與和平》中的娜塔莎這一典型人物時說:“我拿過達尼雅來,把她與蘇尼雅一同搗碎,于是就出現(xiàn)了娜塔莎”。同時在他的一則日記里寫道“藝術是藝術家用來窺視自己靈魂的奧秘,并向人們展示這些一切人都有的奧秘的一架顯微鏡。”車爾尼雪夫斯基將其理論概括為“心靈的辨證法”。黑格爾對人物性格提出了三個具體要求:豐富性、明確性、堅定性。所謂“豐富性”是指人物性格不是單一而是多面的和豐滿的。他歸納荷馬史詩中的人物性格特點:“每個人都是一個整體,本身就是一個世界,每個人都是一個完滿的有生氣的人,而不是某種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同時他強調要處理好性格的主導方面與其他方面的關系,否則“復雜性格的種種方面就會是一盤散沙,毫無意義。”乃至“使性格失其為性格。”這里指的是性格的明確性。所謂堅定性,即人物必須依據(jù)自己的意志發(fā)出動作,作到自己與自己融貫一致,使其性格成為堅定的統(tǒng)一體。杜勃羅留波夫論典型方法說“一個感受力比較敏銳的人,一個有‘藝術家’氣質的人,當他在周圍的現(xiàn)實世界中,看到了某一事物物的最初事實時,他就會發(fā)生強烈的感動。他雖然還沒有能夠在理論上解釋這種事實的思考能力,可是他卻看見了,這里有一種值得注意的特別的東西,他就熱心而好奇地注視著這個事實,把它攝取到自己的心靈中來,開頭把它作為一個單獨的形象,加以孕育,后來就使它和其他同類的事實與現(xiàn)象結合起來,而最后,終于創(chuàng)造了典型。”(《黑暗的王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