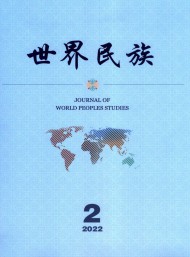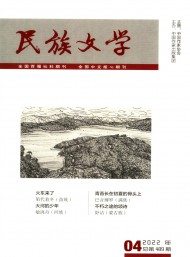民族觀范文10篇
時間:2024-02-28 12:04:22
導語:這里是公務員之家根據多年的文秘經驗,為你推薦的十篇民族觀范文,還可以咨詢客服老師獲取更多原創文章,歡迎參考。

梁啟超的民族觀研究論文
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如何對待民族關系,在歷史上一向是很重要的問題,而梁啟超則是運用近代觀念和方法,比較系統地研究民族關系歷史的第一人。他不僅撰寫有理論著作,運用近代學術觀點論述民族關系史的一系列重要問題,而且在其通史和專史著作中,予歷史上的民族關系以相當的重視。他作為本世紀前期具有突出的進步民族觀點的思想家,對其后的研究者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本文試圖對梁啟超的民族觀加以探討,敬請專家和讀者指正。
一、以近代眼光論述民族問題的奠基之作
1922年梁啟超發表了他的著名學術論文《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中華書局1989年版;又,梁啟超在北京高師史地部以《中華民族之研究》為題講演的記錄稿發表于中國地學會出版的《地學雜志》民國11年第1—7期上,此講演的記錄稿又以《中華民族之成分》為題發表在上海中華書局印行的《史地叢刊》民國12年第2卷第2、3期合刊上,其內容都與《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基本相同。),通過對民族之意義及中華民族之由來、分類、分布、演化融合的歷史軌跡等項重要理論問題的論述,闡發了他的近代民族觀。因而這篇文章在本世紀學術史上,成為運用近代觀點論述民族問題的奠基之作。
首先,關于民族的定義。我國古代文獻對“民”和“族”這兩個概念,雖都有所闡述,但沒有將二字聯起來使用。梁啟超不僅率先將“民族”一詞引入中國思想界(注:1899年梁啟超在《東籍月旦》一文中,在介紹日本史著中多次出現“東方民族”、“支那民族”、“民族之變遷”、“民族之立國大原”等新名詞。詳見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90、94、100頁。),而且是近代中國賦予“民族”一詞比較科學意義的第一人。他明確提出:民族既與種族不同,也與國民不同。種族是人種學研究的對象,國民是法律學研究的對象,而民族雖以血緣、語言、信仰為成立之有力條件,但斷不能以此三者作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識’之發現與確立。”(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1頁。)何為民族意識?我們今天看來,民族意識即是共同心理狀態于共同文化上的一種表現形式。從這個意義說,梁啟超關于民族的界說與斯大林關于“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的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注:斯大林:《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頁。)這一經典定義很相近,明顯地體現了梁啟超論述問題的科學性。進一步說,斯大林強調,這四個要素缺一不可,而梁啟超卻強調民族意識是惟一要素。事實上,語言、信仰、地域、經濟生活等因素,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是可以改變或消失的,惟有共同的民族意識與民族感情是一個民族得以確立和長久保持其民族特性的關鍵,缺此要素便不成其為民族。因此,梁啟超強調民族意識對一個民族的重要,正是抓住了“民族”一詞的實質性內涵。此外,他如此強調民族意識對一個民族形成之重要,也由于當時他借鑒了東西方各國的歷史與現實,深切地體會到民族意識是一個民族自尊自立自強和具有凝聚力的起點和原動力。這一論述蘊含著作者教育國人樹立“我,中國人”(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2頁。)的民族信念和高度的民族自尊自信的良苦用心。總之,理論的探討和實踐的檢驗已經反復證明,梁啟超將“民族意識之發現與確立”作為區分民族的最主要標準是特具卓識的。
其次,梁啟超分析了中華民族是由同一祖宗血胤衍生而來,還是自始即為多元結合的問題。他針對舊史認為吾族純以血緣相屬而成立的傳統觀念,指出:既然唐虞夏商周秦漢皆同祖黃帝,就不應出現《史記》所紀三代世表世次矛盾、罅漏百出的失誤,更不應出現《詩經》關于商周之祖“無父感天而生”的怪論。由此可見,一元說的理論不可信。他進而分析:從我國古帝王各異其都,可知古代各部落在各地發展,各戴各的尊長,即是多元結合的一種暗示,吾族自名曰夏,夏之前而冠以“諸”,亦是多元結合的一個證明。他認為,是在黃河流域大片土地上長期繁衍生息的各小部落,“以聯邦式的結合”,遂形成中華民族之骨干。他強調:中華民族自始即是多元的結合,又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不斷地融匯化合,逐步混“成為數千年來不可分裂不可磨滅之一大民族”。(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4頁。)梁啟超這一觀點的重大科學價值已被后來的考古發現和學術探討所證實,且對打破大漢族主義的優越感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也是在理論上對歷代統治階級實行民族歧視政策的否定。
梁啟超列舉了歷史上各個時期匯入中華民族“新分子”的大量事實,表述了一個重要的觀點:歷史上“諸夏”與“夷狄”二詞之內涵,隨時變遷,“甲時代所謂夷狄者,乙時代已全部或一部編入諸夏之范圍。而同時復有新接觸之夷狄發現,如是遞續編入,遞續接觸,而今日碩大無朋之中華民族,遂得以成立。”(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8頁。)這段論述有兩層重要含義:其一,今天的中華民族之所以人口眾多,富有強大的生命力,是因為在歷史上不斷地吸收、混合了其他民族的成分。其二,他直接繼承和弘揚了我國古代公羊學派以文明或道德進化程度來區分“諸夏”與“夷狄”,并認為二者是可變的民族觀,從而打破了封建傳統的“嚴夷夏之大防”的陳腐觀念,認識到了民族間相互融合的大趨勢。這種動態的進化的民族觀,既符合中國是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和國情,也有利于促進民族間的交流與進步,有利于國家的安定統一,表達了梁啟超豁達的心態、開闊的視野與深遠的理性思考。
梁啟超的民族觀研究論文
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如何對待民族關系,在歷史上一向是很重要的問題,而梁啟超則是運用近代觀念和方法,比較系統地研究民族關系歷史的第一人。他不僅撰寫有理論著作,運用近代學術觀點論述民族關系史的一系列重要問題,而且在其通史和專史著作中,予歷史上的民族關系以相當的重視。他作為本世紀前期具有突出的進步民族觀點的思想家,對其后的研究者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本文試圖對梁啟超的民族觀加以探討,敬請專家和讀者指正。
一、以近代眼光論述民族問題的奠基之作
1922年梁啟超發表了他的著名學術論文《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中華書局1989年版;又,梁啟超在北京高師史地部以《中華民族之研究》為題講演的記錄稿發表于中國地學會出版的《地學雜志》民國11年第1—7期上,此講演的記錄稿又以《中華民族之成分》為題發表在上海中華書局印行的《史地叢刊》民國12年第2卷第2、3期合刊上,其內容都與《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基本相同。),通過對民族之意義及中華民族之由來、分類、分布、演化融合的歷史軌跡等項重要理論問題的論述,闡發了他的近代民族觀。因而這篇文章在本世紀學術史上,成為運用近代觀點論述民族問題的奠基之作。
首先,關于民族的定義。我國古代文獻對“民”和“族”這兩個概念,雖都有所闡述,但沒有將二字聯起來使用。梁啟超不僅率先將“民族”一詞引入中國思想界(注:1899年梁啟超在《東籍月旦》一文中,在介紹日本史著中多次出現“東方民族”、“支那民族”、“民族之變遷”、“民族之立國大原”等新名詞。詳見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90、94、100頁。),而且是近代中國賦予“民族”一詞比較科學意義的第一人。他明確提出:民族既與種族不同,也與國民不同。種族是人種學研究的對象,國民是法律學研究的對象,而民族雖以血緣、語言、信仰為成立之有力條件,但斷不能以此三者作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識’之發現與確立。”(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1頁。)何為民族意識?我們今天看來,民族意識即是共同心理狀態于共同文化上的一種表現形式。從這個意義說,梁啟超關于民族的界說與斯大林關于“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的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注:斯大林:《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頁。)這一經典定義很相近,明顯地體現了梁啟超論述問題的科學性。進一步說,斯大林強調,這四個要素缺一不可,而梁啟超卻強調民族意識是惟一要素。事實上,語言、信仰、地域、經濟生活等因素,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是可以改變或消失的,惟有共同的民族意識與民族感情是一個民族得以確立和長久保持其民族特性的關鍵,缺此要素便不成其為民族。因此,梁啟超強調民族意識對一個民族的重要,正是抓住了“民族”一詞的實質性內涵。此外,他如此強調民族意識對一個民族形成之重要,也由于當時他借鑒了東西方各國的歷史與現實,深切地體會到民族意識是一個民族自尊自立自強和具有凝聚力的起點和原動力。這一論述蘊含著作者教育國人樹立“我,中國人”(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2頁。)的民族信念和高度的民族自尊自信的良苦用心。總之,理論的探討和實踐的檢驗已經反復證明,梁啟超將“民族意識之發現與確立”作為區分民族的最主要標準是特具卓識的。
其次,梁啟超分析了中華民族是由同一祖宗血胤衍生而來,還是自始即為多元結合的問題。他針對舊史認為吾族純以血緣相屬而成立的傳統觀念,指出:既然唐虞夏商周秦漢皆同祖黃帝,就不應出現《史記》所紀三代世表世次矛盾、罅漏百出的失誤,更不應出現《詩經》關于商周之祖“無父感天而生”的怪論。由此可見,一元說的理論不可信。他進而分析:從我國古帝王各異其都,可知古代各部落在各地發展,各戴各的尊長,即是多元結合的一種暗示,吾族自名曰夏,夏之前而冠以“諸”,亦是多元結合的一個證明。他認為,是在黃河流域大片土地上長期繁衍生息的各小部落,“以聯邦式的結合”,遂形成中華民族之骨干。他強調:中華民族自始即是多元的結合,又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不斷地融匯化合,逐步混“成為數千年來不可分裂不可磨滅之一大民族”。(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4頁。)梁啟超這一觀點的重大科學價值已被后來的考古發現和學術探討所證實,且對打破大漢族主義的優越感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也是在理論上對歷代統治階級實行民族歧視政策的否定。
梁啟超列舉了歷史上各個時期匯入中華民族“新分子”的大量事實,表述了一個重要的觀點:歷史上“諸夏”與“夷狄”二詞之內涵,隨時變遷,“甲時代所謂夷狄者,乙時代已全部或一部編入諸夏之范圍。而同時復有新接觸之夷狄發現,如是遞續編入,遞續接觸,而今日碩大無朋之中華民族,遂得以成立。”(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8頁。)這段論述有兩層重要含義:其一,今天的中華民族之所以人口眾多,富有強大的生命力,是因為在歷史上不斷地吸收、混合了其他民族的成分。其二,他直接繼承和弘揚了我國古代公羊學派以文明或道德進化程度來區分“諸夏”與“夷狄”,并認為二者是可變的民族觀,從而打破了封建傳統的“嚴夷夏之大防”的陳腐觀念,認識到了民族間相互融合的大趨勢。這種動態的進化的民族觀,既符合中國是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和國情,也有利于促進民族間的交流與進步,有利于國家的安定統一,表達了梁啟超豁達的心態、開闊的視野與深遠的理性思考。
梁啟超的民族觀探析論文
一、以近代眼光論述民族問題的奠基之作
1922年梁啟超發表了他的著名學術論文《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中華書局1989年版;又,梁啟超在北京高師史地部以《中華民族之研究》為題講演的記錄稿發表于中國地學會出版的《地學雜志》民國11年第1—7期上,此講演的記錄稿又以《中華民族之成分》為題發表在上海中華書局印行的《史地叢刊》民國12年第2卷第2、3期合刊上,其內容都與《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基本相同。),通過對民族之意義及中華民族之由來、分類、分布、演化融合的歷史軌跡等項重要理論問題的論述,闡發了他的近代民族觀。因而這篇文章在本世紀學術史上,成為運用近代觀點論述民族問題的奠基之作。
首先,關于民族的定義。我國古代文獻對“民”和“族”這兩個概念,雖都有所闡述,但沒有將二字聯起來使用。梁啟超不僅率先將“民族”一詞引入中國思想界(注:1899年梁啟超在《東籍月旦》一文中,在介紹日本史著中多次出現“東方民族”、“支那民族”、“民族之變遷”、“民族之立國大原”等新名詞。詳見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90、94、100頁。),而且是近代中國賦予“民族”一詞比較科學意義的第一人。他明確提出:民族既與種族不同,也與國民不同。種族是人種學研究的對象,國民是法律學研究的對象,而民族雖以血緣、語言、信仰為成立之有力條件,但斷不能以此三者作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識’之發現與確立。”(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1頁。)何為民族意識?我們今天看來,民族意識即是共同心理狀態于共同文化上的一種表現形式。從這個意義說,梁啟超關于民族的界說與斯大林關于“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的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注:斯大林:《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頁。)這一經典定義很相近,明顯地體現了梁啟超論述問題的科學性。進一步說,斯大林強調,這四個要素缺一不可,而梁啟超卻強調民族意識是惟一要素。事實上,語言、信仰、地域、經濟生活等因素,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是可以改變或消失的,惟有共同的民族意識與民族感情是一個民族得以確立和長久保持其民族特性的關鍵,缺此要素便不成其為民族。因此,梁啟超強調民族意識對一個民族的重要,正是抓住了“民族”一詞的實質性內涵。此外,他如此強調民族意識對一個民族形成之重要,也由于當時他借鑒了東西方各國的歷史與現實,深切地體會到民族意識是一個民族自尊自立自強和具有凝聚力的起點和原動力。這一論述蘊含著作者教育國人樹立“我,中國人”(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2頁。)的民族信念和高度的民族自尊自信的良苦用心。總之,理論的探討和實踐的檢驗已經反復證明,梁啟超將“民族意識之發現與確立”作為區分民族的最主要標準是特具卓識的。
其次,梁啟超分析了中華民族是由同一祖宗血胤衍生而來,還是自始即為多元結合的問題。他針對舊史認為吾族純以血緣相屬而成立的傳統觀念,指出:既然唐虞夏商周秦漢皆同祖黃帝,就不應出現《史記》所紀三代世表世次矛盾、罅漏百出的失誤,更不應出現《詩經》關于商周之祖“無父感天而生”的怪論。由此可見,一元說的理論不可信。他進而分析:從我國古帝王各異其都,可知古代各部落在各地發展,各戴各的尊長,即是多元結合的一種暗示,吾族自名曰夏,夏之前而冠以“諸”,亦是多元結合的一個證明。他認為,是在黃河流域大片土地上長期繁衍生息的各小部落,“以聯邦式的結合”,遂形成中華民族之骨干。他強調:中華民族自始即是多元的結合,又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不斷地融匯化合,逐步混“成為數千年來不可分裂不可磨滅之一大民族”。(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4頁。)梁啟超這一觀點的重大科學價值已被后來的考古發現和學術探討所證實,且對打破大漢族主義的優越感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也是在理論上對歷代統治階級實行民族歧視政策的否定。
梁啟超列舉了歷史上各個時期匯入中華民族“新分子”的大量事實,表述了一個重要的觀點:歷史上“諸夏”與“夷狄”二詞之內涵,隨時變遷,“甲時代所謂夷狄者,乙時代已全部或一部編入諸夏之范圍。而同時復有新接觸之夷狄發現,如是遞續編入,遞續接觸,而今日碩大無朋之中華民族,遂得以成立。”(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8頁。)這段論述有兩層重要含義:其一,今天的中華民族之所以人口眾多,富有強大的生命力,是因為在歷史上不斷地吸收、混合了其他民族的成分。其二,他直接繼承和弘揚了我國古代公羊學派以文明或道德進化程度來區分“諸夏”與“夷狄”,并認為二者是可變的民族觀,從而打破了封建傳統的“嚴夷夏之大防”的陳腐觀念,認識到了民族間相互融合的大趨勢。這種動態的進化的民族觀,既符合中國是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和國情,也有利于促進民族間的交流與進步,有利于國家的安定統一,表達了梁啟超豁達的心態、開闊的視野與深遠的理性思考。
梁啟超的動態的民族觀,使他摒棄了封建正統史觀和大漢族主義民族偏見,將各民族完全置于平等的地位。他特意為這篇論文加了一個副標題:“本篇即‘五千年史勢鳥瞰’之一部分”(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1頁。)。即將少數民族史作為中華民族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將中華民族融合史視為中國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在中國史學上是開天辟地第一回!新中國成立后,白壽彝提出“中國的歷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歷史”(注: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頁。)這一杰出論斷,可以視為正是梁啟超上述民族觀的合理繼承、發展和延伸。
民族音樂學研究價值觀探討
一、價值觀
(一)什么是價值觀
價值觀,是以某種思維感官基礎上而給出的認知、理解、判斷或決定,換而言之,是人認識物體、辨別對錯的一種思想或價值取向,進而表達出【人、事、物】之間某種的價值或影響;在階級社會中,不同階級有不同的價值觀念。伍國棟出版的《民族音樂學概論》中,價值觀的定義為:“從能否符合及怎樣符合主題的需要方面,來考查及評判不同民族音樂事象的一種概念。”從上述描述中可知,價值觀的形成體現是主體所需;因民族不同意味著文化、傳統也不同,從而使得不同民族的傳統音樂,價值取向及評判準則也是不同的,不一樣歷史發展階段的民族、和不一樣的社會經歷的個體,均會根據自身所需、愛好來估算某一事物的影響或價值。
(二)樹立正確價值觀的重要性
在探究不同民族音樂過程中,難免會因文化的差異產生一定的沖突,主要還是由于研究對象同被研究對象的價值取向有差異,為了避免此類問題的產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就很必要。在實地考察中,我們應該把自己的需求和主觀想法拋在一邊,客觀地去面對研究對象。每一種文化現象能夠傳承到現在,就證明它有著超乎一般的生命力。所以,在評判和研究其他民族的音樂文化時,不可讓自身主觀因素來影響評判結果,需按照客觀實際且不同角度來考察音樂文化,這樣才會提高我們研究工作的準確性和科學性。
二、阻礙民族音樂學發展的價值觀
科學發展觀民族政策要求論文
[摘要]民族政策是推進我國民族發展的重要手段,在促進民族發展方面能夠發揮中介作用、調控作用、促進作用和規范作用。根據科學發展觀的要求,面臨政策實踐環境的諸多變化,我國的民族政策應遵循服務于各民族發展、體現社會公平正義的原則,不斷實現優化與創新。
[關鍵詞]民族政策;科學發展觀;優化;創新
科學發展的實質是創新發展,促進民族發展離不開民族政策的推動,在民族發展問題上踐行科學發展觀,離不開民族政策的優化與創新。
一、民族政策的實質與作用
民族政策是執政黨民族治理理念的具體化,是政府為了處理民族問題、改善民族關系而制定和實施的法規、準則以及措施的總和。
法規和準則作為一種規范,規約和導引國家、各級政府、社會團體、普通民眾在對待民族問題、處理民族關系方面應持怎樣的態度、該如何去做,并通過褒揚與懲戒達到維護道義和秩序的目的。措施是貫徹執行和維護法規、準則的具體手段,一是國家的積極干預,即國家根據法規和準則,主動采取行動,保護和支持少數民族的文化特點,促進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二是為維護法規、準則的嚴肅性,對違反法規和準則的行為予以懲處。我國民族政策的特點是以“積極干預”為主,國家主動介入到各種與少數民族相關的社會事務中,比如身份認定、社區發展、國家直接投入和管理的經濟開發項目以及國家主導的文化活動等。
元代民族史觀研究論文
民族史觀是民族史學研究中的重要方面,同時也是史學史研究中關于歷史思想領域的一個重要方面。這方面的研究,對于認識多民族統一國家的發展和認識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史學的發展,都有重要的意義。
元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了全國的少數民族貴族為主建立的皇朝,在這空前統一的國家內,我國封建社會的民族構成與各民族的融合都達到了新的高度。而史學對這一時代特征的反映,也通過民族史觀更為鮮明、突出地表現出來,本文試圖從時代、史學及其二者之間的關系角度來對此問題加以梳理,希望有助于對民族史觀在中國古代史學中的發展規律的探討。
一元朝大一統與民族史觀的時代背景
與遼、金、西夏等皇朝一樣,元代的政治功績在初期大都經由武力而得。這就決定了它在文化方面亦基本遵循從相對獨立發展本民族文化到吸收融合多民族文化的發展途徑。然而,作為中國歷史上統治疆域最為廣袤的封建皇朝,元朝在文化發展上又具有與前者不同的特征:其一,自魏晉起,少數民族在中國歷史舞臺上開始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他們從割據一方到建立與中原皇朝相抗衡的封建政權,再到君臨萬方,統一全國,其勢力發展、演進的軌跡十分明顯,而這一發展的最高點,無疑是元皇朝。這一客觀歷史事實決定了它在吸收各民族文化方面具有前代任何少數民族政權無法比擬的開闊性、廣泛性;其二,元朝統一戰爭也是中國各民族力量進行新的重組的過程,經過戰爭的洗禮,有些民族消失了,有些新的民族產生了。元代建立以后,中國的民族構成基本確定下來,“中國歷史的民族組合,到了元代,可以說是基本穩定下來了,其后雖有滿族的入關,變動并不太大”[1]。在元代統一過程中,有相當數量的其他民族人材為其所用,并立下汗馬功勞,如畏兀、吐蕃、摩些、契丹、回回等民族,他們或為蒙古貴族沖鋒陷陣,或為其勸降招撫,推動了元統一的進程[2]。這一現象說明且決定了元代民族融合具有深厚而廣泛的歷史基礎,即其民族融合的深刻性;其三,受上述兩點決定,元代的文化成為各民族共同創造的結果。就史學方面來說,元代不僅有本民族的史學名著《蒙古秘史》,又有藏族史家公哥朵兒只所著《紅史》、索南堅贊所著《西藏王統記》等關于藏族歷史、文化的重要史籍問世;至于元修三部正史,更是漢、蒙、康里、唐兀、畏兀兒、哈剌魯[3]等各民族、各地區史家共同努力的結果;此外,契丹族耶律楚材、耶律鑄父子,回回族贍思,也是當時著名的史家。在這種情況下,“壤地有南北,人物無南北,道統文脈無南北”[4]就不僅僅是一種政治上的溢美之詞,而是具有了事實上的依據與可能,并進而成為史學當中一種比較普遍的認識。與此同時,民族政權的封建性質所必然帶來的民族不平等與民族壓迫,也成為元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方面。這兩種看似對立的歷史現象,決定了元代民族史觀的多樣性與復雜性。
二正統論與民族史觀
元代史學中的正統之說,論三史修撰者,以修端、楊維禎為代表;而繼南宋正統問題討論余緒者,則多以對《資治通鑒綱目》及三國史事的續作、改訂、闡發為基本方式;從總論角度闡述正統之說者,則以楊奐的《正統八例總序》為代表。其中每家都各持一說,其討論范圍之廣實為前代罕見。從民族史觀的角度來對這些正統觀點進行概括分析,有這樣幾點值得注意:
少數民族榮辱觀教育分析論文
摘要: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是高校德育工作的重要內容,少數民族大學生的榮辱觀除了具有高校大學生的一般性特征以外,還具有特殊的個性特征。要使高校榮辱觀教育普遍深入人心,取得更大的實效,必須重視少數民族大學生榮辱觀的一般性與特殊性,并探索出有效的途徑。
關鍵詞:少數民族;大學生;榮辱觀
2006年3月4日,總書記在看望出席全國政協十屆四次會議的委員時,發表了關于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的重要講話,提出了以“八榮八恥”為具體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講話概括精辟,寓意深刻,是對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道德價值的繼承,更是對當代中國社會的發展脈搏和時代精神的把握,具有強烈的震撼力和引導力,對于培養高素質創新人才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
高等學校擔負著教學、科研和服務社會的重要使命,是培養高素質人才的搖籃,是知識創新的重要陣地,理應在弘揚和踐行社會主義榮辱觀方面走在社會前列,切實發揮好引領、示范和輻射作用。因此,加強大學生的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使他們樹立正確的社會主義榮辱觀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少數民族大學生由于特殊的環境因素、經濟因素以及文化背景的影響,在榮辱觀上,除了具備高校大學生一般性特征的基礎上,還具有特殊的個性特征。隨著我國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和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高校少數民族學生的數字也在不斷增長。要使高校榮辱觀教育普遍深入人心,取得更大的實效,必須重視少數民族大學生榮辱觀教育的一般性與特殊性,并探索出有效的途徑。
一、少數民族大學生榮辱觀的基本特征
遼宋夏金時期的民族史觀研究論文
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歷史格局形成過程中,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和遼宋夏金元是兩個重要的階段。千余年中,中國歷史上的各少數民族與漢族一起,在歷史這個大舞臺上通過矛盾、斗爭、交往、融合,各自為中華文明的發展壯大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亦由此據有了愈來愈重要的歷史地位;與此同時,中國歷史上分裂與統一交互出現,政局時而相對穩定、時而相對動蕩的局面,至元代以少數民族貴族為統治核心建立起空前統一的封建皇朝,基本宣告結束。上述兩點,決定了魏晉至宋元時期民族史觀發展的相對完整性[1]。而其中的遼宋夏金時期,由于少數民族及其統治者所建立的政權對中國歷史面貌起著重要的作用,從而使得民族史觀產生了某些變化與發展,這些變化與發展在受客觀歷史決定的同時,也在不同程度上促進或制約著民族融合的歷史進程,影響著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政治面貌與文化特征;從史學發展的角度講,這些變化與發展不僅成為中國古代史學思想史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且也使多民族史學的固有特征得到了更為突出的反映。基于這一思路,本文大致依據這一時期歷史發展的時間順序和民族關系的特點,粗線條地勾勒不同政權下民族史觀的基本特征,以求得對這一時期民族史觀整體面貌的普遍性認識。
一、兩宋民族史觀的理論形式與史學活動
史學作為意識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發展受到諸多因素的制約,其中最重要者,一是客觀歷史環境的變化;二是占據當時社會主導地位的思想或思潮;三是史學本身的歷史傳統與時代特色。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這三個方面所起作用各不相同,其各自的影響亦或大或小。縱觀宋代史學,在社會相對穩定的北宋時期,史學發展似受后兩種因素影響較為明顯;南宋時期,由于民族問題異常突出,史學則更多地反映出政治方面的要求。
(一)正統論的新發展與夷夏之辨的淡化
作為對傳統儒學的新的闡釋,理學在宋代得到了巨大的發展,成為影響社會各個層面的思想潮流,并對后世政治思想及學術思想產生了深遠影響。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之下,宋代史學的發展亦不免帶有時代的特征,并通過史學著作與史家思想有所體現。具體地講,受理學影響,對當時民族史觀的面貌、特點發生作用的史學思想,首要者當是正統觀的時代內涵。關于正統論的起源,一般以鄒衍五行說為其發端,歷來學者們對它的解釋與運用各執一詞,莫衷一是。然究其本質,卻不外乎以儒家經典的政治思想概念“天”、“德”、“人心之公”、“大一統”等為根本判斷標準,論述某一封建政權是否得其“正”而已,是為史學與政治相結合的產物。大致說來,隋唐以前的正統之說,多側重于從運次、歷數、帝系等五行說角度來展開闡述,故可以“正閏”一詞來概括;而隋唐以后的正統論,則多以功業之實為討論依據,強調“大一統”的成分較多。這說明正統論的發展為了適應現實政治的需要,有一個從五德終始說、運次說的神秘色彩向實用的政治傾向轉變的過程,而這一轉變,需要歷代史家對歷史與現實不斷的思考、推動,經過相當長的時期才能夠完成。在這一轉變過程中,宋代史家功不可沒。
北宋史家言正統,最為系統與最具代表性者,是歐陽修與司馬光。前者側重于從理論角度闡發己意,后者則多通過史書撰述中的論說來揭示主旨。歐陽修論正統的系統觀點,集中體現于他的《正統論》上、下篇中。文章的主要論點可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括定“正統”之義。在歐陽修看來,所謂正統,依據《左傳》的說法,“正”乃“君子大居正”之義,“統”則為“王者大一統”之意。“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后正統之論作”。概言之,“正”乃倫理道德的評價標準,“統”則是政治功業方面的評判原則。二是依據上述標準,對歷代政權作“統”與“非統”的評判,并據此提出了“統”可以續而后絕、絕而后復續的觀點。三是對當時流行的錯誤觀點進行批駁。他認為,“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跡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此觀點“可疑”;魏、梁雖不得予“正統”,但亦不應歸之為“偽”。四是對史學評價中的錯誤方法進行分析與批判,認為“五行之運”是“繆妄之說”,以此為準繩判斷歷史,是“肆其怪奇放蕩之說”;歷史評判過程中的另一個弊端是“挾自私之心”,“為南史者,詆北曰虜;為北史者,詆南曰夷,此自私之偏說也”;因而,作者針對“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晉宋而見黜”的疑問,是從魏的“才德”與功業入手回答的,而不是從夷夏之辨的角度立論[1](卷十六)。由此可見,歐陽修的正統論在理論上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其倫理方面的突出要求反映了理學發展的主要內容;其以功業之實為據評判前代政權的方法則體現出作者對儒家大一統思想的繼承與發展。而上述兩個標準在評判少數民族政權時的同樣適用,則說明正統論在當時史家的認識中,一方面已成為一個有系統的、相對完整的理論;另一方面更體現了民族史觀與正統論在理論上的進一步剝離[2]。
元代民族史觀分析論文
一元朝大一統與民族史觀的時代背景
與遼、金、西夏等皇朝一樣,元代的政治功績在初期大都經由武力而得。這就決定了它在文化方面亦基本遵循從相對獨立發展本民族文化到吸收融合多民族文化的發展途徑。然而,作為中國歷史上統治疆域最為廣袤的封建皇朝,元朝在文化發展上又具有與前者不同的特征:其一,自魏晉起,少數民族在中國歷史舞臺上開始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他們從割據一方到建立與中原皇朝相抗衡的封建政權,再到君臨萬方,統一全國,其勢力發展、演進的軌跡十分明顯,而這一發展的最高點,無疑是元皇朝。這一客觀歷史事實決定了它在吸收各民族文化方面具有前代任何少數民族政權無法比擬的開闊性、廣泛性;其二,元朝統一戰爭也是中國各民族力量進行新的重組的過程,經過戰爭的洗禮,有些民族消失了,有些新的民族產生了。元代建立以后,中國的民族構成基本確定下來,“中國歷史的民族組合,到了元代,可以說是基本穩定下來了,其后雖有滿族的入關,變動并不太大”[1]。在元代統一過程中,有相當數量的其他民族人材為其所用,并立下汗馬功勞,如畏兀、吐蕃、摩些、契丹、回回等民族,他們或為蒙古貴族沖鋒陷陣,或為其勸降招撫,推動了元統一的進程[2]。這一現象說明且決定了元代民族融合具有深厚而廣泛的歷史基礎,即其民族融合的深刻性;其三,受上述兩點決定,元代的文化成為各民族共同創造的結果。就史學方面來說,元代不僅有本民族的史學名著《蒙古秘史》,又有藏族史家公哥朵兒只所著《紅史》、索南堅贊所著《西藏王統記》等關于藏族歷史、文化的重要史籍問世;至于元修三部正史,更是漢、蒙、康里、唐兀、畏兀兒、哈剌魯[3]等各民族、各地區史家共同努力的結果;此外,契丹族耶律楚材、耶律鑄父子,回回族贍思,也是當時著名的史家。在這種情況下,“壤地有南北,人物無南北,道統文脈無南北”[4]就不僅僅是一種政治上的溢美之詞,而是具有了事實上的依據與可能,并進而成為史學當中一種比較普遍的認識。與此同時,民族政權的封建性質所必然帶來的民族不平等與民族壓迫,也成為元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方面。這兩種看似對立的歷史現象,決定了元代民族史觀的多樣性與復雜性。
二正統論與民族史觀
元代史學中的正統之說,論三史修撰者,以修端、楊維禎為代表;而繼南宋正統問題討論余緒者,則多以對《資治通鑒綱目》及三國史事的續作、改訂、闡發為基本方式;從總論角度闡述正統之說者,則以楊奐的《正統八例總序》為代表。其中每家都各持一說,其討論范圍之廣實為前代罕見。從民族史觀的角度來對這些正統觀點進行概括分析,有這樣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正統之說在元代勃興的原因有多種,政治上的因素當為其中首要方面。與遼、金一樣,元朝在建立之初就聲明自己的“正統”地位。這可從元初兩篇詔文中看出來。一篇是于中統元年(1260年)的元世祖忽必烈的《即位詔》,其中說,忽必烈即位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國家之大統不可久曠,神人之重寄不可暫虛”;一是忽必烈本人“雖在征伐之間,每存仁愛之念,博施濟眾,實可為天下主”。所以,盡管忽必烈“峻辭固讓,至于再三”,還是不得不順應上天的指示,“歷數攸歸,欽應上天之命”,做了皇帝。這種神人共濟,奉天承運、以天下蒼生為己任的思維方式與政治詞令,與漢族歷代皇帝即位時說的話如出一轍。另一篇詔文是于至元八年(1271年)十一月的《建國號詔》,它把自漢唐以來的國號進行了排比分類,認為他們或“從初起之地名”或“即始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見聞之狃習”,因此元朝要改變這種狀況,而改變的具體途徑,就是從經典、古制中尋找幫助,最終“取《易》經乾元之意”,定國號為“元”[5]。如果說第一篇詔書是元統治者以“天下之主”的身分頒布的第一份政治宣言,體現了一統天下的政治理想;那么第二篇詔書則通過國號的確定,明確地把元朝統治與堯、舜、禹等先代賢君聯系起來,表示自己在文化、政統上與他們的精神實質是相通的,從而在政治與文化兩個層面上揭示了元代與前代任何政權一樣,都認可、遵循同一價值與倫理觀念。元代統治者的這一思路,無疑對于當時正統之論的興盛有重要的影響。
第二,元代正統論勃興的文化原因在于對興起于宋的理學的發揚光大。理學起于宋而興于元,史學即是這種“興”的形式之一,故而元學與史學結合的特點較為突出。而理學在民族史觀發展中的具體表現,卻需要做不同情況下的具體分析。毋庸置疑,有些史家通過改訂史書的形式闡發正統觀念,主要目的之一即是為了“貴中國而賤夷狄”[6],但也有多史家在正統問題上已經能夠從理論角度把正統與夷夏問題區分開來,如楊奐在《正統八例總序》中把正統分為得、傳、衰、復、與、陷、歸八種情況,并依此把歷代政權進行分類,而夷夏因素并不是他的分類標準。由此可見,不同時期的史家,對理學的理解與運用角度都有種種差別,他們所得出的結論亦不盡相同,甚至會大相徑庭。這里還需要強調的一點是:元代正統論、理學與夷夏大防有著密切的聯系,但三者的內涵與外延并不相同,因而以宋為正統的觀念,在元初是有其夷夏大防的心理認識與文化背景的,但這并不等于說二者就一定是等同的,否則我們就無法理解元代如揭傒斯、蘇天爵等史家一面為朝廷命官,一面卻對宋統之說反復致意的情況。
科學發展觀民族政策優化論文
摘要民族政策是推進我國民族發展的重要手段,在促進民族發展方面能夠發揮中介作用、調控作用、促進作用和規范作用。根據科學發展觀的要求,面臨政策實踐環境的諸多變化,我國的民族政策應遵循服務于各民族發展、體現社會公平正義的原則,不斷實現優化與創新。
關鍵詞民族政策;科學發展觀;優化;創新
科學發展的實質是創新發展,促進民族發展離不開民族政策的推動,在民族發展問題上踐行科學發展觀,離不開民族政策的優化與創新。
一、民族政策的實質與作用
民族政策是執政黨民族治理理念的具體化,是政府為了處理民族問題、改善民族關系而制定和實施的法規、準則以及措施的總和。
法規和準則作為一種規范,規約和導引國家、各級政府、社會團體、普通民眾在對待民族問題、處理民族關系方面應持怎樣的態度、該如何去做,并通過褒揚與懲戒達到維護道義和秩序的目的。措施是貫徹執行和維護法規、準則的具體手段,一是國家的積極干預,即國家根據法規和準則,主動采取行動,保護和支持少數民族的文化特點,促進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二是為維護法規、準則的嚴肅性,對違反法規和準則的行為予以懲處。我國民族政策的特點是以“積極干預”為主,國家主動介入到各種與少數民族相關的社會事務中,比如身份認定、社區發展、國家直接投入和管理的經濟開發項目以及國家主導的文化活動等。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