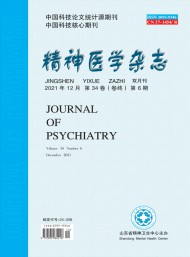精神病學與神經病學的區別范文
時間:2024-03-29 16:55:48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精神病學與神經病學的區別,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軀體化;醫學無法解釋癥狀;醫學史;文化心理學
醫學無法解釋癥狀(Medically Unexplained Symptoms,MUS)是指不能用實驗醫學的生理疾病過程進行合理解釋的軀體障礙,也是軀體化等軀體性心理障礙診斷標準中必不可少的核心條件之一。作為一種精神或心理診斷的必要條件,“醫學無法解釋”的界定卻完全基于實驗醫學的生理判斷標準,反映出軀體化診斷和實驗醫學生理性思維路徑的密切聯系。西方對“醫學無法解釋癥狀”的認識和理解伴隨著近代實驗醫學的發展不斷演變。而對于中國本土來說,這個深刻植根于西方醫學體系的概念在中國文化背景中卻缺乏相應的理解基礎。因此,從本土醫學觀念的角度來反思這一概念,或可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中國人的軀體化問題。
一、“醫學無法解釋癥狀”的解釋變遷
醫學無法解釋癥狀這一概念源自實驗醫學的診斷過程。在西方實驗醫學的解釋模式中,一些軀體癥狀之所以被診斷為“醫學無法解釋”,是因為缺少病理學意義上確定的變化去指向某種疾病實體,比如器官的癌變就能指示癌癥的存在。在臨床實踐中,患者因為癥狀向醫生求助,而醫生則通過診斷來對患者的癥狀做出解釋。當醫生找不到病理學確定的疾病來解釋一個患者主訴中的軀體癥狀,這些患者的癥狀也隨之被稱為難以理解或“無法解釋”的功能性或軀體化癥狀。從這個角度上說,“醫學無法解釋癥狀”的界定建立在一種固定的邏輯基礎上:即通過病理證據對所有疾病進行排除,而這正是在實驗醫學將疾病確定為客觀存在的實體之后才產生的概念。
在歷史上,哪些軀體癥狀或綜合征會進入“醫學無法解釋”的領域和特定時代的醫學技術發展狀況密切相關。隨著實驗室檢驗和病理檢查技術的發展,某些原本被認為是醫學無法解釋的癥狀在發現病因之后變成了醫學可解釋的癥狀;而反過來,新的科學發現也可能否定某些被認為已經得到解釋的癥狀的病因,使其再度成為無法解釋的癥狀。另一方面,某些癥狀在一個時代內“無法解釋”或“原因不明”也并不意味著醫生就會對其置之不理。相反,他們必須做出新的理論假設來努力嘗試解釋這些癥狀。而對“醫學無法解釋癥狀”的解釋假設也是隨著醫學技術和觀念的發展而不斷變化的。
前科學時代的醫學其實并不存在所謂“無法解釋”的癥狀,因為大部分病痛體驗也無非是用前科學醫學觀念下的一些假定的原因來加以解釋的。比如,最初源于古希臘的“歇斯底里”(hysteria)這一概念,其希臘語原意就是“子宮”。整體性的樸素唯物論將這些和情緒激動共同出現的軀體綜合征解釋為集中于特定身體器官的紊亂,尤其是帶有特殊道德意義的生殖器官。文藝復興之后,對解剖學的進一步理解導致神經系統疾病被當作無法解釋癥狀的病因,這種觀念將歇斯底里、疑病癥等原因不明的軀體綜合征逐漸劃歸到一個分類之中。1667年,英國權威解剖學和神經學家Thomas Willis從腦解剖學角度對各類“神經性”疾病做了研究,批判了傳統認為歇斯底里產生自子宮的觀念,轉而認為歇斯底里中的激情癥狀通常來自頭腦,但其源頭仍然是生理性的病變(Sharpe & Carson,2001,pp.926-930)。
在17-18世紀,精神病學逐漸發展,心理因素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但在精神病學發展的初期,醫生們所認為的“典型”精神疾病只包括喪失心智,抑郁和躁狂等單純具有心理癥狀的狀況,很少有學者將歇斯底里和疑病癥拿來和這些疾病相提并論(福柯,2005,第399頁)。而到了19世紀,隨著精神病學逐漸建立自己的體系,越來越獨立于普通醫學體系,醫學無法解釋癥狀開始在兩種不同的解釋路徑上發展,而這兩種路徑分別處于身體和心理兩個平行的維度上。其中一條路徑是神經學家和生理學家的生理性解釋,另一條路徑則是將發展為精神分析理論的心理生成論(Psychogenesis)觀點。在精神分析學派崛起之前的一段時期,神經生理的解釋一度占據主流,無法解釋癥狀公認的病因是神經系統的可逆性失調。但是,逐漸發展的病理檢查技術始終未能證明腦部或其他器官存在可觀察的解剖學異常,這就導致這些生理失調被稱作微妙的或“功能性的”(Trimble,1982,pp.1768-1770)。
這種神經生理解釋的一個典型就是19世紀中期由George Beard提出的“神經衰弱”的概念。Beard總結了當時在美國廣泛流傳的一類原因不明的軀體綜合征,將其命名為“神經衰弱”,即“由過度疲勞引起的神經機能衰竭”,其癥狀包括多系統多項軀體痛苦,比如全身不適,功能衰弱,食欲不振,長期神經疼痛,失眠,疑病以及其他類似癥狀(Beard,1869,pp.217-221)。Beard認為這些神經系統上的虛弱或疲憊以及各種精神和身體的低效癥狀是由于神經功能的一些可逆的失調所造成的。神經衰弱的概念幾乎包括了所有非器質性生理功能紊亂和多種由于心理社會原因引起的心理生理障礙。而雖然身為神經病學家的Beard和那個時代的其他醫生一樣,都沒有直接的科學證據證明中樞神經系統真的存在功能失調,但他仍然更強調神經衰弱病因學上的生理性而不是心理性。其后,同為神經生理學家的Charcot將Beard總結出的這種疾病在理論上進行了進一步擴展,使其從先前被人認為的“美國病”變成了一種國際化的疾病(Goetz,2001,pp.510-514)。
19世紀的解釋模式轉向最終明確地區分開了生理和心理的病因,而所謂的“醫學不可解釋”根據這種二元劃分,最終被交給了精神醫學。20世紀,心理分析的時代到來了。腦部功能失調的概念大部分被心理發生概念所替代。由此,無法解釋的軀體癥狀的治療完全成為心理學以及精神病學的管轄范圍。Freud的支持者,奧地利精神醫師Stekel(Stekel,1924,p.341)創造了“軀體化”一詞用來解釋精神問題如何表現為軀體癥狀,其所表達的心理機制和Freud的“轉換”概念如出一轍。當1980年,美國精神病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APA)修訂《精神疾病診斷和統計手冊》第三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Ⅲ)時,特別劃分出一類以軀體痛苦為主的精神障礙,即軀體形式障礙(somatoform disorders),這個診斷逐漸被世界其他重要的精神診斷手冊所接受。而伴隨這個診斷分類及其標準一直延續下來的核心條件之一正是“醫學無法解釋癥狀”。
二、“醫學無法解釋”的邏輯基礎:普通醫學和精神醫學的二元分裂
回顧“醫學無法解釋癥狀”在啟蒙時代之后的歷史可以發現在實驗醫學內的一種解釋模式的反復和循環,而這也是普通醫學(medicine)和精神醫學(psychiatry)逐漸分裂的一個寫照。17世紀Willis對歇斯底里的分析和19世紀Beard對神經衰弱的定義都曾經是一度占據主流并影響巨大的理論觀念,他們的理論代表了原因不明軀體癥狀的解釋模式中一種相似的路線:從生理角度將此類綜合征歸于一種神經生理系統的疾病。而在Willis和Beard對歇斯底里和神經衰弱的經典論述之后,兩種疾病理論的發展也同樣經歷了一個相似的“轉向”:由“真實”生理疾病變成“無中生有”的心理障礙。在歇斯底里的例子中,傳統的子宮沖動學說隨著解剖和生理學的發展,逐漸轉變為由大腦主導的神經系統作為中介的紊亂,但并沒有改變此類疾病植根于身體的基本觀念。可這個主題在18世紀卻從身體空間的動力學變成了心理空間的倫理學,使歇斯底里和疑病癥進入了精神病學的領域(福柯,2005,第410頁)。同樣,在神經衰弱的例子中,隨著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心理學和精神分析理論影響的日漸擴大,神經衰弱也被逐漸納入到精神分析的情感沖突框架中。導致癥狀的潛在的情感因素變得比表面的軀體癥狀更加重要。在診斷上,神經衰弱也逐漸被認為是一種純粹的心理問題,最終被抑郁癥爭情感障礙或心境障礙所替代(汪新建、何伶俐,2011)。這些例子顯示出,在醫學科學的疾病分類一直到精神病學理論觀念建立之初,醫生首先會嘗試從神經系統疾病的角度解釋“醫學無法解釋癥狀”。在現代的醫學系統中,醫生也是首先從他們自身所屬的醫學專科考慮能否對癥狀做出解釋。而當病痛和癥狀被醫學排除在外,它們才最終落腳于心理學和精神醫學的領域。由此可見,被認為是“醫學無法解釋”的這些軀體綜合征與其他典型的心理問題或者精神障礙不同。按照醫學科學的身心二元觀念,這些主觀的軀體癥狀和病痛體驗最初進入的應該是非精神科的普通醫學話語體系。
科學觀念中的機械身心二元主義對疾病和醫學觀念的主要影響之一就是精神病學從普通醫學中分離出來,將身體病痛留給醫學,將精神病痛留給精神病學。在笛卡爾的機械二元論之后,被客體化的身體只是一種“機器”,它與遵循科學規律運行的物質世界中的其他“系統”沒有什么本質區別。身體獲得了機器的隱喻,而疾病就是“機器拋錨、燃料缺乏或者摩擦過多引起的機械故障”(波特,2007,第59頁)。這個純粹物質性的“機器”是神學家和倫理學家不能涉及的,專門屬于醫生的領域。而心靈卻又經歷了另一種意義的轉換,一方面心靈是理性的來源,是決定人類思維與意識的基礎。另一方面,心靈也是一種系統,一種“機器”,它也能被科學化,并逐漸喪失原本的道德倫理意義,而變成另一種客觀存在物。這個心靈被降格的過程則是心理學和精神醫學產生的起點。
在西方醫學科學的體系中,精神病學雖然誕生自醫學,也一直被當作一個醫學專科來看待,但在很多語境中它明顯有異于其他醫學專科,甚至和它們對立起來。對于以生理解釋為主體的現代西方醫學體系來說,精神病學始終缺乏等同于普通醫學的合法性。20世紀中期Szasz曾針對精神病學展開頗有影響力的全面抨擊。通過分析歇斯底里和精神分析這段經典歷史,Szasz聲稱精神疾病并不像癌癥等醫學意義上的疾病一樣“真實”,因為沒有生物化學檢驗或神經生理發現能夠證實其存在(Szass,1974)。他認為精神疾病是用來偽裝道德倫理沖突的神話:“嚴肅的人不應該將精神病學當同事――它只是對理性、責任和自由的威脅。”(Szasz,2008,p.2)雖然有不少學者和精神醫學從業者認為Szasz的批判過于極端,但卻也難以否認其主張中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精神病學分類中的疾病和障礙確實缺乏科學意義上的充足證據,特別是以軀體病痛為表現的心理問題,比如軀體化。進一步說,圍繞軀體化疾病分類和診斷邏輯的爭論正是整個精神病學遭到批判的縮影。普通醫學和精神病學在身心歸屬明確的疾病或問題上,兩者分工明確,“合作愉快”。但在軀體化現象這種本體和性質模糊的問題上,兩者似乎就產生了齟齬。一定程度上,正是疾病分類體系對疾病體驗的規訓使得軀體化成為現代生物醫學的“棄兒”(汪新建、王麗娜,2013)。
三、從本土醫學觀念看“醫學無法解釋癥狀”
對于大多數非西方社會而言,西方的現代醫學體系是一個外來物,與醫院模式、醫療保健體制相互捆綁,隨著整個現代化進程“空降”而來。對于中國來說,雖然早在明清之際就對一些流傳而來的西方醫學知識有所了解,但真正采用西方的醫療體制和診斷系統,也不過就是一個世紀以內的事情。本土社會接受的是在西方經過長期發展,已經成形的一整套體系,對于“醫學無法解釋癥狀”中所反映出來的普通醫學和精神醫學具有歷史淵源的糾纏與競爭,恐怕沒有多少切身感受。
首先,從中國傳統身體觀和醫學觀的角度看,將患者的病痛原因劃分為“醫學可以解釋”和由其他原因解釋的“醫學無法解釋”是一種不太自然的做法。在本土醫學觀念中,“醫學解釋”應該是一個整體性的知識,包括對所有病痛和不適的解釋。其典型如宋代陳無擇提出的三因學說,將病因根據來源分為外因、內因、不內外因三類,“然六,天之常氣,冒之則先自經絡流入,內合于臟腑,為外所岡。七情人之常性,動之則先自臟腑郁發,外形于肢體,為內所因。其如飲食饑飽,叫呼傷氣,盡神度量,疲極筋力,陰陽違逆,乃至虎狼毒蟲,金瘡圻,疰忤附著,畏壓溺等,有背常理,為不內外因”(陳無擇,2011,第22頁)。外至風邪入侵,內至情志所傷,這些病因全部共同作用于患者的身體。
而這種傳統的病因解釋和診療模式究其根源則在于傳統的思維模式和身體觀。傳統思想與醫學理論往往以天人類比的方式,建構身體概念。身體通過陰陽五行、四象八卦等天地萬物的共有本源與整個自然世界相互貫通。又有“五行配臟”的理論,使身體各部分不但和陰陽之象相互對應,而且喜、怒、悲、憂、恐也是通過配屬于五行而與各自對應的臟器聯系到一起。由此,個人的情志通過陰陽五行的意象連結到身體各部分以致宇宙萬物上。中國文化中的身體也就成為了一個天人相應、內外相通、與自然世界具有有機聯系的功能系統。純粹物質的軀體只是身體系統的一部分,而軀體與心理之間又存在天然的聯系,共同組成一個身的整體,其內部存在普遍聯系、相互交感的關系。中國人談到“身體”時,并不進行軀體和心智的劃分。身體本身是人的健康和疾病狀態的基礎,它同時也參與心理、精神層面的活動。因此,中國人的“身體”牽涉到無形的精神、心靈、情志,是生理與心理的交互作用而成的一個整體。
正因為這種傳統的身體觀,傳統中醫也不存在針對軀體、器官或針對精神、心理的兩種醫學專科的二元分裂。在整體性的身心系統中,心理與生理并無本質區別,而只具有功能和形式的區別;它們的運作沒有機理的不同,只有具體表象的不同。因此,在本土觀念中,身體的疾病也自然涵蓋心理與生理的雙重維度,不必再行區分。在傳統中醫的臨床實踐和診療模式中也并不是不存在分科,患者的疾病原因也有內外之分,但醫生必須能夠對所有可能的病因做出判斷并加以應對。
除了中國本土身心整體觀念和西方二元論的差異,從傳統中醫的診斷方法上看,“醫學無法解釋”的說法也很難被習慣了傳統醫學診療模式的患者所接受。無論古今中外,所有醫學體系都必須為患者的病痛尋找某種“解釋”,這也是診斷的意義:醫生必須要通過他的診斷告訴患者,他的痛苦是什么,原因何在。但是“解釋”的方式以及能夠被患者接受所必須具備的條件卻可能因為文化不同而有所差異。以科學主義為基礎西方實驗醫學的“醫學解釋”必須要依賴于生物病理證據建立的嚴格因果。而在中國本土社會,中醫對疾病病因和過程的解釋依據的則是中國人傳統的意象思維模式。這種思維模式的因果判定方式與科學模式不同,它以主體意向判定事物之間的聯系,對因果關系進行主觀性、體驗性、感悟式的論證,因此傳統醫學的理論通過理論本身的自洽性和個案例證即能建立其自身的合法性(呂小康、汪新建,2013)。這種解釋模式并不用證實關于某種疾病實體的“假設”,也就不要求科學嚴謹的因果性證據。
意象思維的影響又體現在中醫的“辯證”模式中。中醫的對象并非是西方科學定義下的“疾病”,而是一個本土概念“證”。中醫所說的虛、寒、熱等證候并不是西方醫學中的“疾病”那樣的客觀實體,它們既是現象的描述,又附有本質的概括,這就是所謂“西醫辨病,中醫辨證”(呂小康、汪新建,2012)。而在中醫的辨證模式下,其實所有體驗都可以和這些體驗性、感悟性的隱喻及意象連通到一起。一些帶有情志因素的身體病痛按照嚴格的科學觀念無法加以解釋,但是其中卻表現出直觀的心身影響或交互作用,在本土的文化中被歸結于意象性的“氣”、“火”、“經絡”等概念。對于并不太了解醫學理論的患者而言,這些概念也可以被看作是對某些生命“力量”或“能量”的隱喻,它們也許是直接從外界侵入,也許是身體受到外界刺激后而產生。通過這些隱喻所給出的“為什么生病”的解釋也不難接受:這些力量或能量的起伏擾動了身體系統的整體平衡和正常狀態,導致了各種非正常狀態的產生。
已有研究發現,即使在西方社會,對軀體性病痛給出純粹“心理和精神”的解釋也較難得到所有患者的接受,其主要原因是患者主觀體驗到的病痛是身體狀態(Kirmayer,Robbins,Dworkind,& Yaffe,1993,pp.734-741)。而中國傳統意象性診療觀的文化環境熏陶下的本土患者可能更難以理解和接受“醫學無法解釋”。患者并不清楚“醫學無法解釋”中暗含的普通醫學和精神醫學的劃分,因此在科學角度上嚴謹合理的“醫學無法解釋癥狀”這一條件,對于患者來說卻更像是醫學在解釋他們的問題時表現出的一種“無能”。“醫學無法解釋”還暗示著患者的癥狀不是真的,這種對想象性疾病、詐病和偽病的暗示也是對醫患相互信任的一種損害。而本土的診療模式卻相當依賴這種信任關系來獲得體驗性的病痛主訴,并總能根據患者的主訴提供一種寬泛的醫學指導,形成一種“治未病”的醫學傳統(呂小康、鐘年、張紫馨,2013)。這種傳統未必能夠在所有案例上得到科學的驗證,但仍是極強的文化傳統,對塑造患者的求診模型和疾病表達體驗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四、軀體化診斷的本土反思
“醫學無法解釋癥狀”的種種問題反映出軀體化這個概念及一系列相關診斷在西方醫學體系中的內在矛盾。從西方實驗醫學體系內部而言,“軀體化”作為一個獨立的心理障礙面I臨合法性危機。“醫學無法解釋癥狀”這個軀體化定義和診斷的核心條件突出地反映了近代以來西方科學醫學體系中普通醫學和精神醫學的二元分裂。而這種貫穿本體論和方法論的二元主義又恰恰是中西方醫學在觀念和診療模式上差異最大的部分之一。這種矛盾在中西方的文化差異中被進一步放大,導致軀體化顯示出獨特的文化不適應性。
在治療方面亦是如此,身心二元主義劃分的代價是限制了有效的心理療法和普通醫學實踐的整合。以目前的臨床醫學系統來說,如果患者首先不是進入精神病學專業科室,而是進入初級保健中,那么大多數主訴是“醫學無法解釋的軀體癥狀”的患者都能夠得到各個專科的解釋:纖維肌痛、腸易激綜合征、神經性胃炎等等。對于各專科醫生來說,這些診斷能夠被患者接受,而患者也能夠得到處置,也就是說這些解釋在初級保健系統中具有很好的適應性和“合法性”。對于內科各科室的醫生來說,主訴軀體癥狀的精神障礙,比如“軀體化”等概念,其合法性可能還不如各類功能性綜合征。因此,雖然心理療法可能對患者很有幫助,但仍然有很多去非精神科看病的患者無法得到這些治療,而另一些患者則根本不接受精神疾患的解釋。一方面,在普通科室,醫生和病人可能不斷重復沒有結果的醫學檢查和干預;另一方面,稱這些病人具有精神病學問題,轉介精神科,讓他們覺得受到誤解和污名化。患者可能被留在一個狹窄的“無人區”:生物醫學方法否定他們的癥狀是生理性質的,而他們自己又拒絕心理解釋(Quill,1985,pp.3075-3079)。
西方醫學和精神病學界并不是沒有注意到這些問題。正是因為“醫學無法解釋”這一條件造成了軀體形式障礙診斷在病因學上的模糊性,美國精神病學會在新版本的修訂中去除了這條標準(APA,2013)。但是這種修訂卻引發了更大的爭議。眾多反對者認為,如果去除“醫學無法解釋癥狀”這個條件,就會模糊軀體化一類心理障礙和醫學狀況之間的明確界限。而界限的模糊將可能會擴大精神障礙的范圍,將很多確實患有醫學疾病的人群錯誤的指為“精神障礙患者”(Frances,2013)。可見,在基于身心二元主義的西方實驗醫學體系中,跨越身心兩個領域的軀體化問題是個難以解決的“痼疾”。如果嚴守科學主義的機械二元論分野,當前被診斷為“軀體化”的心身病痛體驗無論如何都必須被一分為二:或是歸為心理領域的疑病癥,或是歸為普通醫學中的各種功能性綜合征。如果像此次DSM修訂一樣,簡單地在診斷標準上去除二元主義暗示,就會陷入與醫學科學觀念的基礎相抵觸的境地,使精神病學本身遭到“試圖入侵醫學領域”的指控。
篇2
對于醫學的哲學反思同醫學以及哲學的歷史一樣古老,諸多哲學家和醫師都對此有著獨到的見解。20世紀中葉,美國的醫學人文運動方興未艾,促發了許多學者對醫學的哲學探索。當時,具有代表性的工作有:馬賽爾(Marcel)、梅洛龐蒂(Merleau-Ponty)和斯派克(Spicker)對身體哲學的研究;斯特勞斯(Straus)等對精神病學和心理學的哲學基礎的反思;恩格爾哈特(Engelhardt)對健康與疾病觀念的關注,以及對醫學倫理學的哲學基礎的研究;拜談迪克(Buytendijck)對生理學和人類學的融匯;萊因恩特格(Lain-Entralgo)對醫患關系境遇的分析;瓦托夫斯基(Wartofsky)對人類本體論和醫療實踐的質詢;甄納(Zaner)在一系列文章中,深入地研究了人類自身的本質屬性、人際間的紐帶(尤其是在醫學語境中)以及“促因”在醫學教育中的含義。到了晚近出現了是否存在這樣一個領域即醫學哲學的爭論。如果存在的話,是由哪些部分組成的?能將其與科學哲學相區分嗎?它與剛剛出現的生命倫理學是什么關系?這些區分會引發什么樣的實踐后果?佩里格里諾肯定醫學哲學的存在,指出醫學不是純技術的科學,他認為置于科學與人文之間的醫學,是一種人類增進個人和社會福祉的最有力的潛在工具。為了實現這一目的,醫學必須對當下的潮流有所回應,并在其科學的、倫理的和社會的視角下建立起一種新的聯合。如果達到這一目的,醫學就擁有了世界急需的新人文主義的能力,即,使技術服務于人類的目的。而醫學哲學能夠成為新的聯合的載體。在《醫療實踐的哲學基礎》一書中,佩里格里諾和托馬斯馬提出了一種醫學哲學觀點,即醫學的核心在于醫患之間的關系,而這種關系的目的則直指治愈。當然,這不是否定來源于還原論的科學技術能力的重要性。正如佩里格里諾和托馬斯馬指出的,“如果不能充分的滿足技術上勝任的預期,那么,醫療職業行為必將是虛偽和謊言。”技術上的勝任,對于治療行為而言,只是必要而非充分條件。“勝任本身必須服從于醫療行為的根本目的,即為特定的病人提供正確的和良善的醫療行為”。佩里格里諾的醫學哲學直接而清晰地來源于他對這一學科的本質與目的等基本問題的探討。臨床醫學這門學科并不是科學、藝術或者手藝,它是一門完整的、實踐的學科,植根于不變的醫患之間存在的治療關系這一事實。換句話說,臨床醫學是兩個個體之間的關系,一方是尋求治療的個體,另一方是承諾運用知識、技藝、經驗以及為了病人的利益而進行治療的個體。那么,這種關系的目的或目標便是為病人提供正確的、善意的治療措施。佩里格里諾認為醫學哲學要解決兩個問題:除了回答“是否存在,由哪些成分構成”這個基本問題,還要探究其構成的模式。因此,他比較、對比和區分了四種不同的對醫學進行哲學探究的模式,即醫學和哲學、醫學中的哲學、醫學的哲學以及醫學哲學。第一種關系型式,醫學和哲學(PhilosophyandMedicine),醫學和哲學仍然是完全獨立的學科,每一個學科都從另一個學科的內容或方法中吸取某些東西來闡明自己的事業,例如,精神哲學家利用神經病理學的經驗資料提出身—腦—心關系這一概念;或者,醫生利用形式邏輯這個工具建立一個診斷或治療的符號或算法系統。
第二種關系型式,醫學中的哲學(PhilosophyinMedicine),哲學家們運用哲學探究的形式工具,如邏輯、形而上學、價值論、倫理學和美學,來考察作為研究對象的醫學本身的問題。探究的對象是一組認識論的和非認識論的問題。第三種關系類型,醫學的哲學(MedicalPhilosophy),后者與其說是一種哲學類型,還不如說是一種寫作風格。充其量它包括對醫學的職業狀況作了一些富有見識的研究,這些研究純化了其氣質,提高了其志向。但就它最糟的方面而言,醫學的哲學就是一些個人的意見、離題的爭論、或對逝去的榮華和特權的挽歌。即使在它的全盛時期,醫學的哲學也沒有對醫學作集中的形式考察,以使自己有資格作為哲學而存在。這一類型,以當下的術語來定義的話,是最為含混和松散的,包括任何非正式的對醫療實踐的反思。主要是由臨床中的醫生基于自身臨床實踐而產生的反思。當然,這一類型的醫學哲學是善于思考的醫生的臨床智慧,對那些盡責的醫生而言,這些始終是靈感和實踐知識的來源。第四種關系類型,醫學哲學(PhilosophyofMedicine),集中對作為醫學的醫學進行哲學探究。它力求界定“作為醫學的”醫學的性質,建立醫學和醫學活動的某種一般理論。在這個標題下,經受醫學中的哲學考察的一系列問題,要被綜合成為某種自洽的醫學理論。在佩里格里諾看來,一門學科或一種活動不論它是科學、法學、政治學、還是醫學的哲學,探究這一學科或活動的性質——它的發現事實的程序、它的邏輯和它賴以建立的形而上學預設。把一門學科的邏輯學、美學或倫理學同這門學科分開,可能比把它的本體論的、認識論的或價值論的方面同它分開更為困難。但是,在任何一種情況下,該學科的哲學都是運用一些方法并從超越該學科本身的觀點出發,從該學科外部來考察這門作為探究對象的學科。看來佩里格里諾主張的是一種范圍更小更為集中的醫學哲學,旨在探求醫學本身的哲學化知識。也就是,關于醫學是什么和如何將醫學同其他專業和學科相區分的知識。在他的視野中,醫學哲學就是“對終極性的尋求,通過研究去掌握事物的實在根基,而這種研究本身超越了學科自身的認識范圍。”綜合上述所做的分析可以看出,佩里格里諾認為醫學哲學應當定義為第四種關系類型。也就是說醫學哲學是一門可定義的學科,并擁有其獨特的俯瞰醫學的視角。醫學哲學的主題與目的同以科學為基礎的醫學迥然相異。對于佩里格里諾而言,醫學哲學能夠拓展我們對臨床醫學的認識,以及幫助我們如何將其與其他學科相區別。醫學哲學通過審視患者疾病的本質和影響、治療的概念、臨床決策的復雜性、醫患關系中的道德層面、謬論、人類生命的局限以及更多層面來達到上述目的,從而幫助我們認識到臨床醫學與哲學之間辯證關系的重要性。佩里格里諾在其學術生涯中一直以此主題為圭臬,從而展開他的整個哲學計劃。他的哲學計劃有兩個主要目的:其一,發展系統的醫學哲學;其二,揭示醫學的道德基礎,即一些能夠限定特定的醫療行為中人際關系道德性的不可消減的理論資源。
二、需要什么樣的醫學倫理學?
佩里格里諾認為,醫學哲學不只是對醫學特有的現象進行哲理探究,即不只是醫學中的哲學。它力求理解和規定醫學現象的概念基礎。醫學哲學是具有實踐后果的不可缺少的事業。我們認為醫學是什么促成醫學做什么,我們如何塑造醫生角色,以及或許最重要的是如何構造醫生倫理學。盡管在醫學領域的哲學家們已經擴展了我們對于當代醫學中的倫理學問題的理解,但很少有人把他們的倫理學論述建立在醫學理論的基礎之上。隨著倫理學問題變得更加困難和對醫學應該是什么的理解變得更加歧異,迫切需要形成作為一種活動的醫學的某種自洽的理論。一種醫學哲學有助于建立解釋醫學活動的性質的命題庫。提出這些命題,對它們進行批判性考察并綜合為一種自洽的理論整體,乃是這種醫學哲學的任務。無疑,佩里格里諾是在獨特的歷史背景中提出這種主張的。在談及二戰前美國醫學倫理學的情況時,佩里格里諾回憶道:“以我為例,我并不記得什么時候醫學倫理學被關注過,除了在學生和住院醫師之間的一些非正式討論以外。天主教的學生對涉及產科實習的一些難題有所關注。在極大程度上,我們要發現怎么做是正確的。對于天主教學生以及非天主教學生來說,墮胎和安樂死都是被譴責的。同樣,企業化運營的醫學,追求利益的醫生所開設的醫院也是被譴責的。”二戰后,醫學倫理學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主要有兩個根源:首先是科學進步為醫學所帶來的非凡的能力擴張;其次是我們時代所特有的社會經濟力量和政治權力的融合。第一點促進了生物醫學倫理學的發展。第二點則為醫學倫理的發展,即醫師對病人特有的責任,或者說是作為真正的醫師(physicianasphysician)的倫理,提供了契機。在這樣的背景下,他清醒地認識到大多數醫學倫理學實際上只是醫學道德,表現為一系列的缺乏倫理辯護或論證作為根基的道德規則和斷言。沒有倫理辯護作為根基,這些道德規則將是無效的,很容易被挑戰、否定或者折衷。正是由于充分地認識到了原有的作為醫生職業道德規范的醫學倫理學的不足,如希波克拉底誓言中的規范沒有以確鑿的倫理學或哲學為基礎進行證實,佩里格里諾積極撰寫醫學倫理方面的著作,探索以醫學哲學為基礎的醫學倫理學。醫學倫理學建立在對醫學哲學的概念進行歷史的回顧與梳理基礎之上,佩里格里諾指出,醫學事業是具有其自身的合理內核的,這種實在的內核是基于醫學中的三種現象而建立的。即:
(1)生病或疾病作為一種存在的因素;
(2)由為陷入疾病困擾的病人提供幫助的醫生所做出的允諾或表白;
(3)治療的行動,即由醫生領會到的并做出的技術上正確、道德上為善的并滿足病人需要的決定。這三種普遍現象的緊密關系——生病、承諾治療和治療本身——為現實世界中醫生與病人的相互責任提供了基礎。從而,他成為最早認識到醫學倫理學必要性的主要人物之一,并宣告了一個時代的來臨,即嚴肅、批判地理性思考醫學道德的時代——醫學倫理的時代。當對醫學倫理學進行深入的、嚴肅的探究時,歷史學的和社會學的批評解構了希波克拉底的道德規范與方式,古代普遍的醫生守則也被嚴重地蠶食了,當下社會需要一種“新的”更加適應時代和道德多元性的倫理規則。于是涌現出大量的將現有的哲學或神學體系運用到醫學的情況。這些體系被“應用”,或者說得好聽點是被有條理地應用到醫學及其實踐中。醫學的倫理規范沒有從醫學的本質出發,即將醫學視為一種特殊的人類活動,進而審視醫學中的實際道德境遇。與這一潮流相左,佩里格里諾不同于其他理論家的是他主張醫學倫理學研究應當采取“自下至上”的方法,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方法。他認為醫學倫理學的研究應當是首先審視醫學本身,然后再從頭建立起一套醫學倫理學理論,而不是把一套現成的但可能存在很多爭議的一般理論拿來然后應用到醫學實踐中。醫學倫理學要想擺脫這樣一種存在道德紛爭的研究進路,只有對醫學本身進行闡釋,對醫學實踐有一個更清晰的理解,然后再努力尋找醫學的道德義務。換言之,醫學倫理學應當是醫學哲學的一部分,而不是簡單地將倫理學理論應用在醫學問題中。佩里格里諾一直認為,醫學倫理學應當建立在醫療關系的本質上,即醫學哲學之上。“我的論點是,并且仍然是,醫生所特有的義務是從患病的人和他尋求醫治的人之間關系的特殊本質而來的。作為結果的這一關系有著一定的特征并使由此而來的相互之間的道德責任具有了獨特的屬性。”鑒于當今社會的異質性和科學醫學的普遍化特征,任何一種堅實的醫學道德哲學都必須植根于醫學的“內在”之中。不能如既往一般,單單從外在的哲學化體系中抽取而來。這種道德哲學應當建立在以下四個方面的基礎之上:人類疾病的現象;醫學知識的獨特本質;臨床決策的道德特性;對于醫學作為一門職業的強調。直到晚近,職業倫理中仍包含了大量的道德斷言和闡述,并以此定義醫生應當如何行為。這些斷言往往是在缺乏清晰的和正式的道德論證的基礎上作出的,這些構成了希波克拉底倫理的骨架,并在其后繼者中得以延續。大多數情況下,與這些道德論斷相符的哲學預設都是來源于外在于醫學自身的哲學體系。上個世紀60年代末,幾個世紀以來一直被奉行的道德主張出現問題時,作為一門正式學科的醫學倫理學才真正出現。這也是首次,這些道德主張受到正式的分析,并作為普遍倫理的特殊情況加以對待。那些長久以來忽略了醫學倫理的職業哲學家,開始以初確原則(primafacieprinciples),即行善、自主和無傷來澄清醫學倫理學的內容,并在此基礎上闡釋了次級原則,包括保密、講真話和信守承諾。這是英美倫理學的分析路徑,其主要哲學基礎來自于休謨,康德和密爾。佩里格里諾認為這種原則主義的思想進路并不能滿足醫學倫理學的全部需要,因此美德在他的醫學倫理統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它所關注的是邁向理想目標的進程。佩里格里諾頗為認同亞里士多德的美德觀,盡管大多數情況下,他認為美德是一個具有多個方面的“概念”,而并沒有給出一個準確的定義。他采用了美德即“具有良好行為的習慣”這一定義,但反對亞里士多德將美德視作極端的平均。他將美德定義為:“美德是一種品格特性,是一種內在傾向,習慣性地追求道德的完美,生活中遵守道德規范,并且在高貴的思想和公正的行為之間追求一種平衡。”事實上,在佩里格里諾看來,醫學對于道德行為需要一套更高的標準,而選擇這一個行業的人就應當追求美德,并構成一個新的道德共同體。
三、生命倫理學走向何處?
“生命倫理學”(bioethics)是由生物學(biology)和倫理學(ethics)這兩個詞合成而來的新詞。其中的一個術語,“倫理學”,傳統上被視為哲學的一個分支。然而今天,許多自稱為生命倫理學家的人卻不認為他們的工作是哲學的一個分支。他們中許多人認為哲學不足以涵蓋道德生活的復雜性,更有甚者將哲學視為一種障礙。他們認為哲學的倫理學過于理論化、抽象并且對語境的、實踐的和復雜的道德選擇行為不夠敏感。對生命倫理學,他們持有一種更加擴大化的視角,認為它應該包括更廣、更多的學科,并假定這些學科可以彌補哲學倫理學的不足。今日之生命倫理學,已經介入到司法與立法的決策、公眾的爭論、倫理委員會和臨床會診之中。這些形形的大量的“生命倫理學”實踐暗示了一種權威性和可信性。新生的“生命倫理學家”這一職業為技術專家提供對“道德困境”的分析與決議,這些“道德困境”包括臨床、政策信息以及日常生活等方面。佩里格里諾認為生命倫理學應該是各學科之間交互的。需要考察的問題是:在不喪失倫理學中心學科位置的情況下,哲學怎樣和其他學科(比如,文學、法律、歷史、神學、語言和語言學),還有以人文為目的的社會科學(人類學、經濟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相互發生聯系。他說:“我認為生命倫理學意味著廣闊范圍的質詢,但我更意圖指出,在這些領域中,哲學有著獨特的地位。哲學化的倫理學必須與其他相關學科對話,但它不能也不應該被它們涵蓋或取代。”佩里格里諾在其生命倫理學研究中,始終圍繞臨床境遇展開,他致力于定義臨床醫學,而非預防醫學。他主張臨床境遇應當包括:科學知識,醫生的推理過程,人際關系,以及針對每一個病人的治療。這一定義暗含了醫生應當做什么,應當知道什么,以及他們如何被教育。他認為臨床倫理學中的醫療道德之核心是治療關系。這是由三種現象——疾病這一事實,作為職業的行為和作為醫療的行為——所定義的。第一種現象將病人置于一種脆弱的依賴地位,并導致了一種不平等的關系。第二種現象意味著對幫助所做出的承諾,第三種現象則包含了做出醫療上合理的治療決策的行為。因此,臨床倫理學關注的核心是作為個體醫生和病人所做出的決策。而生命醫學倫理則是一個更寬泛的學科,涉及倫理學原則的應用到所有生物醫學知識,并將倫理學分析從臨床境遇拓展到法律和政策層面。臨床倫理學關注的焦點比生命倫理學更為集中:旨在通過明確、分析和解決臨床實踐中的倫理學問題提高衛生保健的水平。臨床倫理希望為病人尋找一個更好更合理的治療決策和行為并成為醫生的工作和醫學實踐固有的一部分。臨床倫理學總是被用于一種非常迫切和緊迫的情況。通常是在急診室或者情緒糾結的氛圍中使用。它需要我們具有扎實的臨床語言和臨床知識。需要面對和處理醫生、病人、家庭、法律、社會習俗和宗教信仰方面價值觀的沖突,從而做出臨床決策。臨床倫理學與治療的標準有關。在過去家長制的醫學形式下,照顧的標準主要是醫生為病人做出的技術層面的決策,如今的照顧標準越來越代表了有能力的成年病人的決策,當然這是在醫生根據技術方面的考量向他們提供一些建議之后。因此,盡管倫理學的考量一直在發揮著作用,但所強調的重點已經發生了轉移。之前,醫學的最高倫理學標準是醫生的能力和良心,而現在則還要兼顧對患者價值觀和自我判斷的尊重。顯然,佩里格里諾堅持認為生命倫理學應當回歸臨床,并且關注病人的尊嚴與價值。與過去不同的是,當代醫學常在科學與人文的對立之間震蕩。盡管在醫療過程中,醫生應當將人看作科學的客體,但絕不能忘記人還是有思有感的人文主體。因此,醫學必須總是權衡事實與價值。如果,醫學過于極端,那將變得不可靠,甚至危險。而關注病人的尊嚴與價值恰恰體現了人文學在醫學領域中的作用,這種作用至少包括三方面的內容,即理解當今臨床境遇中倫理與價值問題的本質需要;對職業本身考察和批判的需要;以及將這些態度賦予那些有教養的而不僅僅是受過訓練的人。人文學是處理倫理學、哲學、歷史學、法學與神學中的關涉人類價值的本源性問題,醫學科學和技術作為工具不足以應對人類價值與目的問題,人文學才能夠教導醫生們敏感且有信心地面對無限的人類存在現象。可以看出,佩里格里諾主張在哲學反思的和各醫學人文相關學科對話基礎上發展生命倫理學,同時,他指出生命倫理學應當回歸臨床,關注具體臨床境遇中具體的那個病人的尊嚴與價值。對于當今生命倫理學的發展而言,這無疑是中肯的建議和明確的方向。
四、結語
- 上一篇:生物醫學工程應用領域
- 下一篇:外貿公司財務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