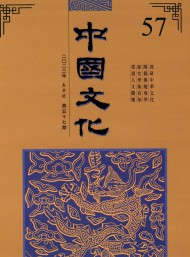清末票號范文10篇
時間:2024-03-05 09:50:46
導語:這里是公務員之家根據多年的文秘經驗,為你推薦的十篇清末票號范文,還可以咨詢客服老師獲取更多原創文章,歡迎參考。
清末票號盛極而衰研究論文
一、票號自身的弊端是票號在清末盛極而衰的內因
在內部組織上,一個嚴密控制的組織,必然導致自閉,而這種自閉將給它帶來災難。例如,最初制定三年不準回家的規定,是受交通條件限制的無奈之舉。可是,后來火車、輪船方便了,票號總部不顧各地員工的苦苦請求,仍然固守這一陳規,導致人才大量流失。為了實施有力的控制,票號等級森嚴。票號里70%的職工地位低下,他們在學徒期間只有飯吃,沒有工資,勞動強度很大。學徒期滿后,一年工資是幾兩、一二十兩。一份協成乾票號光緒32年的工資單顯示,工資有36個等級,其中14%的職員是沒有工資的學徒[2]。剝削嚴重,制度不健全,屢屢出現戰亂中員工攜款而逃的事件。另外,票號東家生活腐敗墮落,紙醉金迷,吸食鴉片,不理號事[3]58,如此不務正業的所有者無法使票號延續興盛。
在業務經營上,票號墨守成規,其經營方向不能適應時展之需要。票號經營存放款的傳統,歷來強調信用而不重抵押,一旦遇到動蕩局面,公私存款不得不如數退還,而貸放給錢莊、商號的款項,卻極易成為壞賬,無法收回。票號比較保守,1903年,袁世凱任北洋大臣時,曾招山西票商經辦天津銀號,晉商不肯。1904年,鹿傅霖任戶部尚書籌辦戶部銀行時,力邀山西票號入股并出人組織,也遭拒絕。1908年,山西票號內部有人提議合組銀行,遭到總號反對[4]559。老號總經理和股東們反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他們不識時務、泥古守舊,以及各懷私心,難于理解有限責任。票號拒絕任何改革終至失敗。比如國內電報通達后,曾一度不準使用電報匯款。在近代工業已經興起的形勢下,仍窖藏白銀不敢向產業投資[3],從而失去了廣闊的獲利渠道。
二、戰亂紛飛、財政困難及國際貿易逆差是票號所處的不良宏觀環境
從中法、中日戰爭到義和團運動及八國聯軍侵略,可謂內憂外患,戰亂紛飛。因為經濟決定金融,所以清末的票號的發展必然舉步維艱。戰亂直接影響了工農業生產和貿易發展,也因此間接影響到金融業,包括票號業的經營與發展,同時戰亂有時還會直接侵襲票號業。例如1900年7月,八國聯軍攻占天津、八月攻占北京,京、津票號紛紛撤莊回鄉,途中又有遭遇銀兩被搶、賬簿丟失的不幸。再如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繼而各省響應,清軍反撲,土匪蜂起,社會混亂,許多城市發生焚燒搶掠,殷實商號和金融業受災最重。天成亨票號僅漢口、成都、西安3處被搶現銀100多萬兩,共計虧損200多萬兩。日升昌票號僅陜西、四川就損失30余萬兩,放款無法收回,損失300萬兩以上[3]58。由此可見戰亂影響票號之慘重。
清末天災人禍接連而至,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國勢衰微孱弱,財源日益枯竭,開支不斷擴大,財政極端困難。財政的突出開支有龐大的軍費,巨額的戰爭賠款等。清政府在資金緊迫之時往往對票號施加壓力。曾國庫的志誠信票號在庚子以后把業務重心移至北京,該號盡收國庫余資,貸放南省,辛亥革命中清廷用款刻不容緩,在應收款400余萬兩、應付款200余萬兩的情況下,因周轉不靈而宣布倒閉,號中經理人員連同股東均被押入大牢[3]58。清政府為了解決軍餉匱乏的問題,增設厘卡,提高厘金征收率,并命令貨捐局嚴追捐銀。這阻礙了商業流通,加劇了“錢荒”,將許多商號推向破產,進而惡化了票號的業務環境,并危及其放款的回收。
清末票號由盛到衰原因分析論文
[摘要]清末票號盛極而衰,年存放款及匯兌額逐年降低,究其原因有其自身的弊端、不良的宏觀環境、現代金融機構的競爭和金融風潮的影響。
[關鍵詞]清末;票號;盛極而衰;匯兌
Abstract:TheExchangeshopsinthelateQingDynastydeclinedfromitsflourishwhichreflectedthatitsstorageandexchangereducedyearbyyear.Bywayofanalysis,wecouldseethatitsowndrawbacks,theillmacroeconomicenvironment,thecompetitivenessofmodernfinancialinstitutionsandtheimpactofthefinancialturmoilresultedinthisdecline.
Keywords:theLateQingDynasty;exchangeshop;declinerightafterflourish;exchange
票號,又稱“票莊”或“匯票莊”,最初是經營地區間的匯兌,以后也兼營并不斷擴大存放款業務的一種舊式金融機構。近年來一些學者大體認為票號產生于19世紀20年代初,相當于清道光初年。從60年代到90年代是票號發展的黃金時期,它促進了商品流通,密切了與晚清政府之間的聯系,成為其財政支柱。陳其田估計票號最盛時,年存款總額1.5億兩,放款利息和匯費等收入每年應在200~300萬兩之間。利潤率也很高,例如平遙幫的百川通資本16萬兩,1900年前后四年中共獲利66萬兩,資本利潤率103%[1]693。但是從1900到1911年票號盛極而衰,年存放款及匯兌額逐年降低,究其原因有其自身的弊端、不良的宏觀環境、現代金融機構的競爭和金融風潮的影響。
一、票號自身的弊端是票號在清末盛極而衰的內因
清末公債的經濟分析論文
【摘要題】經濟專史研究【關鍵詞】國債理論/清末公債/經濟分析【正文】國債是在商品經濟和信用制度一定發展的基礎上產生的,是一個特殊的財政范疇。由于國家職能的擴展,特別是在對外進行戰爭和加強國家干預經濟之際,國家財政支出不斷增加,僅靠增加稅收已不能滿足國家各項開支時,政府往往在信用制度業已建立和發展的基礎上,以國家信用形式集中部分社會閑散資金,以彌補財政資金不足。最初籌措國債的目的,一般是為了克服當時的財政困難。在資本主義初期,國債是進行資本原始積累的重要杠桿。馬克思說:“公債成為原始積累的最強有力的手段之一。它像揮動魔杖一樣,使不生產的貨幣具有了生殖力,……每次國債的一部分就成為從天而降的資本落入包稅者、商人和私人手中,——撇開這些不說,國債還使股份公司、各種有價證券的交易、證券投機,總之,使交易所投機和現代的銀行統治興盛起來”。(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3頁。)在正常情況下,國債的發行都必須以一個發育完善、運作正常、流通順暢的國債市場為依托。如果沒有相當發達的國債市場,特別是發達的國債二級市場,國債的大量發行也是不可能的。國債市場的發展狀況,直接制約著一級市場上的國債發行。同時由于國債市場作為綜合實施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結合點,而日益成為國家運用經濟手段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工具。因此,國債市場的發展狀況直接關系到政府經濟目標的實現和政府調控市場的成效。一、問題的提出清末,由于軍費及各項賠款支出巨大,財政捉襟見肘。為了彌補財政不足,于是便效仿西方,發行國內公債。清末總共發行了三次公債:1894年的“息借商款”、1898年的“昭信股票”和1911年的“愛國公債”。清政府第一次發行內債是1894年的“息借商款”。這次發行公債的目的是為了應付甲午戰爭的軍費,由戶部建議向“富商巨賈”借款,成為“戰爭留下之紀念品”。發行辦法是向北京及各省分額募款,以地丁、關稅擔保,各省實行的募款辦法各不相同,如北京規定分兩年半還本付息,以6個月為一期,第一期還息不還本,自第二期起本息同還,每期還本1/4,月息7厘,印票以100兩為一張,如在1萬兩以上,可“給虛銜封典,以示鼓勵”,舉債對象是“官紳商民”。(注:千家駒:《舊中國公債史資料》(1894—1949),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4頁。)這次發行的公債雖無總額規定,但擬定了六項辦法,實際發行額為1102萬兩,但由于弊病叢生,形同捐輸,1895年遂停止發行。清末第二次公債是1898年的“昭信股票”,比上次的息借商款更接近于近代公債。當時為了償付《馬關條約》規定的第四期賠款,計劃發行總額為1億兩,取名“昭信股票”,意為“皇上昭示大信”的公債。公債票額分為100、500、1000兩三種,年息5厘,以田賦和鹽稅為擔保,分20年還清,并規定10年后用減債基金還本。債券準許抵押售賣,但需報戶部昭信股票局備案。同時規定給官銜以資鼓勵。(注:同上書,第5頁。)此次公債無論發行方法,還是發行程序都較第一次的息借商款更為完備,但是亦因流弊過多而在(1898年)時停辦。從發行至停辦,募款2000萬兩。清末第三次公債是1911年的所謂“愛國公債”。當時正值辛亥革命爆發之際,為籌集鎮壓辛亥革命的經費,維持封建統治,計劃發行3000萬兩,取名“愛國公債”。公債票面額分5元、10元、100元、1000元四種,年息6厘,以部庫收入為擔保,期限9年,前4年付息,后5年平均抽簽還本。這次公債是在清政府行將崩潰之時發行的,各界對清政府已經失去信任,所以一般商民很少認購,只有少數王公貴族、文武官員購買少許。(注:同上書,第6頁。)絕大部分是由清皇室以內帑現金購買,實際發行額1160萬元,未及發行完畢,清政府便被推翻了,后由北洋政府繼續承擔。對于清政府發行的三次公債,許多學者曾經進行了專門的研究,見仁見智。目之所及,大概涉及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1.關于清政府發行公債的原因,一致歸于清政府的財政危機。如有人認為“隨著西學東漸,清朝統治集團內部的一部分人開始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公債有所了解,并主張效法外洋向民間募債。清政府也因財政危機日見嚴重,不得不考慮新辟財源。”(注:朱英:《甲午“息借商款”述略》,《貴州社會科學》1993年第4期。)“一是維持清朝腐敗龐大官僚機構的開支,二是為了應付甲午戰爭軍費的需要。”(注:胡憲立、郭熙生:《中國早期公債》,《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6期。)2.關于清末公債發行中所產生的種種弊端,一方面是由于社會經濟條件的局限,另一方面則是由清政府自身的腐敗而造成的。公債失敗的原因,主要在于:第一,在清政府貪污腐敗的統治下,發行公債變成了官紳的變相捐輸和對人民的變相勒索。第二,公債發行出現許多流弊。如昭信股票發行引起:銀號錢鋪倒閉;籍端勒索、商民賄囑求免;官紳吏役視為利藪,從中漁利;驅民使投洋教,以為護符。第三,這些公債都不用于生產方面,而是用于彌補赤字、補充軍政費用、用以賠款,因而這些公債沒有起到西方公債那種原始積累杠桿的作用,而且從國債市場本身看,當時存在著法律與監管體制不完備、中介機構不成熟、市場發展空間比較狹窄等差距。第四,清末滯后的金融市場嚴重妨礙了國債的發行、流通,國債的金融功能呼喚中國新式金融體系的誕生。第五,從公債發行現狀看,清末公債具有完全的行政攤派、不流動特點。一個規范的國債流通市場,應包括統一的全國國債托管、清算系統、銀行組成的統一的和開放的市場框架,才能推動國債市場的健康發展,清末公債未取得成功的根由之一也在于此。(注:千家駒:《舊中國公債史資料》(1894—1949),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4頁。周育民:《晚清財政與社會變遷》,第五章、第六章有關內容,上誨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胡憲立,郭熙生:《中國早期公債》,《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6期。李巨瀾:《清行的三次公債及其失敗原因探略》,《淮陰師專學報》1992年第6期。)3.關于清末公債的作用和意義,在當時以及后來的史學著作中不斷地受到攻擊和指責,以至于其內在的積極意義被忽視了。有人從政府發行公債增加了商人的經濟負擔的角度出發,認為“如果說洋務運動時期吸收商股創辦‘官督商辦’或‘官商合辦’洋務企業,在某些方面尚一定程度起到了促進中國資本主義增長的作用,那么甲午‘息借官款’則不僅絲毫未產生這方面的客觀積極作用,相反還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注:朱英:《甲午“息借商款”述略》,《貴州社會科學》1993年第4期。)但也有人評論說:在封建社會或奴隸社會,君主的主權神圣不可侵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民”,臣民對君主只有完稅、納糧的義務,絕沒有臣民放債給君主而君主反要還債的道理。把政府和個人當成對立的經濟單位這種觀念的發生是十八世紀資本主義獲得相當發展以后的意識的反映。清政府發行公債,開始接近資本主義性質的公共信用制度,自覺不自覺地把政府(君主)和臣民的關系擺在平等的位置上,公債形成之后,國家和公債認購者是借貸關系。(注:千家駒:《舊中國公債史資料》(1894—1949),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4頁。)在此基礎之上,進一步認為:“是為了抵制外來侵略的財政需要而發行的,具有愛國公債的性質。”“突破了清代慣用的捐輸、報效等封建落后的籌款方式,而采用借債的方式應付朝廷的緊急財政需要,這在財政手段和財政觀念上都是具有進步意義的。”“以皇帝名義向臣民舉債,對于封建等級秩序是一個巨大的沖擊。”(注:周育民:《晚清財政與社會變遷》,第五章、第六章有關內容,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本文即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針對清末公債的影響和意義這一相對薄弱的問題,從經濟學的視野,結合國債理論,就清末公債的李嘉圖等價定理的有效性、公債認購主體——居民的經濟行為、公債發行的貨幣效應等方面對公債的經濟影響進行分析。不當和不足之處懇請斧正。二、李嘉圖等價定理的有效性分析傳統的或流行的關于公債對于財政赤字、財政負擔和財政風險等問題的闡述,西方有一個與凱恩斯理論和弗里德曼的貨幣數量理論齊名的李嘉圖等價定理。這一理論被西方學者廣泛引用,并且被許多國家付諸實踐,指導各國的財政政策。甚至在公債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爭論中,“似乎沒有哪二個命題比‘李嘉圖等價定理’的影響更為深遠和爭執持久的”。(注:袁東:《公共債務與經濟增長》,中國發展出版社2000年版。)所謂“李嘉圖等價定理”(theRicardianEquivalenceTheorem)是指這樣一個命題:無論政府是以征稅來增加收入,還是以借款的方式來增加收入,從效應上看,賦稅和債券融資是等價的。因此,政府支出的特定的融資手段對于其最終效應來說是無關緊要的。該定理以封閉經濟和政府活動非生產性為前提與條件,內容涉及到稅收與公債的基本關系,也涉及到個人與企業在稅收與公債面前的行為變化,還涉及到政府如何在公債與稅收之間進行選擇這樣一系列重大的理論與實踐問題。該定理之所以用李嘉圖來命名,則是由于19世紀初,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人物大衛·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首次明確地表達了這種觀點。羅伯特·巴羅于70年代中期發表了《政府債券是凈財富嗎?》一文,復活并推廣了李嘉圖等價定理。李嘉圖主義認為,在國家非生產性前提下,為了籌集用于純粹消耗性支出(如戰費)的費用,不管是征稅還是借款,效果是相同的。巴羅進一步認為,通過發行公債的政府融資僅僅是延遲了征稅,即雖然政府以公債形式融資支持部分財政支出,從而減少了當期的征稅,但由于債務終究是由未來的增稅償還,因而它與現時稅收在某種程度上是相似的(即等價)。進一步的結論是,在政府財政開支不被削減的情況下,預算赤字的增加應會導致正好與赤字相配合的儲蓄的增加。在近代中國,伴隨著對外戰爭的一次次失敗、一次次巨額賠款以及浩大的軍費、腐朽的封建支出等已使清朝財政一蹶不振,財政負擔日益繁重。至甲午海戰,清政府的財政已經枯竭;而甲午戰爭以后,日本帝國主義又逼迫清政府在短期內支付巨額賠款和還遼費;不久,帝國主義各國又向清政府勒索一筆巨額賠款,即庚子賠款;此外,甲午敗績,使清政府深信武力的大規模現代化刻不容緩:新式軍隊的操練,對中央及督撫來說,俱為額外的財政負擔。這些非常支出,遠遠超過了清政府財政負擔的能力。甲午戰后中國財政的特征,是“出入平衡的長期破壞”。清政府費盡心力,謀求增辟財源以應急需。而清政府一開始并沒有利用國債這一近代經濟杠桿,而是采用增加稅收和大舉外債來彌補財政赤字。如稅收方面,鹽課劇增,1891年鹽課為743萬兩,到1911年預計達到4500余萬兩,20年間增加5倍,導致食鹽滯銷,鹽法紊亂;厘金大增,1891年為1632萬兩,1911年預計可達4319萬余兩,20年間增加1.6倍等。大舉外債方面,1895年清政府向俄、法借款;1896年和1898年又向英、德借款,款額約共三億兩,從而每年還債的本息逾2000萬兩,約占國家歲出1/4以上。(注:[臺灣]何漢威:《京漢鐵路初期史略》,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7頁。)這些外債,資本主義列強都附有苛刻的政治、經濟條件,而清政府把這些外債也主要用于賠款、武裝軍隊等。增加稅收,使城市工商業和農村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廣大人民在繁重的賦稅重壓下貧困潦倒;大舉外債,“多論磅價,折耗實多”,“前以種種吃虧”,“今聞各國爭欲抵借,其言愈甘,其患愈伏”。(注:千家駒:《舊中國公債史資料》(1894—1949),第1、6頁。)由此,清朝政府從1894年起因“海防趨緊,需餉浩繁”,“為籌借華款”等原因,逐漸在使用稅收和外債手段彌補財政的同時,認識到“凡一切講武訓農通商惠工之實事刻不容緩,需款正多,舍己求人,終不可恃,無論洋款何如,華款總當并力圖之,專責任之,克期待之,志在必成,”(注:同上書,第7—8頁。)把發行公債作為“今之急務”。由此可見,對晚清政府來說,發行公債是彌補財政赤字、優于征稅的一種較好的方法。彌補財政赤字有三種做法:增加稅收、向中央銀行透支或借款、政府舉借國債。亞當·斯密認為:“一國在平時沒有節約,到戰時就只好迫而借債。……在危險臨到的瞬間,就得負擔一項馬上就要的大費用;這費用是不能等待新稅逐漸地慢慢地納入國庫來應付的。在此萬分緊急的情況下,除了借債,政府再不能有其他方法了。”(注: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原因的研究》(下),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第472—473頁。)因此,陶爾頓(H.Dalton)曾有“國債乃戰爭留下之紀念品”(注:李厚高:《財政學》,臺灣三民書店印行,1967年版,第273頁。)的概括。用增加稅收來彌補財政赤字除了時間滯后的原因之外,稅收還是一種強制、無償的方式,并不是自愿的納稅人和政府的市場交易,清末增加稅收已經引起鹽法紊亂、厘金大增、城市工商業和農村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廣大民眾貧困潦倒等后果;向外國銀行借款又附帶苛刻的政治、經濟條件,對整個國家安全和當時的社會經濟都“其患愈伏”;而發行國債是一種自愿、有償、靈活的方式,國債發行只涉及資金使用權的讓渡,流通中的貨幣總量沒有改變,不會導致通貨膨脹。因此,舉借國債彌補財政赤字更為有效。從李嘉圖等價定理來看,清末公債的發行雖然具備李嘉圖等價定理所認為的前提與條件,即封閉經濟(清末的自然經濟仍占重要地位)和政府活動非生產性(發行的公債主要用于償還戰爭賠款),但并不能說李嘉圖等價定理適用于清末公債。因為清末特殊的政治經濟環境、戰爭賠款、債券市場不完全、未來稅收的不確定性等事實都動搖或否定著李嘉圖等價定理的正確性,等價性遭到了破壞:第一,政治因素被引入清末公債中性問題中。等價定理要成立就隱含著個人擁有信息和具有完全的預見能力。實際上,在近代特別是清朝末年,未來的稅收與收入都是不確定的,消費者很可能更看重現在,因為他們在政治動蕩、外國入侵、戰爭頻繁、政府腐敗的社會背景下,無法預期自己的收入和未來的生活狀況。于是,現期消費便可能增加,而不愿意去購買公債。于是,清末的商民對公債的購買意愿并不強烈,清政府被迫強迫商民購買,甚至肆意勒索,商民只有向發行官員進行賄賂以求茍免。昭信股票發行時,“督撫下其事于州縣,州縣授其權于吏役,力僅足買一票,則以十勒之,力僅足買十票,則以百勒之。商民懼為所害,惟有賄囑以求其免求減,以致買票之人,所費數倍于股票,即未買票之人,所費亦等于買票。”(注:千家駒:《舊中國公債史資料》(1894—1949),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8頁。)在規范的公債發行市場的條件下,李嘉圖等價定理也許有效,但對于清末公債,需要特別強調當時的政治因素在公債發行過程中所起的破壞作用。正是由于清末政治因素的影響,公債發行的社會成本相對于李嘉圖主義用于分析的西歐公債來說特別高,清末公債的總成本越大,等價性就越差。第二,等價定理實際上假定,當公債替代征稅時,所減的稅是一種總額稅。減少的稅負是均勻地落在每個消費者身上,并且每個消費者具有相同的邊際消費傾向。但是,在近代,減稅的效應實際上不會均勻地落在每個消費者身上,每個消費者之間的邊際消費傾向也不盡相同。近代存在著嚴格的等級制,特權階層不僅不交稅,而且還可盤剝平民百姓,由此特權階層的消費傾向與平民百姓有著天壤之別。這樣便從兩個方面破壞了等價定理的前提。所以康有為就當時負擔不均、侵吞嚴重的弊病指出:“吾見己未之事,酷吏勒抑富民,至于鎮押,迫令相借。既是國命,無可控訴,酷吏得假此盡飽私囊,以其余歸之公。民出其十,國得其一,雖云不得勒索,其誰信之?”(注:《康南海自編年譜》戊戌。)第三,等價定理實質上假定稅收只是總額稅,因此認為公債替代稅收只會產生一種稅收總額的變化,而總額變化又完全可以由公債數量上的變化來抵消。但近代,大多數稅收并不是總額稅,而是針對不同的產品、不同的經濟行為而開征的,如鹽稅、厘金等。不同的稅種具有不同的經濟影響。比如,厘金會限制物品在全國范圍內的流通,鹽稅會直接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因此,不同的稅收會使經濟行為發生不同的變化,而經濟行為的變化就意味著李嘉圖等價定理可能不成立。第四,導致等價定理可能失效的最重要原因或許是有限期界的影響。等價定理一個重要的假設便是:人的壽命期是無限的,不同時期的稅收是向不同的人群組征收的。這樣,債券持有人才會在未來的時期中面臨納稅問題,而且他不可能逃避納稅。但是,每個人在實際上都不可能長生不老,從而不會關注在他死后所開征的稅。如果消費者只關心自己的利益,則他們確實可以通過死亡來逃避將來的稅負,而他們又都享受到了當初由于政府以公債代替征稅而產生的減稅的好處;如果政府把當前的稅收用于支出,那些當時活著的人便承受直接的稅收負擔;如果政府借債以用于支出,并在以后向將來的各代人征稅以償還債務,當稅收提高時那些活著的人可能不在世了。清末發行公債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償還戰爭賠款,不影響政府的其它財政收支,當期稅收也沒有減少,相反還有所增加,因而債券持有人享受不到減稅的好處。三、公債認購主體——“官紳商民”的經濟分析國債本身應該是一個重要的財政杠桿,在調節經濟,尤其是在調節不同階段和階層收入分配方面,具有強有力的作用。清末1894年的“息借商款”、1898年的“昭信股票”兩次公債的認購主體是“官紳商民”,1911年的“愛國公債”則一般商民很少認購,只有少數王公貴族、文武官員購買少許,絕大部分是由清皇室以內帑現金購買。具體到各地,每一次公債的應募情況也不完全一樣。如“息借商款”系首次由政府向民間募借資金,從商民應募的實際情況看,由于統一的章程沒有發揮作用,在京城,應募者主要是在京銀號、銀莊;在廣東,主要應募者為忠義公司、七十二行商等。在“官紳商民”和清皇室看來,認購公債是其可支配收入的運用項目,并不影響其所擁有的財富總量。購買公債的人是富商,這些錢本來會拿去奢侈消費,但購買公債在近代是一種新式的投資行為。這一投資行為,本應是自愿的,而1894年的“息借商款”是向北京及各省分額募款的,帶有很濃的強力攤派色彩。1898年發行“昭信股票”時雖然規定“官紳商民,均量力出借,無庸拘定數目”,“勸令紳商士民一體量力出借,仍不得苛派勒捐,致滋紛擾。”“所擬章程,既不責以報效,亦不強令捐輸,一律按本計利,分期歸還……”。(注:千家駒:《舊中國公債史資料》(1894—1949),第10、11、12頁。)但實際上,公債發行時出現了強迫商民購買、甚至肆意勒索等現象,商民只有向發行官員進行賄賂以求茍免,購買公債的熱情并不高。三次公債實際發行的4262萬兩,是否會改變社會民眾原有的消費決策?在理論上,公債被視作政府調控社會總需求、化消費基金為積累基金的有效手段,居民認購公債的資金主要或全部源于本來打算用作消費的基金。但應注意清末公債發行時的一個事實:商民如果購買公債,往往擠兌錢莊票號,以致造成錢莊票號倒閉,引起金融混亂。據御史徐道琨奏昭信股票的第一個流弊就是銀號錢鋪倒閉:“中國市面流通現銀至多不過數千萬兩,乃聞各省股票必索現銀,民所存銀票,紛紛向銀號錢鋪兌取,該鋪號瘁無以應,勢必至于倒閉,一家倒閉,闔市為之騷然。”(注:《皇朝道咸同光奏議》卷11,第13頁。)如此看來,在清末,發行公債形成了對居民儲蓄存款的沖擊,不是使儲蓄存款減少就是使儲蓄增幅趨緩。所以,清末發行公債帶來的一個結果是:居民認購公債,沒有改變其現期的消費決策,只不過是引起居民資產結構的調整。四、公債發行的貨幣效應在清末公債的發行階段,公債對經濟變量的影響主要取決于清政府的金融政策。甲午戰爭之前,清朝地方政府通過舊式金融機構舉借了多次內債。而到了清末發行這三次公債時,舊式金融機構無力承擔以千萬計的貸款,如在息借商款中,銀號、票號貸款約占10%,昭信股票中明確記載由票號提供的貸款占5.4%左右,清政府只能通過其他渠道向民間募借。息借商款通過各省籌餉局、善后局等籌集,昭信股票則設專局辦理,雖然規定“出入皆就近責成銀行、票莊、銀號、典當代為收付,不經胥吏之手”(注:《申報》1898年2月7日。),但州縣以下之募款幾乎完全依靠原有的征賦機構,因此清朝財政中的各種弊端也就在征借過程中層出不窮。(注:周育民:《晚清財政與社會變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0—351頁。)發行公債的技術條件是要有近代化的金融機關,有全國性的金融市場。有金融機關,才能通過公債吸收社會上的流動或閑置的資金;有金融市場,資本家或投資者才愿意把資金投資于購買公債,而公債亦才有可能當為“有價證券”而流通。中國人自己開設的最早的銀行——中國通商銀行成立于1897年,為中國銀行前身的戶部銀行成立于1905年,交通銀行(1907年)、浙江興業銀行(1907年)、四明銀行(1908年)等都是在20世紀的初期才開始設立。外商銀行在中國的歷史比華商銀行要早三四十年(如匯豐銀行1867年立分行于上海,麥加利銀行為1858年等),但那都是為了壟斷中國的金融和財政,為了保障帝國主義國家在我國勒索的外債與賠款的優先償付。所以當時中國缺乏一個健全的金融體系,一開始中國發行公債的技術條件實在藐藐。1894年的“息借商款”發行時,中國還沒有誕生自己的近代金融機構,所以發行、還本付息都由封建行政機關執行。1898年的“昭信股票”公債章程中出現了“……或交殷實號商代為領票,款存該號侯撥無誤,……惟該號商須有各商號連環保結”,還本付息時“仍準殷實商號代持股票赴局代領……”說明已意識到了中介組織在公債發行、兌付過程中的作用,1897年成立的中國通商銀行與公債還沒發生實際業務聯系。但當“昭信股票”出現流弊時,當時的戶部在奏疏中建議:“經由戶部選擇殷實商號數字,并現在官設之通商銀行,將印就股票,發由該商號銀行領出轉售。以后每年還息還本,即由商號銀行給發,其各處業經保結尚未領票者,并就近赴商號銀行交銀領票,轉補戶部……”這表明當時行政主管部門認識到了銀行參與公債的發行、兌付可消除一些流弊,推動公債的發行。及至1911年“愛國公債”時“公債之募集及本息之償付,均委中國銀行。”(注:千家駒:《舊中國公債史資料》(1894—1949),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5頁。)金融機構正式全面參入公債市場,成為國債市場中介機構。這一中介機構溝通了供需雙方,為交易雙方服務,其經營活動的成果,不僅促成國債的順利發行與流通,還維持著國債市場正常的運行秩序,是近代國債市場的依托,同時,金融機構也憑借公債業務得到了長足發展。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國債“使交易所投機和現代的銀行統治興盛起來。”(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3頁。)有了銀行,清政府就可實施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由于銀行資金較為充裕,公債發行時就不會發生擠兌錢莊票號的流弊。綜上所述,清末公債的李嘉圖等價定理并不成立——在近代,賦稅和債券融資是不等價的;認購公債的商民,沒有改變其現期的消費決策,只不過是引起他們資產結構的調整;清末公債對當時經濟變量的影響主要在于清政府的金融政策,當時行政主管部門認識到了銀行參與公債的發行、兌付可消除一些流弊,推動公債的發行。
建設特征型地方金融文化
三流企業抓產品,二流企業抓營銷,一流企業抓文化。企業文化是價值觀、神話、英雄、象征的集結,是一種精神,是一種意識,是一種境界,是如影隨形、飄飄欲仙的企業靈魂。地方金融要建設具有中國傳統文化、儒家思想、鄉土社會與西方開放兼容、個性張揚相結合的獨立法人經濟文化。
一、地方金融文化應與傳統文化、鄉土社會相結合
我國的地方金融企業植根地方、服務地方,大多都在小氣候、小環境中誕生、成長與發展,無論如何也割不斷濃郁的鄉情和傳統文化淵源。
明清山西商人用孔子“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之觀點來發起利益追逐的進取精神;用“執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的主張,倡導敬業精神;用宗法社會的家族孝悌和睦、鄉誼團結之鄉情建立商幫群體,完成“團隊建設”,因而稱雄國內商界五個多世紀,出現了“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的鼎盛局面。在商業的迅速發展下,山西票號錢莊歷經100多年,給山西創造了億萬兩白銀收入,使山西成為全國首富,山西票號被人們稱為“匯通天下”的金融組織。寶豐社當時的地位可類比當今人民銀行,它曾領導錢莊參與清末晉商行會整理貨幣、建立制度、打擊沙錢、維護正常貨幣流通、穩定社會經濟、組織貨幣交易市場、管理金融機構、組織借貸轉帳、票據流通等等。寶豐社等票號錢莊的財東大都是飽讀詩書之人,深受孔孟之道影響,遵循“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傳統文化道德,并不是亂中撈利。他們實行“銀股”“身股”平均分配;知人善用任人唯賢;抽疲轉快調度資金;預提“護本”防止倒閉;職業教育培養人才;規章制度嚴格要求;經理負責運籌帷幄;誠信為本注重信譽等一系列制度和措施更是構建了當時票號錢莊的文化體系。
商業儲蓄銀行是舊中國最大的商業銀行之一,創辦人陳光甫開辦之初就以“服務社會、以人為本、競爭創新”為核心內容的企業文化。提出“我行一無所恃,可恃者乃發揮服務之精神也”,并在傳票帳單上都醒目地印上“服務社會”字樣,要求業務工作的每一個方面、每一個環節都“務求顧客之歡心,博社會之好感”。陳光甫要求基層行員儀容整潔,熱情待客。“對于本行一切顧客無論何界中人或鄉愚婦女,應謙恭和悅竭誠相待”,“無論貧賤,視同一律。”如有與顧客吵架者,不問是非曲直一律開除;處理業務要認真禮貌。“如抄結單給顧客,必須行列整齊,內容清晰,讓顧客樂于核閱”,否則,“滿紙涂鴉,顧客隨即棄置一隅,不愿詳閱,且對本行發生不好印象。”;業務嫻熟,力求手續簡便,收付敏捷。對于主要存戶的存款余額表要心中有數,對于支票上的簽字或印簽,要能夠一看即知真偽,不必驗對所留模式,以免顧客久等;嚴禁上班時間吸煙、閑談、閱報,應以“全副精神接待顧客,始能得社會之好感”。陳光甫還是中國金融界屈指可數的、在行內推出“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的銀行家,他經常向行員灌輸“銀行是我,我是銀行”的思想。他說,“凡百事業,以人而興,而新陳代謝,尤愿繼起有人,俾可維持事業于永久。”“有人才,雖衰必盛;無人才,雖盛必衰。銀行尤盛”。
中國傳統的“儒文化”強調“仁、義、禮、智、信”。“誠信”是立身之本,修養之首,齊家之基,立國之本。對此,儒學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和廣泛而深入的闡發。孟子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道也”;《中庸》說:“惟天下之誠為能化”,“君子誠之為貴”;《大學》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荀子道:“君子養心莫善于誠,至誠則無他事矣。”;周敦頤說:“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朱熹也曾有“誠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謂也”的見解。“貨之粗精好歹,實告經紀,使好裁奪售賣,若昧之不言,希為僥幸出脫,恐自誤也”;“賒須誠實,約議還期,切莫食言”。可見,儒學的誠,指的是胸懷坦蕩,真實無偽。以誠相伴而生的是“信”,有誠才有信,誠實不欺,謂之“信”。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司馬光認為:“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為國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親。不善則反之,欺其鄰國,欺其百姓,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離心,以至于敗”。言而有信,取信于人是儒家學說推崇備至的倫理準則。儒學乃國之瑰寶,鄉規鄉俗與民約乃傳統文化之要略。在儒家文化和鄉土風情基礎上建立的票號錢莊與舊銀行企業文化應成為現今地方金融企業文化建設的重要參照和借鑒。正本請源,票號錢莊是我們的根,倫理道德、儒家思想是地方金融文化的源。
廣信公司政治經濟研究
一、長期封禁政策嚴重制約了黑龍江社會經濟發展
清政府出于政治和經濟需要,對東北地區尤其黑龍江厲行封禁。在政治上,清朝統治者認為東北是“龍興之地”、“祖宗肇跡興王之所”,應保存滿族騎射風俗,以維護其統治地位。這從清帝所言及諭旨中有所反映。順治帝說過:“我朝以武功開國,頻命征討不臣,所至克捷,皆恃騎射。”[1]雍正帝曾說:“我滿洲人等,因居漢地,不得已與本習日以相遠……但務守滿洲本習,不得稍有疑貳。”[2]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諭軍機大臣稱:“盛京、吉林為本朝龍興之地,若聽流民雜處,殊于滿洲風俗攸關。”[3]而旗民雜處,則使旗人“耳濡目染,習成漢俗,不復知有騎射本藝”。[3]在經濟上,清朝統治者認為“東三省地方,為滿洲根本重地,原不準流寓民人雜處其間,私墾地畝,致礙旗人生計”。[4]所以,把大片土地“留作本地官兵及京旗官兵隨缺地畝之用”或“以備退革兵丁恒產之用”。[2]此外,還圈占了大批牧場和圍場,獨占參、貂等名貴特產,以滿足清政府最高統治者及宗室、貴族的享用。在東北三省中,黑龍江受封禁的時間最長,遲滯社會經濟發展的后果也最為嚴重。一是封禁造成黑龍江地區人口稀少,勞動力匱乏,土地等物質資源得不到應有的開發利用,導致經濟困難,財政拮據,資金短缺。從人口來看,據資料統計,道光二十年(1840年),全國人口有4.1億多,而占全國面積近1/5的東北地區總人口還不到300萬,每平方公里不足2人。其中,200萬人居住在奉天,吉林和黑龍江兩省才100萬人。1903年中東鐵路剛剛通車時,黑龍江人口不過40.8萬人。就經濟而言,奴隸制莊園經濟和少數民族地區的游牧、狩獵和采集經濟在黑龍江長期占據主導地位,1907年清政府正式議準一般旗地可隨意買賣,封建地主經濟制度才正式確立。正如資料所載:“江省僻處邊荒,天寒土曠,滿蒙之族皆以游牧狩獵為主,初不識耕耘為何事。”[5]直到民國時期,黑龍江地區的土地才得到大面積開墾,農業經濟才有明顯發展。同時,其他資源也得到進一步開發利用。封禁造成的經濟落后導致黑龍江財政困難,成為清政府的“協濟”省份。如當時黑龍江將軍所轄官兵俸餉一直由清政府部庫撥付,但咸豐以后由于清政府財政無力承擔,便改由關內各省協濟了,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民國初年。對封禁造成的經濟困難幾屆時任黑龍江將軍也曾奏陳朝廷,以期解決。如咸豐十年(1860年),特普欽上奏清廷,請求在蒙古爾山(今木蘭縣境內)等處弛禁放荒,其中說到:“地方既屬拮據,與其拘泥照前封禁,致有用之地,拋棄如遺,莫若據實陳明,招民試種,得一分租賦,即可裕一分度支”;[6]光緒十年(1884年),文緒奏稱應以兵屯田開墾黑龍江荒地;光緒十三年(1887年),恭鏜奏請開墾呼蘭封禁荒田,并提出開墾十大好處;光緒十五年(1889年),依克唐阿奏請通肯封荒弛禁招墾。二是封禁造成黑龍江地區十分閉塞,切斷了與先進地區的聯系往來,使先進思想、文化、技術等無法進入和交流,阻礙了社會進步,導致社會形態進化緩慢。在被封禁的二百四十多年間,黑龍江的總體社會形態一直處于從原始社會向封建社會的轉型狀態,在少數民族為主的黑龍江地區,則氏族公社制、奴隸制與封建制并存,社會形態更為落后。由于人口稀少,無民可治,加之歷史上八旗制度的原因,黑龍江地區一直實行八旗駐防的“軍治”(設將軍衙門、都統衙門等軍政合一的管理機構)行政管理制度。從1683年設置第一任黑龍江將軍,到1862年于呼蘭城守尉轄區設置黑龍江歷史上第一個民事管理機構理事同知廳,長達近一百八十年的時間。這種軍府制管理和關注的重點在于邊防,而非經濟。此種落后的社會管理制度也是導致黑龍江地區經濟貧困的原因之一。
二、沙俄入侵和“羌帖”流入使黑龍江遭受了嚴重的政治危機和經濟損失
鴉片戰爭使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而俄國資本主義卻在19世紀中葉得到了迅速發展,但其國內依然尖銳的階級矛盾和有限的市場滿足不了資產階級的利益需求,這就迫使原本即侵略成性的沙俄政府加快和擴大了對海外殖民地的爭奪。其中,封建落后的中國尤其與之毗鄰,人煙稀少,邊塞空虛的黑龍江地區成為其侵略的重點區域。開始是以軍事手段進行武力征服和掠奪領土,到19世紀90年代又采取所謂和平的“鐵路———銀行”策略,通過華俄道勝銀行、中東鐵路和盧布進行政治統治和經濟掠奪,使黑龍江逐漸變成了沙俄的殖民地。中東鐵路不僅是沙俄進行商品傾銷和掠奪物產的大通道,而且在中東鐵路沿線及其附屬地沙俄政府還進行駐軍設警司法,乃至對哈爾濱實行自治,攫取政治特權,這就使其所控制的地區變為租界和“國中之國”。正如哈里施瓦茨所說:“滿洲的鐵路區域以及鄰近鐵路和兼并入該地帶的廣大土地完全受俄國的政治和經濟控制。在這個區域,是俄國的法律和法庭在發生作用,警察和武裝力量掌握在俄國人手中,俄國人利用鐵路作為基地,迅速將它的經濟滲透滿洲。俄國輪船獲得在廣闊的滿洲河流上的航行權;松花江的航運成為中東鐵路的活動范圍中的一個重要部分。鐵路又開辦了許多煤礦和林場,并且在全區到處經營著學校、圖書館、俱樂部的網絡。這就是在中國疆域內已經建成的一個俄羅斯帝國!”[7]為修筑中東鐵路,沙俄打著中俄合辦的幌子建立了由其完全控制的華俄道勝銀行,并在中國享有一系列特權。華俄道勝銀行在中國可以行使貨幣發行、經理國庫收支、國家金庫的國家銀行職能,并有權在中國修建鐵路、敷設電線,投資辦廠、對企業貸款等。該行在中國兼中央銀行、投資銀行、商業銀行于一身,其目的就是要控制中國的經濟命脈,以便實施經濟侵略和掠奪,是對黑龍江進行經濟侵略和掠奪的橋頭堡。由于哈爾濱是中東鐵路樞紐地,因而華俄道勝銀行哈爾濱分行成為該行在中國的一個最主要的分支機構,其經營活動包括組織修筑中東鐵路并提供所需巨額資金、對進入黑龍江尤其哈爾濱地區的俄人經辦企業提供貸款、直接投資辦廠開礦等。通過上述經濟活動,使沙俄政府紙幣(羅曼諾夫票,中國人俗稱其為“羌帖”)得以在黑龍江地區大肆推行,至1903年中東鐵路開通時,在黑龍江,“羌帖”占據了統治貨幣的地位,1903年底盧布成為滿洲占支配地位的通貨,被強制納入俄幣體系,黑龍江地區的貨幣主權及金融利權卻嚴重喪失。
三、銀錢匱乏和私帖濫發使黑龍江貨幣金融陷入困境
清政府實行銀銅并行的復本位貨幣制度,而黑龍江地區自然資源中缺銅少銀,因此也沒有條件自設鑄幣局,流通所需的金屬貨幣來自奉吉兩省及關內地區,且多流通于通都大邑,腹地及鄉鎮很少見。據黑龍江省金融志編委會編纂的《黑龍江金融歷史編年》記載:1890年,因呼蘭等處制錢短缺,將軍依克唐阿奏請仿照吉林章程,租賦改為銀錢各半。1896年5月31日,黑龍江制錢缺乏,奏請清政府將部撥本年官兵俸餉劃交鄂省鑄造銀元運黑龍江籍資補救。由于金屬貨幣短缺,商賈往來時大多采取相互記賬的辦法,每年的端午、中秋、年關三大節期再進行清結,屆時彼此抵消后的差額部分由債務方出給欠據。這種欠據最初由具有付現能力的殷實商家簽發,故也稱“私帖”。初期私帖信用良好,可轉讓流通,如同現貨一樣,商民樂意接受。隨著黑龍江開發加快和各業發展,貨幣需求日漸擴大,加之外來勞動力每年都要攜帶相當數量現銀回鄉,導致黑龍江地區貨幣供不應求,私帖發行日益增多,舉凡油坊、當鋪、糧棧、燒鍋等,店不分大小都任意發行,在鄉街市井間私帖成了方便交易的媒介,一度成為流通中的主要貨幣,以致泛濫貽害。據資料記載:“呼蘭因銀貴質重,難于剖析,制錢缺,籍紙帖為交易。此后,燒鍋有帖,當鋪有帖,小本商戶亦往往有帖”;慶城向用現銀、小洋、制錢,自商家私出錢帖后,發行日濫,現銀日益減少”;[8]“江省各城開出紙幣不下數百家,各商不量資本,隨意自開憑帖,每家以五萬吊計之,共出紙幣四五千萬吊。因有射利之徒,以換帖為名,而乘機網利,始雖支持,漸至擁擠,終必荒畢,以至傾家蕩產,而帖債仍未付清。以此自累,又以此累人”。[9]此間更有奸商勾結官府開出無本私帖,欺詐商民,使眾商受累,有冤莫訴。為解決私帖濫發問題,地方政府也曾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如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黑龍江副都統果權鑒于呼蘭商帖泛濫,下令銷毀以制錢為本的商帖,改用銀帖。對近年所發商帖折作六七折使用,發行較早者打折遞減,最少僅三四折。其結果使持有商帖的鋪戶遭受了巨額損失,燒鍋、當鋪紛紛歇業,所存者不過十之一二。
清末的經濟法規論文
經濟法規是保障社會經濟生活正常運轉的重要手段。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完善的經濟法規,政府就不能有效地管理社會經濟,也無法保證社會經濟生活的正常發展。20世紀初,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朝野部分有識之士,初步意識到制定和實施經濟法規的作用;清政府為推行“新政”,發展近代工商業,也陸續制定并頒發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經濟法規。這些舉措,不僅在中國法制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對當時社會經濟生活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本文主要論述清末經濟法規的產生、種類、意義及其局限,不妥之處尚祈方家匡正。
一、清末經濟法規的產生
清末經濟法規的產生,是清政府于20世紀初推行“新政”,實行獎勵工商、振興實業政策的結果。我們知道,重農抑商是中國封建王朝長期奉行的政策,工商業者得不到任何法律保障。但到20世紀初,清朝統治者從歐美列強以工商立國而臻于富強的事實中獲得啟示,認識到“取外國之長,乃可去中國之短”《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四),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4601頁。》,由此從重農抑商一變而為大力振興工商。清廷上諭稱:“通商惠工,為古今經國之要政。自積習相沿,視工商為末務,國計民生,日益貧弱,未始不因乎此。亟應變通盡利,加意講求。”《《光緒朝東華錄》(五),第5013頁。》
隨著重商政策的推行,清朝統治者很快即意識到制定經濟法規的重要性。光緒二十八年(1902)二月癸已上諭已提及擬訂經濟法規之事,此諭雖仍標榜“我朝大清律例一書,折衷至當,備極精詳”,但也不得不承認“為治之道,尤貴因時制宜,今昔情勢不同,非參酌適中,不能推行盡善。況近來地利日興,商務日廣,如礦律、路律、商律等類,皆應妥議專條”。同時還要求各出使大臣“查取各國通行律例,咨送外務部”,并渝令袁世凱、劉坤一、張之洞等督撫大吏“慎選熟悉中西律例者,保送數員來京,聽候簡派,開館編纂”《《光緒朝東華錄》(五),第4388頁。》。清政府推行重商“新政”的實際步驟,首先也是設立商部和擬訂經濟法規,并特別提出要率先擬出商律以盡快頒布施行。1903年4月,清廷渝飭設立商部,同時“著派載振、袁世凱、伍廷芳先訂商律,作為則例。俟商律編成奏定后,即行特簡大員,開辦商部。其應如何提倡工藝,鼓舞商情,一切事宜,均著載振等悉心妥議,請旨施行,總期掃除官習,聯絡一氣,不得有絲毫隔閡,致啟弊端,保護維持,尤應不遺余力”《《光緒朝東華錄》(五),第5013一5014頁。》。由此可見,清政府在推行振興工商政策之始,就比較重視制定和頒行經濟法規。
不僅清廷頒發了一系列上諭,一些督撫大吏和新成立的商部,對制定和頒發各類經濟法規的重要性及其作用也有一定的認識。歸納有關言論,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頒行商律以促進工商業發展。劉坤一、張之洞于光緒二十七年(1901)八月聯名呈遞的長篇奏折中說:“歐美商律最為詳明,其國家又多方護持,是以商務日興。中國素輕商股,不講商律,于是市井之徒,茍圖私利,彼此相欺,巧者虧逃,拙者受累,以故視集股為畏途,遂不能與洋商爭衡……必中國定有商律,則華商有恃無恐,販運之大公司可成,制造之大工廠可設,假冒之洋行可杜。”這樣,“十年以后華商即可自立,骎骎乎并可與洋商相角矣”《《光緒朝東華錄》(四),第4763頁。》。商約大臣、工部尚書呂海寰也吁請清廷“通飭各督撫體察各省情形,統籌全局,訂明東西通行法律,由法律以審定商律,由商律以措施商政”《《商約大臣工部尚書呂奏請速訂東西通行律例以保主權而開商埠片》,《東方雜志》第2卷第6號。》。新成立的商部則指出,沒有完善的商律,工商業發展便有諸多障礙。“從前開設局廠,或官督商辦,或官商合辦,每因章程未善,不免有牽掣抑勒等弊,以致群情疑阻。”《《光緒朝東華錄》(五),第5073頁。》清廷上諭也明確表示,函需擬訂商律,“庶幾商務振興,蒸蒸日上,阜民財而培邦本”《《光緒朝東華錄》(五),第5014頁。》。以上這些論述,都強調了擬訂經濟法規對促進工商業發展的重要作用。
玉米傳播引種管理論文
摘要:玉米在明代晚期即已傳入山西,但直到光緒年間,玉米才在山西得到普遍種植。本文通過對山西與相鄰各省在玉米引種時間上的比較分析,對山西各縣區玉米別稱的來源及玉米傳入山西的途徑和時間做了比較詳細的梳理歸納,進而指出玉米這種高產作物對山西社會經濟發展所起的促進作用。
關鍵詞:山西玉米傳播引種經濟作用
山西方志對玉米的記載,最初比較簡單,明萬歷至清康熙年間,個別地區在物產中只記錄了玉米的名稱。乾隆年間,南部的絳縣和北部的大同先后對玉米的形態特征做了描述,云“其苗葉胥似高粱,穗如秕麥,葉旁別出一苞,垂吐白須,久則苞拆子出,顆顆攢簇”,[1]光緒年間,山西的一些地方志中對玉米的描述增加了新的內容:光緒六年(1880年)《聞喜縣志》記有“玉蜀黍(山地園地藝,補麥缺)”;光緒九年(1883年)《懷仁縣志》中記載:“玉蜀黍(不及秋霜,宜廣種)”;在民國時期方志中,才見到如“玉蜀黍……顆粒有大小之別,小顆粒晚種合宜,大者宜早種”[2]這樣一些對玉米品種和種植技術比較詳細的記載。一、玉米在山西的別稱及來源玉米的別稱甚多,全國約有70余種,在山西有玉蜀黍、玉稻秫、玉高粱、玉秫秫、玉秫、玉茭子、玉茭茭、包谷、玉谷、禹谷、舜王谷、御麥、玉麥、棒子等10多種。在這些別稱中,以“玉蜀黍”通行的范圍最廣,其他別稱通行的范圍都比較狹窄,如表1所示,稱“玉米”的地區只有山西北部的定襄縣;稱“玉蜀黍”的縣份在山西全省各個地區中都有,從北部的大同、懷仁、繁峙,到中部的清源、昔陽、壽陽,再到南部的岳陽、安澤、翼城、襄陵、沁源、安邑、聞喜、絳縣、新絳,都做如此稱呼;稱“玉茭”的地區有北部的定襄、繁峙、河曲,中部的太谷、平定,東南部的襄垣、長子、陽城;稱“包谷”的地區有清源、文水、河津;稱“玉谷”的地區有安邑、芮城;稱“御麥”的地區有陽城和新絳;稱“玉麥”的有南部的鄉寧和翼城;而其他別稱只出現在個別縣的方志記載中。同治《建始縣志·物產》曰“包谷,山陜曰玉高粱”,在山西大多數地區的方志記載中,玉高粱和玉蜀黍都是一起出現的,這是因為“……谷譜蜀黍,一名高粱,一名蜀秫”,[3]“……關西呼蜀黍為稻黍,今山西平陽、汾州諸郡人,余見其通呼為稻黍也”,[4]“……稷曰蜀秫,又曰茭子,即高粱也”,[5]由此可見蜀黍、蜀秫、稻黍、茭子都是高粱的別稱,因為玉米“其苗葉胥似高粱”,[6]所以又被稱為“玉蜀黍”、“玉蜀秫”、“玉稻黍”、“玉茭子”。對“玉秫秫”和“玉茭茭”這兩個別稱,光緒八年(1887年)《壽陽縣志》中這樣記載:“玉秫秫,莖葉似秫秫,為實大而有光澤,故名。一名玉茭茭,蓋秫聲之轉,而字之認猶之椒菽同,從叔聲而異讀也。”[7]玉米之所以又被稱為“包谷”,大概是因為“結實有皮包之”[8]和“《本草綱目》始入谷部”[9]這樣的原因。中國直呼玉米的地區不廣,在云南、貴州、廣東、廣西、湖南、湖北等地區,“包谷”是對玉米最普遍的稱呼。玉谷也是玉米的別稱,在清人的地方志中,也有禹谷或御谷的。章學誠說:“苞谷一名玉米,一名玉谷,謂合五而六也。”嘉慶《河津縣志》:“包谷一名禹谷”,嘉慶《商城縣志》也載:“玉蜀黍一名玉谷”。玉谷的稱呼多流行于北方。徐光啟在《農政全書》中這樣寫道:“別有一種玉米,或稱玉麥,或稱玉蜀秫,蓋亦從他方得種。”[10]玉麥之稱,在明清兩代多見于云南、貴州西部、四川西部、甘肅、陜西中部、河南等地區,另外,安徽、直隸、山東等省的地方志中也有所記載。為什么叫玉麥?據光緒《名山縣志》的解釋:“粒豆,色黃潤如玉,故得玉名”;道光《城口廳志》曰:“麥者,言可磨面如麥也”;道光《新津縣志》則說:“玉麥,言其粒如麥也”。看來,果實外形似玉,又可磨面如麥子,是玉麥稱呼的由來。表1山西玉米別稱及通行縣區分布名稱|通行地區玉米|(光緒)定襄縣玉蜀黍(玉高粱、玉蜀秫、玉稻黍)|(乾隆)大同府、絳縣(道光)繁峙縣、大同縣(光緒)懷仁縣、清源鄉、壽陽縣、聞喜縣、盂縣(宣統)文水縣(民國)昔陽縣、岳陽縣、安澤縣、翼城縣、襄陵縣、沁源縣、安邑縣、新絳縣玉茭(玉茭子、玉茭茭)|(乾隆)陽城縣(嘉慶)長子縣(道光)繁峙縣(同治)河曲縣(光緒)定襄縣(民國)太谷縣、平定縣、襄垣縣包谷|(光緒)清源鄉、文水縣(嘉慶)河津縣玉谷|(民國)安邑縣、芮城縣御麥|(乾隆)陽城縣(民國)新絳縣玉麥|(民國)鄉寧縣、翼城縣禹谷|(嘉慶)河津縣舜王谷|(萬歷)稷山縣棒子|(民國)安邑縣表注:括號中朝代系后列府縣鄉志書的刊版年代。關于“御麥”這一別稱的由來,在同治十三年《陽城縣志》中這樣記載:“以曾經進御,故名”。在兩湖地區也有將玉米叫做“御高粱”和“御米”的,大概也是因為玉米曾經是貢品,而在稱呼前冠以“御”字。總之,玉米在山西的傳播過程中,名稱并未發生太大的變化,主要還是繼承了玉米來源地的名稱。二、玉米傳入山西的時間和途徑玉米在國內的傳播可以分成兩個時期,由明代中葉到明代后期是開始發展時期,到明代后期這種農作物已傳播到全國近半數省區,清代前期全國各省縣份多已種植。在明萬歷四十年(1612年)《稷山縣志》的《物產·谷屬》中列有“舜王谷”,這可能是山西古籍方志中關于玉米的最早記載,和相鄰省份對玉米的記載時間相比,山西早于直隸,晚于河南、山東和陜西。另外,對玉米有較早記載的是乾隆二十年(1755年)刊《陽城縣志》、乾隆三十年(1765年)刊《絳縣志》和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刊《大同府志》。嘉慶、道光年間,南部的長子和河津縣,北部的大同縣和繁峙縣在其地方志中對玉米有了比較簡單的記載。[11]但是山西大多數地區的方志對玉米的記載卻是在光緒乃至民國時期,即使是主產玉米的晉中地區也是在民國時期才有了關于玉米的記載。光緒十八年(1892年)刊《山西通志》中有這樣的記載:“玉蜀黍,亦名玉秫,又名御麥,處處有之”,“……御麥,今潞屬廣植”,[12]這說明直到十九世紀末,玉米在山西的種植才具有了普遍性(但是在光緒年間的大部分縣志中都不見有玉米的記載)。根據以上方志對玉米的記載時間的先后來判斷,玉米在山西省內的傳播途徑是由晉南和晉北同時向晉中地區推進的。情況可能是這樣:明朝末年,晉南的稷山縣首先開始種植玉米;乾隆中后期,晉南的陽城縣、絳縣和晉北的大同府等地也種植了玉米;清朝后期,玉米種植分別由晉南和晉北逐步向晉中地區推廣;光緒前期,晉南、晉中和晉北都已有了玉米的種植,但分布范圍狹小;民國時期,在山西大部分縣份的地方志中都可見到玉米的記載了。從玉米最初傳入山西到玉米在全省范圍內的普遍種植經歷了幾乎三百年的時間,可見玉米在山西的種植發展是比較緩慢的,其原因應與山西的地理氣候條件及有清一代相當頻繁的自然災害有關,尤其是光緒三年的特大自然災害對山西的影響極為嚴重。據方志記載,清朝前期的一些年份里山西省境內的任何地區都發生過十分嚴重的自然災害:康熙《五臺縣志》卷八收錄閻襄《饑荒行》,引言云:“康熙十九年,太原以北至云中,千里大旱,民饑轉徙十之六七,斗米錢數百不得……”;民國《永和縣志》卷一《祥異考》載:“(康熙)五十九年至六十年,晉省連遭大旱,永邑更甚……盜賊遍地,餓殍盈野,性命賤如草菅,骨肉等于泥沙。……”;光緒《長子縣志》卷一二《大事記》載云:“乾隆二十五年春,大饑,民食樹皮草根”;民國《萬全縣志》《雜記》載:“嘉慶九年,夏無麥,秋無禾,糧價騰貴,麥石價銀二十五兩,人民離散。十年,無麥無禾,餓死、逃亡過半。”所以,在玉米傳入山西的最初時期境內各地區就遇到頻繁發生的荒旱。這些災害的直接結果就是農作物的大幅度減產或絕收,饑不得食的農民或就地餓死,或流離失所,勞動力人口受到了很大損失。玉米雖系耐旱作物,但其生長期中要求高溫,蒸發量大,需水量亦多,在降水量不足250毫米的地區,灌溉條件好才能生長。山西南北地理氣候條件迥異,農業生產條件差別很大。晉南與晉東南地區在農業生產資源及地理條件方面,占有一定的優勢,臨汾與運城兩大盆地土地平衍肥沃,水利灌溉便利,無霜期長,氣候較為溫暖,因此,農業生產水平與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比北部地區略強一些,但該地區一直以生產小麥為主,外來作物玉米還一時無法取得主導地位;晉中地區耕地主要集中于太原和忻定兩大盆地,地勢平衍,氣候適中,水利條件一般化,是山西最為普通的產糧區,但由于人口眾多,糧食供給也相當緊張,每有災害,人口流失也很嚴重;與南部相比,晉西、晉北地區土地貧瘠,無霜期短,耕作方式落后,水利灌溉條件極度低下,糧食生產完全依賴于氣候條件,當地農民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非常脆弱。所以,清朝前期玉米在山西的傳播種植范圍和速度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自我朝定鼎以來,迄今二百余歲,中間水旱交咨,在所時有,然或一州、一邑,甚至二、三郡而止,從未有赤地千里,通省旱災如光緒三年之山右者。……”[13]由此可見,有清一代山西境內的自然災害就沒有間斷過,直到光緒初年發生了“丁戊奇荒”這場波及山西全境的特大自然災害,全省上百個縣似乎沒有例外地同罹慘禍,山西南部地區受災最為嚴重。張鑒衡《壽陽縣災賑碑計》稱:“溯自乙亥(光緒元年,1875年)秋雨傷禾,谷米多黑,則晉災之始也。至丙子(光緒二年,1876年),省南一帶,饑謹薦臻,至丁丑,則赤地千里。”[14]山西農業生產條件最為優越的晉南地區尚且如此,更何況自然條件遠不如晉南的晉北和呂梁地區,就更沒有進行玉米種植的能力了。災害造成了農業生產力的絕對下降,過半勞動力的死亡和逃移,[15]這也許就是為什么光緒前期只有少數縣份對玉米做了記載的原因了。“丁戊奇荒”后,在清政府勸荒和招荒政策下,大批外地客民來到山西,補充了嚴重短缺的勞動力,農業生產逐步得到恢復,產量高而穩定,又具有耐旱和耐瘠特性,適應范圍廣,高山、丘陵、平原皆可種植的玉米便以很快的速度在山西尤其是晉南地區普及開來,到光緒十八年(1892年),就處處有玉米了。據研究,玉米傳入我國的途徑有海陸兩路:陸路一自波斯、中亞至甘肅,然后流傳到黃河中下游流域;一自印度、緬甸至云南,然后流傳到川黔;海路則自美洲、東南亞至沿海的閩廣等省,然后向內地擴展。這三路玉米傳播源逐漸向中國腹地進行滲透并最終融合。[16]從玉米在山西通行的別稱來看,山西接受的主要是云南和甘肅兩股玉米傳播源,因為江浙閩粵等沿海省份的玉米別稱絕大多數都尾綴“粟”字、“豆”字,或帶有“蘆”字,山西對玉米的別稱卻不曾有這樣的字,而是像陜西一樣稱為“玉蜀黍”,像云南一樣稱為“包谷”,或像河南一樣稱為“玉麥”。這兩股玉米傳播源相繼抵達山西之后便開始融合,這種融合大概結束于光緒初年,其表現之一是在同一地區具有指示兩種玉米傳播源的別稱,如地處山西中部的文水縣,在其光緒九年(1883年)刊的方志中既有標志云南傳播源的別稱“包谷”,又有標志甘肅傳播源的“玉桃黍”[17];表現之二是這時的地方志中也往往羅列多種玉米別稱,如光緒十八年(1892年)刊《山西通志》記載,“玉蜀黍,亦名玉秫,又名御麥,處處有之。”[18]玉米是如何傳入山西的,由于缺乏相關的歷史資料,不能確切考證。但根據山西在明清時期的情況推測,玉米引種到山西的途徑可能有兩種:一是由當時在外省的山西商人把玉米種子帶回到山西,經過本地農民試種獲得成功,繼而在山西各地推廣開來;二是外省客民流落到山西開墾荒地的時候,種植了在家鄉時曾賴以糊口的玉米,收成不錯,山西的農民也開始種植。關于山西商人的經商活動情況,清代大學者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有這樣的記述:“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歲輒從人學貿易,俟蓄積有資,始歸納婦。納婦后,仍出營利,率二三年一歸省,其常例也。”[19]山西人經商以商品的長途販運為主,明朝中葉以后,山西商人大量地向淮浙地區移居,逐步進入了全國范圍的流通領域,南北各地都有其足跡。如山西票號總號所在地的太谷縣,“自有明迄于清中葉,商賈之跡幾遍全省。東北至燕、奉、蒙、俄,西達秦隴,南抵吳、越、川、楚,儼然操全省金融之牛耳。”[20]明代山西商人在四川、云南、陜西、河南及新疆的經濟活動史料中多有記載:山西潞澤二州是與三吳、越閩齊名的絲織專業區,“東南之機,三吳越閩最夥,取給于湖繭;西北之機,潞最工,取給于閬繭(閬指四川保寧府閬中縣)”,[21]“潞綢所資來自他方,遠及川湖之地。”[22]潞澤絲棉織物的染色,對顏料的需求很大,因而絲綿生產又推動了山西顏料商的發展。山西顏料商見于碑刻記載的有平遙和臨汾縣人,主要在京城、通州經營,所售顏料出自本地,或是販自四川。日升昌票號前身山西平遙縣西裕成顏料莊“所販顏料中,有銅碌一種,出四川省,因自行重慶府制造銅碌,運至天津,以備銷售,亦甚獲利。”[23]明代,隨著山西鹽商在國內地位的日益顯赫,河東鹽銷往“陜西之西安、漢中、延安、鳳翔四府,河南之歸德、懷慶、河南(今洛陽)、汝寧、南陽五府及汝州,山西之平陽、潞安二府以及澤、沁、遼三州。”[24]山西商人有明以來就參與了西茶市與西番的交易(交易地點在碉門、黎、雅抵朵甘、鳥思藏)。弘治十六年(1503年),明朝大臣楊一清向朝廷提出招商買茶,讓茶商與西番直接交易,“自弘治十八年(1505年)為始,聽臣出榜招諭山陜等處富實商人,收買官茶五六十萬斤,其價依原定每千斤給銀五十兩之數,每商所買不得過一萬斤,給與批文,每一千斤給小票一紙,掛號定限,聽其自出資本,收買真細茶斤,自行雇腳轉運。”[25]我們沒有發現山西商人在甘肅的活動資料,但在張掖、武威見到過山陜會館和山西會館的遺址,雖然已經破敗不堪,卻能充分說明山西商人在甘肅曾經有過長期的經營活動。四川、甘肅、云南、陜西、河南、新疆都已在明萬歷之前先后開始種植玉米,[26]在山西商人與這些省份頻繁的經濟往來中,玉米傳入山西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因為按照晉商的經營習慣,分號與總號之間在人員和貨物上的往來都異常頻繁。另外,我們將玉米傳入山西的時間、最初傳入地與山西商人的發跡期、最初發跡地做一比較,發現在時間和地域上兩者都相當吻合。如前所述,山西古籍方志對玉米做最早記載的是明萬歷四十年(1612年)的《稷山縣志》,稷山在明代隸屬蒲州。而山西商人在全國取得顯赫地位是在明代弘治至萬歷年間(1488—1619年),晉南的蒲州、平陽一帶則是山西商人最初的發跡地,明隆慶二年(1568年),進士沈思孝在其《晉錄》、明萬歷進士王士性在其《廣志繹》中都曾指出:“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這兩個事件幾乎是發生于同一時間、同一地域,為我們的推測又提供了一個佐證。從明朝初年開始,山西一直是中國北方一個重要的移民輸出地,但同時也有不少的外地客民流落到山西求生,“在僻遠的州縣,不少外地客民早已在當地從事耕耘”,[27]這些州縣有隰州、吉州、嵐縣、岢嵐、臨縣、永和、浮山、岳陽等。光緒六年(1880年)刊《續修岢嵐州志序》中提到當地的客民問題:“第山高土瘠,絕少平原,地廣人稀,苦無產殖,土人儉而不勤,業農賈者率多他鄉外省之人,以故直、豫、秦、隴、川、楚客民錯趾于境,來往靡常,而客富于主,又人丁欠旺,恒以外姓繼螟蛉,豈五行有所克制歟?”由此可見,進入到山西的客民來源相當廣泛,河北、河南、陜西、甘肅、四川、湖北等省份都有,他們在山西定居之后,勤于稼穡,善于商賈,所以玉米也有可能由這些客民引種到山西。當然,玉米引種到山西的這兩種途徑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有可能兼而有之。總之,明清時期山西人口的頻繁流動對玉米這種高產作物的引進和推廣起了決定的作用。三、玉米在山西的生產概況和經濟作用清代山西有關玉米單產的記載極其罕見,根據表二所示民國時期山西玉米的平均畝產量,可推測清末整個山西玉米的單產水平在40公斤左右(1914年山西小麥平均畝產是44.2公斤[28])。玉米作為逐漸推廣的作物,其種植面積在清代變化較大,但清代末年的情況可以參照民國初年的情況作些粗線條的估計。如表2所示,估計到清朝滅亡時,山西每年至少有150萬畝耕地種植玉米,以40公斤的單產計,清末山西每年可產玉米60000噸左右。表2山西玉米播種面積、產量及畝產年代玉米播種面積(萬畝)總產(噸)畝產(公斤)1919年153.375420491947年663.4250200401949年536.5646395086資料來源:山西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山西通志·農業志》,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252頁。在清代各縣方志中雖然很少見到對玉米產量的記載,但到光緒以后,玉米成為“山農之糧,視其農欠”,[29]“為本地人之副食物,其出產亦頗不少,麥后種之,亦為秋糧之一”,[30]可見,玉米以其高產的特性在山西一些地區的糧食作物中占據了主導地位,尤其是晉東南的潞安府,“今潞屬廣植,每炊必需”。[31]民國27年(1938年)《平定縣志》記載了當地玉米的平均年產量,約為183750石,同時還記載了粟的年產為91875石,豆為18375石,高粱為36750石,小麥及其他年產約為36750石。[32]可見,抗戰前夕玉米是平定縣年產量最多的糧食作物。到1949年的時候,玉米在山西的播種面積為536.56萬畝,年產量為463950噸,雖然只占到山西糧食作物總播種面積的8%,但在山西主要糧食作物的總產量中卻達到17.9%的比例,[33]如表3所示。表31949年山西主要糧食作物產量比例作物玉米谷子小麥薯類高粱比例17.9%29.2%23.4%13.3%11.0%資料來源:山西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山西通志·農業志》,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232頁。根據以上玉米在山西的生產情況來看,玉米在山西的傳播和推廣對當時糧食的增產是有極大意義的:首先,玉米耐旱,能夠適應北方的旱地,種植玉米可擴大耕地面積。山西農田一直以旱地為主,清代旱地面積占到總耕地面積的95%,約有65400萬畝的荒山荒地尚待開發。[34]同治十二年(1873年)至光緒十三年(1887年),山西耕地面積從53,285,401畝增至56,609,070畝,[35]增加了300多萬畝,和當時玉米種植的推廣可能有一定的聯系:其次,玉米是一種優異的高產作物,種植玉米可“種一收千,其利甚大”。[36]對處于封建剝削壓榨下的大多數農民來說,通過推廣特別高產的外來農作物比改良土壤或培育新的品種更容易提高糧食的單位面積產量。總之,玉米的推廣,既擴大了耕地面積,又提高了糧食單位面積產量,因而能為社會提供更多的食糧,特別是有助于“丁戊奇荒”之后山西農業生產的恢復和民食問題的解決。玉米在山西的推廣種植不僅促進了糧食的增產,還間接地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玉米本身用途廣泛,既可當糧,又可充作手工業原料,對山西農戶來說,用玉米釀酒和養豬在光緒時期已是極為普遍的事情,“釀酒磨粉,用均米麥。瓤煮以飼豕,桿干以供炊,無棄物”。[37]玉米的傳播種植對山西社會經濟生活所起的推動作用遠不止以上所述內容,還需我們做進一步地研究與探討。
注釋
[1]乾隆四十七年《大同府志》,卷1,《物產》。
[2]民國18年《翼城縣志》,卷8,《物產》。
玉米對山西經濟發展關系研究
摘要:玉米在明代晚期即已傳入山西,但直到光緒年間,玉米才在山西得到普遍種植。本文通過對山西與相鄰各省在玉米引種時間上的比較分析,對山西各縣區玉米別稱的來源及玉米傳入山西的途徑和時間做了比較詳細的梳理歸納,進而指出玉米這種高產作物對山西社會經濟發展所起的促進作用。
關鍵詞:山西玉米傳播引種經濟作用
山西方志對玉米的記載,最初比較簡單,明萬歷至清康熙年間,個別地區在物產中只記錄了玉米的名稱。乾隆年間,南部的絳縣和北部的大同先后對玉米的形態特征做了描述,云“其苗葉胥似高粱,穗如秕麥,葉旁別出一苞,垂吐白須,久則苞拆子出,顆顆攢簇”,[1]光緒年間,山西的一些地方志中對玉米的描述增加了新的內容:光緒六年(1880年)《聞喜縣志》記有“玉蜀黍(山地園地藝,補麥缺)”;光緒九年(1883年)《懷仁縣志》中記載:“玉蜀黍(不及秋霜,宜廣種)”;在民國時期方志中,才見到如“玉蜀黍……顆粒有大小之別,小顆粒晚種合宜,大者宜早種”[2]這樣一些對玉米品種和種植技術比較詳細的記載。一、玉米在山西的別稱及來源玉米的別稱甚多,全國約有70余種,在山西有玉蜀黍、玉稻秫、玉高粱、玉秫秫、玉秫、玉茭子、玉茭茭、包谷、玉谷、禹谷、舜王谷、御麥、玉麥、棒子等10多種。在這些別稱中,以“玉蜀黍”通行的范圍最廣,其他別稱通行的范圍都比較狹窄,如表1所示,稱“玉米”的地區只有山西北部的定襄縣;稱“玉蜀黍”的縣份在山西全省各個地區中都有,從北部的大同、懷仁、繁峙,到中部的清源、昔陽、壽陽,再到南部的岳陽、安澤、翼城、襄陵、沁源、安邑、聞喜、絳縣、新絳,都做如此稱呼;稱“玉茭”的地區有北部的定襄、繁峙、河曲,中部的太谷、平定,東南部的襄垣、長子、陽城;稱“包谷”的地區有清源、文水、河津;稱“玉谷”的地區有安邑、芮城;稱“御麥”的地區有陽城和新絳;稱“玉麥”的有南部的鄉寧和翼城;而其他別稱只出現在個別縣的方志記載中。同治《建始縣志·物產》曰“包谷,山陜曰玉高粱”,在山西大多數地區的方志記載中,玉高粱和玉蜀黍都是一起出現的,這是因為“……谷譜蜀黍,一名高粱,一名蜀秫”,[3]“……關西呼蜀黍為稻黍,今山西平陽、汾州諸郡人,余見其通呼為稻黍也”,[4]“……稷曰蜀秫,又曰茭子,即高粱也”,[5]由此可見蜀黍、蜀秫、稻黍、茭子都是高粱的別稱,因為玉米“其苗葉胥似高粱”,[6]所以又被稱為“玉蜀黍”、“玉蜀秫”、“玉稻黍”、“玉茭子”。對“玉秫秫”和“玉茭茭”這兩個別稱,光緒八年(1887年)《壽陽縣志》中這樣記載:“玉秫秫,莖葉似秫秫,為實大而有光澤,故名。一名玉茭茭,蓋秫聲之轉,而字之認猶之椒菽同,從叔聲而異讀也。”[7]玉米之所以又被稱為“包谷”,大概是因為“結實有皮包之”[8]和“《本草綱目》始入谷部”[9]這樣的原因。中國直呼玉米的地區不廣,在云南、貴州、廣東、廣西、湖南、湖北等地區,“包谷”是對玉米最普遍的稱呼。玉谷也是玉米的別稱,在清人的地方志中,也有禹谷或御谷的。章學誠說:“苞谷一名玉米,一名玉谷,謂合五而六也。”嘉慶《河津縣志》:“包谷一名禹谷”,嘉慶《商城縣志》也載:“玉蜀黍一名玉谷”。玉谷的稱呼多流行于北方。徐光啟在《農政全書》中這樣寫道:“別有一種玉米,或稱玉麥,或稱玉蜀秫,蓋亦從他方得種。”[10]玉麥之稱,在明清兩代多見于云南、貴州西部、四川西部、甘肅、陜西中部、河南等地區,另外,安徽、直隸、山東等省的地方志中也有所記載。為什么叫玉麥?據光緒《名山縣志》的解釋:“粒豆,色黃潤如玉,故得玉名”;道光《城口廳志》曰:“麥者,言可磨面如麥也”;道光《新津縣志》則說:“玉麥,言其粒如麥也”。看來,果實外形似玉,又可磨面如麥子,是玉麥稱呼的由來。表1山西玉米別稱及通行縣區分布名稱|通行地區玉米|(光緒)定襄縣玉蜀黍(玉高粱、玉蜀秫、玉稻黍)|(乾隆)大同府、絳縣(道光)繁峙縣、大同縣(光緒)懷仁縣、清源鄉、壽陽縣、聞喜縣、盂縣(宣統)文水縣(民國)昔陽縣、岳陽縣、安澤縣、翼城縣、襄陵縣、沁源縣、安邑縣、新絳縣玉茭(玉茭子、玉茭茭)|(乾隆)陽城縣(嘉慶)長子縣(道光)繁峙縣(同治)河曲縣(光緒)定襄縣(民國)太谷縣、平定縣、襄垣縣包谷|(光緒)清源鄉、文水縣(嘉慶)河津縣玉谷|(民國)安邑縣、芮城縣御麥|(乾隆)陽城縣(民國)新絳縣玉麥|(民國)鄉寧縣、翼城縣禹谷|(嘉慶)河津縣舜王谷|(萬歷)稷山縣棒子|(民國)安邑縣表注:括號中朝代系后列府縣鄉志書的刊版年代。關于“御麥”這一別稱的由來,在同治十三年《陽城縣志》中這樣記載:“以曾經進御,故名”。在兩湖地區也有將玉米叫做“御高粱”和“御米”的,大概也是因為玉米曾經是貢品,而在稱呼前冠以“御”字。總之,玉米在山西的傳播過程中,名稱并未發生太大的變化,主要還是繼承了玉米來源地的名稱。二、玉米傳入山西的時間和途徑玉米在國內的傳播可以分成兩個時期,由明代中葉到明代后期是開始發展時期,到明代后期這種農作物已傳播到全國近半數省區,清代前期全國各省縣份多已種植。在明萬歷四十年(1612年)《稷山縣志》的《物產·谷屬》中列有“舜王谷”,這可能是山西古籍方志中關于玉米的最早記載,和相鄰省份對玉米的記載時間相比,山西早于直隸,晚于河南、山東和陜西。另外,對玉米有較早記載的是乾隆二十年(1755年)刊《陽城縣志》、乾隆三十年(1765年)刊《絳縣志》和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刊《大同府志》。嘉慶、道光年間,南部的長子和河津縣,北部的大同縣和繁峙縣在其地方志中對玉米有了比較簡單的記載。[11]但是山西大多數地區的方志對玉米的記載卻是在光緒乃至民國時期,即使是主產玉米的晉中地區也是在民國時期才有了關于玉米的記載。光緒十八年(1892年)刊《山西通志》中有這樣的記載:“玉蜀黍,亦名玉秫,又名御麥,處處有之”,“……御麥,今潞屬廣植”,[12]這說明直到十九世紀末,玉米在山西的種植才具有了普遍性(但是在光緒年間的大部分縣志中都不見有玉米的記載)。根據以上方志對玉米的記載時間的先后來判斷,玉米在山西省內的傳播途徑是由晉南和晉北同時向晉中地區推進的。情況可能是這樣:明朝末年,晉南的稷山縣首先開始種植玉米;乾隆中后期,晉南的陽城縣、絳縣和晉北的大同府等地也種植了玉米;清朝后期,玉米種植分別由晉南和晉北逐步向晉中地區推廣;光緒前期,晉南、晉中和晉北都已有了玉米的種植,但分布范圍狹小;民國時期,在山西大部分縣份的地方志中都可見到玉米的記載了。從玉米最初傳入山西到玉米在全省范圍內的普遍種植經歷了幾乎三百年的時間,可見玉米在山西的種植發展是比較緩慢的,其原因應與山西的地理氣候條件及有清一代相當頻繁的自然災害有關,尤其是光緒三年的特大自然災害對山西的影響極為嚴重。據方志記載,清朝前期的一些年份里山西省境內的任何地區都發生過十分嚴重的自然災害:康熙《五臺縣志》卷八收錄閻襄《饑荒行》,引言云:“康熙十九年,太原以北至云中,千里大旱,民饑轉徙十之六七,斗米錢數百不得……”;民國《永和縣志》卷一《祥異考》載:“(康熙)五十九年至六十年,晉省連遭大旱,永邑更甚……盜賊遍地,餓殍盈野,性命賤如草菅,骨肉等于泥沙。……”;光緒《長子縣志》卷一二《大事記》載云:“乾隆二十五年春,大饑,民食樹皮草根”;民國《萬全縣志》《雜記》載:“嘉慶九年,夏無麥,秋無禾,糧價騰貴,麥石價銀二十五兩,人民離散。十年,無麥無禾,餓死、逃亡過半。”所以,在玉米傳入山西的最初時期境內各地區就遇到頻繁發生的荒旱。這些災害的直接結果就是農作物的大幅度減產或絕收,饑不得食的農民或就地餓死,或流離失所,勞動力人口受到了很大損失。玉米雖系耐旱作物,但其生長期中要求高溫,蒸發量大,需水量亦多,在降水量不足250毫米的地區,灌溉條件好才能生長。山西南北地理氣候條件迥異,農業生產條件差別很大。晉南與晉東南地區在農業生產資源及地理條件方面,占有一定的優勢,臨汾與運城兩大盆地土地平衍肥沃,水利灌溉便利,無霜期長,氣候較為溫暖,因此,農業生產水平與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比北部地區略強一些,但該地區一直以生產小麥為主,外來作物玉米還一時無法取得主導地位;晉中地區耕地主要集中于太原和忻定兩大盆地,地勢平衍,氣候適中,水利條件一般化,是山西最為普通的產糧區,但由于人口眾多,糧食供給也相當緊張,每有災害,人口流失也很嚴重;與南部相比,晉西、晉北地區土地貧瘠,無霜期短,耕作方式落后,水利灌溉條件極度低下,糧食生產完全依賴于氣候條件,當地農民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非常脆弱。所以,清朝前期玉米在山西的傳播種植范圍和速度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自我朝定鼎以來,迄今二百余歲,中間水旱交咨,在所時有,然或一州、一邑,甚至二、三郡而止,從未有赤地千里,通省旱災如光緒三年之山右者。……”[13]由此可見,有清一代山西境內的自然災害就沒有間斷過,直到光緒初年發生了“丁戊奇荒”這場波及山西全境的特大自然災害,全省上百個縣似乎沒有例外地同罹慘禍,山西南部地區受災最為嚴重。張鑒衡《壽陽縣災賑碑計》稱:“溯自乙亥(光緒元年,1875年)秋雨傷禾,谷米多黑,則晉災之始也。至丙子(光緒二年,1876年),省南一帶,饑謹薦臻,至丁丑,則赤地千里。”[14]山西農業生產條件最為優越的晉南地區尚且如此,更何況自然條件遠不如晉南的晉北和呂梁地區,就更沒有進行玉米種植的能力了。災害造成了農業生產力的絕對下降,過半勞動力的死亡和逃移,[15]這也許就是為什么光緒前期只有少數縣份對玉米做了記載的原因了。“丁戊奇荒”后,在清政府勸荒和招荒政策下,大批外地客民來到山西,補充了嚴重短缺的勞動力,農業生產逐步得到恢復,產量高而穩定,又具有耐旱和耐瘠特性,適應范圍廣,高山、丘陵、平原皆可種植的玉米便以很快的速度在山西尤其是晉南地區普及開來,到光緒十八年(1892年),就處處有玉米了。據研究,玉米傳入我國的途徑有海陸兩路:陸路一自波斯、中亞至甘肅,然后流傳到黃河中下游流域;一自印度、緬甸至云南,然后流傳到川黔;海路則自美洲、東南亞至沿海的閩廣等省,然后向內地擴展。這三路玉米傳播源逐漸向中國腹地進行滲透并最終融合。[16]從玉米在山西通行的別稱來看,山西接受的主要是云南和甘肅兩股玉米傳播源,因為江浙閩粵等沿海省份的玉米別稱絕大多數都尾綴“粟”字、“豆”字,或帶有“蘆”字,山西對玉米的別稱卻不曾有這樣的字,而是像陜西一樣稱為“玉蜀黍”,像云南一樣稱為“包谷”,或像河南一樣稱為“玉麥”。這兩股玉米傳播源相繼抵達山西之后便開始融合,這種融合大概結束于光緒初年,其表現之一是在同一地區具有指示兩種玉米傳播源的別稱,如地處山西中部的文水縣,在其光緒九年(1883年)刊的方志中既有標志云南傳播源的別稱“包谷”,又有標志甘肅傳播源的“玉桃黍”[17];表現之二是這時的地方志中也往往羅列多種玉米別稱,如光緒十八年(1892年)刊《山西通志》記載,“玉蜀黍,亦名玉秫,又名御麥,處處有之。”[18]玉米是如何傳入山西的,由于缺乏相關的歷史資料,不能確切考證。但根據山西在明清時期的情況推測,玉米引種到山西的途徑可能有兩種:一是由當時在外省的山西商人把玉米種子帶回到山西,經過本地農民試種獲得成功,繼而在山西各地推廣開來;二是外省客民流落到山西開墾荒地的時候,種植了在家鄉時曾賴以糊口的玉米,收成不錯,山西的農民也開始種植。關于山西商人的經商活動情況,清代大學者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有這樣的記述:“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歲輒從人學貿易,俟蓄積有資,始歸納婦。納婦后,仍出營利,率二三年一歸省,其常例也。”[19]山西人經商以商品的長途販運為主,明朝中葉以后,山西商人大量地向淮浙地區移居,逐步進入了全國范圍的流通領域,南北各地都有其足跡。如山西票號總號所在地的太谷縣,“自有明迄于清中葉,商賈之跡幾遍全省。東北至燕、奉、蒙、俄,西達秦隴,南抵吳、越、川、楚,儼然操全省金融之牛耳。”[20]明代山西商人在四川、云南、陜西、河南及新疆的經濟活動史料中多有記載:山西潞澤二州是與三吳、越閩齊名的絲織專業區,“東南之機,三吳越閩最夥,取給于湖繭;西北之機,潞最工,取給于閬繭(閬指四川保寧府閬中縣)”,[21]“潞綢所資來自他方,遠及川湖之地。”[22]潞澤絲棉織物的染色,對顏料的需求很大,因而絲綿生產又推動了山西顏料商的發展。山西顏料商見于碑刻記載的有平遙和臨汾縣人,主要在京城、通州經營,所售顏料出自本地,或是販自四川。日升昌票號前身山西平遙縣西裕成顏料莊“所販顏料中,有銅碌一種,出四川省,因自行重慶府制造銅碌,運至天津,以備銷售,亦甚獲利。”[23]明代,隨著山西鹽商在國內地位的日益顯赫,河東鹽銷往“陜西之西安、漢中、延安、鳳翔四府,河南之歸德、懷慶、河南(今洛陽)、汝寧、南陽五府及汝州,山西之平陽、潞安二府以及澤、沁、遼三州。”[24]
山西商人有明以來就參與了西茶市與西番的交易(交易地點在碉門、黎、雅抵朵甘、鳥思藏)。弘治十六年(1503年),明朝大臣楊一清向朝廷提出招商買茶,讓茶商與西番直接交易,“自弘治十八年(1505年)為始,聽臣出榜招諭山陜等處富實商人,收買官茶五六十萬斤,其價依原定每千斤給銀五十兩之數,每商所買不得過一萬斤,給與批文,每一千斤給小票一紙,掛號定限,聽其自出資本,收買真細茶斤,自行雇腳轉運。”[25]我們沒有發現山西商人在甘肅的活動資料,但在張掖、武威見到過山陜會館和山西會館的遺址,雖然已經破敗不堪,卻能充分說明山西商人在甘肅曾經有過長期的經營活動。四川、甘肅、云南、陜西、河南、新疆都已在明萬歷之前先后開始種植玉米,[26]在山西商人與這些省份頻繁的經濟往來中,玉米傳入山西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因為按照晉商的經營習慣,分號與總號之間在人員和貨物上的往來都異常頻繁。另外,我們將玉米傳入山西的時間、最初傳入地與山西商人的發跡期、最初發跡地做一比較,發現在時間和地域上兩者都相當吻合。如前所述,山西古籍方志對玉米做最早記載的是明萬歷四十年(1612年)的《稷山縣志》,稷山在明代隸屬蒲州。而山西商人在全國取得顯赫地位是在明代弘治至萬歷年間(1488—1619年),晉南的蒲州、平陽一帶則是山西商人最初的發跡地,明隆慶二年(1568年),進士沈思孝在其《晉錄》、明萬歷進士王士性在其《廣志繹》中都曾指出:“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這兩個事件幾乎是發生于同一時間、同一地域,為我們的推測又提供了一個佐證。從明朝初年開始,山西一直是中國北方一個重要的移民輸出地,但同時也有不少的外地客民流落到山西求生,“在僻遠的州縣,不少外地客民早已在當地從事耕耘”,[27]這些州縣有隰州、吉州、嵐縣、岢嵐、臨縣、永和、浮山、岳陽等。光緒六年(1880年)刊《續修岢嵐州志序》中提到當地的客民問題:“第山高土瘠,絕少平原,地廣人稀,苦無產殖,土人儉而不勤,業農賈者率多他鄉外省之人,以故直、豫、秦、隴、川、楚客民錯趾于境,來往靡常,而客富于主,又人丁欠旺,恒以外姓繼螟蛉,豈五行有所克制歟?”由此可見,進入到山西的客民來源相當廣泛,河北、河南、陜西、甘肅、四川、湖北等省份都有,他們在山西定居之后,勤于稼穡,善于商賈,所以玉米也有可能由這些客民引種到山西。當然,玉米引種到山西的這兩種途徑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有可能兼而有之。總之,明清時期山西人口的頻繁流動對玉米這種高產作物的引進和推廣起了決定的作用。三、玉米在山西的生產概況和經濟作用清代山西有關玉米單產的記載極其罕見,根據表二所示民國時期山西玉米的平均畝產量,可推測清末整個山西玉米的單產水平在40公斤左右(1914年山西小麥平均畝產是44.2公斤[28])。玉米作為逐漸推廣的作物,其種植面積在清代變化較大,但清代末年的情況可以參照民國初年的情況作些粗線條的估計。如表2所示,估計到清朝滅亡時,山西每年至少有150萬畝耕地種植玉米,以40公斤的單產計,清末山西每年可產玉米60000噸左右。表2山西玉米播種面積、產量及畝產年代玉米播種面積(萬畝)總產(噸)畝產(公斤)1919年153.375420491947年663.4250200401949年536.5646395086資料來源:山西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山西通志·農業志》,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252頁。在清代各縣方志中雖然很少見到對玉米產量的記載,但到光緒以后,玉米成為“山農之糧,視其農欠”,[29]“為本地人之副食物,其出產亦頗不少,麥后種之,亦為秋糧之一”,[30]可見,玉米以其高產的特性在山西一些地區的糧食作物中占據了主導地位,尤其是晉東南的潞安府,“今潞屬廣植,每炊必需”。[31]民國27年(1938年)《平定縣志》記載了當地玉米的平均年產量,約為183750石,同時還記載了粟的年產為91875石,豆為18375石,高粱為36750石,小麥及其他年產約為36750石。[32]可見,抗戰前夕玉米是平定縣年產量最多的糧食作物。到1949年的時候,玉米在山西的播種面積為536.56萬畝,年產量為463950噸,雖然只占到山西糧食作物總播種面積的8%,但在山西主要糧食作物的總產量中卻達到17.9%的比例,[33]如表3所示。表31949年山西主要糧食作物產量比例作物玉米谷子小麥薯類高粱比例17.9%29.2%23.4%13.3%11.0%資料來源:山西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山西通志·農業志》,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232頁。根據以上玉米在山西的生產情況來看,玉米在山西的傳播和推廣對當時糧食的增產是有極大意義的:首先,玉米耐旱,能夠適應北方的旱地,種植玉米可擴大耕地面積。山西農田一直以旱地為主,清代旱地面積占到總耕地面積的95%,約有65400萬畝的荒山荒地尚待開發。[34]同治十二年(1873年)至光緒十三年(1887年),山西耕地面積從53,285,401畝增至56,609,070畝,[35]增加了300多萬畝,和當時玉米種植的推廣可能有一定的聯系:其次,玉米是一種優異的高產作物,種植玉米可“種一收千,其利甚大”。[36]對處于封建剝削壓榨下的大多數農民來說,通過推廣特別高產的外來農作物比改良土壤或培育新的品種更容易提高糧食的單位面積產量。總之,玉米的推廣,既擴大了耕地面積,又提高了糧食單位面積產量,因而能為社會提供更多的食糧,特別是有助于“丁戊奇荒”之后山西農業生產的恢復和民食問題的解決。玉米在山西的推廣種植不僅促進了糧食的增產,還間接地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玉米本身用途廣泛,既可當糧,又可充作手工業原料,對山西農戶來說,用玉米釀酒和養豬在光緒時期已是極為普遍的事情,“釀酒磨粉,用均米麥。瓤煮以飼豕,桿干以供炊,無棄物”。[37]玉米的傳播種植對山西社會經濟生活所起的推動作用遠不止以上所述內容,還需我們做進一步地研究與探討。注釋
[1]乾隆四十七年《大同府志》,卷1,《物產》。
[2]民國18年《翼城縣志》,卷8,《物產》。
社會經濟發展論文
摘要:玉米在明代晚期即已傳入山西,但直到光緒年間,玉米才在山西得到普遍種植。本文通過對山西與相鄰各省在玉米引種時間上的比較分析,對山西各縣區玉米別稱的來源及玉米傳入山西的途徑和時間做了比較詳細的梳理歸納,進而指出玉米這種高產作物對山西社會經濟發展所起的促進作用。
關鍵詞:山西玉米傳播引種經濟作用
山西方志對玉米的記載,最初比較簡單,明萬歷至清康熙年間,個別地區在物產中只記錄了玉米的名稱。乾隆年間,南部的絳縣和北部的大同先后對玉米的形態特征做了描述,云“其苗葉胥似高粱,穗如秕麥,葉旁別出一苞,垂吐白須,久則苞拆子出,顆顆攢簇”,[1]光緒年間,山西的一些地方志中對玉米的描述增加了新的內容:光緒六年(1880年)《聞喜縣志》記有“玉蜀黍(山地園地藝,補麥缺)”;光緒九年(1883年)《懷仁縣志》中記載:“玉蜀黍(不及秋霜,宜廣種)”;在民國時期方志中,才見到如“玉蜀黍……顆粒有大小之別,小顆粒晚種合宜,大者宜早種”[2]這樣一些對玉米品種和種植技術比較詳細的記載。一、玉米在山西的別稱及來源玉米的別稱甚多,全國約有70余種,在山西有玉蜀黍、玉稻秫、玉高粱、玉秫秫、玉秫、玉茭子、玉茭茭、包谷、玉谷、禹谷、舜王谷、御麥、玉麥、棒子等10多種。在這些別稱中,以“玉蜀黍”通行的范圍最廣,其他別稱通行的范圍都比較狹窄,如表1所示,稱“玉米”的地區只有山西北部的定襄縣;稱“玉蜀黍”的縣份在山西全省各個地區中都有,從北部的大同、懷仁、繁峙,到中部的清源、昔陽、壽陽,再到南部的岳陽、安澤、翼城、襄陵、沁源、安邑、聞喜、絳縣、新絳,都做如此稱呼;稱“玉茭”的地區有北部的定襄、繁峙、河曲,中部的太谷、平定,東南部的襄垣、長子、陽城;稱“包谷”的地區有清源、文水、河津;稱“玉谷”的地區有安邑、芮城;稱“御麥”的地區有陽城和新絳;稱“玉麥”的有南部的鄉寧和翼城;而其他別稱只出現在個別縣的方志記載中。同治《建始縣志·物產》曰“包谷,山陜曰玉高粱”,在山西大多數地區的方志記載中,玉高粱和玉蜀黍都是一起出現的,這是因為“……谷譜蜀黍,一名高粱,一名蜀秫”,[3]“……關西呼蜀黍為稻黍,今山西平陽、汾州諸郡人,余見其通呼為稻黍也”,[4]“……稷曰蜀秫,又曰茭子,即高粱也”,[5]由此可見蜀黍、蜀秫、稻黍、茭子都是高粱的別稱,因為玉米“其苗葉胥似高粱”,[6]所以又被稱為“玉蜀黍”、“玉蜀秫”、“玉稻黍”、“玉茭子”。對“玉秫秫”和“玉茭茭”這兩個別稱,光緒八年(1887年)《壽陽縣志》中這樣記載:“玉秫秫,莖葉似秫秫,為實大而有光澤,故名。一名玉茭茭,蓋秫聲之轉,而字之認猶之椒菽同,從叔聲而異讀也。”[7]玉米之所以又被稱為“包谷”,大概是因為“結實有皮包之”[8]和“《本草綱目》始入谷部”[9]這樣的原因。中國直呼玉米的地區不廣,在云南、貴州、廣東、廣西、湖南、湖北等地區,“包谷”是對玉米最普遍的稱呼。玉谷也是玉米的別稱,在清人的地方志中,也有禹谷或御谷的。章學誠說:“苞谷一名玉米,一名玉谷,謂合五而六也。”嘉慶《河津縣志》:“包谷一名禹谷”,嘉慶《商城縣志》也載:“玉蜀黍一名玉谷”。玉谷的稱呼多流行于北方。徐光啟在《農政全書》中這樣寫道:“別有一種玉米,或稱玉麥,或稱玉蜀秫,蓋亦從他方得種。”[10]玉麥之稱,在明清兩代多見于云南、貴州西部、四川西部、甘肅、陜西中部、河南等地區,另外,安徽、直隸、山東等省的地方志中也有所記載。為什么叫玉麥?據光緒《名山縣志》的解釋:“粒豆,色黃潤如玉,故得玉名”;道光《城口廳志》曰:“麥者,言可磨面如麥也”;道光《新津縣志》則說:“玉麥,言其粒如麥也”。看來,果實外形似玉,又可磨面如麥子,是玉麥稱呼的由來。表1山西玉米別稱及通行縣區分布名稱|通行地區玉米|(光緒)定襄縣玉蜀黍(玉高粱、玉蜀秫、玉稻黍)|(乾隆)大同府、絳縣(道光)繁峙縣、大同縣(光緒)懷仁縣、清源鄉、壽陽縣、聞喜縣、盂縣(宣統)文水縣(民國)昔陽縣、岳陽縣、安澤縣、翼城縣、襄陵縣、沁源縣、安邑縣、新絳縣玉茭(玉茭子、玉茭茭)|(乾隆)陽城縣(嘉慶)長子縣(道光)繁峙縣(同治)河曲縣(光緒)定襄縣(民國)太谷縣、平定縣、襄垣縣包谷|(光緒)清源鄉、文水縣(嘉慶)河津縣玉谷|(民國)安邑縣、芮城縣御麥|(乾隆)陽城縣(民國)新絳縣玉麥|(民國)鄉寧縣、翼城縣禹谷|(嘉慶)河津縣舜王谷|(萬歷)稷山縣棒子|(民國)安邑縣表注:括號中朝代系后列府縣鄉志書的刊版年代。關于“御麥”這一別稱的由來,在同治十三年《陽城縣志》中這樣記載:“以曾經進御,故名”。在兩湖地區也有將玉米叫做“御高粱”和“御米”的,大概也是因為玉米曾經是貢品,而在稱呼前冠以“御”字。總之,玉米在山西的傳播過程中,名稱并未發生太大的變化,主要還是繼承了玉米來源地的名稱。二、玉米傳入山西的時間和途徑玉米在國內的傳播可以分成兩個時期,由明代中葉到明代后期是開始發展時期,到明代后期這種農作物已傳播到全國近半數省區,清代前期全國各省縣份多已種植。在明萬歷四十年(1612年)《稷山縣志》的《物產·谷屬》中列有“舜王谷”,這可能是山西古籍方志中關于玉米的最早記載,和相鄰省份對玉米的記載時間相比,山西早于直隸,晚于河南、山東和陜西。另外,對玉米有較早記載的是乾隆二十年(1755年)刊《陽城縣志》、乾隆三十年(1765年)刊《絳縣志》和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刊《大同府志》。嘉慶、道光年間,南部的長子和河津縣,北部的大同縣和繁峙縣在其地方志中對玉米有了比較簡單的記載。[11]但是山西大多數地區的方志對玉米的記載卻是在光緒乃至民國時期,即使是主產玉米的晉中地區也是在民國時期才有了關于玉米的記載。光緒十八年(1892年)刊《山西通志》中有這樣的記載:“玉蜀黍,亦名玉秫,又名御麥,處處有之”,“……御麥,今潞屬廣植”,[12]這說明直到十九世紀末,玉米在山西的種植才具有了普遍性(但是在光緒年間的大部分縣志中都不見有玉米的記載)。根據以上方志對玉米的記載時間的先后來判斷,玉米在山西省內的傳播途徑是由晉南和晉北同時向晉中地區推進的。情況可能是這樣:明朝末年,晉南的稷山縣首先開始種植玉米;乾隆中后期,晉南的陽城縣、絳縣和晉北的大同府等地也種植了玉米;清朝后期,玉米種植分別由晉南和晉北逐步向晉中地區推廣;光緒前期,晉南、晉中和晉北都已有了玉米的種植,但分布范圍狹小;民國時期,在山西大部分縣份的地方志中都可見到玉米的記載了。從玉米最初傳入山西到玉米在全省范圍內的普遍種植經歷了幾乎三百年的時間,可見玉米在山西的種植發展是比較緩慢的,其原因應與山西的地理氣候條件及有清一代相當頻繁的自然災害有關,尤其是光緒三年的特大自然災害對山西的影響極為嚴重。據方志記載,清朝前期的一些年份里山西省境內的任何地區都發生過十分嚴重的自然災害:康熙《五臺縣志》卷八收錄閻襄《饑荒行》,引言云:“康熙十九年,太原以北至云中,千里大旱,民饑轉徙十之六七,斗米錢數百不得……”;民國《永和縣志》卷一《祥異考》載:“(康熙)五十九年至六十年,晉省連遭大旱,永邑更甚……盜賊遍地,餓殍盈野,性命賤如草菅,骨肉等于泥沙。……”;光緒《長子縣志》卷一二《大事記》載云:“乾隆二十五年春,大饑,民食樹皮草根”;民國《萬全縣志》《雜記》載:“嘉慶九年,夏無麥,秋無禾,糧價騰貴,麥石價銀二十五兩,人民離散。十年,無麥無禾,餓死、逃亡過半。”所以,在玉米傳入山西的最初時期境內各地區就遇到頻繁發生的荒旱。這些災害的直接結果就是農作物的大幅度減產或絕收,饑不得食的農民或就地餓死,或流離失所,勞動力人口受到了很大損失。玉米雖系耐旱作物,但其生長期中要求高溫,蒸發量大,需水量亦多,在降水量不足250毫米的地區,灌溉條件好才能生長。山西南北地理氣候條件迥異,農業生產條件差別很大。晉南與晉東南地區在農業生產資源及地理條件方面,占有一定的優勢,臨汾與運城兩大盆地土地平衍肥沃,水利灌溉便利,無霜期長,氣候較為溫暖,因此,農業生產水平與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比北部地區略強一些,但該地區一直以生產小麥為主,外來作物玉米還一時無法取得主導地位;晉中地區耕地主要集中于太原和忻定兩大盆地,地勢平衍,氣候適中,水利條件一般化,是山西最為普通的產糧區,但由于人口眾多,糧食供給也相當緊張,每有災害,人口流失也很嚴重;與南部相比,晉西、晉北地區土地貧瘠,無霜期短,耕作方式落后,水利灌溉條件極度低下,糧食生產完全依賴于氣候條件,當地農民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非常脆弱。所以,清朝前期玉米在山西的傳播種植范圍和速度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自我朝定鼎以來,迄今二百余歲,中間水旱交咨,在所時有,然或一州、一邑,甚至二、三郡而止,從未有赤地千里,通省旱災如光緒三年之山右者。……”[13]由此可見,有清一代山西境內的自然災害就沒有間斷過,直到光緒初年發生了“丁戊奇荒”這場波及山西全境的特大自然災害,全省上百個縣似乎沒有例外地同罹慘禍,山西南部地區受災最為嚴重。張鑒衡《壽陽縣災賑碑計》稱:“溯自乙亥(光緒元年,1875年)秋雨傷禾,谷米多黑,則晉災之始也。至丙子(光緒二年,1876年),省南一帶,饑謹薦臻,至丁丑,則赤地千里。”[14]山西農業生產條件最為優越的晉南地區尚且如此,更何況自然條件遠不如晉南的晉北和呂梁地區,就更沒有進行玉米種植的能力了。災害造成了農業生產力的絕對下降,過半勞動力的死亡和逃移,[15]這也許就是為什么光緒前期只有少數縣份對玉米做了記載的原因了。“丁戊奇荒”后,在清政府勸荒和招荒政策下,大批外地客民來到山西,補充了嚴重短缺的勞動力,農業生產逐步得到恢復,產量高而穩定,又具有耐旱和耐瘠特性,適應范圍廣,高山、丘陵、平原皆可種植的玉米便以很快的速度在山西尤其是晉南地區普及開來,到光緒十八年(1892年),就處處有玉米了。據研究,玉米傳入我國的途徑有海陸兩路:陸路一自波斯、中亞至甘肅,然后流傳到黃河中下游流域;一自印度、緬甸至云南,然后流傳到川黔;海路則自美洲、東南亞至沿海的閩廣等省,然后向內地擴展。這三路玉米傳播源逐漸向中國腹地進行滲透并最終融合。[16]從玉米在山西通行的別稱來看,山西接受的主要是云南和甘肅兩股玉米傳播源,因為江浙閩粵等沿海省份的玉米別稱絕大多數都尾綴“粟”字、“豆”字,或帶有“蘆”字,山西對玉米的別稱卻不曾有這樣的字,而是像陜西一樣稱為“玉蜀黍”,像云南一樣稱為“包谷”,或像河南一樣稱為“玉麥”。這兩股玉米傳播源相繼抵達山西之后便開始融合,這種融合大概結束于光緒初年,其表現之一是在同一地區具有指示兩種玉米傳播源的別稱,如地處山西中部的文水縣,在其光緒九年(1883年)刊的方志中既有標志云南傳播源的別稱“包谷”,又有標志甘肅傳播源的“玉桃黍”[17];表現之二是這時的地方志中也往往羅列多種玉米別稱,如光緒十八年(1892年)刊《山西通志》記載,“玉蜀黍,亦名玉秫,又名御麥,處處有之。”[18]玉米是如何傳入山西的,由于缺乏相關的歷史資料,不能確切考證。但根據山西在明清時期的情況推測,玉米引種到山西的途徑可能有兩種:一是由當時在外省的山西商人把玉米種子帶回到山西,經過本地農民試種獲得成功,繼而在山西各地推廣開來;二是外省客民流落到山西開墾荒地的時候,種植了在家鄉時曾賴以糊口的玉米,收成不錯,山西的農民也開始種植。關于山西商人的經商活動情況,清代大學者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有這樣的記述:“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歲輒從人學貿易,俟蓄積有資,始歸納婦。納婦后,仍出營利,率二三年一歸省,其常例也。”[19]山西人經商以商品的長途販運為主,明朝中葉以后,山西商人大量地向淮浙地區移居,逐步進入了全國范圍的流通領域,南北各地都有其足跡。如山西票號總號所在地的太谷縣,“自有明迄于清中葉,商賈之跡幾遍全省。東北至燕、奉、蒙、俄,西達秦隴,南抵吳、越、川、楚,儼然操全省金融之牛耳。”[20]明代山西商人在四川、云南、陜西、河南及新疆的經濟活動史料中多有記載:山西潞澤二州是與三吳、越閩齊名的絲織專業區,“東南之機,三吳越閩最夥,取給于湖繭;西北之機,潞最工,取給于閬繭(閬指四川保寧府閬中縣)”,[21]“潞綢所資來自他方,遠及川湖之地。”[22]潞澤絲棉織物的染色,對顏料的需求很大,因而絲綿生產又推動了山西顏料商的發展。山西顏料商見于碑刻記載的有平遙和臨汾縣人,主要在京城、通州經營,所售顏料出自本地,或是販自四川。日升昌票號前身山西平遙縣西裕成顏料莊“所販顏料中,有銅碌一種,出四川省,因自行重慶府制造銅碌,運至天津,以備銷售,亦甚獲利。”[23]明代,隨著山西鹽商在國內地位的日益顯赫,河東鹽銷往“陜西之西安、漢中、延安、鳳翔四府,河南之歸德、懷慶、河南(今洛陽)、汝寧、南陽五府及汝州,山西之平陽、潞安二府以及澤、沁、遼三州。”[24]山西商人有明以來就參與了西茶市與西番的交易(交易地點在碉門、黎、雅抵朵甘、鳥思藏)。弘治十六年(1503年),明朝大臣楊一清向朝廷提出招商買茶,讓茶商與西番直接交易,“自弘治十八年(1505年)為始,聽臣出榜招諭山陜等處富實商人,收買官茶五六十萬斤,其價依原定每千斤給銀五十兩之數,每商所買不得過一萬斤,給與批文,每一千斤給小票一紙,掛號定限,聽其自出資本,收買真細茶斤,自行雇腳轉運。”[25]我們沒有發現山西商人在甘肅的活動資料,但在張掖、武威見到過山陜會館和山西會館的遺址,雖然已經破敗不堪,卻能充分說明山西商人在甘肅曾經有過長期的經營活動。四川、甘肅、云南、陜西、河南、新疆都已在明萬歷之前先后開始種植玉米,[26]在山西商人與這些省份頻繁的經濟往來中,玉米傳入山西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因為按照晉商的經營習慣,分號與總號之間在人員和貨物上的往來都異常頻繁。另外,我們將玉米傳入山西的時間、最初傳入地與山西商人的發跡期、最初發跡地做一比較,發現在時間和地域上兩者都相當吻合。如前所述,山西古籍方志對玉米做最早記載的是明萬歷四十年(1612年)的《稷山縣志》,稷山在明代隸屬蒲州。而山西商人在全國取得顯赫地位是在明代弘治至萬歷年間(1488—1619年),晉南的蒲州、平陽一帶則是山西商人最初的發跡地,明隆慶二年(1568年),進士沈思孝在其《晉錄》、明萬歷進士王士性在其《廣志繹》中都曾指出:“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這兩個事件幾乎是發生于同一時間、同一地域,為我們的推測又提供了一個佐證。從明朝初年開始,山西一直是中國北方一個重要的移民輸出地,但同時也有不少的外地客民流落到山西求生,“在僻遠的州縣,不少外地客民早已在當地從事耕耘”,[27]這些州縣有隰州、吉州、嵐縣、岢嵐、臨縣、永和、浮山、岳陽等。光緒六年(1880年)刊《續修岢嵐州志序》中提到當地的客民問題:“第山高土瘠,絕少平原,地廣人稀,苦無產殖,土人儉而不勤,業農賈者率多他鄉外省之人,以故直、豫、秦、隴、川、楚客民錯趾于境,來往靡常,而客富于主,又人丁欠旺,恒以外姓繼螟蛉,豈五行有所克制歟?”由此可見,進入到山西的客民來源相當廣泛,河北、河南、陜西、甘肅、四川、湖北等省份都有,他們在山西定居之后,勤于稼穡,善于商賈,所以玉米也有可能由這些客民引種到山西。當然,玉米引種到山西的這兩種途徑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有可能兼而有之。總之,明清時期山西人口的頻繁流動對玉米這種高產作物的引進和推廣起了決定的作用。三、玉米在山西的生產概況和經濟作用清代山西有關玉米單產的記載極其罕見,根據表二所示民國時期山西玉米的平均畝產量,可推測清末整個山西玉米的單產水平在40公斤左右(1914年山西小麥平均畝產是44.2公斤[28])。玉米作為逐漸推廣的作物,其種植面積在清代變化較大,但清代末年的情況可以參照民國初年的情況作些粗線條的估計。如表2所示,估計到清朝滅亡時,山西每年至少有150萬畝耕地種植玉米,以40公斤的單產計,清末山西每年可產玉米60000噸左右。表2山西玉米播種面積、產量及畝產年代玉米播種面積(萬畝)總產(噸)畝產(公斤)1919年153.375420491947年663.4250200401949年536.5646395086資料來源:山西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山西通志·農業志》,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252頁。在清代各縣方志中雖然很少見到對玉米產量的記載,但到光緒以后,玉米成為“山農之糧,視其農欠”,[29]“為本地人之副食物,其出產亦頗不少,麥后種之,亦為秋糧之一”,[30]可見,玉米以其高產的特性在山西一些地區的糧食作物中占據了主導地位,尤其是晉東南的潞安府,“今潞屬廣植,每炊必需”。[31]民國27年(1938年)《平定縣志》記載了當地玉米的平均年產量,約為183750石,同時還記載了粟的年產為91875石,豆為18375石,高粱為36750石,小麥及其他年產約為36750石。[32]可見,抗戰前夕玉米是平定縣年產量最多的糧食作物。到1949年的時候,玉米在山西的播種面積為536.56萬畝,年產量為463950噸,雖然只占到山西糧食作物總播種面積的8%,但在山西主要糧食作物的總產量中卻達到17.9%的比例,[33]如表3所示。表31949年山西主要糧食作物產量比例作物玉米谷子小麥薯類高粱比例17.9%29.2%23.4%13.3%11.0%資料來源:山西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山西通志·農業志》,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232頁。根據以上玉米在山西的生產情況來看,玉米在山西的傳播和推廣對當時糧食的增產是有極大意義的:首先,玉米耐旱,能夠適應北方的旱地,種植玉米可擴大耕地面積。山西農田一直以旱地為主,清代旱地面積占到總耕地面積的95%,約有65400萬畝的荒山荒地尚待開發。[34]同治十二年(1873年)至光緒十三年(1887年),山西耕地面積從53,285,401畝增至56,609,070畝,[35]增加了300多萬畝,和當時玉米種植的推廣可能有一定的聯系:其次,玉米是一種優異的高產作物,種植玉米可“種一收千,其利甚大”。[36]對處于封建剝削壓榨下的大多數農民來說,通過推廣特別高產的外來農作物比改良土壤或培育新的品種更容易提高糧食的單位面積產量。總之,玉米的推廣,既擴大了耕地面積,又提高了糧食單位面積產量,因而能為社會提供更多的食糧,特別是有助于“丁戊奇荒”之后山西農業生產的恢復和民食問題的解決。玉米在山西的推廣種植不僅促進了糧食的增產,還間接地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玉米本身用途廣泛,既可當糧,又可充作手工業原料,對山西農戶來說,用玉米釀酒和養豬在光緒時期已是極為普遍的事情,“釀酒磨粉,用均米麥。瓤煮以飼豕,桿干以供炊,無棄物”。[37]玉米的傳播種植對山西社會經濟生活所起的推動作用遠不止以上所述內容,還需我們做進一步地研究與探討。注釋
[1]乾隆四十七年《大同府志》,卷1,《物產》。
[2]民國18年《翼城縣志》,卷8,《物產》。
[3]山西省農業廳農業志編寫組:《山西方志物產綜錄》,1995年,第39頁。
農村人口消長及其流動研究
人口壓力與小農經濟的關系,作為一個理解明清以來資本主義化的問題,已引起國內外學界的廣泛討論,對美籍學者黃宗智的《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1986年版)、《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華書局1993年版)及《中國經濟史中的悖論現象與當前規范認識的危機》(《史學理論研究》1993年第1期)等論著中提出的理論模式,國內學界評價不一。本文擬在考察近代華北農村人口消長及其流動的基礎上,就黃宗智先生的理論提出拙見,不妥之處,尚祈指正。
從區域地理的角度而言,本文所指的華北地區指通常所說的黃河中下游地區,大體以長城為北界,秦嶺—淮河為南界,包括今山西、河北、河南、山東及周邊地區,雖較黃氏所指范圍更為廣泛,但對問題的討論當不會有太大影響。
一
古代華北地區不僅是中華民族的重要發祥地,而且是全國人口最為集中的地區。據《漢書·地理志》記載,紀元初年全國13州及司隸部人口總數為5760余萬,而位于黃河中下游地區的兗、豫、青、冀、徐、司隸、并州的人口即有3800余萬,占全國總人口的66%,班固所謂“地小人眾”正是對此時這一地區人口狀況的高度概括。自紀元初年至明后期的1000多年間,中國人口經歷了一個緩慢增長的過程。研究表明,西漢末年,全國人口總數增加到6000萬;自東漢至五代末,幾經增減,總數未突破8000萬;12世紀初突破1億;13世紀初達到1.2億;17世紀初達到約1.5億(注:見袁永熙主編《中國人口·總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1年,46頁。)。伴隨著王朝的興衰,周期性的波動是人口數量變化的明顯特征。華北地區是中國封建時代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也是戰亂最為頻仍和集中的地區,幾乎每一次社會動蕩都給華北地區社會經濟造成極大破壞,人口的流亡也相伴出現。正是由于長期的社會動蕩,華北地區的人口在全國總人口中的比重逐漸下降。大體而言,唐“安史之亂”后,華北已失去作為全國人口重心的地位,胡煥庸等認為,唐末黃河流域在全國總人口中的比重跌至40%,明初已不足30%(注:參見胡煥庸、張善余《中國人口地理》上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4年,14-17頁。)。具體而言,西漢元始二年(2年),華北人口總數為38041307人,唐天寶元年(742年)25232884人,明萬歷六年(1578年)22724951人(注:據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以下簡稱《統計》)甲表2、甲表25、甲表72計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整個封建時代,華北地區人口總數呈下降趨勢,總量當不會超過4000萬人。
清代是中國人口發展史上一個極其重要的時期。清初,歷經近20年的兵荒馬亂,全國人口亡失嚴重,直至17世紀末全國人丁戶口才大致恢復到明代末年的水平。康熙二十年(1681年)后,清王朝在全國范圍內的統治趨于穩定,人口總數恢復并平穩在1億左右。乾隆一朝,全國人口總數突破3億,此后嘉慶、道光朝仍繼續增長。1840年,全國人口總數為412814828人。咸豐元年(1851年)增長到4.3億多,達到清代人口總數的最高點。同全國各地人口增長大勢一樣,華北地區的人口總數也有了明顯增長。統計資料表明,乾隆朝后期,直隸、山西、山東、河南四省人口共計80677833人,嘉慶時期增加到93991016人,道光朝后期達94234910人,咸豐元年達到96341715人(注:據梁方仲《統計》甲表82計算。)。值得注意的是,乾隆朝以后,華北地區的人口數量雖然也呈上升趨勢,但卻明顯低于全國平均增長值。若以乾隆末年人口平均數為基數100,至咸豐元年直隸為101.02、山西118.09、山東144.82、河南112.88,四省平均上升到119.20,而全國已上升到145.42。此時,全國各省區人口增長速度最快的當屬四川、奉天、巴里坤、烏魯木齊、吉林、云南等邊緣地區(注:見梁方仲《統計》甲表84。)。此種人口發展態勢說明,在一定的生產力條件下,華北地區已出現“人滿為患”之勢,未開發和待開發的邊疆地區則成為全國人口增長最快的地區。
咸豐元年爆發的太平天國農民戰爭,是清代全國人口由升而降的轉折點。這一時期,全國人口最為稠密的江南地區成為太平軍和清軍及外國侵略軍長期廝殺的主要戰場,戰后,江南地區人口銳減。以蘇、浙、皖三省而論,江蘇戰后“一望平蕪,荊榛塞路,有數里無居民者,有二三十里無居民者”(注:李鴻章:《李文忠公奏稿》卷3。)。浙江“人民死于兵燹,死于饑餓,死于疾疫,蓋幾靡有孑遺”(注:左宗棠:《書牘·家書》卷上。)。安徽“人民死傷無數”(注:民國《安徽通志稿·民政考·戶口》。)。據清官方統計,三省在此期間凈減人口5400多萬(注:有關太平天國起義前后江南地區的人口變動,可參見何炳棣《1368-1953中國人口研究》下卷,第10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王業健《太平天國對于蘇南人口的影響》,載《中國論叢》(英文版)19卷;行龍《論太平天國革命前后江南地區人口變動及其影響》,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1年2期。)。而在華北地區,雖然也有捻軍起義、太平軍北伐等戰事,但除直隸而外,河南、山東、山西三省人口仍在繼續增長,而直隸人口數字銳減實為統計缺失(注:據清官方統計,直隸人口1851年為23455000人,1858年減至974000人。按1858年數字僅為承德一府人口數字。)。到光緒三年(1877年),華北四省人口總數增長到1億,按清朝戶部清冊,是年山東人口35657000人,河南23944000人,山西16443000人,直隸若以1857年數字23032000人計之,則四省人口總數為99066000人,比咸豐元年凈增約270萬人(注:1858年至1898年直隸人口僅承德一府造報。),這一數字達到清代華北人口增長的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