軟實力哲學思索
時間:2022-04-13 09:53:00
導語:軟實力哲學思索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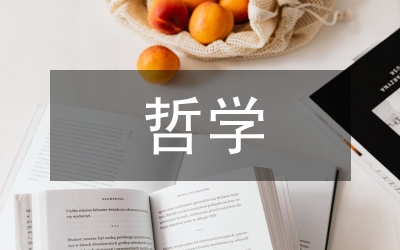
近年來,“軟實力”概念已經成為國內學術界、各級政府部門和廣大群眾耳熟能詳的術語;不過,這并不意味著它的使用者已經非常明了它的基本含義、實際載體和具體表現形式——只要看一看國內迄今為止有關研究論述所得出結論的眾說紛紜狀態,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這一點。而這顯然意味著,國內學者對“軟實力”進行的學術研究尚處于未經嚴格和徹底的哲學反思的表面層次上,沒有也不可能得出既具有鮮明的現實針對性又具有比較充分的理論解釋力的研究結論;此外,這同時也意味著,我們要想真正通過嚴格的學術探討和研究來促進一個城市的“軟實力”的不斷提升,就完全有必要對這個概念進行嚴格和徹底的、哲學上的批判反思。有鑒于此,本文試圖在三個方面對“軟實力”進行幾點簡單的哲學反思:第一,進行反思的必要性;第二,“軟實力”的基本內涵究竟是什么?第三,如何通過切實考察“軟實力”的實際生成路徑,有效推進一個城市的人文精神建設?
一、對“軟實力”概念進行哲學反思的必要性
有必要對“軟實力”進行學術研究進行嚴格和徹底的哲學反思嗎?答案是肯定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
(一)從現實背景和具體的學術脈絡角度來看
這個概念的主要使用者,美國當代著名國際關系學家小約瑟夫奈(JosephNye),雖然首次比較系統全面地論述了“軟實力”的方方面面,但他并沒有對這個概念所具有的基本內容進行過嚴格的學術界定,因而并沒有提供準確的定義,只不過提出了下列基本觀點:隨著各民族國家間國際競爭的不斷加劇,國家綜合實力的競爭已經不再限于傳統的軍事、經濟、科技等方面的實力競爭,亦即并不限于“硬實力”(hardpower)的競爭,而是進一步擴展到由社會制度、發展模式、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文化等所具有的吸引力方面的競爭,亦即擴展到了“軟實力”(softpower)的競爭。[1-2]因此,他所謂的“軟實力”指的是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生活方式、價值觀念以及文化等方面所具有的“吸引力”,并沒有單純強調文化抑或學術所具有的、作為“軟實力”而存在并發揮作用的“吸引力”。這顯然表明,“軟實力”這個概念既具有非常鮮明的現實針對性——它所指對的完全是當代民族國家之間的綜合國力競爭,同時也具有特定的學術脈絡——它實際上完全處于國際政治、國際關系研究領域,而非國內研究者通常所涉及的、一般的人文精神培養與建設領域抑或文化研究領域。這樣一來,下列問題自然會鮮明地顯現出來,即人們究竟有何種可靠的現實依據和學術合法性,能夠直接把它應用于既無國際競爭色彩,又非國際政治領域的日常人文精神培養和文化建設之中呢?而在我看來,要想對這樣的問題做出確切的回答,研究者就需要進行嚴格和徹底的哲學層次上的批判反思。
(二)從概念本身所涉及的內容范圍角度來看
在小約瑟夫•奈那里,“軟實力”本身指的是諸如“社會制度、發展模式、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文化等”所具有的“吸引力”,但是嚴格說來,所有這些方面所涉及的具體內容究竟是什么并不是非常清楚的,而且這些方面本身都具有非常大的交叉性和隨之而來的含糊性——且不說“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本身都具有非常廣泛和特別復雜的指代對象,“文化”本身就更是如此了①而在這樣的情況下,只要人們并不僅僅停留在常識性的“比喻”層次上,并不停留于表面上的認知和膚淺的理解層次上,而是出于在社會實踐過程中逐步增強“軟實力”的現實需要和根本愿望,試圖弄清它的基本含義是什么并加以卓有成效的具體運用,那么,人們馬上就會“如墜五里霧中”,這是因為在這里,人們根本無法、也不可能嚴格地確定這種作為“軟實力”而存在并發揮作用的“吸引力”的具體內容究竟是什么。
(三)從學術研究所需要的嚴格性角度來看
毋庸贅言,要想使一種學術研究的結論既具有鮮明的現實針對性,又具有比較充分的理論解釋力,研究者不僅需要走出作為“觀念的王國”的象牙塔而直面現實,充分認識和了解現實之中存在并迫切需要解決的各種重要問題,同時也需要從盡可能客觀嚴謹的學術態度和徹底的批判反思精神出發,對這樣的問題進行探討和研究:如果說“客觀嚴謹的學術態度”為所有學術領域之中的研究者所共有的話,那么,“徹底的批判反思精神”則只有從哲學研究的學術層次、基本立場和根本要求出發方有可能——這既包括研究者對自己所使用的基本立場、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進行的、系統深刻的批判反思,同時也包括在此基礎上對其研究結論的嚴格的學術定位和系統全面的把握。實際上,只有通過進行這樣的徹底批判反思和學術定位,包括“軟實力”在內的各種作為研究結論而存在的概念和論斷,才有可能因為得到了比較嚴格的學術定位,真正把自身的基本內容和適用范圍清晰地展示出來。綜上所述,我認為,只有采取對“軟實力”概念進行嚴格的、處于哲學研究層次上的批判反思的學術立場,我們才有可能嚴格地確定它的基本內涵、實際載體、具體表現形式,從而通過嚴謹扎實的學術研究,得出既具有現實針對性又具有理論解釋力的科學結論。那么,“軟實力”的基本內涵、實際載體和具體表現形式究竟是什么呢?
二、“軟實力”的基本內涵、實際載體和具體表現形式
如上所述,在小約瑟夫•奈那里,所謂“軟實力”指的是“社會制度、發展模式、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文化等”所具有的“吸引力”;那么,這種“吸引力”的基本內涵是什么,它以什么實際形式作為其存在和發揮作用的載體,又是通過什么具體途徑表現出來呢?從表面上看來,這種作為“吸引力”而實際存在和發揮作用的“軟實力”的基本內涵似乎并不復雜,它似乎相當于人們在以往的日常生活之中不時會提到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優越性”所具有的吸引力。不過,一旦研究者試圖在學術研究所要求的理論抽象層次上,通過學術研究通常所訴諸的形式化手段,在這里得出具有一定普遍意義的相應結論,馬上就會感到非常棘手。這是因為在現實當中,所謂“社會制度、發展模式、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文化等”都是具有實質性內容且不斷發展變遷的,因而不是能夠輕而易舉地形式化的,而研究它們的“優越性”及其“吸引力”也同樣會如此。那么,這難道意味著這樣的“吸引力”是無法進行研究,只能在常識層次上加以談論和運用嗎?顯然不是。
在我看來,這里的關鍵問題并不是作為被研究對象的“軟實力”能不能被研究,而是研究者究竟如何才能對它進行恰當的研究①[4]——概而言之,在這里,研究者不應當繼續自覺不自覺地沿用自然科學研究者所慣用的、竭力試圖通過僅僅從被研究對象的共時性(synchronical)現狀出發進行一系列的抽象過程,便得到似乎涵蓋了其歷時性(diachronical)生成維度的,通常所謂“絕對普遍有效性”的研究結論的基本傾向和做法,而是必須通過探討和運用能夠將被研究對象的共時性維度和歷時性維度、個體維度和社會維度有機統一起來的“社會個體生成論”(TheSocialIndividualGrowing-upTheory)的基本立場、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才有可能對這些方面的優越性及其相應的“吸引力”做出盡可能恰當的探討和研究,從而得出一般的抽象形式和具體內容相統一的,既具有現實針對性又具有理論解釋力的研究結論。
正是基于這樣的基本觀點,我認為,所謂作為“軟實力”而存在的“社會制度、發展模式、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文化等”所具有的“吸引力”,實質上就是這些方面的“優越性”所具有的“吸引力”,是通過飽含情感的感性符號體現出來的“魅力”——也就是說,是這樣的符號所表現出來的、直接訴諸受眾的主觀精神世界的、能夠激發這些受眾追求并滿足他們享受特定的精神性自由之要求的“魅力”。這種觀點需要做出以下幾點解釋。
第一,這種作為“魅力”而存在并發揮作用的“吸引力”,本身是“軟的”,亦即是直接訴諸受眾的主觀精神世界的,而根本不是諸如經濟實力、政治實力、軍事實力乃至社會制度等方面的具體的物質性力量本身,而是這些方面的經過主觀情感世界具體體驗和折射的,進而以感性符號的形式展現出來的“魅力”。
第二,這樣的“吸引力”本身雖然并不是上述這些現實的物質性力量本身,但卻并非與這些現實的物質性力量毫不相干,而是以它們為自身的生成母體(medium)、直接現實基礎和表現對象的——從最簡單的意義上說,假如一個民族國家沒有比較強大的經濟實力、政治實力、軍事實力,乃至為世人公認的優越的社會制度,她實際上也就根本不可能具有什么“軟實力”了:在這里,不僅“弱國無外交”是正確的,“弱國無軟實力”也同樣是正確的。
第三,要想恰當地探討和研究這種作為“軟實力”而存在和發揮作用的“魅力”,研究者既不能僅僅孤立地關注這樣的“魅力”本身,也不能出于它們是對“硬實力”的某種體現便轉而去集中關注“硬實力”,抑或僅僅以自然科學的平面化研究方式來機械地探討它們與“硬實力”的“相互關系”,而是應當從動態生成的研究視角出發,在能夠使被研究對象的歷時性維度和共時性維度有機統一的基礎上,來探討和研究這兩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在這里,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已經可以看到的關鍵性問題是“倉廩實”而未必“知禮節”,亦即“硬實力”的發展和逐步提升并不與“軟實力”的發展和逐步提升同步!正是從這種意義上來看,一個城市在發展“硬實力”的過程中如才能逐漸形成相應的“軟實力”,而逐漸培養起來的“軟實力”又如何進一步促進“硬實力”的發展,都是既具有特別重要的現實意義,又具有重大學術價值的關鍵性問題。在我看來,確定了“軟實力”的基本內涵,有關它的實際載體的問題也就基本上一目了然了:無論特定的“軟實力”所包含的具體內容是社會制度方面的、發展模式方面的、意識形態方面的、價值觀念方面的,還是生活方式抑或文化方面的,其實際載體都只能是上面已經提到的,作為“文化”之“文”而存在的“飽含情感的感性符號”,惟此而已,概莫能外——我們在這里之所以得出這樣具有絕對論色彩的結論,主要依據的是“軟實力”本身所特有的本質特征,也就是說,恰恰是由于作為它的基本特征的“軟”,決定了它所針對和影響的是所有受眾的主觀精神世界而不是他們那作為肉體而存在的身體,亦即它所發揮的作用不是以肉體方面的物質性影響和具體征服形式為基本特征,而是以“攻心”、“誅心”為根本目的,是力圖通過形象鮮明生動的表現形式,以潛移默化的方式來影響和感化受眾的主觀精神世界,從而使之心悅誠服地接受它所產生的特定的影響,因而最終實現其目的——也可以說,“軟實力”的實際載體顯然不可能是現實當中實際存在并發揮具體作用的,諸如政治制度或者軍事力量這樣具有壓制和征服色彩的現實力量,而只能是具有象征意味和感性特征的,飽含情感的,因而使其受眾能夠通過各種感官來直接感受和體驗其特定內涵并接受其相應影響的符號。既然“軟實力”的實際載體只能是各種各樣飽含情感的感性符號,它也只有通過諸如此類的符號才能把自身包含的特定內涵具體體現出來并發揮特定的影響,所以,所謂“軟實力”的具體表現形式實際上不可能是別的,而只能是生活在現實生活之中、處于特定的文化生存場域的人們,通過不斷創造各種各樣的、積淀了他們對自己的現實生活氛圍的主觀體驗和心靈感受的、飽含情感的感性符號,而進行的文化創造和文化傳播活動!為了對符號進行嚴格的學術界定,這里需要強調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盡管人們對“符號”的基本含義理解、表述和運用表現出極其多樣的形式,諸如從日常生活中作為記號(mark或token)被稱為“符號”,科學研究中使用的作為“指號”(sign)被稱為“符號”,乃至各種民俗儀式和審美活動中使用的、具有形象的象征意味的符號(symbol)也被稱為“符號”,但是,我們在這里所指涉的“符號”(symbol)卻并不會因此而具有任何歧義性——它所指的既不是因為具有效用的轉瞬即逝特征而難以深刻地觸動人的心靈的“記號”,也不是數學自然科學之中常見的,以抽象和嚴謹的方式表達作為研究結論之內容的某種客觀規律的“指號”,而是通過富有民族特色和時代特色的、形象鮮明生動的感性直觀形式,來表達和展示特定的社會個體或群體對其特定的自然環境、歷史傳統特別是對其現實生存氛圍的主觀體驗和感悟,以及在這種體驗和感悟的基礎上生發出來的、對特定的精神自由的追求和享受。正因為如此,我們可以比較形象地說,能夠使人類在其中享受精神性自由的精神家園,實質上就是由諸如此類飽含情感的感性符號建構而成的!
第二,作為“軟實力”的實際載體,符號本身既具有其所表達的基本內容的某種普遍性,同時又具有具體表現形式的特殊性——概略說來,其基本內容之所以具有普遍性,是因為盡管它所傳達的是特定的社會個體和群體對其現實生活環境的情感體驗和感悟,但這種情感體驗和感悟本身卻并不是他們對其日常生活事件的表面上的直接感受,而是立足于自身的生存境遇而對與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息息相關的一般性生存現狀及其變化趨勢的、非常深刻的內心體驗和感悟,因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其突出表現之一即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之中所說的“這才是人應當過的日子”!另一方面,其具體表現形式之所以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是因為任何一種這樣的內心體驗和感悟都是處于特定的自然環境、歷史傳統現實生活氛圍之中的具體的人的體驗和感悟,因而它的表達方式必定會具有民族性、地方性、時代性和個體性,從而具體表現為“軟實力”的具體表現方式的特殊性。此外,由于符號本身具有非實體性,亦即它本身只有借助于各種各樣的物質性載體才能存在并發揮一定的作用,所以,同一個符號可以通過截然不同的物質載體而體現出來,從而在某一個階段的現實生活之中發揮普遍性的作用。
第三,盡管究其起源,任何一種作為“軟實力”之實際載體的符號都是由特定的社會個體創造或者建構出來的,并且因此而具有一定的個性特征,但毋庸置疑的是,這樣的個性特征本身根本不會也不可能徹底掩蓋該符號的社會特征,更不會因此而使其特定的社會影響受到任何削弱——之所以如此,既是因為一般說來,任何一個現實的人都是實際存在于一定的現實社會環境之中的個體,根本不可能完全脫離其所處的這種環境,而是在這樣的現實環境之中不斷生成和發展的;而且也是因為,具體來說,他/她之所以能夠創造抑或建構出具有重大而廣泛的社會影響的符號,使之產生相應的“軟實力”效應,不僅是因為這種創造者所處的社會環境已經對他/她的心靈施加過各種各樣的塑造性影響,也是由于他/她對這樣的社會環境的體驗和感悟,本身都是以這樣的塑造性影響為基礎和反應對象的。這樣一來,我們在探討和研究作為“軟實力”的實際載體的符號時,顯然就不能僅僅著眼于符號本身,或者僅僅著眼于現實社會個體具體創造符號的特定過程本身,而是必須把這些相關的現實社會因素都充分考慮在內——只有如此,我們才有可能系統全面地認識和把握以符號為實際載體的“軟實力”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而且,也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才有可能進一步通過探討和研究這些承載著“軟實力”的符號的社會功能,為探索不斷通過人文精神的培育來提升一個城市的“軟實力”的有效途徑,奠定堅實的學術基礎,打開廣闊的研究視野。綜上所述,我認為,只有運用嚴格的學術性批判反思精神,通過對“軟實力”的基本內涵、實際載體和具體表現方式進行嚴謹的學術研究并得出科學的研究結論,我們才有可能擺脫要么“人云亦云”,要么只是在常識(commonsense)層次上以運用標語口號的方式來使用“軟實力”這個概念的不良局面,通過使這樣的研究結論因為既具有學術上的嚴謹性,又具有鮮明的現實針對性而能夠真正落到實處,使一個城市能夠在大力發展“硬實力”的同時,真正行之有效地不斷通過培養和發揚人文精神而使其相應的“軟實力”不斷得到提升。既然如此,在基本確定了“軟實力”的基本內涵、實際載體和具體表現形式之后,我們究竟應當怎樣做才能通過有效推進一個城市的人文精神建設,來不斷提升其“軟實力”呢?
三、如何通過考察“軟實力”的實際生成路徑,有效推進城市人文精神建設
實際上,我們之所以對“軟實力”及其基本內涵、實際載體和具體表現形式進行探討和研究,就是為了通過有效地推進一個地區或者城市的人文精神建設,使其“軟實力”也同樣能夠在其快速發展“硬實力”的同時得到相應的發展和提升。在我看來,就“硬實力”、“軟實力”和“人文精神建設”這三個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和重大學術價值的方面而言,我們在這里面臨著兩個不容忽視的根本性問題:第一,發展“硬實力”與發展“軟實力”的關系是什么?也可以說,究竟是不是一個地區或者城市的“硬實力”得到了發展和提升,其“人文精神建設”和“軟實力”也就必然會隨之得到發展和提升?第二,如果一個地區或者城市的“硬實力”并沒有得到長足的發展和提升,那么,究竟如何才能通過進行“人文精神建設”而不斷有效地發展和提升其“軟實力”?就第一個問題而言,雖然我們上面已經提到過的“弱國無軟實力”,亦即如果沒有“硬實力”的迅速發展和提升,也就根本不可能發展、提升并擁有相應的“軟實力”。但是,這既不意味著只有一個地區或者城市的“硬實力”得到了足夠的發展和提升,其“軟實力”才能開始得到相應的發展和提升,更不意味著其“硬實力”處于較低水平上的欠發達地區或者城市沒有資格和條件發展“軟實力”,因為人們根本不能也不應當認為“硬實力”與“軟實力”會完全同步發展,更不應當把“硬實力”和“軟實力”完全等同起來。實際上,認為這兩者完全可以等同起來的觀點是把科技與人文混為一談,進而把以科技發展為基礎的“硬實力”與以人文精神發展為基礎的“軟實力”混為一談了。在我看來,前者與后者的關系實際上類似于邏輯學上所說的充分條件與結果之間的關系,亦即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實質上是“無之必不然、有之未必然”的關系——也就是說,這里的一方面是“弱國無軟實力”,而另一方面則是,即使一個民族國家抑或地區主要依靠發血腥的戰爭財,或者主要通過對自然環境的無限掠奪而發展起非常強大的“硬實力”,使自己變成實力雄厚的世界霸主,其“軟實力”從根本上說也并不強大,因為這樣的“社會制度、發展模式、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文化等”并不會或者說很難得到其他民族國家之成員的認同和艷羨,因而也不會產生多么重要的,可以作為“軟實力”而發揮實際作用的“軟實力”。另一方面,如果這里所謂“硬實力”和“軟實力”的關系確實是類似于邏輯學上所說的充分條件與結論之間的關系,我們就有可能探討那些其“硬實力”并不是最強大的民族國家或者地區、城市,究竟是不是有可能有效提升自身的“軟實力”的問題,從而回答這里的第二個問題了。
在我看來,在一個地區、城市的“硬實力”不斷得到發展和提升的情況下,要想恰當地解答這個問題,就必須注意以下三個至關重要的方面。
第一,一個地區或者城市持續提升“硬實力”的根本目的究竟是不是為本地區、本城市的廣大成員的根本利益服務,究竟是不是能夠持續不斷地給群體內的成員們的生存和發展帶來實質性的好處——如果實際情況根本不是這樣,那么,這些成員顯然就不可能認同并擁護這樣的“硬實力”提升,因而其各種各樣的運行機制便對自己的局內人都沒有什么“吸引力”,更不用說對作為局外人的其他民族國家、地區或者城市的成員產生作為“軟實力”的“吸引力”了。
第二,在對不同地區、城市的“硬實力”進行比較的時候,比較者所進行的究竟是橫向比較還是縱向比較——前者所涉及的主要是本地區與被比較地區之間的當前現狀的比較,而后者涉及的則主要是本地區自身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這三種狀況之間的比較。毋庸贅言,在進行這樣的比較的時候,絕大多數比較者往往都會自覺不自覺地進行橫向比較,亦即他們所看到的往往是被比較地區目前如何先進、強大,相形之下則是本地區如何落后、弱小,而這樣一來,比較者顯然就有可能妄自菲薄,看不到自己所處的群體和地區的“軟實力”同樣也在其不斷發展和提升“硬實力”的過程中得到發展和提升的基本趨勢。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便很可能對自身的“軟實力”及其發展態勢處于“視而不見”抑或“麻木不仁”的狀態,因此其“軟實力”也不可能對身處其他群體的局外人產生相應的吸引力了。
第三,正因為存在著上述兩種可能性,所以,任何一個地區和城市的決策者和研究機構,都應當在不斷運用各種手段發展和提升其“硬實力”的同時,對“軟實力”及其實際生成路徑開展卓有成效的探討和研究,以期能夠通過扎扎實實的學術研究和建設,正確地探索、認識、把握和運用這兩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及其規律性,從而一方面在對“軟實力”的實際載體、基本內涵和具體表現方式進行系統全面的研究的基礎上,在符號建構和符號傳播方面做好引導和規范工作,為“軟實力”的具體展示和傳播做好“硬件”方面的準備;另一方面,只有在積極開展這樣的學術研究,逐步認識和把握“軟實力”的實際生成路徑的基礎上,決策者和研究機構才有可能針對廣大社會個體成員的帶有自發性的群體意識和社會心理,通過卓有成效的人文精神培育和建設,啟發和引導人們把自己的關注焦點更多地放在縱向比較上,使之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和體會到自己所處的“社會制度、發展模式、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文化等”之越來越多的“優越性”所具有的“吸引力”,從而使之更加自覺地投身于當前的“硬實力”和“軟實力”建設過程之中,最終實現這兩者之間的良性的相互影響、相互促進和共同發展。
綜上所述,我認為,在對“軟實力”概念進行嚴格的學術定位,并且進而確切地認識和把握其實際載體、基本內涵和具體表現形式的基礎上,一個地區或者城市的決策者和研究機構只有認識和把握了“軟實力”的實際生成路徑,才有可能切實推進和加強自己所在地區的人文精神的培育和建設,從而在不斷發展和提升自己所在地區的“軟實力”的同時,使自己所在地區的“硬實力”得到越來越健康和快速的發展。最后有必要說明的是,由于與“軟實力”有關的各種現實問題都非常復雜,相應的學術研究也仍然處于不斷探索的過程之中,本文提出的所有觀點都帶有很強的摸索性,作者只希望能夠做到“拋磚引玉”并得到廣大讀者的批判指正。
- 上一篇:檔案局先進性教育活動工作匯報
- 下一篇:旅游局創業服務工作情況總結